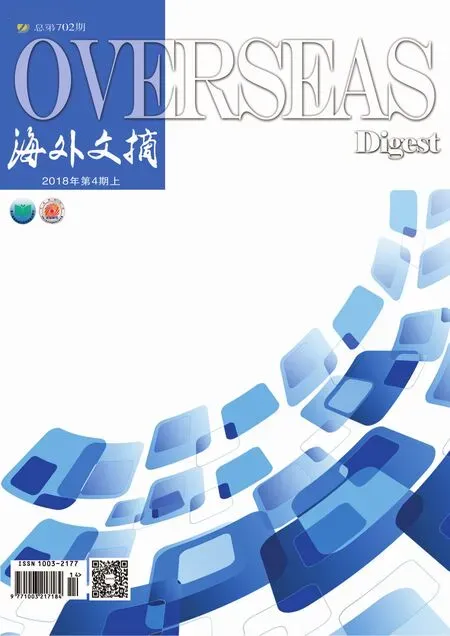探究王家卫电影中空间与情感的对应关系
——以《东邪西毒》《重庆森林》《花样年华》为例
乔源桢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 250358)
1 《东邪西毒》——空间的失衡性与情感的迷失性
《东邪西毒》采用欧阳锋独白的方式展开剧情,以时间为线索,将一系列平行故事串联。摆脱了传统的武侠片类型模式,披着武侠的外衣单纯讲述江湖人的爱恨情仇。以失衡性的空间设置来表现侠士内心的不安与困惑,情感的孤独与迷失,以电影的隐喻性来讲述现代都市人的迷惘和游离。
电影中人物固守的那个空间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外化,在茫茫大海,各据一方的侠士各占一片自己的蓝天黄土。西毒,在茅草盖成的土屋里以绝情的交易逃避对现实的失望;慕容燕的居所,更为迷离。她忽男忽女的变换,在爱与恨的极端来回摆动,挂在洞中那只鸟笼就像是慕容被禁锢住永远无法逃脱的情结;盲剑客一直要赶在眼瞎之前回家乡看桃花,然而未尝所愿。他要去的地方,对他来说,只是幻梦一场,因为那是桃花的空间。桃花是盲剑客的妻子,而似乎永远都没离开那条幽静的河,牵着一匹马,站在五彩河中。基本上,每个人物都被他所处的空间所框定。正像被封闭人物的内心,自己走不出去,别人也走不进来。
沙漠是广阔的,同时也是荒凉的。正如东邪问西毒:“这沙漠的后面会是什么呢?”西毒说:“还不是另一个沙漠,每个人都以为这座沙漠的后面会比这里好,但走到那里时,又觉得原来比较美丽。”镜头下,看到的是西毒一个人孤独地在这荒凉的沙漠中做着江湖生意,丝毫不会动摇自己的商业原则帮助别人。落寞的背景处在广阔的沙漠空间中,人与景的比例是失调的,正是这比例的失衡,表现出了人物情感的迷失与内心的寂寞。
故事在广袤的沙漠中展开,也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影片中人物内心的情感荒漠。沙漠的一望无际给予人荒凉的同时也给了人无限的好奇心与探求欲。总以为明天是更好的,然而,多年后发现自己还在原地,或者过着差不多的生活,这也是现代都市人一直存在的现象
夜色中,欧阳锋想起自己爱人的一幕,镜头的倾斜使得空间呈现得失衡,空间的失衡实则也是人物内心的失衡。失衡画面充斥着挥之不去的回忆,越想忘记的回忆反而记得愈加清晰。电影中武侠人物的困惑,实也暗示了时间辗转中,都市人无法忘怀而又无法释怀的心理现状。
沙漠中,慕容燕与欧阳锋的谈话,慕容燕的脸呈45度倾斜,眼神中透着犀利与冷漠。开始处,欧阳锋交代自己的职业,人物面部主要居于画面内,而又没有全部入境。而欧阳锋与他人的接触,多依靠在门框上,人物所占的空间狭小而边缘。失衡的画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怪异的画面空间实则诉说着人物失裂苦楚而几近癫狂的内心独白。
《东邪西毒》以武侠为假托,将那片孤独寂寞的沙漠看做是寓言化的现代都市。因为怕被拒绝,所以先拒绝别人,因爱发疯,因爱生恨。种种爱恨情仇,是现代生活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冷漠与困惑的写照,是人与人交往的隔膜与猜忌的影射。
沙漠的广阔,多无望,多凄凉。空间的失衡,多分裂,多苦楚。
2 《重庆森林》——空间的封闭性与都市的冷漠性
《重庆森林》讲述了发生在香港的两段爱情故事。第一个故事讲述了漫游在街头的金发女杀手与编号223的警察相遇相爱的故事;第二个故事则讲述了在快餐店里工作的阿菲与编号663的警察的爱情故事。外界人对香港的想象是:浪漫的维多利亚港湾、高楼耸立的商场,这自然也是报刊电视所构建的媒体真实。而在从小生活在香港的大眼王家卫的镜头下,通过展现嘈杂熙攘的街道,各国人口聚集的重庆大厦,贩毒吸毒的人群,拥挤脏乱的公寓,还原了一个真实、本土化的香港。在这部影片中,以封闭性的空间构造,展现了现代都市的冷漠与人的自我封闭。
《重庆森林》中的空间是动荡不安的,充满着躁动情绪的封闭空间。人物在动荡漂离的空间中寻求生存的安定,在丧失真实的空间中寻找个人的真实。在商业化的公共场所,人物始终处于流动的状态,223与女毒枭的相遇如此,663与阿菲的接触也是如此。封闭性的空间不仅展现了香港本土真实的环境,更成为人物情感发展的地点背景。
在公共场所的呈现上,我们可以看到狭长、拥挤的街道;脏乱、喧闹的小吃街;人群快速流动的酒吧,涌动的扶梯人群。人群的流动与空间的狭小正是现代都市的写照。观影之外更有真切的感受,如同在北京赶地铁,一列车次驶离,人群拥满车厢,可依旧还有一大批人在等候着下一列列车的到来。人群流动中,步伐永远在加快。如此狭小的空间,没有交集,没有沟通。人群的流动性,更突显了个体存在的疏离。在电影中,梁朝伟饰演的663以极其缓慢的动作喝咖啡,而周围的人却以快得近于模糊的状态行走,这种人群中的“孤立”,正是当下每个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现实的冷漠便是这样:“人与人这样的孤单,在人潮之中相知相爱却根本不可能,即使我们最接近的时候,只有0.01公分。”这种冷漠性亦是一种悲哀。
663的住所,窗外是一条人来人往的电动过道;房内,空间局促而又狭小。663在前女友离开后,便将自己牢牢地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他排解自己内心孤独、压抑的感受大多不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而是自言自语。“失恋的时候去跑步,把身体里的水分蒸发掉就不会流泪”“当一个人哭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卷纸,而一间屋子哭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不难想象平日沉默寡言的人,背后这种自言自语的矛盾性格,这是封闭冷漠的环境下,自我安慰的方式。
封闭的空间既是环境的真实写照,也表现了人物的自我封闭。人群的流动性是快节奏生活的步伐,也表现了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而越是封闭的世界,越需要温情的存在,需要得越强烈,就越容易失落。空间的设置,不仅仅是情感的对应表达,更推动了叙事,通过空间设置来进行人物内心的情感宣泄。
3 《花样年华》——空间的限制性与爱恋的隐忍性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
当有妇之君遇上有夫之妇,这样一男一女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街上走来走去,看后又叫人为这隐忍的爱意想哭,就是《花样年华》所带来的。电影中,男主人公周慕云和女主人公苏丽珍,碰巧搬家成为邻居,两人发现他们的另一半发生了婚外情。婚姻生活的另一半出轨,使得周慕云与苏丽珍有机会相处。在相处过程中,两人发现对方有许多的共同爱好,感情越来越深厚,但最终他不够勇敢,她矜持顾虑,只得分道扬镳。电影中通过空间的限制性构造表达出了这段爱恋的隐忍性。
户主租客之间走廊的限制性空间,为这段隐忍的爱恋埋下了伏笔。房间和门口的墙壁成了人与人之间心理遮瞒的象征,逼仄的空间,只暴露了角色身体的摆动。狭小的空间造就了男女主人公最初关系建立的桥梁,也是男女主人公感情发展的道德屏障。房东太太暗示性地对苏丽珍说,年轻人应该懂得自爱,形成了外在的道德力量束缚。而人物内心对既成家庭婚姻的维持,是内在的不可逾越的束缚。道德束缚的存在,通过限制性的空间表达,诉说出了相爱而无法共处的隐忍。
拐角街道的限制性空间呈现,将这段隐忍的爱恋推到情感发展的高潮。拐角街道有斑驳的墙面,墙面中间是一条醒目的红线。墙面生锈的铁窗常常作为周慕云与苏丽珍的谈话背景。空间是封闭的,更有些禁锢的意味在其中。当周慕云与苏丽珍在铁窗前时,便有一种压迫、束缚的感觉。更像是枷锁,束缚了情欲的发展。而墙面上的红线,是两人之间存在的道德警戒线的明示。角落化的空间中,男女主人公从他们的角色扮演和情节假设到回归自己身份演绎的离别场景,传达着周慕云与苏丽珍的寂寞不安以及相处而不能相爱的克制。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挤满灰尘的玻璃,看得到却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返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无疑,《花样年华》是一个关于婚外情的故事,但同时也是一个对失落的年代记忆的追思。有的是爱情来去皆身不由己的怅惘,以及如花美眷的似水年华……
王家卫以电影空间来对应人物情感,使影像与现实相互映射。《东邪西毒》以失衡的空间来表现迷失的情感;《重庆森林》以封闭的空间来表现冷漠的都市;《花样年华》以限制的空间来表现隐忍的爱意。将空间的建构作为情感的表达,涵盖了导演对于现代都市人的人文关怀和对当下都市生活状态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