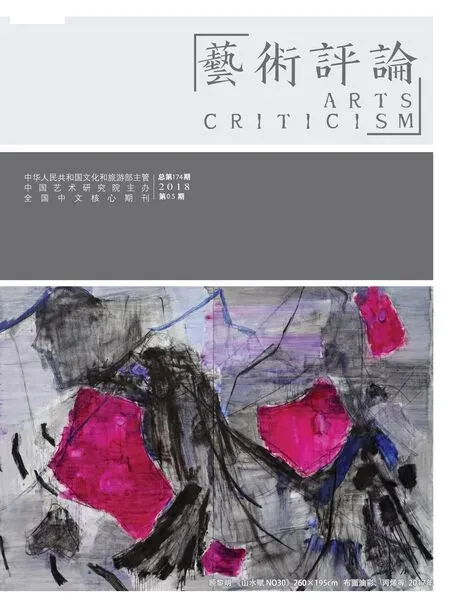《国家宝藏》:基于媒介的新故事化策略
吴 静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博类电视节目模式显著转变。早期节目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注重现场互动氛围的综艺类节目,如引起民间寻宝热的央视《鉴宝》节目,随后被各大卫视纷纷仿效而风靡全国。该形式以大众的收藏品为对象,通过现场专家鉴定、讲授知识、估价的形式,挖掘收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达到传播艺术文化知识、提高大众艺术鉴定鉴赏水平的目的。二是以纪录片为主要形式,如从2004年至今播出的《国宝档案》,节目以国宝级文物为对象,通过主持人口述、情景再现、多角度展示文物等方式,展开对文物及其背后故事的讲述。
2015年,在国家与社会对“匠人精神”普遍关注的时代要求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独特的视角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博物馆及其中的人与物,以清新平实的叙述风格,让博物馆与文物不再是聚光灯下、警戒线后遥不可及的存在,观众在理解博物馆生活和文物的同时有了真实的情感投入。可以说,《我在故宫修文物》掀起了一股博物馆的关注热潮,由此成为文博类纪录片里程碑式的转折点。2017年末,现象级文博类大型综艺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接力《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携手八家重量级博物馆(院)集体亮相,开启了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新形态。节目一开播遂即引爆舆论,截至2018年4月,基于央视这一主阵地,微博话题#CCTV国家宝藏#阅读量达18.7亿,粉丝讨论量破100万,居文化类综艺节目第一,豆瓣评分达到9.2,使其一举荣登内地年度综艺节目得分榜首。
自2017年12月初《国家宝藏》开播以来,“博物馆”已成为国内旅游产品搜索的热门词汇,“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是众多旅游项目新口号。博物馆与其藏品再次成为社会焦点,公众除了走进博物馆进行常规参观外,开始更加渴望深度体验博物馆,感受其间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运用电视媒介传播博物馆文化,内部嵌套着两个叙事系统:博物馆文物自身的故事,以及媒介对前者进行“新故事化”塑造的过程。博物馆提供的是内容基础,媒介呈现的则是叙述形式。这类节目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根据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创新媒介内容的编排方式,讲好博物馆和文物故事。“好”的标准至少包含两方面考量:博物馆文物的知识与内涵的表达到位;观众对知识与情感的接受到位。这要求以博物馆与博物馆文物为核心的节目编排中,既要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让知识立体化、多维化,又要寻求合理的叙事策略,让这些“故事”通过新的叙述更加深入人心。
一、语境还原:关于文物故事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通过特定方式激活文物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让文物不再只是柜子里冰冷的实体、而是蕴含历史、人文温度的所在。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国家宝藏》,在重新活化文物生命这一点上无疑都是成功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以纪录片的方式将关注点放置于“文博工作者”和“他们眼中的文物”;《国家宝藏》则融合了纪录片、真人秀、舞台表演等综合艺术形式,创造出纪录式的综艺样态。围绕的文物产生背景和流变过程,《国家宝藏》通过多元的叙述方式,将文物做了“语境还原”,这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一种崭新尝试与探索。
从综艺节目的角度看,要让文物活起来,首先体现在文物的出场与展示方式的创新上,即考量如何从博物馆的静态展示转变为媒介上的动态呈现。其次,如何让文物信息更加立体、生动地出场与展示成为关键。《国家宝藏》利用了舞台展示的优势,结合大量科技手段,尽可能呈现出文物的全貌与辉煌。如第一期故宫博物院《千里江山图》的出场,观众焦点被集中于舞台上设置的巨型led环幕上。通过移动的千里江山图卷,现场与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产生“人在画中游”的移步换景之感。数字化手段的运用让这幅在博物馆里长时间沉静的卷轴画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观众也在极强的视觉冲击下,产生了对所见之物的好奇与尊敬。
对文物信息的全方位展示,是让文物能“说话”的关键。这一信息传递,不再如以往说教式的知识传输,是在对文物的多元演绎与立体知识展现中,让观众找到文物与它所衍生流变环境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展览形式多限于静态展柜陈列模式,除了使用标签对文物基本情况做文字说明外,很难还原围绕文物的相关历史与文化语境。如藏品如何被发现,在发掘现场,它与周边文物的关系如何,在它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它都经过哪些历史阐释和意义变化才成为今天的文化状态,人们该如何欣赏它们等。现实中博物馆的陈列方式,常将文物与原生环境割裂,也因此让观众产生了对博物馆文物的碎片化感受,多数观众只能对文物形成浅表和直觉似的印象。
通过媒介的再叙述,《国家宝藏》很大程度上重建了文物与环境的关系,它弥补了现实中博物馆静态展示所产生的局限,让文物在电视屏幕上真正的“活”起来。在《国家宝藏》“前世传奇”+“今生故事”的叙述结构中,前半部分对文物“前世”的说明含有演绎成分,但通过这种真实背景结合推测性的新阐述方式,与文物相关联的历史文化信息,如制作者、具体材质、创作机缘、发掘时空等,得到了全方位的呈现。
博物馆中所蕴含的巨大文化能量,其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对过往的追溯。“了解很久以前发生其间的故事会使当下的体验更为充实。”《国家宝藏》讲述过程中的“今生故事”,出于这类考虑。通过文物与现时时空的嫁接,以及“人”与“时间”对文物的渗透,历史久远的文物背后蕴含的内涵得以深化。流失文物的国外追索、当代复制技艺、最新研究进展等信息的陈述,“今生故事”的呈现本质上是一个文化共享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享了文物的阶段性内涵,使节目对古代之文物的讲述,不再只是询问过往,理解过去,而是对当下的人和事产生影响。《国家宝藏》的每一个文物故事,都经过了前期调研,一个剧本的敲定至少要经过 20 稿修改。经过漫长的制作,最终才是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宝藏》。
诚然,《国家宝藏》所能展现的文物只是博物馆浩如烟海藏品中的极少部分。这种语境还原的效应在于,它引起了人们对文物知识的探索兴趣,并指明了在深入理解一件博物馆藏品内涵时所应遵循的基本逻辑与途径。这一启蒙的导向作用或许才是《国家宝藏》展开对文物的叙述时所看重的意义。
二、人、物与情感:媒介的新故事化策略
如果说节目挖掘文物的内涵与知识的能力决定着博物馆文化表达是否到位,它需要借助充分的文物信息和相关文博领域专家来辅助进行,那么观众的兴趣引发和情感接受能否实现则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介的组织化策略。
通过电视媒介讲好关于文物的故事,要充分考虑受众对文物知识的普遍认知程度、情感关联和共鸣点,并恰当掌握迎合与引导间的分寸。为实现这些目的,新故事化的进行仅仅依靠文物本身或关于它的知识难以实现。打动观众需要在博物馆藏品与他们之间建立起关联,让物质形态上冰冷的文物因为人的情感介入变得温暖起来,以此引发观众对博物馆文物和文化的亲近感和足够的前期兴趣。《我在故宫修文物》和《国家宝藏》虽有纪录片叙事与舞台化叙事的差异,但在内在思路上都是通过建立起了一种核心的“人-物”关系来实现陈述的感染力。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特殊之处是关注了鲜为人知的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通过平实地记录和讲述修复师的日常工作,它展现了一个个“文物会生病”的故事。虽然没有太多围绕文物自身的知识性输出,但从文博工作者的视角,将真实世界的“人”与博物馆里有着深远历史感和文化感的“物”联系在一起。它让观众感觉到,博物馆里的藏品并非都锁闭在库房和展柜中的冰冷之器,也不都是聚光灯下高高在上的千古传奇,它们会受伤、生病,它们需要一代代“文物医生”的精心呵护。在新奇和生动感受下,通过文博工作者与文物建立起的这种关联,观众和文物之间也产生了一种奇妙而特殊的亲近感。相较《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尽管在文物知识传递上较少,但它的意义在于经由这一叙述方式,在现代人和博物馆中的这些文化载体间搭设起一座“桥梁”。观众在文物修复师的视角下感受到博物馆生活的平静与温暖,以及对博物馆藏品的情感。这种对文物的真实亲近感引发了良好的后续效应,人们愿意更多地走进博物馆看看这些经过人所感化的文物,并想要认真研究它们背后的故事。这激发了更多的年轻人主动报考文博专业,投身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
《国家宝藏》所搭建的人和物的关联完全是另一种方式。节目中最夺人眼球的创新是邀请了和文物本身关系并不大的27名影视明星来参与文物故事的演绎和讲述。不管这些明星有多么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能激起大众多少的亲切感,他们和文物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短暂而略显突兀的,甚至可以说是脱离的。它容易造成一种关注度困扰:观众的焦点是明星还是文物?从全部节目效果来看,文博教授齐东方对于考古心得和对文物情感的讲述,效果要好于明星们的背诵与演绎。这可以说是人为建立起短暂的“人-物”关系和类似于《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那些基于文博工作者与文物之间真实的情感关系带给观众心理感受上的不同。当然,这种临时搭建的“人-物”关系有着自身的客观考量:《国家宝藏》的节目性质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固定的舞台空间中拉开一个虚拟的情境,它无法实现“人-物”情感关系的娓娓道来。这种短暂的“人-物”关系也是追求收视效果的需要。作为一种产业,媒介的重要任务是保证足够的收视率。除了内容本身的丰富性和吸引力外,话题内容、演示方式、明星效应都是需要考虑的收视因素。从最终效果来看,策略使用是成功的:各守护人都有着自己庞大的粉丝群,尤其是青年群体。据大数据分析,《国家宝藏》观众的主体构成人群中,年龄集中度最高的是20岁到25岁,排名第二的是15岁到20岁年龄段,广大年轻观众持续在B站、豆瓣、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刷屏、点赞及分享。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将传统文化转变为年轻一代喜闻乐见的方式,确实可以达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与学习的效果。当然,让年轻观众从“感兴趣”到有所思考和行动,是媒介叙事最核心的使命。《国家宝藏》也通过明星演员在节目中的恰当演出,最终将观众引导回节目的本质——对文化与历史的深切感受上。
从表面上看,《国家宝藏》的叙事本质和整体逻辑与传统教科书的知识传递方式差别不大:介绍国家的重要文物,及其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九大博物馆选取的文物多是镇馆之宝,如长沙窑诗文执壶、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可以说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历史,在制作中极易开展宏大叙事。在节目过程中,不断叩动文物所蕴含的遥远和陌生的知识,以高频率的悬念设置激起观众的好奇心理,达到吸引观看的目的。
媒介采取的故事化形式,其选择标准与最终价值落脚点息息相关。与《我在故宫修文物》所致力于实现的“拉近”感不同,《国家宝藏》试图通过强化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与文化,让它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抬高”,成为带着绚烂光环的“国家宝藏”,在历史和文化陌生感的展开过程中,文物和现代人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这种“抬高”与“拉近”的差异,来自《国家宝藏》与《我在故宫修文物》内在价值落脚点不同——《国家宝藏》的根本价值理念是要让观众通过文物,激起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三、结语
文化自信的树立,首要前提是对文化本身有着深入的了解。挖掘传统文化使之产生新的公共影响力,需要借助特定和实在的载体。博物馆是蕴含艺术、历史、文化和各种人文内涵的巨大宝库。“一座好的博物馆能够吸引观众,为观众提供娱乐,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引发疑问——从而促进学习 。”但如何让公众意识到博物馆不再只是一个“藏有古董的建筑”或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文化“黑洞”,而是一个充满有趣故事,蕴含历史、人文温度的文化宝藏,以此让他们更愿意走入博物馆,理解中华文化,树立对民族与国家的自信。从目前的社会效应来看,电视以及新兴媒介的介入对博物馆文化的社会传播功不可没。通过媒介对博物馆的新故事化叙述,博物馆文物承载的文化生命被重新激活,并被更加广泛地认知与喜爱。中华文明中的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也经由媒介的策略化推广,润物细无声地渗入公众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建构和文化认同中。
注释:
[1]〔美〕大卫·卡里尔.博物馆怀疑论[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43.
[2]〔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玛丽·亚历山大.博物馆变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