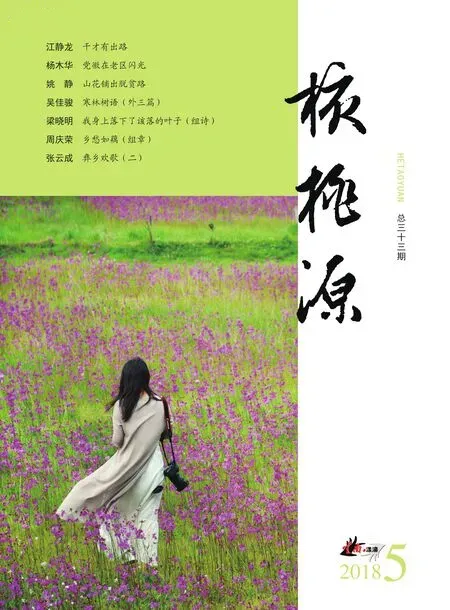寒林树语(外三篇)
吴佳骏
我曾经常走进那片树林。
有时,是受一只鸟的引领;有时,是受一种莫名的情绪引领。那片树林不大,树种以青杠树居多。特别是夏季,下过几场雨之后,树林里杂菌丛生。这时进林,准能捡到大小不等的菌子。拿回家洗净,炖成汤,真是又鲜又香。
可现在是冬天,无菌可捡。也没有鸟为我引路,我的情绪也很正常。我之所以走进树林,是我听到了树的召唤。离开故乡多年,我时常在梦中看到树披头散发的样子,在风中奔跑。边跑边喊我的名字。醒来,树又全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它的喊声,不断在我耳边萦绕。我的脊背一阵冰凉,泪珠像两枚细小的卵,在眼眶搭建的肉巢里滚来滚去。
那些树都还认得我。我从树底下走过,落叶铺了厚厚一层。脚踩在上面,软软的,挺柔和。这是它们为迎接我这个游子,专门铺设的地毯。这仪式太隆重了,我感到十分羞愧。我伸出手,顺着树干一棵一棵地抚摸。我不仅摸到了树那潮润的皮肤,也摸到了自己的年轮。有的树杆上结了痂,手摸上去,硬硬的。我怕碰疼它们,就住了手。每一个疤痕,都是曾经的一道伤口。那些伤口里,藏满了生长的秘密。
遥记当年,我利用上学的间歇,养了几只兔子。每天放学后,我唯一要干的事情,便是去菜地里给兔子扯草。短短几个月时间,兔子被我养得又肥又胖。父亲为犒赏我,还特地砍来竹子,替兔子编织了一个大笼子。看着兔子在笼子里活蹦乱跳的样子,我感觉生活无比的美好。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有天我放学归来,跑到兔笼前一看,其中一只灰毛兔爬在笼内一动不动。我揭开笼盖,用手一摸,兔子的身子已经僵硬了。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既不想把这事告诉还在坡地干活未归的父母,也不想压抑自己的悲伤。低泣一阵之后,我抱着死去的兔子,提起墙角的一把锄头,向那片树林里走去。我将那只灰毛兔埋在了林子西边一棵苦楝树下,还用随身带的小刀在树身上刻下“爱兔”两字,以示对这只兔子的哀悼。埋掉灰毛兔,天已经黑了。父母早已回家,他们看到我沮丧的表情,一句话都没说。母亲接过我手里的锄头,就转身去灶房煮晚饭去了。从那天起,他们再没向我提过那只灰毛兔。他们不想去触碰我的伤疤。
如果树也有记忆,它们一定会记得当年有个孩子,在一个薄暮时分,曾静静地走近过它们。那个孩子,他独自穿过密林,穿过正在降临的黑暗,穿过被无限放大的悲伤。他徘徊又徘徊,站在树下,听风吹树响。所有的树,都在默默地看着他。尔后,树们开始窃窃私语。议论着一个孩子内心的风暴,和一只兔子的死亡。最终,它们又看见那个孩子,在绝望的笼罩下,摸索着找到了回家的路。
我不能再继续回忆了,也不能替树去回忆。不管是树或人,都不应该老是活在回忆里。我绕着树林走了一圈,林子里寒气森森。雾霭包裹着树叶,湿漉漉的,仿佛刚刚哭过。只是我不知道,它们是因为高兴哭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棵树站久了,也会很独孤。别看它们伴侣多,其实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之间,永远难于靠近,也根本不会走进彼此的内心。真正了解一棵树的,不是树,也不是种树者和伐木工;而是风和雨,阳光和空气,水分和气候。这跟人类很相似,一个人倘要走进另一个人,那中间永远横亘着一道鸿沟。不论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多么亲密,多么特殊。因此,也才有那么多渴望被了解的人,悄悄走向山川河流,旷野丘陵;走向一朵花,一块石头。他们相信,只有自然界的这些东西,方能安妥他们迷离彷徨的心灵。
如此说来,我在这个冬季走进一片树林,也是在为自己那渴望被知晓的心灵寻找一条路径吗?
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惟有树梢动了动,像是摇头,又像点头。
青 瓦
昨夜。风大。屋后的竹子受风的指使,扫掉了我家屋顶上的几匹青瓦。那时正值夜里十一点钟,青瓦落地的响声惊醒了沉睡中的父亲。他从床上爬起,打着手电筒,到屋外转了一圈后,又回屋蜷缩进了被窝,像一个患梦游症的人。我躺在隔壁的木床上翻看一本名为《旧都的味道》的书,作者是一个叫薄田泣堇的日本作家。我合上书页,准备入睡。这时,父亲的鼾声穿过墙缝,在我的耳膜上此起彼伏。屋外的风更大了,咆哮着,像个黑夜中的暴徒。瞬间,我的睡眠和父亲的鼾声都被风粗暴地掳走了。又一匹青瓦,从房顶坠落,砸向黑夜的脊背。
第二天清晨,风停了,我赶紧跑去屋后察看。两根老竹,一根嫩竹,倒在屋顶。竹叶尽脱,竹枝插在瓦楞中,形象十分狼狈。瓦脊上,蹲着一只鸟,羽毛被晨雾濡湿。我轻轻摇动老竹,想让它飞走。可鸟就是不飞,依旧静静地蹲着,也许它早已厌倦了飞翔。我凝视着鸟,鸟也凝视着我。一下子,我的心中涌起太多的话,却不知道对谁说。这些话语,闷在我心里若干年,跟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全都长满了青苔。
青苔长在瓦上,就像白发长在父亲的头上。青苔和白发,都是岁月的物证。正这么胡思乱想着,我脚底一滑,身体撞在一根竹子上,落下的水珠滴进我的脖颈,寒冷迅速将我包裹。我一个激灵,仿佛大梦初醒。回转身,见父亲拿着一把柴刀向我走来。他要将倒在屋顶的竹子砍掉。不然,竹子还会扫掉青瓦。在父亲眼中,每一匹青瓦,都如鱼身上的一片鳞甲。鳞甲每掉一片,鱼就会疼痛一次。青瓦每掉一匹,房屋也会疼痛一次。父亲最怕见到疼痛,因为他一生都在被疼痛追杀和围剿。
夏 屋
那屋子,筑在一条河岸上。灰旧,破败,像是早已被废弃多年。夏日的早晨或黄昏,屋子静谧的影子倒映在河面上,有种不真实感。倘若有风吹过,水波一皱,那屋影就全被揉碎了,只剩下河水对屋子的追忆。
许多年以来,那屋子的门都关闭着,阳光照不进去,只能照在那两扇褪色的灰白的木门上,以及木门上雕刻的同样褪色的残朽门神上。早些年,或许是出于好奇,村里人上坡干活或收工回家,路过那屋门前时,都要习惯性地从窗户外朝里瞅瞅。屋子里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是一张桌子,一张床,几条凳子和两张椅子。最显眼的,是堂屋的香案。香案上一年四季都燃着香,袅袅青烟环绕和弥漫在屋内。香案旁侧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黑白照片,落满了灰尘。那是一张中年男人的面孔,目光呆滞,神情麻木,蜘蛛网罩着他的眼,耳,鼻,舌;也罩着他的瘦,冷,和苍白。很显然,这个照片上的男人,已经被死亡领走了,去了一个非常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后来的一天,那屋子的窗户被一块蓝印花布给遮住了,村人们的窥探的视线因之被挡在了窗外,只余下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在村子里游走。从此,那座房屋成了村里一个漆黑的“城堡”。这个城堡比卡夫卡笔下的城堡还要令人费解。然而很可惜,我们村里没有土地测量员,只有石匠和木匠。否则,就可以找个借口,派人去悄悄靠近那个城堡,靠近城堡里面的秘密和幽暗了。
现在是六月里的一天,我回乡居住的第123个日子。我那天的心情很烦躁,书也看不进去。拿在手里翻开,书上的字迹全都模糊一片,像画家滴在宣纸上的墨团。文章更是写不出来,打开电脑,又关上。一会重新打开,还是写不出,灵感全都被电击了似的。我索性拿起鱼竿,提着桶去河边钓鱼。当我从那座屋门前走过时,我嗅到一股淡淡的青香燃烧的气味。我停下了脚步,站在院子里。那院子很干净,连一片树叶也没有。更看不到鸡、鸭和狗的身影,也听不到有猪和羊的叫声。太阳依旧明亮而放荡地照耀着。屋子依旧落寞而封闭地存在着。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没了钓鱼的兴致。
我伫立在院坝里,脑海里不断地闪过这屋里住着的那个女人的模样 。她把自己关在这屋子里已经十几年了。她不是个疯子,精神很正常的,可偏喜欢将自己幽闭起来。她怕见光,怕淋雨,怕吹风,怕屋外的一切。她活在村子之中,又活在村子之外。这十几年来,只有少数几个村民看到她走出过屋子——她在院坝里站了一会后,很快又钻进了屋,掩上门,拉上窗户的蓝印花布——整个世界又一次剩下她独自一人了。
印象中,我还是在多年前的一个盛夏的午后,看到过她一次。那年天大旱,高温持续了两个多月,滴雨未下,田地都龟裂着,树木和竹子有的也被骄阳晒死。我回乡看望父母,刚爬到山路的转弯处,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出现在路边,着实吓了我一跳。她手里拿着一把割草刀,好似在找什么草药。那会儿村人们都还躲在家里午休,野外没有人。她一见到我,似乎也被吓到了,转身就跑,像被太阳追着似的。跑着跑着,她就化掉了,不见了影子。
那个女人有个儿子,年龄四十好几了,单身,在外地一家不知什么工厂打工。逢年过节,还能看到他回来。平常是绝看不到的。但即便是儿子在家,那个女人也是不会从屋子里出来露面的。她的儿子也不会强迫她出来。他们似乎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即便他们彼此间还有那么点爱,也难以治愈他们那各自心里的终极的孤独。这孤独多像卡森•麦卡勒斯的那部《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书里所昭示的孤独啊——那个镇上的哑巴——一个名叫辛格的银器雕刻工的孤独。
从屋子里弥散出来的青香的气味越来越浓,我再一次看了看这屋子。我知道里面住着一个女人,那屋子既是她的壳,也是她的心;既是她的监狱,也是她的佛堂。
草 药
夏日。早晨。初升的朝阳是傲慢的。它目空一切,发出万道金光,狠狠地将那光的芒刺扎进大地的肌肤。大地静穆着,承受着,既不嚎叫,也不喊疼——莫非是大地已然习惯了将那太阳的芒刺当作扎入土层的疗伤的针灸了么?
这样想着,我便跟着村子里的几个老人走向了山坡。我们要去山上挖草药。我好多年都没挖过草药了,怕认错,只能跟着几个老人走。他们熟悉各种草药,宛如熟悉大地上的每一条路,每一道坎,每一滴水,每一棵树。那些草药仿佛都是他们种植的。他们个个都是我们村里的李时珍,遍尝过百草——酸的,甜的,苦的,涩的,有毒的,没毒的,他们都咀嚼过。他们吃粮食长大,也吃草药长大。他们是农民,命贱如草。他们生了病,没钱去医院治疗,又不想在家等死,就自己上山挖草药救命。他们无论生了什么病,普通的,怪异的,疑难的,轻微的,都吃同样的药。他们只有一张药方,村里所有的病患者都按照这张药方去抓药。有的人吃了好了,有的人吃了疯了,有的人吃了笑了,有的人吃了哭了,有的人吃了活蹦乱跳,有的人吃了呆若木鸡,有的人吃了益寿延年,有的人吃了命归阴曹……
我每次回乡,奶奶都要叫我去给她挖草药。她身体不好,疾病缠身。我劝她去医院,她死活不去。她说唯有草药可以维持住她的性命。这次也是她叫我去挖的。她说趁我在家,多替她挖一些。山坡上杂草丛生,弥漫着山野气息。朝霞落在草叶上,形成淡淡的一抹红。我在几个老人的指引下,低头仔细地寻觅着,辨识着,我希望替我奶奶找到更多的“还魂草”,使她远离疾病和痛苦,恐慌和灾难,困厄和死亡。我慢慢地在草丛里走着,我多想找到那些藏在草间的宝贝——金银花、紫地丁、夏枯草、石菖蒲、过路黄、忍冬花……,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我怀疑它们都被太阳晒化了,或者被那几个老者提前挖完了(他们身上的疾病并不比我奶奶的少)。难道是他们怕我抢挖这些救命仙草,故意不告诉我的么?不然,那些草药为何找不见了呢——它们不会是跑到我奶奶的身体里去了,抑或跑到鲁迅先生的小说《药》里去了吧?这些“野草”哟,乡下的野草,梦里的野草,呐喊中的野草,救治生命和精神的野草。
太阳又升高了一些,照得大地热辣辣的。然而,大地依旧静穆着,承受着,既不嚎叫,也不喊疼。那几个老人也不喊疼。他们领着我,从这个坡走到那个坡,捉迷藏似的。有时走到一株野草旁,他们故意低下头,脸上流露出惊喜。随即,又摇摇头,直起身,继续朝草地前面走去。我跟在他们后头,亦步亦趋。当我走到他们刚才低头看过的那株草旁时,我凭借童年的印象和记忆,断定那的确就是一株草药,只是我叫不出名字。我追上他们,很真诚地问道:那不就是草药吗?几个老人相视莞尔一笑,全都摆摆手,陷入长久的沉默。
整整一个上午,我们都在山坡上晃悠。我知道,那几个老人委实是在骗我。他们不希望我挖到草药。我毕竟比他们年轻,体力比他们好,动作比他们快。若挖起草药来,他们肯定抢不过我。尽管,他们都知道,我来挖草药并非是为自己,而是为我多病的奶奶。但我不明白,这几个老人都是我的长辈,平素在村子里也都是最为慷慨的人,为何这会儿就变得那么自私了呢?那一刻,我的内心有风暴在肆虐。我很想冲上去,拆穿他们的谎言,就像我很想以自己的愤怒去抵抗这初夏的朝阳的傲慢。但我最终还是忍住了。倘若我真的跟他们过不去,也就是在跟我的奶奶过不去,跟衰老过不去,跟活着本身过去不。
那么,我索性就这样跟着他们走。他们走到那里,我就走到那里。他们从草旁走过,我就从草旁走过;他们从药旁走过,我就从药旁走过。只要他们不说那草是药,我就绝对不会弯腰去割。我宁可辜负我的奶奶,也不会伤害这几个老人。因为,我的奶奶和他们都很老了。老了的奶奶身边至少还有我这个孙子,可那几个老人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只剩下他们自己。
他们都把自己活成了一味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