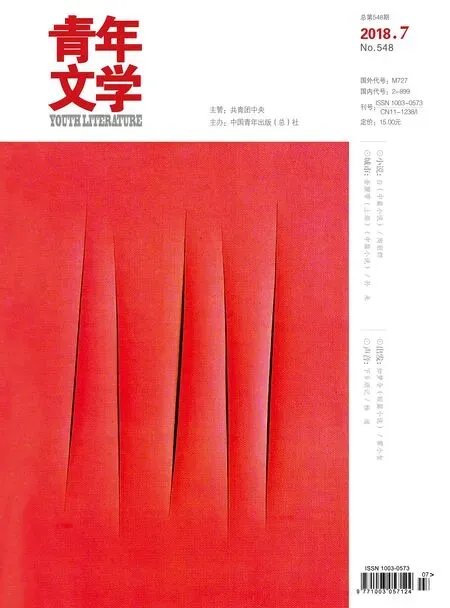东阿之行
⊙ 文/蔡 东
最近几年,我跟家人都不太愿意旅行了。所到之处虽与长居之地风物迥然,出行过程中却有个感觉越来越强烈,接下来要经历的一切都是定制好的,深陷于某种样式难以挣脱,链条式地一环接着一环。野地的尽头,孤山的深处,也活跃着极其职业化的经营者,一颦一笑皆滑熟,所有的步骤清晰明白,闭着眼也能走完流程。我隐隐感到时态出了问题,人们并不忠实于现在,没有偶然,没有即兴的元素,多义让位于确然,未知被已知强行覆盖。
路上被不停提醒,提醒我正走入一个高度成熟反复运转的体系中,陌生感越来越稀薄。商业模式的天经地义,那种懒得遮掩的直白和明确,既让人惊骇,也让人羞愧。山川草木经由多年的驯养,神魂恍惚若失,一处处风景不光被命名,还要被所谓的传说故事陈腐而低俗地表达着。
这样的旅程无法让人专注,也注定无法提供灵光乍现、物我两忘的生命瞬间。刚想沉进去好好体会一番,就有一种人工的造作,愣愣地把你从美妙的临界状态中拉出来。后来,脑海里一个词语渐渐清晰起来,是个流行用语,恰恰也因为流行语特有的轻浮浅陋,用在这里才格外贴切。
套路。蓦然惊觉自己身处套路的一刹那,兴味全无,真实感也消散了,好像置身于一个经不起细看的大片场。套路天然地与诚恳和认真无关,而大抵与平庸联袂相伴,套路意味着确定、重复、省劲儿、无须用心,抄近路,走捷径,浮皮潦草地在表层上滑动。一个套路化的行业,很难见到认真的人和认真的活计。
回想前人的游记,登山,踏青,访梅,游园,文字记录的是随心随性、不拘格律的游历,是人跟世间万物的无尽情味。山林溪湖,轩榭廊坊,也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姿态。读李元阳《清溪三潭记》,“源出山下石间,涌沸为潭。深丈许,明莹不可藏针。小石布底,累累如卵如珠,青绿白黑,丽于宝玉,错如霞绮”,文字之清丽,状物之传神,读来心生愉悦,但真正让我“出神”的是后面的语句,“才有坠叶到潭面,鸟随衔去”。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呆呆地坐了很久才回过神来。周围的时空消失了,倏忽间仿佛已来到水畔,亲眼看着这一幕,叶落,飘坠水面,鸟来,衔叶而去,这是人跟物象心领神会才能“看见”的妙境。描绘潭水是铺开一幅平面图,到这里,笔宕了出去,图画开始活动,一重又一重次第伸展,它变得深远了,也变得复杂和开阔了。树生长的岸,鸟飞来的天空,风景和生灵,静谧和跳脱,纳进了平实而富有神性的只字片言中。而图景对面的那位游人,松弛,心定,安住于那一刻,即使隔着千里再加上百年,我依然能体悟到他的心境。
从一个套路匆忙赶往另一个套路的行程,来不及跟山水互生情愫,也不太可能沉浸到幽渺的秘境中。路上遇到的人,往往极其精明理性,并且不惮于暴露冷漠,精于毫无缓冲的急停,一转身便是没有下文的两讫的干脆。我心里明白于其不过是一份营生,但对于那新鲜寒凉的茬口,那蓦然出现的大片空白,还是很难马上接受和适应。
不期然地,在本以为寻常的一次文学采风中,却感受到对方情感的注入,体验到盘桓流连的人情味儿,也了解到认真做产品的难度,做实业,的确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东阿离我老家不远,这个地名从小听到大,仅限于听说,去年的秋末冬初,才总算有机会来这里看看。到了东阿,先见到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的马淑敏女士,也许是因为她的热情实在,见面后不觉得生疏,又加上她工作之余也写小说,话题就更多了。此后的几天,也时时能感受到同行的工作人员的周到细致。对企业来说,组织类似的作家采风想必不是头一回了,但相处下来,感觉组织方一点儿也不疲沓,气氛始终和乐,也没有走过场的感觉,他们尊重此时此刻,身心真正地处在此时此刻的相遇和交流中,自然而然地投入情感。后来过了很久,我还会回想起在东阿的那几日,觉得是值得记住和可堪重温的一段经历。
除了定好的几处参观地点,采风过程中亦有闲笔和分岔。聊天时我们才知道曹植葬于东阿城南,见大家都有兴趣,便临时安排去拜谒曹植墓。那天早晨,空气有些清寒,我从侧门进入,发现墓园倚着平原地区低矮的山而建,遍植松树,辟邪、石马等雕像列于石板路的两侧,园中几座亭子里放着几块残碑,其中一座亭子似乎有些年月了,顶上瓦片缝隙间长出一把把细瘦的蒿草,风吹过来,摇摇荡荡的。墓园里人不多,清静中有些寥落,作为埋骨之地是正相宜的。来曹植墓之前,我才意识到此前从没想过曹植死后的去处,好像他这般的仙才,只会让人记得他的年轻,他的放旷,以及不惧时光流逝的星辰般的诗文。
接下来的生产区参观相当于入正题,刚进去时有些恍惚,隔着透明玻璃,看到里面设计极简,色调上白色为主,各种仪器和闪烁的电子屏,像电影大片里的高科技实验室,跟自己想象的中医药“古风”制作方式完全不同。从产品上讲,我很喜欢阿胶糕系列,外观设计有美感,配的几个小布包用料讲究有情致,也含着一份体贴的心思,里面的糕点美不美容不知道,总归是美味的,香甜可口。
一路走下来,能体会到他们盛名之下依然愿意用心的纯粹和赤诚,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情感和心力更多的付出。虽有传统可以依傍,名声可以仗恃,但总有人不接受套路的诱惑,深知这诱惑背后是对创造力的禁锢,做一件事可以老于世故,只追求轻松流畅无难度,也可以冲开已有经验去找寻其他的可能。
万事万物相通,这大概也是真正的艺术创作者跟“流水线”俗手的差别所在,有些文字和电影,看完会有一个感觉;感觉是机器写的、机器编剧的,敷衍成篇,似曾相识,没有打动人的细节,丝毫感受不到人的智慧和情感的力量。看的过程中没有会心了然的笑,更不会有眼睛湿润,呼吸骤停,无法言语,既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活着,又恍然无我的美妙体验了。总觉得,不管构思和具体书写之间的鸿沟有多深,不管最终成品如何,至少在创作之初要有突破程式的追求。
所谓的通俗文学,看似情节老套、类型化倾向严重,但天赋、艺术自觉加上苦心孤诣,依然能在行文中创造性地逃脱程式的落网,跃升到另一重境界。高中时读的《射雕英雄传》,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铁掌峰顶的那个章节,我被金庸的处理方式深深震撼过。
黄蓉托大被裘千仞所伤,郭靖抱着她飞奔到峰顶的禁地中暂避,查看之下伤势严重,此时铁掌帮众举着火把在山腰叫骂,洞内偏又遇上狡诈的裘千丈,四处无路可逃,情势诡谲危机,让人揪心。不料接下去金庸是这样写的:郭靖进洞内探看,发现木盒拿到外室,见盒里是岳飞留下的两本册子,黄蓉让他读一段来听,于是在如此危急的时刻,郭靖朗声读起《五岳祠盟记》,原文写道:“这篇短记写尽了岳飞一生的抱负。郭靖识字有限,但胸中激起了慷慨激昂之情,虽有几个字读错了音,竟也把这篇题记读得声音铿锵,甚是动听。”接着他又顺次读了岳飞的《小重山》《题翠光寺》几首诗词,这会儿铁掌帮众仍喊声不绝,紧逼不已,郭靖让黄蓉枕在腿上,读完“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这般的诗句,两人在松柴火光中静静依偎,说着话。
读到这里时,我愣住了,不再往下读,好像不再关心二人怎么脱险,觉得那不是很重要紧迫的事情了,我只想在这微妙至深的情境中待一会儿,再多待一会儿。震撼我的,不仅仅是韵味的复杂、收放的自如、节奏感的精妙、手法上的高明,而是险境中这个画面本身所包孕的飞扬而奇异的诗意。那种别致的意趣,感染我的是生命的天真淡然,是作者本身秉有并赋予人物的小孩心性和少年意气,真正让意境得以诞生的,也恰恰是这些元素。
读书好就好在常会经历这样的时刻,和创作者遥相感应,精神上狂喜、如痴如醉,领悟后清明澄澈,虽短暂易逝,却刻骨难忘。一年一年每次重读“射雕”,我依然觉得这一章很动人,并为年少时便遇上这样不落窠臼的作家而对生活充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