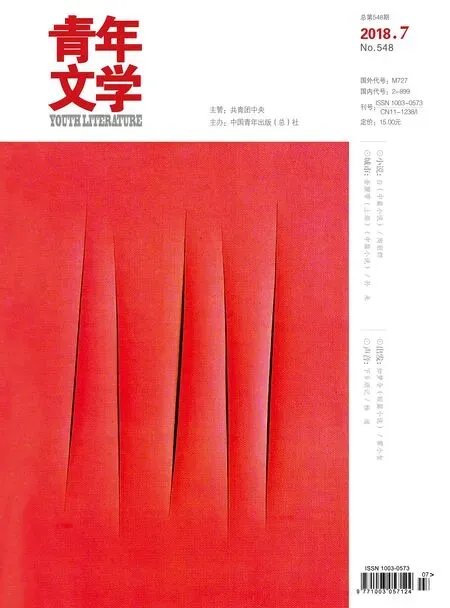守住本分也是一种美德
——读陶丽群小说的一点感想
⊙ 文/陈集益
在小说创作上,我一直推崇创新,但这并不是说,一味追求文本探索、技术革命等等,就一定是件好事。相反,盲目地放大所谓创新的意义,有时候会导致文学传统精髓丢失,写出过于炫技、脱离现实或者刻意违背伦理的作品。陶丽群的先见之明,是知道自己的长处、短处在哪儿,文学矿脉在哪儿。她的小说有独属于她的经验、情理、逻辑,轻与重、灵与肉。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精致、扎实,从容、耐心,恰如其分。王安忆曾说:“福楼拜(的小说)真像机械钟表的仪器一样,严丝合缝,它的转动那么有效率……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观,你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陶丽群的大部分小说也可以拿“严丝合缝”来形容。比如《杜普特的悲伤》,把杜普特为父亲买棺材的过程及她复杂的心理,还有那个暴力家庭对她的伤害,纤毫毕现地呈现,读者就像目睹作者解剖一个病人的心理。《骄阳似火》里一对“怀着诡计,又很可怜”的姐妹,因为想摆脱落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如何被不同渣男乘人之危,姐妹俩的卑微心理、脆弱的尊严,就像被人钉在了城墙上。其成名作《母亲的岛》写的是被拐卖来的母亲终其一生想从岛上逃走。小说第一句“母亲做出一个决定,‘我要出去住一阵子。’”,让人想起世界名篇《第三河岸》的开头:“有一天,父亲居然张口订购了一艘木船。”两篇小说都以家中长辈要出走开头,但是接下来,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风格。《第三河岸》追求的是神秘、含糊其词,而《母亲的岛》中的逃离是一个具体可感的“坐实”过程,像“机械钟表”一轮扣一轮。
陶丽群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乃至想要表达的思想,基本是清晰可辨的。传统写作的“小说三要素”,在小说中被严格遵守着。且不要小瞧“严格遵守”的意义。就目前一些人的写作,总让人觉得缺少一点什么,部分原因是创作基本功训练不够,或者不屑于遵守前人积累下的创作经验。而小说又是这么一个跟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紧密相连的文体,除了天赋才华,还要具备人生阅历、知识储备、逻辑思维、洞察能力。如果一个作者总在避重就轻,或者眼高手低,凌空蹈虚,那么势必会背离经典之路,越滑越远。之所以要强调这些,是因为我在陶丽群的小说中体会到小说的深度与广度,有时候并非源自题材多么宏大,情节多么复杂,手法多么独特,而在于写得比多数人更认真,更投入,更敬重“工匠精神”。仅以细节描写为例,《杜普特的悲伤》中杜普特去棺材匠家等着运棺木,这时刚好午饭时间,萍水相逢的两个人一起下面条、吃面条的过程,“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氛围充盈着”,悲惨的故事里忽而涌出一股暖流,震撼心灵。比如这篇《白》中,与母亲生疏了的孩子,紧盯住母亲的肚子探究,是想从肚子上有没有留下疤痕来判断母亲是不是生过她(小孩还不知道女人能自然生产)。而《漫山遍野的秋天》中,大量衬托人物内心活动的春耕秋收的农事细节描写,让我看到一个作家如何通过“严格遵守”传统叙事,认真挖掘人物的内心,分析每个情节的演变,双手沾着泥土和血,从普通素材中抠出珍珠般闪亮的一个个细节来。固然,作家分好几种,有的擅于天马行空,有的擅于标新立异,我想强调的是,同样走现实主义写作路线的作家,现在还有多少人能沉下来,像陶丽群这样精心打磨细节,推敲对话(并用引号一句一句分开),描写心理活动,同时还注意到人的五官、神态、着装,乃至身边的风景?
二〇一一年,我第一次读到陶丽群的小说《漫山遍野的秋天》,小说写的是侏儒症女人三彩想怀上孩子,像正常人一样做个母亲。然而上门夫婿黄天发患有不育症。一天黄天发发现三彩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气得卷起铺盖走人,但是最后因为离不开丰产的土地又回转来,并且原谅了三彩。小说主要涉及四个人,均是被人瞧不起的“畸零人”。叙述之从容,细节之缜密,内心活动之丰富,让人惊叹。很显然,陶丽群擅于书写这类小人物内心的图景,悲苦艰难的处境,而且笔端始终涌动着关爱和理解,很少采取批判的姿态。因此这些小人物,谁弱、谁强,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并不容易界定。而且,他们当中除了极少数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灵魂深处的孤独。这孤独主要源自人与人之间几无可能的心灵沟通。比如《白》中的绿妮与朗山,拉丽与老方、大力,以及她那先天患病的孩子,近在咫尺又仿若隔着千山万水;《水果早餐》中的老代、阿兰、老板娘等人,无不活在各自的牢笼中。《柳姨的孤独》中,姐姐、妹妹,还有那个夹在其中的中学教师,三个人相互排异、相互折磨的人生,让人想起萨特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
然而,陶丽群尽管反复书写着人的悲苦,但其小说整体上并不让人感到绝望。这就说到她的小说另一个优点,精神内核的“趋光性”。这里所指的“光”,是指小说具有“呼唤爱、引向善”的趋向。现实生活中,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并存,我们往往对恶的揭露得心应手,对善的书写缺乏信心。陶丽群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她并无意渲染“光”的强大,而是通过书写黯淡来衬托“光”的存在,光的重要性并且让人体会到爱的珍贵。其笔下大多数人尽管有着难言的苦痛,命运坎坷,人生多舛,几乎没有人拥有一个正常的、温暖的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苦命人”心中并没有淤积戾气与仇恨,在历经磨难之后他们往往选择隐忍,依然渴望爱,渴望亲情,渴望善。《寻暖》中被亲生父母卖掉的陆嫂子,终其一生寻找着家的温暖。《冬至之鹅》中,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失去儿子的老人,多年之后领养了一个越南来的孩子,他们相依为命的形象,不禁让我想到在黑暗中坚持生长的植物,尽管得不到阳光直射,但是它们的叶面总是朝着有光的方向倾斜,生长。《夫妇》中的紫玉、桂七、大伯哥,也是如此。在《白》中,最典型的人物是帮拉丽矫正有自闭倾向的孩子上善的杨老太。她由于幼年不幸导致成年后没有结婚也无孩子,但是由于从事特校老师这个特殊职业,让她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阴影,并且力所能及地把爱给予更弱小的人。相比陶丽群之前的小说,《白》的叙述基调变得明朗,好比上善从幽闭的环境正走向人群。总之“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让人觉得熨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