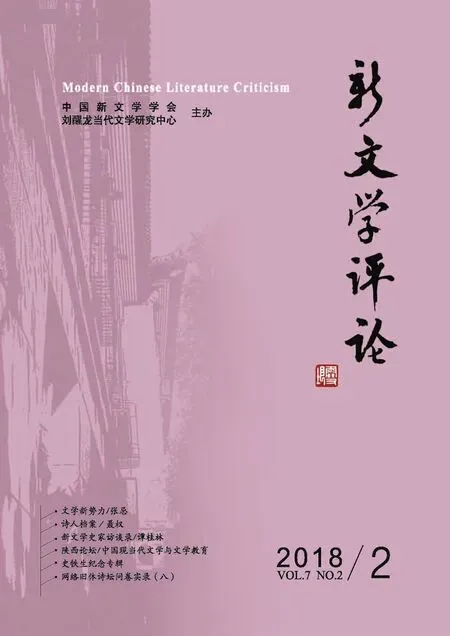从《藏珠记》看乔叶的创作现状
◆ 吕鹏娟
一
河南这块土地,大约自南宋以来,便丧失了曾经的荣耀。几百年来,连续不绝的战乱、天灾,逐渐使它陷入了令人同情的尴尬境地。不过,灾难给这块土地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使其文化艺术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滋养——文化艺术乃至宗教总是和苦难结缘的。我们看到,近现代以来,中原大地的精神产出并没有随着它物质上的萧落而萧落,比如书法、绘画、文学等,都在全国保持着它的尊严。以当代文学而论,河南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实力最雄厚的省份,这块土地上贡献的优秀作家不胜枚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佩甫、刘庆邦
及至新世纪以来,这个名单还可以加上乔叶、邵丽等人的名字。在年轻一代河南作家中,乔叶是佼佼者。在她那些为人所知、也受到文坛肯定的中短篇小说中,她展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天分和潜质。这种天分和潜质,首先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敏感,她总能够以其独到的眼光,发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裂隙、尴尬、创伤;其次是一种赤诚,她在对待生命尤其是自我方面,有一种不多见的坦率、勇气和真诚。也正是这两种素质,让她写出了《拆楼记》、《认罪书》那样的作品。
如果说衡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水平应该根据其最优秀的作品来评断的话,那么截至目前,就乔叶的创作而言,我认为可以拿出来供以评判的作品是:《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最慢的是活着》是无比动人的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充满了浓郁的自传色彩,而主要描写的人物却是奶奶。小说以“我”的眼睛去审视和思考了奶奶的一生,这是一个北方乡村最底层的女性如何经历、面对“苦难”的一生,也是她在生活和命运的重重夹击中,如何以个人生存毅力、耐性、智慧去创造生命“奇迹”的一生。当然,这个“奇迹”只有进入她的生活内部我们才能够发现,否则她就是我们从某个乡村经过时所看到的那些再平凡不过的乡村老人中的一员。“我”(实际上就是作者)便是那个进入她生活内部的人。乔叶借由“我”进入了一个乡村老人(当然也是作家的亲人)的生命史,所探求的则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隐秘。在《最慢的是活着》中,这种隐秘是“小”的,却能以“小”见“大”。
如果说《最慢的是活着》是从“小”处着手的话,《认罪书》却是从“大”处入手。前者处理的是个人史、家族史,后者处理的则是民族史。小说首先写到“文革”,通过一桩放在那个年代来看并不鲜见的“杀人”案,揭露了人性的罪恶;然而,作品最让人惊异的不是这个,而是它所写的现实。这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也就是说,时代虽已变换,但阳光底下无新事,同样的罪恶仍在上演,只是形式不同罢了。小说通过挖掘历史和现实的内在关联(它们乃是一种彼此相生相因的关系),揭露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痼疾。这种痼疾源于人性之恶,源于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中先天缺失的对于人性之恶的钳制。
《最难的是活着》和《认罪书》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个作品: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回味悠长,一个压抑沉重。这其实也显现了一个年轻作家的自我成长:她从生活、自我、家族中走来,逐渐走向民族、历史、文化;从一个比较狭窄的世界,走向一个开阔的天地;从感性,走向理性。这种成长,是让人欣喜的。尤其是《认罪书》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力度,让人印象深刻。有论者称赞它在表达人性反思、忏悔与救赎方面的力度,认为这部作品“触摸到了一个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一个不甚熟悉的领域”。《认罪书》发表于2013年,其实距离乔叶开始写小说,差不多才过去了刚刚10年,而这个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作家探讨问题的视野,和通过“文学”探讨“问题”的能力(主要是“思想”和“艺术”的结合方面),已经达到了让人惊喜的地步。
但《认罪书》之后呢?乔叶还会向我们奉献什么样的作品?说实话,我是抱着很大的好奇和期待的。不过,好奇之余,我也在担心,她是否还能写出更好的作品?这种担心,当然也是因为《认罪书》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还会有更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问世吗?
二
带着这种期待,我读了《藏珠记》(2017)。此时,距离《认罪书》发表,过去了四年。
《藏珠记》写的故事非常虚幻:一个唐代女子(自己取名唐珠),吞下了波斯人给她的一颗珠子,从此长生不老,一直活到了今天。在今天,她遇到了一个名叫金泽的年轻人,这是个“官二代”,但和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官二代”不同,他有自己对于生活的追求。然而,金泽的父亲却突然自杀,而且死前留下一份光盘材料,用以要挟自己的前司机赵耀,让他在自己死后继续给金泽分红。恼羞成怒的赵耀,对曾经的上级恨之入骨,并处心积虑寻找光盘。唐珠因在赵耀家做保姆,无意中卷入了这一场争斗,并发现了金泽的无辜,以及他的单纯,由此和他产生了爱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之后,二人终于战胜了赵耀,并打破了千年明珠所暗含的符咒,长久、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其实,刨除了作品这层“虚幻”外衣,我们发现,小说所讲述的无非是一个很“现实”的故事:“官二代”、官商勾结、利益争夺所以整个读下来,这个小说虽然写了爱情,但其实仍然延续的是乔叶小说写作惯有的沉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阅读的原因,而是故事本身便“沉重”——主人公唐珠、金泽都包裹在金泽父亲和他的前任司机的利益斗争中,他们的爱情同样也是。矛盾冲突是小说的核心性元素,《藏珠记》的这个核心元素便是金泽和赵耀的冲突,而非唐珠和金泽的爱情。小说的悬念在于此,它试图传达的精神意蕴也在于此。
在小说中,赵耀和金泽所代表的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人格。如果说赵耀是世俗的,那么金泽就是超越世俗的;如果说赵耀是功利的,那么金泽就是超越功利的。而为了突出这种对比,小说为两个人安排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赵耀是司机出身,在官场摸爬滚打的他,深谙官场规则和作风,并以此发家致富,跻身当代成功者行列;金泽身为“官二代”,却以此为耻,坚决拒绝父亲为他安排的人生,竭尽所能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在小说中,赵耀从未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过反思,而金泽则是一个“反思者”,他依靠其纯洁的天性,抗拒着这个世俗社会的污染,努力做一个自由而清白的人。这样一个金泽,是作者着力打造的人物,乔叶打造这个人物,自然也在向我们传达着她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和心愿。
乔叶的心愿,除了通过金泽体现外,还通过另外一些人来体现——金泽的爷爷、松爷。这两个人都是曾经的豫菜大师,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手艺精湛,并且无比热爱自己的职业。他们都有一种罕见的职业热情,这种热情让他们在从事自己所做的工作时,都无比专注、痴心不二、精益求精。这种精神用当下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在功利化、世俗化的今天,这种精神已经弥足珍贵。乔叶在小说中不惜用大量篇幅描写松爷的手艺,描写豫菜的经典菜品“黄河鲤鱼”的做法,描写如何选材、烹饪、品尝这都是在表达一种敬仰,也是在表达一种“古风不再”的追念。在“厨师课”一节中,通过松爷之口,小说向我们介绍了豫菜的精髓:
豫菜的关键?就是汤。这是豫菜的命根子。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有汤开张,无汤打烊。在咱们这儿,一个厨师不会吊汤,哪儿还能叫厨师?只能叫伙夫!为啥吊汤这么要紧?这得从海鲜说起。海鲜咱中原没有鲜的,只有干货。想把干货做好,就需要好汤入味,汤就成了豫菜的鲜味之源。豫菜吊汤是用老母鸡和肘子,三洗三滚三撇沫,先熬毛汤,一部分毛汤通过扫汤来得清汤,另一部分毛汤再加进棒骨来熬奶汤。用奶汤的料渣加水再熬,得二汤。清汤可以做开水白菜、清汤竹笋和酸辣乌鱼蛋汤。奶汤用来做奶汤广肚和奶汤蒲菜。二汤用来烧家常菜。最好的清汤叫“浓后淡”,看起来就像是一碗白开水。端上桌的时候,没见过的人都以为是涮勺子的水。但是,尝上一口你就知道了,这就是好清汤。好清汤有个说法,叫“清澈见底,不见油花”,好奶汤也有一个说法,叫“浓如牛奶,滑香挂齿。”
吊汤的味儿是什么味儿?所有的好汤,你喝了以后跟喝老酒一样,醇。你先用舌尖儿品,舌尖是尝味道的。然后汤就到了咽喉部,咽喉部是找感觉的。舌尖让你知道咸甜酸辣苦,但是真是找感觉,就是在咽喉。好茶,好菜,好饭,这些好东西到了咽喉部,都能把喉咙打开,都是能回甘的。
这样不厌其烦的介绍,也正是在表达一种追念和向往。也就是说,《藏珠记》无论从故事内容本身,还是从价值观念表达来看,它的重心都是在传达一种现实忧患。换句话说,它的骨子里仍然是延续了从《最慢的是活着》一直到《认罪书》那种一贯的焦虑和沉重。
然而,乔叶在小说后记中却说,她意不在此。她说,她写这个小说是为了致青春,这是个“满足自己的小说”。一个作家想要改换风格,就像一个人穿一件衣服太久了想换一件穿穿一样,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而且乔叶在后记中还引用了卡尔维诺的话(卡尔维诺关于小说写法的那套“轻”的理论,就像马尔克斯的那个句式一样,几乎已经成了当代作家言必称是的“法典”),卡氏那套“轻”的理论是否也让惯于沉重的乔叶受到了某种“启发”,从而动了写这样一个小说的念头呢?至少在后记中,乔叶是这样说的——“如果说,《认罪书》的取向偏重,这个长篇,我想让它偏轻。”
可是,问题是,一个人的习惯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吗?这里说的“习惯”,不只是说话的语气、方式,而是更包含了人生经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而后面这些,可以说构成了作家的某种精神底色。底色难以更改,就像《藏珠记》这个小说中,作为故事核心情节和线索的,其实不是爱情(这可能是这个作品中唯一能让小说变“轻”的元素),而是“官商争斗”(围绕那张藏匿了秘密的光盘)——正是后者使得小说故事一步步往前推进。爱情只不过是穿插在“官商争斗”中的点缀和装饰而已。将爱情作为某种深度表达的附属、媒介,这是乔叶习惯的方式,就像在《认罪书》中那样。但是这一次,她却试图改变这种习惯。
三
当乔叶有了改变的意愿,作品自然也留下了痕迹。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小说中的爱情:“千年处女和帅哥厨师”的爱情。而且,乔叶明显是想把爱情作为这个小说的重心来加以打造的。所以,她赋予了爱情主角唐珠以传奇的身世,让她从遥远的唐代穿越而来,背负神奇的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符咒但是不管乔叶为这个爱情故事增添多少复古的、传奇的元素,这个爱情故事却始终都不曾获得一种独立性的地位。或者说,它始终都是和那个现实的充满批判和讽喻色彩的故事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当然,纯粹写爱情的小说似乎也并不多见,因为爱情毕竟不是空中楼阁,它联系着道德、风俗、文化,关乎经济基础、社会制度。但是,爱情同时还关乎人性最幽微复杂的领域,它联系着人的情感、理智,以及贪婪、嫉妒、牺牲等意念和情绪,这些同样也为文学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供研究的话题。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而言,受制于我们这个民族长久以来的文化习惯,这一方面却并不为他们所擅长。在西方作家笔下,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可以说都有这一类型的写爱情的典范之作,甚至连并不以写爱情见长的托尔斯泰,他笔下的爱情(如《安娜·卡列尼娜》等)也总能让我们窥见人性深处的那些隐秘的侧面。而在中国作家笔下,这种爱情却比较少见。
中国作家笔下的爱情,大多还是像《认罪书》中那样,更多的是在爱情之外那些社会、伦理、道德等层面展开各种话题,而缺少对于爱情本身的探讨。《藏珠记》更是如此。单就小说中围绕爱情所展开的那些描写来看,它们都很难算得上“关于爱情的探讨”。在作品中,唐珠和金泽很偶然地便相遇了;接着,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周折,他们便相爱了;再接着,他们遇到了一点周折(赵耀的阴谋、金泽姑姑对唐珠的怀疑),但也没有经过太大的困难,这些周折便化解了如果单独把爱情这部分提取出来加以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非常平淡无奇的。可能是为了弥补这种平淡,作者在里面设置了很多关于金泽和唐珠的爱情对话,但是它们大多不过是青年男女的打情骂俏、撒娇发嗔罢了,并看不出有多少能让爱情变得幽微复杂的意味,而至于那些情爱描写,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给人以画蛇添足之感。
总而言之,小说关于爱情的描写,总体给人的感觉是粗疏、刻意。粗疏,指的是小说并没有真正揭示爱情本身的幽微复杂;刻意,则指的是为了使这份爱情具有传奇性而有意设置的那些“虚幻”元素(唐珠身世、处女的符咒)。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唐珠不是这样一个“虚幻”的身份,而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人,小说在展开关于爱情的探讨方面是不是会好一些?小说中唐珠为了强调自己这种“穿越”性身份,必须时不时背一背古诗词、回忆一下往昔年代里的遭际。说实话,这些地方,常常让人为唐珠的记忆力担忧(万一她把诗词背错了怎么办),当然也就为乔叶的“杜撰”感到辛苦。其实,这些真的是必需的吗?在乔叶自己而言,这些显然是必需的。因为如果不这样(而是像我们假设的那样让唐珠成为一个现实中人)的话,她写出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和之前一样的作品。而这一次,乔叶想改变原来的习惯。
但事实上,小说本身其实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就像前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藏珠记》在虚幻和爱情的外衣下,实际仍然是一个极其现实化的作品。而当乔叶非要为这个现实化的作品披上一件虚幻和爱情的外衣时,便使得这个作品给我们一种“两头都不落好”的印象。它既没有得到乔叶所渴望的“轻”,又损失了她惯有的“重”。
乔叶在后记中谈到她以这种方式写这样一个故事时说:“这种选择我知道会有人说幼稚、可笑、肤浅,或者别的什么,我统统能够推想得到,没关系,对于读者,我没有期待。这是我满足自己的小说”从这段话似乎可以看出,她对于这个小说其实并不自信。
我始终觉得,乔叶是一个可以写出大作品的作家。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她的出身、生活积累,以及前文所说的她的“天分和潜质”。然而,这种期待的被激起,乃是因为乔叶在《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气质和创作可能,而它的被满足,我觉得也应该是依循着那样的一种气质和可能。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生长着苦难,也生长着苦难养育的艺术,它们共同的精神底色便是“沉重”。这是现代以来一代一代河南作家所共有的。浪漫、想象力似乎总是和河南作家无缘,这其实并不是河南作家之所“短”,而是他们脚下的土地和历史所赋予他们的所“长”。只是,要发挥这种“所长”,可能需要他们有实打实的生活、实打实的情感、实打实的积累与付出。
我不知道乔叶究竟为什么要写《藏珠记》这样一个作品,是否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完全出于一种创新的愿望。毕竟,在今天的文学环境之下,作家身在体制之内,又不得不面对市场,不得不面临各种考验(以及诱惑)。但不管怎样,文学创作最终是靠作品说话的,而作品又是无法欺骗人的。就乔叶这样的“70后”(乃至“80后”)等年轻作家来讲,他们已然年届不惑,就一般的写作规律而言,这样的年纪正是他们刚刚摆脱原来初始的、比较艰辛的状态,进入新的生命周期的阶段,但这也是一个早期生命经验渐趋耗尽、需要重新寻找写作资源和写作动力的阶段。这是一个无比关键的阶段,也是让很多作家陷入危机无法自拔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承受寂寞,需要沉潜——有沉潜,才会有积蓄和真正的爆发。以上是对于《藏珠记》的批评,却更是对乔叶的期望!
注释
:①李勇:《批判、忏悔与行动——贾平凹〈带灯〉、乔叶〈认罪书〉、陈映真〈山路〉比较》,《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
②乔叶:《藏珠记·后记》,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