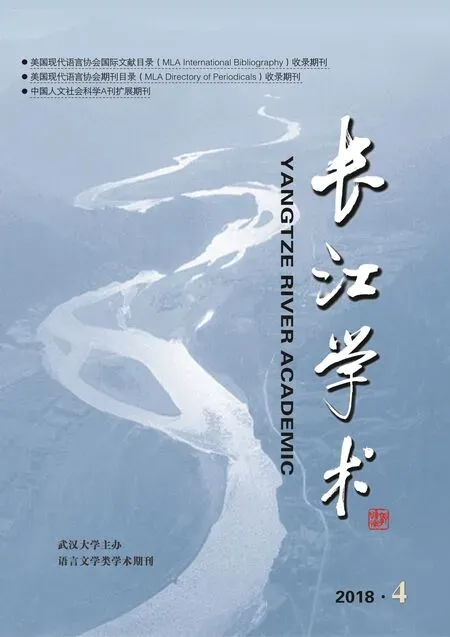论胡适新诗理论中的跨界式叙事
——从“作诗须得如作文”的诗学命题谈起
姜玉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上海 200439)
一、承上启下的“作文如作诗”
相对于古代的抒情传统,确切说是以抒情为主体的传统,胡适论诗明显是剑走偏锋:他搁置了抒情这一因素,其实也就意味着搁置了整个中国诗歌传统的主线,从非主流视角,即“写实”的角度切入新诗理论的构建中,提倡“作诗须得如作文”。也就是说,主张要像作“文”一样来作“诗”。
“文”历来是不同于“诗”的。《说文解字》对“文”的解释是:“文,错画也。象交文。”而对“错画”的阐释是:“交错而画之,乃成文也。”“文”就是要一笔一画地反复“描画”,“描画”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像”。无疑,“文”强调的是写实性。假如把这样一种思想引申到文学创作中,自然在美学上彰显的就是描画、刻画之功能。事实上,胡适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描画的层面上来理解与接受“文”的。正如他以传统的、最为缺少“描画”的写景诗为例说:“就是写景的诗,也须有解放了的诗体,方才可以有写实的描画。”显然,胡适引“文”入“诗”,就是把“文”的“写实的描画”功能引入诗歌中。如果说传统诗歌主要是沿着抒情这个维度发展、构建起来的,新诗的发展与构建则开始转向了从“文”中寻找支撑。
胡适这种要求诗歌“写实的描画”的思维方式,与以往那种习惯从玄虚、抽象的抒情层面来言说诗歌的传统有着本质性差异。或许正是由于挑战了传统诗歌的审美规范和创作条例,所以自从胡适提出这个新诗写作的命题始,就遭受到众多新诗从业者的反对与攻击。如穆木天就指认胡适为“罪人”:“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直到今天,新诗研究者们对胡适的这个“作诗须得如作文”的理论主张依旧充满偏见:“这个理论抛弃了白话诗的诗性,致使新诗先天不足。此后,大量用白话的非诗也大量产生……”“作诗须得如作文”到底是新诗发展中的一块“绊脚石”,还是一种新的美学诉求在“五四”时代的崛起?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返回到肇始该理论的时代语境中。
1916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围绕“文学革命”之想法写了一首长诗,送给同样在美国留学的好友梅光迪。由于此时的胡适正被“古人作古,吾辈正须求新”的激情激荡着,所以为了达到“求新”之目的,在该首诗歌中使用了不少外国字的译音。胡适这一明显为“新”而“新”的举动,引起了他们两人的另一位好友,也在美国读书的任叔永的“耻笑”。他把胡适这首诗中的外国字一一挑选出来,编成了一首诸如“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的游戏诗,回赠给胡适。胡适从该诗中读出了好朋友的嘲讽之意——讽刺他写诗不守规矩,胡乱使用不该使用的文字。以今天的眼光看,胡适这样做,一方面有捣乱成分,另一方面更有出于“实验”的考虑。说其捣乱,是因为胡适有意采用这种“越位”手法对禁锢传统旧诗词发展的清规戒律予以冲击;说其有出于“实验”的考虑,是因为他当时的确有把过去那些不能入诗的文字引入诗歌的想法,即要扩大诗歌使用的词汇量,不但雅文字可以入诗,就是俗文字也可以入诗。事实上,他的这一反叛本身就是对“诗界”发起的进攻。
他的这番苦心非但没有得到好友们的理解,反而引来了一番讪笑。或许胡适觉得有必要再解释一下,或许也是出于争取“同道人”的考虑,他在接到了任叔永的讽刺诗后,又提笔写下了另一首诗:“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啄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儒腐生。”从这首诗中不难窥探出“作诗须得如作文”出笼的前因后果:胡适认为中国旧诗词“啄镂粉饰丧元气”,意思是这些诗看上去貌似诗,其实早已丧失了“元气”,只是凭靠对语言文字的雕琢和粉饰勉强存在而已。正是基于这一估价——旧体诗词已经沦落成了伪诗,胡适才号召伙伴们起来“革命”,不要再作“儒腐生”。
从这样一个去旧更新的框架出发,可以说“作诗须得如作文”并非是胡适随口一说的一句话,相反是建立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即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项基本策略而有意识地提出来的。这并非有意拔高“作诗须得如作文”的作用,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下的一篇文章中曾回顾和交代过这件事。他说:“在这首短诗里,我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方案,从这个方案上,惹出了后来做白话诗的尝试。”话不多,逻辑线索却清晰地呈现出来:“诗国革命”——“要须作诗如作文”——开启了白话诗创作的闸门。在这个逻辑链条中,“诗国革命”是目标,“要须作诗如作文”是实现目标的方案和手段,由这个方案、手段引发出了中国白话诗的创作大潮。而位于这一逻辑链条中心的环节无疑就是“要须作诗如作文”。
这说明“要须作诗如作文”或者“作诗须得如作文”,看似没有太多的含金量,其实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它在中国诗歌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往前,它继承和推进了近代以来的诗歌革新精神,一举捣毁了中国上千年的诗歌传统;往下,它发扬光大并奠定了白话新诗的创作传统。自此以后,中国诗歌便走向了一条像“文”一样自由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在这个看似直白而简单的命题里,其实蕴藏着一系列新的美学诉求,这个诉求里既有破旧的成分,又有立新的意义。在那个缺乏桥梁的年代,是它把旧体诗词与新诗创作架通起来,开辟出了一段新的诗歌历史。
二、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诗学理论的赓续与超越
胡适的朋友们显然并未意识到潜存于该诗学理论中的玄机。其表现是,他们一方面对“我辈不作儒腐生”的反叛精神深表赞同,另一方面又对“诗国革命”的策略——“作诗须得如作文”的倡议怀有强烈的异议。言辞最激烈的当属梅光迪,他直截了当地与胡适展开商榷:“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不可也。……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以其太易易也。”梅光迪并不反对胡适要对“诗界”展开革命,但他坚决反对把“诗国革命”的起点设置在“作诗如作文”的框架上。其理由是,“诗”与“文”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诗歌有诗歌的语言文字,散文有散文的语言文字,这两种文字绝不可以混同。
梅光迪的这一说法看上去也有道理,“诗”就是“诗”,“文”就是“文”,如果模糊了二者间的界限,或者说“诗”完全像了“文”,“诗”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了。无疑,梅光迪是从两种文体的差异性角度来反对“作诗须得如作文”的。梅光迪论诗有与胡适一致的地方,即二人都是把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加以讨论的。他们的分歧之处在于,梅光迪论诗的思路始终没有离开诗——他试图通过诗歌这一文体内部的改良来改革和完善诗歌,强调的是诗歌自身语言形式的革命和转变。胡适则认为,单纯从诗歌语言到诗歌语言是无法完成诗歌文体变革任务的,唯有采用“跨界”策略,也就是把“文”的一些文体优点吸收和采纳到诗歌中来,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诗界革命”的任务设定。
由于两人立论的基点不同,一个拘泥于诗歌自身,一个立志于把诗歌从封闭的体式中解放出来,所以面对梅光迪提出的“文之文字”不可入诗的说法,胡适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致,只淡淡地应付了一句:“我不相信诗与文是完全截然两途的”,“我的主张并不仅仅是‘文之文字’入诗”这么简单。至于“诗”与“文”为何不是“截然两途”,以及“文之文字”可以“入诗”这一行为自身有何更深刻内涵,胡适并无解释,而是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前行:“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梅光迪与胡适商榷的是“诗之文字”就是“诗之文字”,意在强调要维护“诗之文字”的纯洁性;胡适回答的则是“今人之诗”的文字、音韵和修辞都无比讲究,一首首诗歌看上去像是货真价实的诗歌,其实它们只是徒有空壳,揭去华丽的外表,内容都是空虚无比。胡适不但总结出了旧诗词的弊病,还找出了造成这一弊端的原因——由“文”胜“质”,也就是形式大于内容之传统所造成的。显然,梅光迪是主张要捍卫“诗之文字”。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诗歌文体的独立存在性;胡适则认为正是围绕着“诗之文字”所形成的那些清规戒律,才导致了中国旧体诗的虚假繁荣——繁荣了外在的文字,空虚了内在的思想内容。因此说,胡适之所以坚决反对“诗之文字”,或者说他主张让“文之文字”入诗,主要是出于诗歌内容的考虑。
当然,在胡适的“作诗须得如作文”理论构想中,也包含有一定的语言文字问题,如写诗不避“文之文字”本身就是一个语言形式问题,只不过他的语言形式与梅光迪的语言形式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梅光迪通过语言文字的差异性,说明“诗”不能越界到“文”中去;胡适则是要通过对“文之文字”的使用来解决“文”胜“质”的问题。无疑,“作诗须得如作文”的终极目的,是指向诗歌的内容,也就是“质”。对胡适而言,他就是要通过“文之文字”入诗的方式,实现对传统旧诗词内容的改换与替代。
思想内容第一,语言形式第二。辨别清楚这一点,对我们认识胡适的“作诗须得如作文”理论,乃至于整个“五四”时期的新诗理论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新诗理论的出笼看似一个语言形式,即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问题,其实不是,语言形式转变的背后隐藏的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科技的渴望与焦虑。换句话说,新诗理论工作者试图借用一套西方先进的思想价值理念来瓦解已经腐朽了的,妨碍我们前进的旧思想体系。这样一种强烈理念表明“五四”新诗运动首先是一场思想上的解放运动,其次才是一场有关于诗的审美运动。归根结底,这场“诗”的运动主要是围绕人的思想观念的大变革展开的,其他都是为此服务的。
这种奉人的思想观念为上,而不是人的审美观念为本体的文学革命,其实并非“五四”新诗运动的首创,而是对以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等所开创的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近代诗学的一种赓续。当然,如果仅仅止步于赓续,胡适的新诗理论也就没有走出近代诗学的认识水准。我们之所以说胡适的诗学理论具有现代性意义,就在于他在赓续中又予以了改造与推进。为了更好地说明它与近代“诗界革命”的关系,需要先回顾一下以变法图强为目的这一诗学流脉的特质。
正如文学史所揭示的那样,这一流脉肇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和时间节点注定了该诗学理论的特殊性: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一己的悲欢离合已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诗歌参与到民族救亡的社会思潮中来,并使之成为行之有效的宣传武器。这样一来,必将存在着一个诗歌文本如何与危机意识、“救亡”主题相契合的问题。抑或说,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危机意识和“救亡”主题将以何样的形式参与到诗歌文本的构建中来?
这无疑取决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社会危机的认知情形。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但其最直接的作用是,它在一举击毁中国封建主义价值体系的同时,也让一直酣睡于“天朝上国”美梦中的知识分子认清了一个现实:我们这个所谓文明古国无论是在现代科技,还是人文思想方面都已远远地落后于西方诸国。而落后的直接后果就是要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欺侮与掠夺。所以奋起直追,由“弱”变“强”就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为了尽快赶上西方文明的进程,他们制定了内外两套行动方案。对内,高举变革、革新的大旗,号召人们从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努力使自己变成一名“新人”,即通过“变”达到“强”的目的;对外,主张大力引入、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即试图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来改良、夯实我们的思想与精神,通过对他国的学习来达到最终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目的。
以上两大变法方针很快就从思想界传播到了诗歌界,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黄遵宪率先向自明代以来就在形式主义、拟古主义道路上愈行愈远的旧诗坛开火,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的口号。黄遵宪在此为何采用“我手写我口”和“俗语”“登简编”的方式来颠覆传统诗坛?道理很简单,就是鼓励诗人们不要被“传统”束缚住手脚,要勇于发现和探索“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即强调创新的精神。当时思想界的另一重要人物梁启超也是从创新性角度倡导诗歌创作的,他在《夏威夷游记》《饮冰室诗话》中多次呼吁诗人要开辟出“新意境”。黄遵宪、梁启超都呼吁诗人们要在“古人”从未涉猎过的“物”和“境”中开辟出诗歌的新纪元。
显然,“未有之物”也罢,“未辟之境”“新意境”也罢,最终指向的都是诗歌的内容。因为“未有之物”的“物”,“未辟之境”“新意境”中的“境”最终都与题材相关,而“题材”导向的则是内容。这说明黄、梁两位都已经意识到,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之间,前者才是当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旧有的诗歌内容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需要,必须要有新的内容来取而代之。
然而,到底该取用何样的新内容来取代旧内容?有关这一点,此时的他们似乎还尚未考虑清楚。这个问题一直拖宕到几年后为配合戊戌变法而出现的“诗界革命”时,才算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黄遵宪说,“扫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前者主张用“今人”的“所见之理”“所用之器”和“所遭之时势”来取代传统旧诗词中的“陈陈相因之语”;后者主张今日的诗歌要从欧洲的“精神”和“思想”中寻找诗歌的新材料,以此来取代旧体诗中的落后之内容。无疑,两位都是从社会实用、功用性层面来寻找和设定诗歌内容的,即在他们的价值视阈中,诗歌内容之“新”都是与当下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想、时事政治,甚至与20世纪出现于欧洲的新事物、新名词、新科技联系在一起的。
由上可见,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诗学理论所强调的诗歌内容之“新”是有着特定运行轨迹的:“内容”必须要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这种时代性常常通过具体的“时势”——社会时势和政治时势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诗歌的“内容”一定要具有反映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功能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时代性也就是社会、政治性的意思。廓清了这一前提,也就顺理成章地明白了该诗歌流脉一直把其重心搁置在诗歌内容方面的逻辑动因了。
经过以上这番溯源,回过头来再勘查胡适“作诗须得如作文”的诗学理论,不可理解的也就理解了。譬如,在诗歌中并不关心社会意义和政治性的胡适,为何在论述诗歌的时候却一反常态地以诗歌内容为先,而且还格外重视诗歌内容的时代性?只有从承传的角度加以勘测,才能解释其矛盾性,即胡适诗论中的这一特点其实就是对近代诗歌以诗救国之传统的赓续。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诗运动的确与黄遵宪等为代表的近代诗歌有着难解之缘,正如朱自清在1935年对二者间关系的梳理,他说黄遵宪“一方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朱自清从“观念”的角度,把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近代诗歌与“五四”新诗运动衔接到一起,使之成为互为逻辑和互为因果的一个统一体。
朱自清在当时的这一指认还是颇有见地的。胡适所秉持的这种以内容为上的新诗“观念”,就是对黄遵宪等人思想的继承。当然,这种继承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中予以重大变革:或许“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已经渡过了最为危机的关头;也或许胡适本人天生就对艺术自身的问题更有兴致,反正到了他的诗学框架里,隐藏在变法图强派诗歌中的那种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悄悄隐退了身影。这种“隐退”大致可总结成,胡适继承了近代诗歌强调要有新颖而充实内容的传统,但在继承中他又有意识地让诗歌与社会现实,特别是时事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胡适在保持以内容为上的前提下,把近代诗歌从社会时势中提取内容的精神特质摈弃掉了,从而给这个原本偏于社会政治性的诗学理论注入更多的文学审美性。
三、以“文”之长补“诗”之短
当然,胡适的这种摈弃是小心翼翼地摈弃,用“不说”代替“说”的。有关这点从他发表于1918年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不难看出来。在该文中,他以易卜生的戏剧为例,反对诗人、作家以及文学活动家动不动就给社会开“药方”的做法,理由是:“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泻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这番话正代表了胡适对中国诗歌改良的一个基本态度:中国传统旧诗词的内容浮泛、虚夸、僵化,的确是亟需改良,但怎么个改良法,即要用什么样的内容来取代和替换,他则不肯“下药”了,只是借易卜生的话说,“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不能指定”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他并不认可黄遵宪等人所倡导的那种以诗歌来救国的思想。
既然如此,是否表明胡适的“作诗须得如作文”的理论,除了在诗歌内容需要重铸的这一点,即要像“文”一样有着充实而新颖的内容方面,与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近代诗歌达成一致外,其他方面都是分道扬镳的?当然不是。诚如前文所言,朱自清认为近代诗歌主要是在“观念上”,而不是在“方法上”影响了“五四”新诗。前一个无疑是正确的,后一个则有些偏颇。或者说,朱自清由于囿于“五四”新诗的白话,即白话是“五四”新诗最为主导的特征,所以他就从作诗的“方法上”割裂了“五四”新诗与近代诗歌的逻辑关系,以此来与较为保守的近代诗歌划清界限。事实上,“五四”新诗不但在“观念上”与近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在“方法上”也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牵连。具体说,胡适所说的“作诗须得如作文”中的“如作文”的艺术手法,就是取法于以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近代诗歌的。
黄遵宪们的诗歌理论虽然是以变法图强为目的,注重的主要是内容的变革,至于形式的变革在当时还无暇顾及,但是由于他们重视的是诗歌内容的“实”,而且这种“实”还不是一般的“实”,往往是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历史、政治大事件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黄遵宪一生创作了一千多首诗歌,其中绝大多数的诗歌都属于此类,以至于被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之为“诗史”,这就决定了严沧浪所标举的那种以“虚”为上,即“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诠释方式——其实这也正是中国传统诗歌最为正宗的表达方式,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设定的。这一窘况决定了以黄遵宪等为代表的近代诗人们,必须要另辟出一条更适合于展示思想内容的创作手法。这种手法就是“以文为诗”的手法,即为了能在诗歌中更有效地展示出诗人的忧国情怀,使诗歌成为启蒙救国的舆论武器,把“文”的一些语言表达方式引入“诗”中来,从而扩大诗歌内容与思想的表现力,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在“语言方面则表现为以文为诗的特点,挥洒淋漓,汪洋恣肆,以此适应表达壮阔的思想内容和奔放不羁的感情的需要”。“以文为诗”,就是为了满足“壮阔的思想内容和奔放不羁的感情”的需求,而不得不使用的一个策略。
当然,“以文为诗”的手法并非近代诗人们的首创,中国古代诗歌中也有。在唐代时,韩愈就曾提出过“以文为诗”的口号,主张将古文中的一些谋篇布局的技巧以及古文中的句式和文字等引入诗歌中。他的这一主张到了宋代又被欧阳修等人发扬光大,从而对宋代的诗歌创作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以文为诗”在唐代还主要表现为口号的话,在宋代则成为了诗人创作的一条不可忽视的准则。而且这一思想还一直绵延在其后的诗歌创作中,正如赵翼对其的总结:“以文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把“以文为诗”之手法总结成“成一代之大观”,或许有夸大的成分,毕竟中国的诗学一直还是以抒情——不是以描写事件、描摹物状为正宗。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非常适合于近代诗歌的叙事性要求。从技术层面上看,胡适所言的“作诗须得如作文”就是继承了近代诗歌的这种借鉴“文”的一些叙事手法来写诗的传统,正如他说:“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话说得虽然有些笼统,但至少可以说明胡适反对那种以“虚”写“虚”的写法,倡导一种更能叙事、写实的,即能把诗歌内容更好地彰显和诠释出来的艺术手法。
总之,对胡适而言,所谓的“作诗须得如作文”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想把“文”中的叙事、抽象、说理之思维引入“诗”中来,另一方面也想借“文”中的“事”来填充“诗”之内容的空疏,即借“文”之长来补“诗”之短,从而为中国新诗构建起一种新的,也就是像“文”一样有着充实的思想内容的灵魂。
由以上论述可见,“作诗须得如作文”非但不是一个“非诗”主张,相反它是中国诗歌发展到20世纪初期必然出现的一次美学转型:旧体诗的那种以抒情为主导的表达模式,艺术性超凡,但只能让诗歌的思想内容沿着“虚”的方向发展。而且,唯有此,才算得上是好诗。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则是一个崇尚思想观念,尤其是先进的思想观念为上的特殊时代,这就宣告了旧体诗表达模式的出局。既然旧有的表达模式不能满足彰显“内容”的要求,胡适便大胆采用了跨界取用的策略——把更适用于表现“内容”的“文”的一些特长,如描写、叙事等特点汲取到诗歌中来,弥补了诗歌不擅长表达和诠释思想性的问题。以今天的眼光看,胡适把“诗”与“文”融合为一体,也就是使之既有传统诗歌的抒情性,又有“文”的描写、叙事性,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不但让中国诗歌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而且为其发展开辟出了一条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