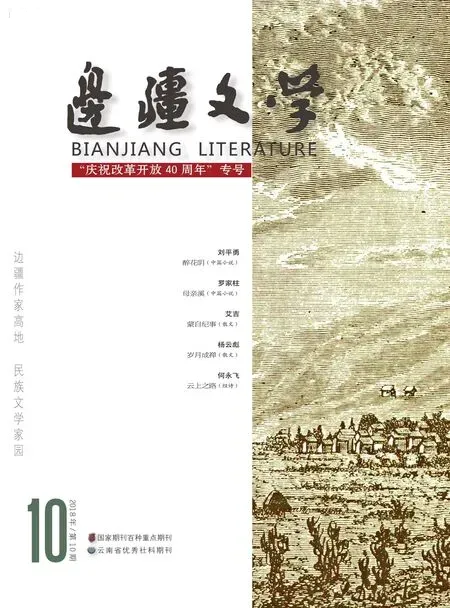砥励奋进40年的《边疆文学》
张永权
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眨眼的瞬间,在我们的生命里,却差不多经历了半个人生。从眼前回望走过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一段历史,在5000年中华民族的厚重史诗中,却是独特而辉煌的一页篇章。我有幸在人生的盛年到耄耋之年,与史同行,走过了这不平凡的40年,成为历史上这个40年的亲历、亲为的经历者,见证了40年的伟大历程: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创刊的第一家文学刊物《边疆文学》的编辑者,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又从我们文学刊物砥砺奋进40年、与史同行的40年中,亲历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40年来创造出的人间奇迹,书写出令子孙后代引以为骄傲和光荣的时代史诗。
下边,我以一名走过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刊物的老编辑,老文学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走进那砥砺奋进40年的《边疆文学》。摘取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文艺百花园中的一花一叶,从某个侧面来呈现一个伟大时代的绚丽风彩。
一
在浓厚的云层中蕴酿了多年的那一声惊雷,终于在1978年的12月18日响起,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这年的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这一消息如一声春雷,震撼了神州山川大地,也惊动了整个世界,仿佛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关注着中国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当时我作为省委农村工作团的一员和我们工作团的团长,诗人,刚复刊不久的《边疆文艺》主编,著名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的词作者李鉴尧,正在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勐遮公社工作。22日早上就从县委办公室得知,让我们明天晚上19:00注意组织社员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那时在城市党政机关虽然有少量的黑白电视,但在边疆还没有任何人看过电视。在边疆农村靠挂在大青树上的那个大喇叭,村寨广播室早中晚都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来传送国内外的信息。开社员大会时,也是先在广播中通知。村头大青树上的大广播,俨然成了一个生产队的指令官。当时广播中的开始曲《东方红》几乎是伴随着澜沧江畔那轮初升旭日响起的。大概在1978年初,广播的开始曲才变成了《歌唱祖国》。
鉴尧说这个广播很重要,你叫广播室依香多通知几次,让大家早点到大青树下听广播。依香是傣族,勐海县中毕业,算是公社的大知识分子(后调州上某中学教书去了),她汉话、傣语都很流畅,她的广播通知很有号召力,夕阳还没落进流沙河,社员们早早就带着竹编小凳来了。吸旱烟的老波涛,绣筒帕的老咪涛,还有穿着紧身背心的农英和一群披着红色袈裟的小和尚,把个大青树围了个水泄不通。晚上19:00正,大喇叭在《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后,一个雄浑的男中音,通过电波和大青树上的那个大喇叭,准时把一个重大的新闻传送到祖国边疆的傣族村寨:
下边请听“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整个嘈杂的人群,随着那春雷般的一声,顿时便安静了下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全都目不转睛的望着大青树上的那个银色的高音大喇叭,不管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汉语的,人们都在听,在望,在想……
我和李鉴尧才听到广播中的第一句话,我们就心有灵犀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仔细地倾听着公报中的每一句话,生怕漏掉了当中的一字一句,越听越觉得新鲜,越听越觉得有希望,过去在工作中多次说过的话,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理论”等,今后都不那样说更不能那样做了。还有许多新的提法,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等,我都是第一次听见。肯定了天安门事件是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特别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更是让我感到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向着我们走来。公报还说到我们的文艺和宣传工作,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要少宣传个人。这个“少宣传个人”我想一定是有所指的,我们的文艺工作将面临着一个崭新的环境。
晚上回到驻地,我拿出差不多用了我两个月工资买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在22︰00的晚间新闻节目中,再次聆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全文。鉴尧和我边听边议论,我开玩笑说,过去的“纲”不抓了,这就让我们这些日夜提心吊胆的改造对象,终于可睡个安稳觉了。鉴尧说今后要围绕一个重点搞经济建设,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创作环境,他预感到文艺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到来了。他若有所思地说,什么是改革,什么叫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会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了。我们的责任也更重了。我们办好《边疆文艺》这份文艺刊物,真是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我从老领导的目光中,感受到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文艺家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他说,我们有全省创刊最早的《边疆文艺》,这不仅是你我做好文艺工作,出作品出人才的平台,也是广大作家大显身手的阵地。云南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众多,好些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很少,文化不发达,还没有自己真正的书面作家诗人,今后我们的担子不轻呀。所以才粉碎“四人帮”不久,省委宣传部领导梁文英就找我们讨论恢复“边疆文艺”这件大事,作为文联要抓好文艺工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我告诉他,我在读中学时就拿父亲给的零用钱订阅了《边疆文艺》,很喜欢上边发表的徐怀中、彭荆风、刘澍德、田间、徐迟、季康、白桦、杨苏、周良沛等老师那些反映边疆生活的小说、诗歌。还有他的散文《芒市风情》,诗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等,都让我十分向往云南。可以说是《边疆文艺》那些反映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文艺作品,把我吸引到云南来的。我1965年10月到云南工作,1966年初就连续两期在上边发表文章。当时稿费取消了,就给我送了一本浩然的《艳阳天》,上盖有“边疆文艺社赠”的蓝色长方型条印,“边疆文艺”四个字是集鲁迅手迹刊名字体,过去多少书都丢了,这本书却保留下来珍藏,成为一个时代的纪念。聊到怎样办好刊物,鉴尧说,特点即个性,办好文艺刊物,就是要办出自己的特点。《边疆文艺》创刊时就强调要突出边疆民族特色,当时受到《人民日报》肯定,赞扬她是一朵绚丽的山茶花。立足云南,面向全国,发现和培养云南各民族的作家、诗人,出作品,出人才,是我们刊物的宗旨。
是啊,如今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朵扎根在南国的山茶花,一定会开得更加灿烂。
当晚我们聊到深夜,最终落脚到刚刚复刊不久的《边疆文艺》上,才各自进入一个美好的梦境。
二
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很有名的题画诗《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篓篙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诗是为当时的一个名叫惠崇的和尚画家的同名画作的即兴题诗。随时光流逝,画作早已不知何踪,而苏轼的诗却留传下来了,特别是其中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成为诗眼佳句,被历代诗人、诗论家推崇。它不仅把鸭一年四季都在水中而最先感知水的冷暖的自然现象抒写得如诗如画,把画中有诗化成了诗中有画的美诗,还从一个实践参与者、探寻者敏感于生活时世的体验,升华出了一种诗的哲理,含有深厚的人生社会内蕴。文艺,可以说就是变革中的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文艺家对社会、时代的敏锐感悟,往往都会作出不同于社会常理常规的超前判断和不平凡的举动。
1978年的初春,李鉴尧正在西双版纳勐海带领我们帮助农民完成春耕春播任务的关键时节,一个电话把他召回昆明,几天后他再次回到勐海,带来了两个让人惊喜的消息,一是于1956年1月创刊,1966年7月停刊达12年之久的《边疆文艺》,经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批准,于1978年4月复刊。二是在“文革”中被砸烂的云南省文联及各协会,立即恢复工作,并于1978年5月召开云南省第三次文代会。
真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啊,在全国,多数省级文艺刊物都还没有复刊,多数省级文联还没恢复工作,全国的文代会也还没召开,但南国春来早,“山茶”朵朵齐开了,云南省文艺界出于对时代发展的敏感,却率先走出了第一步,连省文联、省作协都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却让《边疆文艺》首先复刊,当时这在全国还是罕见的。李鉴尧告诉我:他被任命为复刊后的《边疆文艺》主编。副主编有李钧龙和已调回刊物的杨昭、从部队转业到云南日报社的张昆华也调来任副主编。担任兼职副主编的还有省委宣传部的诗人晓雪,昆明军区创作组的作家彭荆风等,这是一个多么强大、多么亮丽的编辑领导班子啊!省委历来对《边疆文艺》都十分重视,1956年创刊时,就任命延安时代的女诗人黄铁担任主编,省委宣传部长袁勃同志亲自写发刊词。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就研究《边疆文艺》的复刊问题,让云南文艺界预感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即将到来,《边疆文艺》迎着早春的阳光复刊,成为云南艺界改革开放走出的坚实一步,也是云南改革开放初期开放在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报春花”。
《边疆文艺》在1978年4月复刊时,我们还在西双版纳的村寨进行春耕工作。刊物通过邮寄,都按时收到。那时还在揭批查“四人帮”在文艺界的流毒,刊物每期都有一两篇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为在“文革”迫害致死的作家诗人李广田、刘澍德等平反昭雪,还为曾经错误批判过的小说《侗家人》等作品的作者、编辑公开平反。这就为云南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除草浇花,正本清源,复苏重启,平反冤假错案,正确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发展繁荣云南边疆的民族文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在改开放的早春,一个省级文学刊物给人们送来的美好春信。
我在西双版纳的田野,读到这一封又一封的春信中,还有当年以《美丽、神奇、丰富》为题歌颂云南的诗人徐迟,又重新以这个题目,再次歌颂彩云之南这片神奇土地的诗篇,就发表在复刊号的第一期上。
那时除了《人民文学》《诗刊》外,各省级文艺刊物复刊的还不多,随着早春般的时代气息,中老年作家预感到百花齐放的文艺即将到来,他们那被压抑了很久的创作欲火重新燃起,更多的年轻作者,勃发着创作的激情,初生牛犊不畏虎,寻找发表阵地。于是一本刚复刊的《边疆文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编辑部每天收到的稿件用麻袋装,送信件的邮递员的绿色邮包,装不下给我们刊物的稿件,只好装进麻袋用三轮车送来。负责登记稿件的黄克娟、许秀华每天忙到下班时还登记不完各类稿件。当时编辑部的编辑有10多个,每个人差不多一两天都要签收大堆稿子,把编辑桌子上待处理的稿件比喻成稿山也不为过。
那时无论是老作家、还是文学爱好者,他们都爱把新创作的稿件投寄给我们刊物。在大量自由来稿中,也不乏名人新作。在我审阅的自由来稿中,就有名诗人梁上泉,著名作家高缨等人的作品。我还在读中学时就购阅过梁上泉抒写云南的诗集《喧腾的高原》《云南的云》。我上大学时,中国作协为扶持诗歌新生力量,作家出版社于1963年特别为当时很活跃的5个青年诗人李瑛、严阵、张永枚、雁翼、梁上泉各出了一部诗选,梁上泉的《山泉集》就是我当时喜欢的一部诗选集。其中不少写云南的诗就发表在“文革”前的《边疆文艺》上。高缨当时是四川很有影响的作家,他编剧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在全国引起轰动。他们把自己的新作主动投寄给《边疆文艺》,可见这份刊物的影响力之大。
今天,我以一种“怀旧”或纪念的感情,来翻阅改革开放初中期的刊物,云南的一大批老中青作家李乔(彝族)、彭荆风、苏策、晓雪(白族)、张昆华(彝族)、周良沛、李鉴尧、杨苏(白族)、杨昭、饶阶巴桑(藏族)、张长(白族)、公浦、兰芒、黄尧、沈石溪、胡廷武、吴然、汤世杰、夏天敏、原因、黎泉、米思及、李霁宇、杨伊达、戈阿干(纳西族)、石锐(景颇族)、白山(回族)、黄玲(彝族)、彭鸽子、湘女、李光云、毛诗奇、潘灵(布衣族)、于坚、欧之德、杨红昆、李开义、李成生(彝族)、吕克昌、吉成、段平(回族)、周祖平(彝族)、尹坚、高文翔、刘扬、彭国粱、张稼文、汪凯利、段瑞秋、李勃、沈骏康、何晓坤、宋德丽等频频亮相,他们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雨,用自己的时代新篇或处女作,使云南文学的百花园灿烂夺目,一派生机。更有已是文学大师的林斤澜、季羡林、艾芜、贺敬之、冯牧、徐迟等人的作品为刊物增光添彩,还有当时尚无任何名气,而现在已是文坛红人,各类文学大奖荣获者,如贾平凹最初与人合作的散文和他自己的小说,叶延滨的小说,王英琦的散文,李松涛、熊召政、张新泉、徐康、李发模等人的诗歌。这些人的作品当时大都是他们自由投给《边疆文艺》的,今天他们成为著名作家、诗人,荣获茅奖、鲁奖或当鲁奖评委,是改革开放使他们还是业余文学爱好者时就与《边疆文艺》结缘,也可见当时那一代办刊人的文学眼光,从稿山中掏金,把他们的作品掏出来发表,或许也给他们成为著名作家的起步时加过油,雪中送过炭?
三
1979年10月3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上的祝词,如又一声春雷,送来了开放在文艺百花园中那一个又一个让人惊喜的春天故事。
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边疆文艺》编辑部形成一股改革开放的冲击波,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创作,是刊物的时代使命。
于是,小说《谁杀了她》《香客》《一个县委书记的失眠》《阿惠》等,首先冲破了一些题材禁区,要去打破多年形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两篇好看能引起轰动的作品,一时间《边疆文艺》在广大读者中争相传阅,刊物及时开设专栏对《阿惠》《谁杀了她》等进行讨论,读者、作者、编者和文艺评论家一起参加,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据,畅所欲言,真是百家争鸣,扩大了刊物的影响,造成一时洛阳纸贵的局面,发行量飚升。当时为了把新出版的刊物及时送到读者中,我们这些年轻的编辑还在周日把新出版的刊物用三轮车拉到百货大楼去零售,一车刊物几百册,不到半天就全卖完了。然后便各自回家,自行解决吃饭问题,钱款如数上交。由于新闻纸供求紧张,刊物发行到15万册时,只好限量订阅。
刊物为了及时反映改革开放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编辑部实行每人一年三个月深入生活的创作假制度。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用创作假采访过靠勤劳致富,做豆腐成为万元户的“王十万”,报告文学《豆腐状元王十万》发表后,引发诸多小商贩到编辑部来购买那期刊物。更让我难忘的是,编辑部领导还提出,编辑深入生活,不要只到版纳、瑞丽那些风光好的地方去,最好深入到老少边穷的地区,去体验和反映贫困地区的生活。
1986年,省委组织扶贫工作队时,我主动报名,杨苏带队,和杨红昆、屠夑昌、杨庆隆等来到国家级的贫困县剑川生活工作几个月。其中有一个被雪邦山挡住的象图乡,高山峡谷,不通公路,解放以来,都没有任何省上的干部去过,我和杨庆隆在乡长带领下,爬雪山,越深谷,历经艰辛,步行三天才到达。爬上雪邦山时,突遇狂风,乡长拉起我就跑,躲进路边的救命房。他说这里的狂风能把人刮到半空摔死。那里的贫困让人震惊,不少老百姓家连一个完整的铁锅都没有,种地没有锄头,国家的救济粮也没钱买回,把他们全家的物资加起来,也不值一两百元。唯一的一所乡村小学的学生,用三个石头搭个火塘煮野菜生活。改革开放的阳光,还沒照进这个背阴的角落,极度贫困灼痛着我的灵魂,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一个多月,首先想到的是要为贫困山区的老百姓呼吁,让省、州领导知道云南还有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让改革开放的阳光尽快照进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于是奋笔疾书成《在云南,有这样一个贫困山区》的报告散文。领导考虑到作品写落后的地方多,就放在末尾发表。想不到这篇文章真的传到省州县领导的办公桌上,剑川籍喝过延河水的老革命、有云南鲁迅美誉的白族诗人、省人大副主任张子斋读完含泪批示:“凭着党员起码的党性和政治责任感,我仔细地读了这篇文章,心里难过得要掉泪。”他还因此给大理州委写信,要求“切实地、真诚地、具体地帮助贫困县迅速摆脱贫困状态。”剑川县白族业余作者陆家瑞还以《拳拳赤子心愫愫诗人情》为题,在《云南日报》发表了致作者和刊物的公开信,表示真诚的感谢和鼓励。我们刊物从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编发了相关综述文章。省交通厅及时拨专款修通了从县城到象图乡的公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还为此编发了一期简报。剑川老百姓至今还记得这篇文章在当年刮起的一股“旋风”,称“一本刊物,一篇文章”为他们送来了“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热情反映改革开放的成就和讴歌时代新人,一直贯穿在《边疆文学》40年来的办刊历程中,像何真、王洪波的长篇报告文学《热土之惑》,欧之德、黄晓萍的长篇报告文学《滇西大动脉》,都用了整期的篇幅。为歌颂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杨善洲,还特别出了专号。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刊物的天地十分广阔,作家的创作自由前所未有。但如何掌握好这个度,自由有没有限制,往往也会有片面的曲解,妄想鸟在海中飞,鱼在天空游,只能是自掘坟墓。在这方面《边疆文艺》也是有教训的。
在自卫还击作战中,我们刊物的编辑、作家如张昆华等及时深入到战火纷飞的前线,不仅自己创作出了感人的散文、诗歌,还组织发表了李瑛、陆柱国、公刘等著名作家的诗歌、散文、小说,受到前线官兵的欢迎。但对某些稿件的处理由于没把作品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对创作自由、文责自负理解片面,就出了问题。当时一位老作家写了一首《将军与士兵》的诗,诗歌编辑看后,没有认真把关就同意签发。我作为诗歌组的负责人,仔细审阅了诗稿,诗中将军华美的勋章的花纹“那是士兵身上的斑斑血痕”,纪功碑上颂文“那是勇敢的士兵用白骨写成”……一将功臣万骨枯,就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我想否定,但又在“解放思想”的大势下怕同仁说我保守,只在稿笺上写下了这首诗如发表,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意见。便交领导去审阅。最后一路绿灯,在1980年的12期的《边疆文艺》发表。那时正是自卫还击作战的关键时期,广大士兵为保卫祖国边疆在前线流血牺牲,发表这样的诗,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受到广大官兵和读者的严历批判,《解放军报》《云南日报》和本刊,都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成为《边疆文艺》几十年历史上的一个深刻教训。
四
改革开放40年,对于我们这份文学刊物,既受到了阳光、雨露的沐浴滋润,也经历过曲折坎坷,但几代办刊人,无论是在春光明媚的坦途,还是在风雨中徘徊,都不改初心,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40年砥砺奋进,才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份真正的“边疆作家高地 民族文学家园”的文学刊物。
作为亲历者,我们曾经欢乐过,骄傲过,彷徨过,思考过,但始终都是在行动,在奋斗,为了文学的尊严,为了出作品,出人才,为了云南这份有着光荣历史文学刊物的生存发展,几代办刊人砥砺奋进,无怨无悔。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春光中辉煌过的《边疆文艺》,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在商品大潮袭来时,显得很不适应。读者不再像复刊时那样对文学刊物有兴趣了,读文学作品的人少了,刊物发行量急剧下降,办刊经费紧缺,刊物面临断炊的危机。
怎么办?改革开放时代就从改革开放找出路。
当时新上任的主编冯永祺同志,以开放的眼光,想把刊物做大做强,认为《边疆文艺》的刊名不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的形势,决定改刊名为《大西南文学》,造成一种大势影响,还派出张长、王洪波等到重庆、成都、贵州组稿,开辟了“大西南作家谈大西南文学”栏目,并于1985年1月正式改刊名《大西南文学》,在改刊致读者中表示“我们将立足于改革,不断创新,努力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发表了丁玲、冯牧谈大西南文学的寄语,推出了名家周克芹、李宽定的小说,邵燕祥、流沙河等人的诗,的确有些新气象。但改刊一两年后,虽作了不少努力,刊物的影响力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不少来稿的信封写的还是边疆文艺收,发行量仍在下降。
后来永祺同志调新闻出版局后,李钧龙同志主持刊物工作,面对纯文学刊物日益困难的形势,他和我商量,文学刊物现在面临的危机,是和整个文化发展遇到的困难一样,改革不能离开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改革不一定等于改刊名。就是改刊名,也要有一个恰当的时机,如《贵州文艺》改《山花》,就是在刊物刚复刊时,时机好,《山花》的影响力也顺势而上。《边疆文艺》从1956年1月创刊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是省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省级文艺刊物,实际上已形成了云南文艺刊物的一个品牌,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品牌来对刊物进行改革创新。他和我为此还专门分别拜访了苏策、李乔、彭荆风、晓雪、杨苏、李鉴尧等,广泛征求意见,因为刊物只发文学作品,不发其他文艺作品,决定把“艺”字改为“学”字,基本还是原刊名。于是从1990年8期开始,《大西南文学》改名《边疆文学》,至今已有28年的历史了。
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边疆文学》经历了《边疆文艺》《大西南文学》《边疆文学》三个阶段。这三个时期,刊物始终和改革开放同行,又始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坚守着纯文学刊物的神圣品位。刊物在40年砥砺奋进中的每一个足迹、都见证着李鉴尧、冯永祺、李钧龙、杨昭、张昆华、张永权、陈见尧、何真、范稳、欧之德、潘灵、杨浩、晏国珖、马艳琳、张长、杨伯铸、杨知秋、刘永年、王洪波、李治中、李玉昌、徐维良、邬德辉、王朝晖、雷杰龙、柏桦、屈宁、屠夑昌、许秀华、哈丁、黄克娟、李锐、祝立根、龙宗武、何睿等办刊人付出的心血和智慧。这些在改革开放时代坚守着文学刊物宗旨的办刊人,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不少人也离开了工作岗位,但继承者还在坚守,还在奋进,这里特别记下他们的名字,在纪念《边疆文学》这个不平凡的40年时,也记住他们作出的奉献。
这里有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要给刊物“断奶”的风声鹤起,《边疆文学》还要不要办?还要不要培养各民族的文学新人?不少人给省文联党组施压改刊,党组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分管刊物的一位副主席命我立即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决定改刊,拟用《边疆文学》的刊号去办一份“赚钱”的“大文化”刊物。说《边疆文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不应有培养民族作者的任务了。我遵从党组决定,先后三次召开了座谈会,同时也明确表示,改革开放决不是砍掉一个省文联唯一的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如果那样还建设什么民族文化大省?如要办吃喝玩乐的“大文化”刊物,我就辞去主编,还以各种机会向上反映。想不到2001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省委书记令狐安和他的秘书,分别骑着一辆半新半旧的单车,来到翠湖畔的省文联。对令狐书记这种轻车简从的作风早有所闻,这天亲眼见了,很是亲切。前不久他还给我写过一封关于诗歌问题的信,我约请他把古风诗整理出来给我们集中发表,他欣然应允,我们先后两次发表他的古风诗40首,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从不转载旧体诗词的《诗选刊》给予全部转载。特别是《访贫有感》一首写的“草顶泥墙旧板房,面青肌瘦破衣裳,春城一席红楼宴,深山贫家十年粮”在我刊首发后,处处转载,家喻户晓,老幼皆诵。这样好的作品,我们给他评了“边疆文学奖”,也是情理之中。但他却叫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给我们,不要给他评奖,把奖评给优秀的民族作者。他还专门给云锡公司矿工诗人邵春生写信,写读到他的矿工诗忆起“文革”中当矿工的生活经历和感受,让人感到书记的亲切和温暖。他这次来省文联干什么?我心中暗忖道,充满了期待。
不几天,省文联分管刊物的党组成员在一个会上传达了令狐书记的指示,说令狐书记专门为《边疆文学》改刊之事,向党组说了他的两点意见,一是《边疆文学》还是要办成文学刊物;二是《边疆之学》还是要培养民族作者。保下了云南省文联这个唯一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一份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最早创刊的《边疆文学》,与改革开放同行,就这样走到了今天。
五
那是2009年的春天,我作为《边疆文学》的退休老人,走进翠湖畔《边疆文学》编辑部,拿起一本新出版的刊物,翻阅着,抚摸着,既亲切,又陌生。望着封面上“国家期刊百种重点期刊”“云南省优秀社科期刊”的标识,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精神高地人文边疆”是他们追求的文学境界。内文已由过去的标准16开本80页改为112页的大16开本,成了一份中型文学刊物。显得凝重沉稳。这不就是我过去向往的《边疆文学》吗?当时正在阅稿的马艳琳见我久久凝视着刊物,便问道:“有变化吗?”“有,有,有。”我连说了三个有,表示肯定。还说过去我一直想把《边疆文学》办成中型文学刊物,因没有解决经费问题,退休时留下了一个遗憾。今天,你们把我的愿望实现了。我想,在改革开放中砥砺前行,《边疆文学》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文学高地。
刊物的封二、封三为广吿,封底是让人眼睛一亮的“边疆文学·昊龙年度文学大奖”的广告词。这无疑是刊物为出作品、出人才,办好刊物,和企业联手的重要举措,是充分利用《边疆文学》这一品牌,开放办刊物的改革行动。
刊物品牌,为刊物和企业联合,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动力。《边疆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就先后和多家企业、有关单位举办过许多文学活动,如和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省民委、省公路局、个旧云锡公司、普洱水泥厂、一平浪煤矿等举办的各种征文活动、民族作者笔会,还有富源交运公司年赞助10万元的办刊行动,在省委秘书长、诗人张宝三支持下,与多家企业联合设立“边疆文学奖”等等,都会记录在《边疆文学》的历史上。但就力度和影响力而言,“边疆文学·昊龙文学大奖”开了新篇,直到设立“边疆文学·金圣担保文学奖”的10万大奖,又进一步体现了《边疆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不断提升的文学刊物含金量和品牌效应,大大增强了刊物的影响力。就评委队伍来看,那可都是全国的名家、大师,获奖者既有云南的文学新人,如藏族年轻女作家央金拉姆、彝族作家包倬,年轻诗人唐果、王单单等,也有茅盾文学奖荣获者张炜,鲁迅文学奖荣获者彭荆风、于坚、海男、雷平阳等。文学刊物通过和企业联合办刊物,设立大奖,还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特别是近几年出版的“学习杨善洲专号”“昭通抗震救灾专号”“青年诗人专号”“少数民族作者专号”“军旅文学专号”“走进独龙江专号”“农民作者专号”等,社会效益好,也有不少好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2014年4月,我参加过一次边疆文学·金圣担保大奖的颁奖典礼。坐在我旁边的新时代舍己救人的英雄徐洪刚,他还是文学的爱好者和书法家,过去我们刊物发过他的诗,说到这次金圣担保大奖时,他赞扬道:“金圣担保”这样的企业,很有文化眼光,和你们举办这样的文学大奖,是可以写进文学史的,这是拿多少钱做广告,都买不到的社会效益。他无不感慨地说,这也是潘灵为《边疆文学》的发展,做的一件好事。
这次10万元的大奖授予“鲁甸8.03抗震救灾作品特大号”的全体作者和编辑,而获奖者又一致作出决定,把10万元奖金捐献给鲁甸的重灾区,从而把这个颁奖典礼推向了高潮。
六
《边疆文学》在改革中有“变化”,在开放中有发展。但从创刊到今天,62年的风雨历程,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时代的40年砥砺奋进,不变的却是呈现在今天刊物封面上的“边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学家园”的办刊宗旨。出作品,出人才,出的是高水平的作品,出的是从高原迈向高峰的作品,出的是各民族的作家诗人,出的是云南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要有自己优秀的作家、诗人。
我的案头和书房,堆放着几十年《边疆文学》的合订本,这是潘灵他们为我完成云南文学艺术志编撰任务,花费很大精力清理,用车拉来的。远的不说,翻开这40年的刊物看,当今活跃在文坛上的很多云南作家、诗人,特别是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都是以《边疆文学》为平台走进文坛的。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都发表在《边疆文学》上。像黄尧、朱运宽荣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生命近似值》就发表在改革开放初期复刊不久的《边疆文艺》上。老作家彭荆风的《香客》《阴阳两隔》,丹增的《“半半哲学”之大智慧》,张昆华的《炊烟》,杨苏的《带血的腊梅》,晓雪的《迎接新世纪》,李鉴尧的《故乡》,周良沛的《聂耳,你就是一支歌》,李钧龙的《赶马人的故事新编》,和国才(纳西族)的《兰魂》、黄晓萍的《剑川女人》,夏天敏的《断头桥》、存文学(哈尼族)的《火之谷》,艾扎(哈尼族)的《红河水从这里流过》,吕翼(彝族)的《雨水里的行程》,周祖平(彝族)的《红高原恋歌》,马明康(回族)的《沙甸女老板》,于坚的《诸神之河》选章,傅泽刚的《红殇》,张桂柏的《进村入户》,罗汉的《两地落血》,杨佳富(彝族)的《小妹》,鲁若迪基(普米族)的长诗《独龙江》节选,樊忠慰的《精神病日记》,哥布的《词语的村庄》,聂勒(佤族)的《情凝佤山》,朗确(哈尼族)的《女儿山》,扎戈(苦聪人)的《绿月亮》,柏叶(彝族)的《清晨,有一只鸟儿在歌唱》,何松的《云南的河》等,还选载了范稳的长篇小说《水乳大地》,这些都是发表在《边疆文学》上的力作,是云南各民族作家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留在我刊的足迹。
让我欣喜的是,从《边疆文学》的“世纪力作”“边疆开篇”“民族花环”“民族书写”等栏目和一年一度的《边疆文学》笔会、改稿班以及各种文学专号,走出了一大批云南各民族的作家、诗人,特别是使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有了自己真正的作家、诗人。像在我刊发表小说《女岩神祭》等作品的怒族作家彭兆清,成为怒族第一个用汉文创作小说、散文的作家,是怒族第一个出版小说集、散文集的作家,是怒族中第一个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作家,是怒族中的第一个中国作协会员。他在我刊发表的小说《女岩神祭》是这个民族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小说卷》的唯一作品。在我刊发表叙事诗《山妹子》的米切若张,因这首诗荣获全国贫困地区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二等奖,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奖杯。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在我刊发表的《金沙讧》(外三首)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后,受到巨大鼓舞,诗歌创作从高原向高峰迈进,创作出版了大量受到好评的作品,成为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委员。彝族作家周祖平在边之学创刊50周年时特别撰文《诗歌发表之后》,写他还是马关边陲的一名山寨业余作者时,苦恼于作品不能发表在省级、国家级的文学报刊上,当时《大西南文学》到文山的编辑就面对面辅导他修改作品,还带回了他的修改稿,很快就在1990年2期的《大西南文学》发表了他的《草果的梦》《拥有八角的山村》两首诗,他仔细端详着刊物,“翻来覆去阅读,像拣到了一个金娃娃,更是激动了好几天,疯狂了好几天”,受到巨大鼓舞,说“激活了我的创作热情,增强了我创作和投稿的信心”,以后不少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民族文学》《文艺报》《文学报》《云南日报》上,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出席了全国文代会,现在是文山州文联主席,省作协常务理事。他说:“注定了,我挚爱边疆文学到永远。”更有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哈尼族女作家黄雁的《胯门》、纳西族年轻女作家和晓梅的《深深古井巷》《女人是蜜》,佤族女作家袁智中的《落地的谷种开花的荞》,藏族女作家央金拉姆的《独克宗13号》、海男的《红河流域漫记》、彝族女作家段海珍的《红妖》、徳昂族女诗人艾傈木诺的《艾傈木诺的诗》、佤族女诗人伊蒙红木的《伊蒙红木的诗》、独龙族女作家罗云芬的小说《在路上》、黄豆米的报告文学《伟哉,滇缅公路》等等,都曾形成一波又一波各民族女作家作品冲击波,或荣获全国骏马奖,或荣获边疆文学奖,或被选刊转载等。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是云南第一个荣获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这之前他在《边疆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随水而去》由刊物主编亲自写评论推荐《作品与争鸣》作为优秀小说头条发表,他发表在我刊的中篇小说《牌坊村》推荐到《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引起好评,他获过的4届“边疆文学奖”成为他荣获鲁奖的序曲。还有从本刊发表中篇小说《鹤舞高原》特招入伍的刘广雄,成为影响广泛的军旅作家。又如刘建华发表在我刊的中篇小说《艰涩的口香糖》不仅被《小说选刊》及时转载,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受到好评。
这里有两个小故事,来自我表扬我们这一代办刊人为推出优秀的文学人才,发表好作品的良苦用心。
于坚已是当今诗坛的名家,当年他在一家工厂当锻工,铁锤锻造工业用具,心灵却活跃着缪斯女神的美好形象。上世纪70年代末他考进云南大学中文系时,已有一本厚厚的手写诗集,同学们看后惊叹其诗才,据说他也投稿却很难发表。同学们便把他的那些诗抄下来传阅,也就有了个于坚的手抄本不径而走,有一天他的手抄本,被一个在“文革”后期招到省文化局创作班的知青学员廖婉霞拿到我们编辑部,我翻了几页,禁不住赞叹,真有好诗呀。廖婉霞说就是难以发表。我当即叫她抄下三首,送给李鉴尧审阅,他看后批示立即发表。于坚今天已是闻名国内外的大诗人了,但他却一直记着这件事,经常在诗人中说起。普米族是被顾彼德称为没有希望的民族。上世纪90年代初,编辑部分管诗歌的负责人,在如山的手写稿堆中,翻阅那些自由来稿。当他翻到一份诗稿,映入眼帘的署名鲁若迪基,引起他特别的注意,一看是一位普米族业余作者,便立即阅读下去,他是这样写母爱的:“恬静的山寨/母亲开始呼唤/晚归的孩子//那声音/在我眼里/渐渐长高/最终支撑起/那一黑色天幕”。他从这首诗中,看到了一个普米族诗人的即将出现,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他破例未经过三审就直接发表其中的两首诗。以后鲁若投给刊物的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他的那组《金沙江》诗由编辑部直接推荐给中国作协骏马奖评奖办公室并获奖。他发表在“世纪力作”栏目的组诗《云南的天空》被《诗刊》的刊中刊“诗选刊”转载,说鲁若是从《边疆文学》走进诗坛的,我想也是事实。1985年当潘灵还是一名学生时,他的处女作《七月的山村》就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省级文学刊物《大西南文学》上,我想他所受到的鼓舞也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当他已是发表自己处女作刊物的总编辑,又是省作协的副主席,从写小诗到创作长篇小说,荣获全国“骏马奖”,他从《边疆文学》起步,是真正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一名作家,与《边疆文学》共命运的办刊人,他的故事一定很多,但已不是这篇文章可承载的了。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边疆文学》40年砥砺奋进,改革开放中前行,仍未有穷期。作为一个刊物的老编辑,和她共过命运,和她一路同行,那种生死与共,欢乐荣辱,铭刻在心。今天看到她仍坚守着“边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学家园”的办刊理念,看到新一代办刊人的时代贡献,我充满了感激,也感到欣慰。到下个40年后的《边疆文学》就该100余岁了,我虽然无缘看到100年后的《边疆文学》,但我坚信,有一代代办刊人的坚守和砥砺奋进,《边疆文学》决不会消失,一定会越办越好,一定会更加发展繁荣。这也是《边疆文学》一个老编辑的殷切希望和衷心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