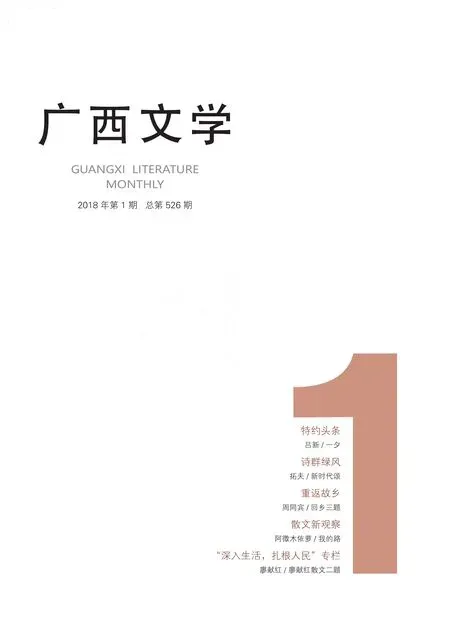我的路(外二章)
阿微木依萝 /著
我的路
我刚到这闹市中来,在沥青路上很多车子蜜蜂般飞过去,留在我耳边的声音“哧溜哧溜”,谁知道具体是什么个响法。
我第一次来城市。
我的乡下已经很远了。
妈妈第一次送我到镇里赶车,别过脸哭。可怜的年轻妇人,她三十五岁了,或者三十六岁,从未真正到闹市中去过。她对远方着迷,也仅仅停留在着迷上。她的脚又踏进那片庄稼地,那些草咬住脚踝。
我希望有一位朋友出现在我面前,最好她有在闹市待过的经历,那我会很感激。她将指引我在十字路口怎样行走,这样就不会对那几颗大灯摸不着头脑。
“我们乡下可不这样。”我会跟她这样说。
“这是明灯。”她会这样回答。
“也许是指路灯。”说完这句话,我就走进车流。
她站在原地。扛着她那双茫然的眼。
就是这样,过了路口我就要自己走,她站在那儿就好。我们永远不会选择走同一条道路,我并不需要一个时时跟在身边的朋友,也不想到人群中相互拥挤。事实上我连一个朋友也并不真正需要。如果我打算去闹市,心中早就打定了要独自一人。我只需要一种声音。她作为一种声音在我这里进行对话就行。
我这样说您能听懂吗?无所谓的。我的想法不会就此停止。
妈妈说:你要假设自己是有同伴的。
她有她的道理。可这句话或许并不适合我。她生了我,也就一同生了与她不一样的性情的我。
突然,有一个路人在喊叫,当我的脚踏入车流,车子被我逼停的那一瞬间,他脱口而出:哪里来的土包子呀!
他是拍着胸口说的,似乎我踩的不是脚下的沥青路,而是踩在他的心尖上。他瞪着眼。
这是我第一次在闹市中走路。
这种路怎么会错呢。妈妈说,城里的路都是四通八达。书上说,条条大路通北京。
可是一双手就这么死死地拽住我。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家伙。抱歉,我实在不能喊他老大爷。这么别扭的脸我是第一次见。妈妈说,城里有很多活路,城里人个个都很亲切。现在我知道了,她的话全是靠着想象的经验。这个人的脸不和善。
我不能指望有谁来解救我。凡是类似的危机,面对它们的都是我一个人。
“你是怎么回事!”抓住我的人这样责备我。
“走路啊!”我也大声吼。
“你会不会走路!”
“会!”
妈妈说,在外面混,不要输了底气。
“这是你的路吗?”
我说是。咋就不是了?
这位老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就像被鱼刺卡住了,终于要吐一口大气,暴跳着双脚说,你是傻子吗!我在救你知不知道!
我走我的路,他急什么?
他差不多是拎小鸡一样把我拎到车流外面,那条很窄的,一排树占了差不多一半位置、人们挤着挤着走的那条小路上来。
我就不爱在人群中走路。太挤。
可是他偏要将我提到这样的道路上来。
他还冲我发火呢!
还准备打我吧?扬起手。好在众目睽睽,他只是扬起手比画。他说,这儿是你可以走的路,那儿是你不可以走的路,那儿的路任何人都不可以走。
我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任何人不走我就不能走吗?
他说是。
他用手里那根小黄旗子赶着我,在我的脚偏那么一小步的时候,将我赶到画了白线的路里面。这里面有人骑着自行车,拼命地摁铃铛,我又随时被他们的车子赶得左右不是。于是我在这里面走路只好歪来扭去,像个没有断奶的孩子,重新学习怎样控制双脚,怎样保持身体的平衡。
我感觉那位大爷一直在后面监视。很多年了,他的眼睛始终盯在背后,就像在我的身后长了个眼样的瘤子。
我也感觉那位路人一直在耳边叫唤,仿佛我破坏了不该破坏的,每一步路都可能踩在谁的心尖上。
“你要坚持住。”我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我先前假想朋友的。现在我希望它出自一位故友,落实在一个实体身上,即便这位故友带给我的仅仅是关于她的传说,很多年前我们已经失散,她比我早一步去了闹市,并且一去不返。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已经不在世间:在某条街的角落,一个破败的出租房里,她病死了。
也好,既是病魔缠身,她抽离肉体便是最好的解脱。这样一来她的声音就不受任何阻碍。
我相信她依然有能力将我对她的情谊进行重建,在我心中重建之后,她很容易就能将这句“你要坚持住”的话传达给我。
我早就知道有些故人不需要重逢。她的存在从未消失。
如今我要留意的是,不能在走向我自己的出租屋的路上再出差错。不能再像她那样不幸。我要坚持住,每走一步,即使崴脚这样的意外都不可发生。于是,很多个时日,我便假设这个朋友就在身边,某个时刻只要我喊一声她就来了,我们在深夜抱头痛哭。
那些路太难走了。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乡下可不这样。
然后我进入回忆,而她会自行离开。
接下来我将很长时间不喝一滴酒,不掉一滴眼泪,不跟任何新朋友说一句话。完全履行母亲的嘱托:多见世面,多锻炼。
我将独自学习在闹市生存。
事实上我干得不错。靠着某种力量我在闹市的每一步还算走得稳妥。我贴着车流的边缘走,偶尔才从画了白色格子的区域穿到路对面。这儿的路每一条都有名头,每条路都有标注,车行道,人行道,自行车道。
似乎是,自从那个老人的手将我提起来扔在人行道上,我便一直无法摆脱。这是我感到奇怪也感到害怕和恐惧的。我意识到,谁第一次出远门被拎起来扔到那条路上,谁一生都在那条路上。
所以才有人想到这个解闷的方法吗?在路的两边植上树木。假设它们的前方不远就是一大片草原。
我甚至看到了黄桷树,到了季节,它就不管不顾地开花。很多黄桷兰掉在地上,月亮出来的晚上,地上的香气便从脚踝升起。
人们是踏着黄桷兰过去的,从不看脚下,也从不回头。他们只在晚上的一小会儿——这时候月亮还没有完全升到中空——跑到属于他们的路上,捡起一朵黄桷兰凑到鼻子跟前,感叹一句“好香啊”然后丢在地上,然后慢慢走回家中。他们从未将黄桷兰串起来挂在脖子上,路边也看不见有人捡了这样的花卖,或者送给小孩。
人们种了树但失去尽情欣赏它的能力。
我时常回到乡下。乡下已经通了公路。没有划分,所有动物走在一条路上:牛、羊、猪、狗、猫、鸡、老鼠,甚至小的松鼠和大的兽类。我只是打个比方,假如有大的兽类,这条路也不会排斥,不过它最好只在夜间出没。至于我们,车子来的时候让开,没有车子的时候就走在马路中间,很宽的路,可以用内八字走,也可以用外八字走。
妈妈说,你要假设自己一直没有离开老家。
我相信这是她的经验。她是个远嫁的人。她的一生都在靠“假设”而活。她希望我在外面锻炼和长见识,更希望我在一条独路上走完之后发觉更多路的重要性。
不错,我得按照她的经验来。事实上我从未改变,依然是一张土包子脸、土包子打扮、两脚稀泥和一口老掉牙的方言。我在岭南住了很久没有学会一句岭南话,在江浙生活很久没有学会一句江浙话,在所有的闹市小心翼翼走他们规划好的属于我的路,却一直没有走习惯。我只有回到这儿才感到踏实。当我看到村边那个很老很老的人时,看见他握着那根滑溜溜的拐杖坐在一条小沟边,凭着记忆——我敢肯定他的眼睛坏掉了——用手抓地上的草,当他抬起头问我,你是某某某吗,你放学啦?我就立即辨出他的声音想起他中年时期的样貌,能顷刻记起他的姓名和对他的尊称。我对这儿的一切还保持着熟悉,并很容易跟他们对话。
甚至,那个晴天的下午,凭着双脚记忆,我爬上两百米悬崖,其间的经验会告诫我不可回头,我便不回头。在悬崖的高处,我再掉头看看那原本无路的悬崖,寻找新踩出来的路。到了高处,我用狂欢的情绪跟妈妈说,这条路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我上来的速度和从前一样快。
只有回到这儿我才能将处于闹市之中不得不收于鞋底的路释放,让它们该去悬崖的去悬崖,该去深沟的去深沟,该在树上的回到树上。我的路,在经历了闹市之后,得回到它的原乡。
“不错,你走得很稳。”我已经猜到妈妈在悬崖下面要说的话。即使我不能真正听清楚,却知道她很高兴自己的孩子能保持对乡下众多道路的熟悉。
这好比是一盏马灯,它即使被尘灰蒙蔽了,依然能擦亮,能生出自由的光亮。
我的牛
来说说我的第一头牛吧(第二头等下再说)。温顺,老实巴交,走路缓慢,吃草也是慢吞吞的。它干活也不毛躁,我母亲时常架着犁头耕地,我则牵着牛鼻子走。它从不因为我是个孩子而跟我耍脾气,牛鼻子里穿来的那根绳子从未在我手中脱离。
虽然它是牛,我却觉得它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朋友。
六岁那年,我跟着姑姑学会了怎么放牧。从羊群到单个的庞大的牛,我知道怎样把握它们的习性并且针对性地去放牧。羊群喜欢散放,到了草原上就分散出去了,有特别不听话的羊甚至会脱离队伍,爬到连它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上去的悬崖顶端,在那儿蠢叫蠢叫,下不来了,它在喊人上去抱它下来。我得时刻在周围注意它们的走向。
牛相对来说要好放。牵到水草丰茂的地方,假如放牧的又是像我这么小的孩子,找棵树将它拴起来,吃完脚周围的草再换一个地方。吃饱牵回家即可。
这个办法是懒牧人想出来的,也可能出自一位腿脚不便的老者。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小牧人。
小牧人放牛处于劣势,对牛这样大个的食草动物,在身高和胆量上,是不敢像拍着羊屁股那样拍着牛屁股吼:走!走!它如果跑到悬崖边或者陡峭的高坡,孩子无法将它赶下来。
好在我的第一头牛从未给我惹麻烦。所以我放它从不用绳子。
我们相处得不错,白天牵它去“高松树”草深水肥的地段,傍晚就骑在牛背上回来。
可惜后来它死了。它被借去耕地的人家不小心用敌敌畏药身上的牛蚊子时,药水穿透皮肤,中毒了。一开始他们争论,有人说药水穿透皮肤不致死,有人说会死,并且等到药性完全发作死掉的肉就不能吃了,那就浪费了。人们害怕它被浪费。
我赶去看它的时候,是个天擦黑的时辰,它还没有死。还站在那儿。周围坐着一群人,他们之中没有会杀牛的人,只有见过别人怎样杀牛的人,他们在研究和推举到底由谁去放翻它。斧头放在一边,是一把砍柴的斧头,略微有些生锈。我不知道它在那儿意味着什么。直到人们推举的杀牛的人拿起这把斧头,在牛面前站住脚跟。
母亲将我藏在身后。我又拱开她的衣角,眼睁睁望着。就在那个人举起斧头的时候,我跑去抱着牛脖子,它低头在我头发上碰碰,我知道它在和我打招呼,但它已经快要死了,脚站不稳,眼睛里有好大一颗泪珠。我伸手摸摸它的背。这时候一根草都可以将它压垮吧?
我被母亲再次拽到身后藏起来。
斧头砸在它的头骨上,很大的一声响,我感觉自己的脑门“嗡”的一声。也许只用了两三下,它就一头栽倒,我跑去摸它的尾巴,没有反应了。
让开,小孩子别在这里碍手碍脚。他们赶我。
这是我放了半年的牛。他们把我的牛杀死了。掏出肠子,掏出它的胃,其余的脏器,将它们扔到深沟里去。然后他们分吃了牛肉。
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吃牛肉。也许我也吃了。就像一个人,长着长着,就回过头将他的童年一口吞掉。
我的第二头牛是疯的。这时候我已经七岁了。两岁左右父母给我拜了两个干爹,一个彝族的一个汉族的。这头牛是汉族干爹的,他要让我这个闲下来没事干的孩子帮忙放他的牛,父母双手赞成。
这头牛与前一头牛刚好相反,但有时候我更喜欢这头疯牛。它像个反叛者,有勇气,能疯,也能恢复正常。它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比如放牧,想去哪里吃草根本不是我能左右的。就连大人也拿它没有办法。犁地只能选在它神志清醒的时候,但即使这样,它的脾气一上来,比如说我们耕地耕了很久不收工,它就发脾气,像是质问劳作时间为什么这样长,从它的牛鼻子底下发出“嗡嗡”声,然后,在我们眼前甩开犁头逃跑了。
我喜欢它从地里逃跑的样子,会提前在地上拱土,甩甩脑袋,蹄子乱七八糟蹦几下,将它的身段扯得和老猫一样柔软,往后缩的时候却是往前一纵身,扬长而去。尾巴伸成一条直线,尾尖上那一小撮毛发散乱在风中摆晃。
这个时候我母亲或者父亲就会大喊:又装疯了!又他妈装疯了!
我心里很高兴。它跑起来真是不要命的样子,豁出去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有时它能把身子在奔跑途中弯成一张弓再弹开。
父亲说,太糟糕了这头牛,我要宰了它。
妈妈说,快抓回来,给它穿上牛鼻绳。
我站在一边非常自信,对我的牛很有信心。没有人能杀得死它,如果它不自己回来,也没有人能捉住它。
我现在琢磨起来觉得,它或许是前一头牛的另一个化身。就像人,很多时候都在厌倦他的前半生,便试图做出惊人举动。
这头牛总喜欢拱土,也不和别的牛一起吃草,连和它们相遇都带着敌意,但它自己玩得很好,简直可以算是自闭症中的狂欢者。人们对这头牛摸不着头脑,由于没人能把握它什么时间会突然发疯,所以任何时候,我的牛只要遇着路人,那人就会自行绕道或者靠边走。
他们从未想过借它犁地,也在讨论并得出结果:疯牛肉是坚决不能吃的。
我的牛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闲得无事可干。说来也怪,它虽然是疯的,却从未伤害人,我如果要骑上牛背,它就稳稳地站住脚跟让我爬到背上。反而是别的正常的牛,把我从路上一牛角挑到路坎下。还好运气不坏,路坎下没有石头,牛角也并没有挑中要害,我在床上躺了半天,又可以四处乱跑。
我们家旁边是一大片油茶林,油茶树下全是青草。我的牛最爱往那个方向走。另一边的松树林它不去。由于我也无法左右它想去哪儿,就只好成天跟着,完全听从牛的指挥。这一点惹来很多大人取笑,说我不是放牛,而是牛在放我。
他们也只敢跟我说这样的话,见了牛还是要躲。
牛在油茶林玩得最欢腾,有时候我觉得它到那儿根本不是为了吃草,而是去发疯。它发疯也要挑个风清草好的地段。到了秋天草色枯黄但是长得还很高,我站在牛后面根本冒不出头来。也不知它是不是忽然回头看不见人,这个看不见人不知对它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突然就疯了。只要它看不见有人跟着,只要它发觉自己单独在草丛中,它就甩开尾巴跳到没草的地面上,在那儿扭弯了身子狂蹦。照表面看去,用一个孩子的理解,它是高兴到发疯,就像终于摆脱了什么锁链,发觉全世界只它一个,又在那么多的枯草旁边。如果用大人的眼光看,在太阳的映照下,草色枯黄,一头牛在地面上将它的影子从身上弹落,那影子落到地上还在蹦跳,阳光照在影子上,光线越亮越能清晰地看到影子的舞,尘土能掩埋一切,就是不能掩埋牛的影子。
可下边就是悬崖。牛不知道这些。它似乎也不怕,每一次跳完之后都要直冲往悬崖方向跑,就像那前方摆着它至高的自由。在狂奔途中,我听到牛的尾巴扇出风响,身体扯成一条直线,仿佛它有足够的信心一步能跨过悬崖,弹到对面的山顶。我只能跟在后面使劲喊它。幼童的声音尖利,能穿透它发疯的神经,并且每一次——尽最大努力——我都拽着它的尾巴,后来才知道,它尾巴扇出的风响就是我本人,我挂在牛尾巴上就像一件小衣服,它叼着这件衣服可以左右摆动。
很多次我们都差一点冲到悬崖,人们将那儿称之为“崖口”。只要到了崖口,牛和我,就彻底完蛋了。从那儿掉下去可以直接毫无悬念地落到深沟里去,那下方是一条河,我们会是两道不错的荤菜,人肉饺子和牛肉饺子。我试图喊周围的人救命,又总是想到那把生锈的斧头,无法将声音真正传出去。
我只能使劲喊它,不管它能不能听懂。我觉得它是可以听懂的。
它往上跳我往下拽,它朝前我朝后,这样的僵持总算惹来很多人注意,不过他们是不会帮我的,他们只会站在远处对我说,你是小傻瓜吗?你不知道它是疯的吗?你也疯了吗?快放手啊,你想吃牛尾巴吗?
他们说到吃牛尾巴,我的心就“扑通”一声,像被人丢了一块石头。
最后除了牛自己停下来,没人可以阻止。它站在离悬崖五十米的地方拱土。我也放开牛尾巴,爬到树上坐着。只要它开始拱土,那就是在发泄最后一点怒气。
人们散去之后,我的牛垂头丧气,满脸都是泥巴,不吃草不拱土不叫唤,像人一样有些神色茫然,也许不发疯对它来说太无聊了。我也垂头丧气,不过我说不好为什么是这样的情绪。
我的狗
如果不下雨,我的狗就趴在墙脚晒太阳。它已经习惯和自己的妈妈分开了。好几个晚上不再听到它的叫声,也不再试图逃走。我真不敢想才断奶的狗娃娃和妈妈分开心里有多害怕。我们只为它准备了一个鸡窝大的家,每个晚上它就抱着自己的前腿缩在里面睡觉。有时候它拱一拱周围,发觉自己的兄弟姊妹真的不在身边,又呜呜两声睡去。
我隐约觉得它很可怜。不过我才五岁,很快这件让我觉得不太高兴的事情在第二天就忘记了。第二天它也并没有表现得多难过,照样吃我家饭,也和我们几个小孩一起玩耍。它只在晚上闹情绪。
妈妈说,这是正常的。这就是狗命。所有的小狗生下来就会被别的人家领走。或用钱买,或用粮食调换。
我好害怕,那如果这样的话,我长大了也会被换走吗?我值多少钱,或者值多少粮食?妈妈很不在乎,她说好的坏的都是一个语气。她说我完全不用担心被换走,长大了我自己就会走的,“谁会待在这个狗窝?”这话不太像专门给我说的了,她望着周边的山,脖子很痛的样子。
我的狗完全接受和妈妈分开这件事后,我就带着它四处闲逛。有一天它和妈妈相遇,它们只是跑在一起互相蹭蹭,打个招呼,就随我走了。
它表现得很勇敢。
我带着它去刨草根,那种叫“丝茅草”的东西,根茎嚼起来有一股甜味,但是嚼久了会变苦。叶子很尖,不留意手就出血了。我们的大多数时间就在这座山上度过。几乎每个白天都来。父母很少管我。奶奶更不会管我。她喜欢孙子。我们家族的每个男孩都能从奶奶那儿得到一把糖果,只有我不能。奶奶说我是“外面的人”“不值钱”“赔钱货”,反正她对我很有意见,她对我的狗也有意见。
我们躲在山上不会遇到人。这儿几乎不会有人来。爱吃这种又甜又苦的东西的人,好像只有我一个。
说实在的,我对大人们也有意见。懒得跟他们说话是我对这种意见的表现。也不喜欢和别的孩子玩耍,他们都长着一张缩小版的他们父母的面孔,好讨厌。
只有我的狗,它的脸上全是泥。说也奇怪,不用怎么教,它已经会帮我干活了。用嘴咬住凸在表面的草根使劲拖。
中午太阳很热时我们回到家中,蹲在桃子树下或者墙根下。桃树很少开花,也许它不用开花吧,反正我也不怎么见着几朵桃花,我感兴趣的是桃子。只有桃子成熟我才会注意。狗也爱吃桃子,我摘一个它啃一个。不过这件事它干起来相当费力,转着圈子啃,好像牙和脖子都要掉了。
之后,桃树因为挡着底下几根玉米和豆子,他们说,怎么可以挡住庄稼呢,砍掉吧!
大人的手劲真不小,我现在知道他们搞起破坏来比我们严重多了,但是他们从来不承认。
砍掉这棵树的是一把菜刀,斧头临时丢哪儿找不着,就用菜刀将桃树解决了。我很愿意看到菜刀突然坏掉。但是它不仅没有坏,在主人的手中还挺有表现,两三下工夫,桃树就站不住了。
他们砍了我的桃树。
从那天开始我就和大人们没有话说了。
我五岁,隐约觉得自己失去什么东西,又说不好。那之后我恍惚以为自己的脚不行了,以往我喜欢爬到树上捉个虫子啥的,走到桃树原先站的位置,一只脚就不由自主地抬起来,是上树的动作。
但是他们把我的桃树砍掉了。脚不知道这件事。
他们很有伎俩,砍树的时候也跟我商量,是这么说的:这棵树有毒,我们砍掉它,明天我给你重新栽一棵比这好的,结很大果子的那种。
我同意了。我说,要很大果子,又大又甜的那种。
往后我就和狗每天等着另一棵树长起来。他们说树种已经栽下了,还在准备发芽呢。听说发芽要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要等多久,但是每个早晨和黄昏,都去看一眼。
那儿只有桃树桩。后来烂掉了。
我终于搞清楚,大人们说谎也是很厉害的。
当我不再想着桃树,脚也习惯放在地上的时候,我的狗已经长成一条大狗。才一年时间,或者两年,它差不多可以驮着我四处走了。
人们时常取笑,说骑狗是不好的,长大了出嫁那天会下雪。
我的狗长得很强壮。外人极少来我家串门。就是因为它的强壮声名远播,连我的大姨妈都知道它很威猛。那个老女人,我不爱她。如果她不打我的话,我可以承认她是我妈妈的姐姐。听说她要来借狗。她种了一大片西瓜,急需一条守西瓜的狗。这件事把我吓坏了,也听得糊涂,我跟妈妈说,老子长到五六岁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借狗。
说完这句话我必须承认,我大姨妈和妈的确是一个妈生的,她们都爱打人。
大姨妈来那天,吓得我和狗赶紧躲进树林。我爬到树上,狗在树下,我两个谁也不敢出声,但还是被他们抓了出去。我爹很好地发挥了他老兵的特长,在好远的地方就说,你和你的狗已经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
我们两个出来投降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绳子。大姨妈讨好地拿着一包饼干。我在山上很少尝到这种东西,思考再三之后我把饼干接过来吃了。我的狗就这么被他们套上了绳子。
我跟在狗后面走,这是我爹的主意,他看出来狗不情愿,大姨妈拖得满头大汗,狗就是不肯挪步。它是完全被拖着走的。被拖一步叫一声然后回头看我一眼。我好像有点懂了,知道大人们为何要说,人是无情的,狗最有情义,狗还会跟主人摇尾巴。
我的狗一路对我摇尾巴,还用求救的眼神看我。
它的叫声越来越像一些石头,堵进我的喉咙。我在狗后面哭,大姨妈说,你哭个屁呀,又不是不还你。她很恼火,因为她发觉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将狗拖回去。几十里山路会让她瘫掉的。
又是我爹的主意,让我跟着狗一起去。意思是,专程送狗到她家。然后我玩几天再回来。这个办法果然好,我的狗一看到是我牵着它走,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说实话,她家还挺好玩。有个比我大一些的姐姐。狗去守西瓜之后,我感到很无聊,只好和这个没见过面的姐姐一起玩耍。她大概十二岁,说起来我和她没什么共同语言,虽然我只有六……可能七岁,却觉得她实在幼稚,我的很多话她都听不懂。
她喜欢抢东西,这一点真让人伤心。有一天我们两个在院坝下方的水田边玩,田埂上种了很多番茄,我一眼瞧见个红透的,又大又红,一把摘来抱住。她上前就跟我要。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你给不给?”
“不!”我使劲摇头。
“那我去告诉那家人,把你抓走。”
“你去告。”
“不要在我家玩了,滚你家去。”
我准备转身走,她上前就把我的番茄抢住,我一着急,脱口而出:日你妈!
她立刻就把手缩回去了,跑去大姨妈那里告状。
我大姨妈是拿着棍子来的。那天我的屁股差点就开花了。她一直追问,我喊她喊什么,敢这样骂。又说她是我妈的姐姐,妹妹的娃就是她的娃,姐姐打妹妹的娃就像妹妹自己打自己的娃。
她把我头都绕晕了。
我从来不知道“日你妈”是什么不好的话。大人们着急的时候也这样说。他们说得,我为什么说不得。
第二天我爹就去接我了,这事情也很巧,我没有求救,救星自己跑来。大姨妈特意上街给我买了一双钉子鞋。穿起来跳很高的那种。我知道穿上它很舒服,但我就是不要,至少我不会亲自从她手里接过来。她跟我爹说起打我的事情,说得完全错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却是摸着我的脑袋说的,一副爱怜的完全为了我好的样子。
离开那天,我很想要我的狗。自从送它到大姨妈家,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说西瓜成熟之后,就把我的狗还回来。我不信。
我的狗是回不来了。因为冬天了,西瓜早就摘完。我爹只好承认,那条狗在西瓜成熟的某天晚上,被贼毒死了。他说,会给我重新买一条狗,比那条更好的。
这话听起来和从前那些话是一样的味道:砍掉桃树,给我栽一棵更好的,果子又大又甜。
我保留着那只狗碗很长时间,是一只缺边的花瓷碗,事实上也是我自己的碗,我和狗经常趁着没人的时候一起吃饭,我一勺它一勺。但是后来那只碗坏掉了,我也差不多十岁,父母将我送进学校。在那矮趴趴的土墙房下,老师每次念拼音weng(嗡),我就会读成wang(汪)。
我的好几个学期,耳朵里都是狗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