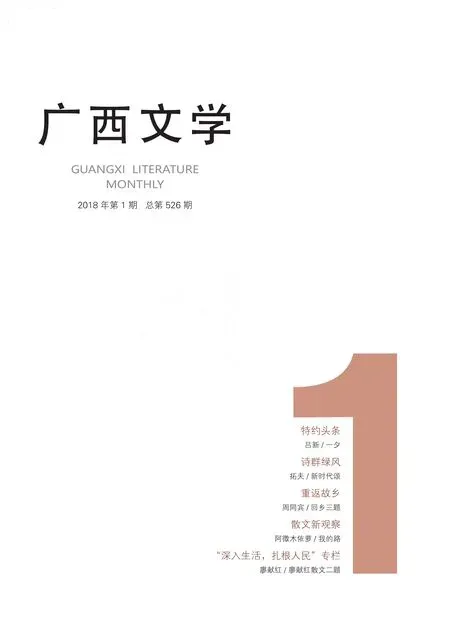《广西文学》2017年度优秀作品评委评语
小说奖
田瑛《尽头》
作为重返文学现场的老手,田瑛的小说叙述于平直、率性中显现出奇突的风景。在《尽头》之中,生活中的沉重苦难多以心理与行为映射,叙述嘈嘈切切有如心跳,卒章之时倚赖轻盈的反转、回旋统摄全篇,弥散出深沉的善意。
乔叶《进去》
乔叶擅长捕捉人与人之间隐微不发的感情线索,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指向生命本身的复杂与玄奥。《进去》里面,人事无常,人性奇诡,若有若无的情感力量牵引着女主人公的恍惚远行,并以一个流变又快又稳地终结全篇,展现出一位高手令人炫目的技艺。
光盘《金色蘑菇》
作为一位高产稳产的熟手,光盘熟知小说的秘径与秘境,而荒诞性则是他驰骋秘境的通行证。《金色蘑菇》中的各种元素——悬疑、荒诞、魔幻——倚赖对精神异态的描述而不可思议地融汇于一处,斑斓绚丽,恍惚有如梦境。
周耒《风不撒谎》
周耒的笔墨饱蘸边地气息,而小说中有如公路电影的场景转换,也忠实地还原了西南边陲特有的生活场景。一次跨国寻亲之举,利刃般剖开了边民的生态群像,生之艰辛,活之道义,在亲情的导引下生发成一声浊重的叹息。
杨彩艳《我们的童年谣》
杨彩艳的小说创作出手不凡,《我们的童年谣》初步彰显出朴直大气的写作品质。作品继承了现已罕有的风格,散淡的记叙中保有最初的乡土气息,人情的美好、人世的艰辛和山野的灵动糅为一体,诚挚而隽永,亦是地域创作中值得期待的新气象。
明媚《南方的格桑花》
明媚保有了小说家日渐稀有的锐性和探索精神。《南方的格桑花》以细腻的心理白描,揭示了贫困人群的欲望与生存,挣扎与艰辛,冒险与幻灭。巧妙的叙述角度,快速的跳切,以及对彼岸长久的眺望,使得明媚的文字始终氤氲着沉重的诗意。
焦冲《小说与生活》
在焦冲的笔下,常见的剧情反转成为勘探人性的利器,小说也因此成为躬身自省的文本。小说里的小说家直面现实的勇气,却在自身境遇中溃退,又只能以虚构聊以自慰。多重反转引发多重意向,有如显微镜,引领读者清晰地面对生活中的无奈与束手无策。
臧北《臧北小小说六题》
臧北拥有显微镜一般的视觉以及温润而通感的心境,周遭的事物在这视觉与心境穿插抚摸中皆含有了独特的意义。这组作品以简短而细腻的文字打通了文体的界限,是小说,是散文,是思想短札,构筑出影影绰绰的文字场域,予人欲罢不能的阅读张力。
诗歌奖
臧棣《回音中的印记(组诗)》
臧棣以敞开的心灵观照日常生活的景象,通过充满警觉的文字在看似很小的格局中连通生命个体与世界,在词语的缓缓推进中呈现了内在感受向外在宇宙的无限延伸,以及这种敏感和延伸所带来的丰富与孤独。
康雪《照耀(组诗)》
康雪用细腻、灵动的笔触,抒写生命的成长和迷茫,透过瓜、果、花、树等意象见证和呼应生命的神秘年轮,以女性的敏感与温柔,将具体的爱、孤独、疼痛及恐惧包容在无限的珍惜和怜悯中。
胡弦《胡弦的诗》
胡弦的诗执着地探索生命的在场和缺席、拥有和失去,在悖论式的场景中注入了对人事的深层透视,这种悲悯与希望、过去与现在的并置和叠加,增强了诗歌文本的张力。
散文奖
黄祖松《日久他乡即故乡》
作者对生活有了深刻体验之后,仍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无论是描述故乡的山水、人事,还是先祖、父母,都呈现出如和风细雨般切入心田的挚爱深情,其浓郁醇厚的情感表达堪称客家人的典范。
陶丽群《赤红色的墙》
作者以她特有的灵气及对世界细腻的感知,讲述了自己将近四十年的生命历程。文中小说笔法的娴熟运用,拓展了散文的创作空间,也为文本带来了玄幻的魅力。
草白《劳动者不知所终》
作者以内化于心的朴素与诚挚追忆父亲的过往时光,并对生活与劳动的关系给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文字优雅沉静而富有张力,平实准确而又饶有趣味。这种包孕着智慧的写作在这个深度稀缺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
安宁《外乡人(两题)》
作者葆有一颗仁慈善良的热心,因此才能真切地看见世界上、生活里除了自己还有他人,而一切也各有来路。以此同理心,作者以“正午的阳光重重砸下来,落在脊背上,有微微的疼”作为全文的基调,而这基调也足够震动人心。
白琳《楼中记》
作者以陌生化的视角打量岁月深处的自我经历,通过包含着负面因素的尖利所造成的肉体感官及思维意识的伤口表达触目惊心的真实和“诗意的残酷”,这种精神性的蜕变锻造了成熟的自我意识,于冷静的叙述中展现成长的复杂与撕裂,让人战栗。
评论奖
罗小凤《在童年的回望中想象历史——论严风华〈总角流年〉的叙事策略》
罗小凤的评论从特定的童年视角分析作品的叙事策略,把握了评论对象最重要的创作机制和艺术特征,在行文中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对所评论的文本进行清晰、到位的解读,尤其对童年视角中的历史想象做了令人折服的评断。
容本镇《踏遍青山 行吟八桂——论石才夫的诗歌创作》
容本镇的评论格局宏大,从家国情怀、骆越根脉、人间真情几个层面切入评论对象,不仅对具体的诗歌文本做了深入的分析,更对作者的个人经历与情怀加以评说,具有知人论诗、知诗论世的特点,弘扬主旋律,并杜绝了学院派研究僵化烦琐的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