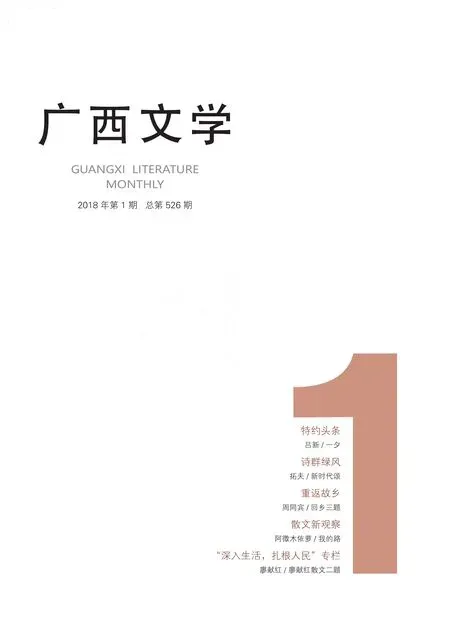高 人
王闷闷著
1
秋风一抖身子就凛冽不已。喧嚣的城市,道路旁铺满黄叶。行人裹紧衣裳,生怕狡猾的冷风钻入咬啄,到时浑身惊颤。小寨是西城的繁华之地,四座天桥环绕,盘旋于上空。上下台阶光滑不算,铁栏杆被使了好大劲才从雾霾深处逃离出的阳光照得好冰好凉。我跳下公交车,就随着人流涌向台阶。耸耸肩膀,提提背上的书包,重新与背贴到出门时的甜蜜得体,看对面的什么跑了神,脚尖碰到台阶的滑棱,咯噔,差点摔个狗吃屎。危险啊,惊魂未定,几乎门牙不保。
在天桥上绕了个圈,来到那会思索得出神,差点付出惨重代价的目的地。此次出来,不为别的,专门为后天的工作踩点。此地人流量大是不假,可要想做到任务圆满完成却着实不容易。省文化厅要举办一个级别甚高的音乐会,到时候肯定不乏省内外的名家出席。我所在的学校踊跃承办,几轮竞争后,如愿以偿。为积极宣传,省上做了功课,下了力气。在学校召集数十名学生,发高额工资,用最笨拙的方式宣传——发传单。我不懂音乐,在学校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来挣几个做零花钱。今儿出来做预备工作,也是有报酬,不多罢了。负责人说,不可图完成任务胡乱发,随时会有人转悠监督。如果发现乱发,将扣除所有工资。我被分到这里,人们川流不息,好运气。别人看着只能流口水。
绕转几圈,疲倦不堪,依靠在身后的废弃铁箱上。咔啦,铁箱上出现凹陷。不多会,觉察到有力气在抵触,一阵比一阵足。就是凹陷上涌,也不至于有如此劲道。我移开身子,铁箱的门子呼啦敞开。我震惊,盯着里面看。走出个白发老人,瘦脸,长眉,下巴留有白胡须,头发扎起。七十出头。别说,倒是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意思。可惜衣着不搭。不是长袍布鞋。上身着陈旧的黑灰色布衫,袖口有棉袄的毛口子突出。黑裤下接,一双过了气的运动鞋。整体而言,无论如何看鞋或头发都有些突兀。
他看见两三步外正发愣怔的我,忙说,刚才开门把你磕碰到没?我反而慌了神,结巴地说,没没没有。他打量了我一番,确定没伤到,说,那就好。转身从铁箱里提溜出个有些肮的黑红色旅行箱,轻放地上。又去提一米多长圆滚滚的黑色袋子。我站在边上。看他这般准备,接下来会有什么惊喜。箱子拉链刷地滑过,箱子被摊开。我凑近,像是见到了百宝箱。有红色收音机样式的音响,方正古旧的纸盒子,几个药瓶,笔和本子等。他用同样手法打开黑色袋子,小心翼翼地取里面的物什。轻托出来。原来是把二胡。接通电线后盘腿席地而坐。
没赶上演奏,我就离开了。从公交车窗看去,他吃块冷馍,喝几口矿泉水。车子转过弯,发了力,他就不见了。也好。寒风中,看多了,让人难受。口袋里的手机响声连片。几条短信过来。我打开看,是后天工作的有关事项。不知谁开了玻璃窗,风可劲往里灌,腿上凉森森的。有人受不住,搓手,说,谁把窗户关下。不多时,车里就暖和多了。
2
领到宣传单,掏出一张看,做得好精美。远远超出宣传单的标准,分明是册子,由五页组成。纸质光滑厚实,遇到亮的东西能反光。第二天九点半,我提着宣传单来到指定地点。第一眼看的就是废弃铁箱。与上次不同的是,上面贴了两张售房广告。八点半,我开始工作。看那两扇铁门依然静默,他大概是离开了。我庆幸,眼不见心不烦。正想着,铁门哗啦推开。和昨天的程序一般。他更没变化。
行人逐渐多起来,我没想到,本以为轻而易举就能发完,谁想却异常吃力。发不出去,给行人,不是摆手不要就是绕行。我郁闷,为何这么精美的宣传单没人要。众人像是见了瘟疫,急忙避开。到下午,不过才发出去一打,还有三打等着发。肚子早就叫唤了,不管如何,先填饱肚子再做打算。前面忙,没顾得上看他,他此刻也在休息。边看书边啃冷馍。旁边放多半瓶矿泉水。
我到路边的夹馍摊吃了夹馍,喝了几口热水锅里温着的牛奶。付钱时,我给了双份的。风吹着,看他几根没绾起的头发,直往脸上眼上黏。他不再吃馍,双手捧着书看着。我回到天桥楼梯口,坐在石桩上,喝完牛奶。坐了好一会,下定决心,既然买了,就送过去。走到他跟前。他感觉有影子压过来,抬头看我。我蹲下,从包里拿出夹馍和热牛奶,递给他。他吃惊地看着我,双眼晶亮,没接。我的手伸着,眼睛给他示意,拿着。他反应不过来。
我说,拿着吧。
他又看了十几秒,放下手中的书,双手接住。看会手里的食物看会我。
我说,趁热吃。
我蹲得腿麻,不得不站起来活动。还有三打,任务艰巨,忙碌前不忘对他说,快吃了,趁热,不够我再买。晌午暖和了不少,正是人流量大时,我加入了介绍,一场高端品质的音乐享受,先生,您看看。这位女士您看看。穿着甚好及较好的路人把我的话当作了耳边风,一闪而过。接住传单的,不过是些穿着一般甚至刚从工地下来的人。再就是一个老太太。起初,她站我跟前,不走。我问,要吗?她点点头。我给了一份。一会又出现在我面前,我看不过,问,还要?她说,嗯。无奈,再给一份。后来,我好为难。给吧,违背了负责人发的工作事项;不给吧,她站在那里,七十多岁。唉。第六次上,我只好严厉地说,最后一次了哦。她笑嘻嘻地说,嗯。谁想,更难堪的事情出现了。我发完当天的传单。看眼手表,整五点。还好,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半小时。舒展下身子,往远处看,吓了一跳。她抱着多半沓子的宣传单。像是我一次性拿给她的。让负责人看见肯定误会。到时候百口莫辩。
这天,我好运气,负责人过来时,她已经走了。不过我还是张望了多次。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多天就麻糊糊的,走转了一天,脚板针刺般生烈烈地疼。路灯照亮街道,大楼四周的霓虹灯忽闪不止。肚子咕咕叫唤几声,想起不远处坐着的老人,他收摊了吗?思索中,在嘈杂喧闹车辆的轰鸣声中听到了细若游丝的琴声,时有时无,时隐时现,一阵紧一阵弛。脚步随琴声而动,来到老人的所在。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搓揉多次,依旧如此。昏暗的路灯光边缘刚好圈住老人。盘腿坐着,几绺白发耷拉于脸颊,琴筒搁在膝盖上,右手按琴弦,左手拉琴弓,双眼闭合,如痴如醉。登时,琴声突起,徐徐走高。眼看就要到顶,却刷地落下,缠缠绵绵。浸润着无数哀思。微风起,人潮涌动,叫卖声四起,反而让人觉得无限凄凉。皮箱里散落着几张褶皱的钱,两张被风怂恿得不安分,直往外蹿。到了沿上,再要是无动于衷,可就要飞散到车水马龙的道路上去了。不觉有些可惜。我看他没有丝毫察觉,就上前去,把冰冷的水瓶压在上面。路过的人向我投来奇怪的目光,不看老人,更不听二胡发出的琴声。匆匆过去,消失于夜色下。
十几分钟后,他长舒口气,睁开眼睛。准备收拾东西,看我站着。抬起头,对我笑。我被他的笑感动。黑红的脸颊舒展着,粗糙的双手精细地安放每件东西,挨个轻放进铁箱里,生怕劲使过头。等他收拾毕,天色完全暗了下来。看我还不离开,他嘴唇嚅动几下,没张开。我知晓他要说什么,轻声说,去吃饭?他顿了顿,转身打开铁箱的门,取了什么装在口袋。
在一家面馆坐定,问他,吃什么面?他认真地看着桌子玻璃下面印着面的图片,手指停在油泼面上。我点了西红柿鸡蛋面。起身倒了两碗热面汤。明净灯光下的他是那样的可亲,我几次想抱住他。刚才他走路时,我才看清他穿着多么的单薄,身体多么枯瘦,路过衣服店,甚至想拉他进去,给他买几件厚衣裳。面上来,他没吃,直至我的上来才动筷子。我们紧锣密鼓地吃着,他剥几瓣蒜放进碗里。吃到一半,他站起来,去了柜台一趟。吃完我去结账,老板告诉我,已经结过了。我懊悔不已,早知这样就不带他来吃饭了。他用手揩抹下嘴巴,出了面馆,独自走在已然冷清的街道上。我跟在后面。到了公交车站,他停住脚,转过头看我,等我走近后,说,回去吧。
我点点头。看着他单薄的背影,忽然,刮起好一阵子的风。
3
拉开窗帘,顿觉兴奋。世界白了,大自然的精妙之作,那般的悄无声息。负责人打来电话,问起床没。我说,刚起,正洗漱。负责人说,今天正常工作。我说,好。说到工作,我想起传单,想到昨天捡拾传单的女人,不知怎么拐到了他那里。雪下了足有五六厘米,空枯的树被装饰得丰满肥硕,单色的世界原来是这样。虽然不会保存很久,毕竟看见过,知足。下了雪,又是星期天,就担心卖早餐的不出来,顺路到学校食堂吃了。想给他拿,转念想,到那里早就凉了。不拿心里又过意不去。对着蒸笼上热腾腾的包子发呆,学校这家包子好吃是出了名的。皮薄馅多,咬一口,那个鲜啊。我返回宿舍,背了书包,装件棉衣。买到包子后,把包子裹在了棉衣里。热气就散发得慢些。
路上有积雪,公交车开得很慢。我心里着急,手伸进书包,摸包子是否热乎。好容易到了地方,跳下车。铁箱被雪覆盖,宽大的顶子戴上盏雪白的帽子。铁门紧闭着,里面指定冰冷。没有办法取暖。我犹豫许久,决定上去敲门。没有反应,静寂一片。又敲了几下。想,再不见动静就直接去拉。此时,门吱呀有了缝隙。他看着我,通红的脸颊、鼻子,抖动几下。我赶紧从书包里掏出还热乎的包子和豆浆给他。几片从天桥上吹下的雪花,端端落进门的窄缝隙里。打湿他的嘴唇。双手笼在袖子里,看我几眼,接住包子豆浆。路上没几个人,我不急着发传单。
他要把铁门敞开,我给挡住了。
吃完,他一如往常,摆好那一套,身子依靠在铁门上,坐下。我看他屁股下就垫几个塑料袋,反正传单多,何不给他铺几份。这样要比发出去没走几步就被扔到垃圾桶里有意义得多。这次我不经他同意,由着自己性子去做。果然,他来不及拒绝,看几眼后只好坐下。拿出箱子里的书看。我凑近看书名,着实吓我一跳。他看的是本破旧不堪的《老子》,我扫眼盒子里的书,还有石涛的 《画语录》。我想不通,拉二胡,不看琴谱看这些,有何关系,是何道理。
整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晌午,路上的雪消融得湿漉漉,车辆过来过去发出刺啦啦的声响。整整一个上午,他没挣得分文。本就行人不多,加之寒风刺骨,每个人恨不得赶紧到达目的地。谁有心思看周边,听老头子拉悲伤的二胡曲。我发了差不多有一半,说是发,不如说是硬塞。没得好脸色,碰了许多壁。可不发怎么办?也可以扔垃圾箱或给清洁工,但这岂不是太浪费了。簇新的宣传单,还没宣传就被扼杀?责任在谁,毋庸置疑指定是我。所以我剩了至少有一半。
下午,我走到他跟前,说,去吃饭。
他没言语,只顾收拾东西。路灯光打在雪地上,格外耀眼。人们怎么会错过这般景致,纷争向前。好生热闹。堆雪球,拍照,打雪仗。他收拾毕,我们缓缓行进。还是昨天的面馆,他要了烩面片,我要炒拉条。他叫住服务员,说,炒拉条改成烩麻食。服务员看我,我说,好。他拿了瓣蒜,把玩着,说,天冷,吃热热滚滚的,身子暖和。我那会想说那么多的话,此刻反倒消失殆尽,不是点头就是嗯啊几声。脑袋里急速转动,试图寻得一两个可行的问题。
我说,您来这里是……
他说,要不要喝一口?
我惊诧之余点点头,对,怎么把这茬忘了。家乡人冬天常喝烧酒,暖身体。能在体内燃起无数股火焰。
他叫服务员,拿瓶二锅头来。看此架势,喝酒怎么能没有菜,我让服务员再上个凉菜。大部分他喝了,我就一盅,慢慢抿。
喝着喝着他话就多起来。他说,我来这里为寻人,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好,家乡人一个个被吸走,听说都到这里来了。我懂得他说的意思。现在的农村成了空壳,里面的人皆被推走。端起酒盅,一仰头,刺溜喝个精光。酒香弥漫在空气里,闻着就很是享受。看他吃饭的样子,真是心疼,我不自觉地说,您尽快回家吧。这里住的吃的,受罪,家里就算艰难,住的暖和吃的热乎。说完又觉得哪里不对,补充道,等开春再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我能熬过这个冬。
回到宿舍躺下,空调的热风吹拂着,暖气热腾腾地烘烤着,像是在春天里。不自禁地想到他,回来时天上又飘起了雪花,让我走,他自个能回去。为他安全,我悄悄跟在他后面,看他到了铁箱处,身子蜷缩进去,关上门。归于平静,雪花落在铁箱上脚印上,不多久就会被完全遮盖住。所有的踪迹将不复存在。就像他吃饭时说的,人生在世,不过就是看了几场雪,终有消散的那天。路灯静静地亮着,车辆在结了冰的路面上踽踽前行,霓虹灯在寒风中寂寞地闪烁着。不知他此刻是什么情况,冷不冷?几次想看铁箱里面的布局,没得机会。说是铁箱,实则是个废弃的变电箱,旁边修建了更新更大的,旧的自然就没了用处。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铁箱是废弃了,里面那千丝万缕剪不清理还乱的电线就都没用了吗?万一……唉,有心想而无力做。只能祈祷上天保佑,让他顺利度过每个夜晚。
玻璃窗上凝结了厚厚的冰,模糊了外面。舍友说,睡吧。嘎嘣,开关按下,灯光尽失。沉浮在黑色里。外面偶尔有脚步经过,那是保安在做夜间巡逻。不知雪还有没有下,别淹没了铁箱就好。
4
我们渐渐熟络起来,发传单时,他会拉不同的曲子。这天我来得早,看他坐的地方湿淋淋的,就跑了几个角落,抱来几块砖再在上面铺上厚厚的传单。然后在不远处的早点车买了早点。敲几下铁门,不知怎么,只要能看到他就开心不已。再敲几下,好半天没动静。起初还兴致勃勃,此时却紧张起来。难道?不由我往坏处想。昨夜的雪下得实在,积了厚厚一层。忽然听到里面有咳嗽声,我一把拉开铁门,不错,他还活着。我激动不已,竟然落了泪。
天还是阴沉沉灰蒙蒙,晌午,就在我俩要去吃饭时,负责人过来检查。总体是满意的。正当她要离开时,看到站起的他坐垫下露出的宣传单。不由分说走过去,猛地揭开,几十张光鲜亮丽甚至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宣传单映入眼帘。他登时也明白了是什么情况,赶忙说,这是从地上捡的。负责人说,轮不着你解释,转身问我,怎么回事,最好老实说。我知道隐瞒不过,那会铺时,是想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存了侥幸,心想,只要盖上坐垫就能瞒天过海。谁想,唉,只好认栽。再者,我铺时,也没顾及往开搓,七八张粘黏着,分明是新的,还没来得及散发。我说,对不起。负责人勃然大怒,呵斥道,我是让你来散发,不是给老乞丐做床褥,还能不能做,不能做赶紧走人。感觉不解气,又指着边上站着已然傻眼的他说,他懂个啥,给他铺垫,屁用没有。他蹲下,把宣传单一张张压平,递过来,说,大部分好着,还可以发。负责人失去了理智,哪里像是学校工作的人,分明就是怨妇泼妇一个。猛地甩手,打掉他递过来的传单。我胸中的怒火在燃烧,定要用锋利的话语刺痛她。但我看到他摇摇头,去捡掉落的传单,我只好把气压下去。负责人看我蔫了,再者大概也觉得有些过头,就含糊说了几句,走开。
他把捡起的传单给我,我接过来,反倒拿出更多,重新铺垫在砖上面。他茫然不知所措,呆站在那里。害怕他顾虑有负担,我说,不打紧,莫说给你几张传单,就是数百张都值得。看看宣传单上的那些人,放着自以为最漂亮最惹人的照片,冠冕堂皇,其实是最滑稽的。太多沽名钓誉之辈,依靠某些方面的便利,谋得此职,在灯光四溢的舞台上耀武扬威。他面无表情,坐下,拉起曲子。
对面大楼是这里人气最旺盛的地方,里面有各种消费区。只要有钱,没有买不到的。七八层像是吃饭的地方,玻璃窗上雾气朦胧。隐约看到几个移动的身影。进出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挽着对方的胳膊,有说有笑,好快乐。
当天晚饭后,我们走出面馆,依旧各走各的。我没忍住,叫住他,那个音乐会你也可以来观看。他没回头,手摇摆几下,走开了。
回去时,看时间早,就没有坐车。走着回去。虽说今儿没见太阳,雪最终还是融化了些,这会就结了冰。灯火璀璨的夜晚,我像是一叶浮萍,飘荡在漫漫无边的城市。迎着风,穿梭于大大小小的巷道,哪里才是我的家?路边的饭店餐厅,热气滚滚,如何才能感觉到玻璃后面的温暖。突然,一滴灼热的液体落在脸颊上,抬头看到底出自哪里?天空一片漆黑,迷迷蒙蒙。眼睛酸涩得紧,大概是注视天空太久,忍不住掉了泪。
按说这天应该特别累,从工作地点走到学校,睡过头都是理所当然。我却没有,反倒四点多就醒来,睁着眼睛思索什么,盯着黑色看不停。六点,宿舍楼通了电,我轻手轻脚地下床,在洗漱间洗漱。舍友在迷糊中,听到我洗漱,惊讶不已,问我不瞌睡吗?每天如打了鸡血一样,哪里来的劲头。我笑而不语。老套路,去食堂吃早餐,顺便给他带些。精神抖擞地坐上车,向着那个地方前进。谁想,心急之下竟然来得太早。偌大的地方,只有零星几个人经过。冻得站不住,环视一圈,找到家肯德基店,不管怎样进去暖暖。理论上不点吃的也可以坐,为不显得尴尬,我还是点了杯牛奶。八点多,人渐渐多起来,天气转晴,东方溢出道道亮光。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只是加倍的寒冷也要开始了,初中学过物理,消融冰雪需要大量的热量。我轻车熟路地走到铁箱前,敲门。没人应,我想许是他睡得沉。再敲,还是没人应。我就叫,老爷子,我给您送早餐来了。等待许久,里面仍没响动。不远处的清洁大姐向我走来,说,小伙子,里面的人是你什么人?这可把我难住了,什么人,我说不清楚。说是路人?太疏远。说是亲人,那是什么亲人,爷爷、外爷、叔伯?大姐看我为难,也就不再追问,说,昨晚十一点多,这边有座大厦突然停电,就找来电力局的人抢修。找寻线路时,在这个箱子里发现了人。维修人员那个生气啊,说,快出来,憨老汉,知晓这里面有多么危险不,满是老旧的高压电线,你压在上面万一哪根漏电出了乱子怎么办?我焦急地说,后来呢?大姐说,后来老人连忙致歉,收拾起东西走了。这么冷的天,他能去哪里?我不甘心,说,阿姨,那您知道他去了哪里不?大姐摇摇头,只是说,当时向西北方向走了。我顿时浑身无力,没心思做任何事情,对着紧闭的铁门发愣怔。比起前面,不知什么时间,有人在上面又贴上了数十张售房单子。白纸黑字格外显眼,不少人会停住脚步,瞅上几眼。他的座位还在,估计是走得急,连坐垫都没来得及收。说是坐垫,其实就是件被人扔掉的破棉袄。下面有我铺的传单和砖块。
我在大楼前的台阶上坐下,享受着寒风与阳光争斗下的温暖,说不出其中的滋味。感觉整个世界都空了,回想这几天,好虚幻。仿佛他不是真的,从初次给他吃的,到我们一起吃饭,像是演了场电影。温暖被不时吹来的寒风分割撕裂,落下碎片,人们直打冷战。我倒是希望这几天的所有都是假的,那样他就不用受那份罪。可这一切明明是真的,冷就是冷,暖就是暖,容不得半分质疑。
5
负责人说,最后一天了,认真干,工资会直接打在卡上。越快结束越好,我实在没心情在那里待。自他走后,我发传单发得很快,管你是谁,统统发。只要接,我就发。雪消融得残迹斑斑,只有拐角阴凉的地方还有存留。铁箱里有动静,我激动不已,是不是他回来了?在期待中,有人出来,不过是新来的住户。疯女人,爬出来对着太阳伸懒腰。大概用不了多久,也会被赶走。
对面楼宽大的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视频——再造优美村庄。世外桃源式的农村,山清水秀,山脚下卧着的村庄,每户几间茅房,烟囱上升起袅袅炊烟。田地里的老黄牛哞哞地欢叫。农人持着鞭子在空中摔打。一群小孩围聚在村头弹玻璃球。太阳西落,女人站在家门口,亲热地喊孩子回来吃饭。疯女人对着屏幕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着说弄错了弄错了。没人搭理她。唉,他可能已经离开这里了。去了更远的地方,寻找他所要寻找的。
我草草发完宣传单。看眼手表,不到三点,去哪里坐会。选择了几百米外的咖啡馆。起初我不适应这样的地方,觉得太假,且价格昂贵。就那么小杯咖啡,几十块钱。和同学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不得不去融入其中。喝这个不能用多少大小贵贱来衡量,如果按吃面喝米汤的方式计算,那亏得不是一两点。按舍友的说法,这喝的是情怀、高雅。音乐会后天开幕。负责人发来短信说还缺个会务,问我如何。我说,做什么?负责人说端茶递水。我答应下来。明天好好休息,养足精神,继续去工作。
音乐会在学校最高端的音乐厅举行。去年才修建起,所有的设施都是新的。这是首次承接大型的音乐会。学校领导很重视。不知到过会场多少次,千叮万嘱,不能出岔子。所有负责人都谨小慎微地做着,不放过每个细节。我被安排到门口,引来宾签到。
音乐厅的富丽堂皇超出了我的想象,自修建好我也是第一次进来,从前都是经过。空中的吊灯,水晶点缀,通上电真可谓是星光璀璨、流光溢彩。投射在光亮簇新的木质地板上,如一池流动的水,清澈见底。绵软的椅子已然摆好,有几十排。舞台背景是偌大的电子屏,已经闪烁起耀眼的大字,与艳丽夺人的画面配合着。指挥台、音乐席,就差每位音乐家来就座。半个多小时的进场,看没人再来了,负责人让我进到里面,做些零碎的事情。主持人让所有人安静,音乐会开幕式马上开始。先是市领导讲话,然后分别介绍到场嘉宾。省内外重量级的音乐家悉数到场。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走路颤颤巍巍,还是我和另一工作人员给扶进去的。出来后,负责人和我们说,这位是全国顶尖的音乐家,绝对是大师级别。先是一通轰轰烈烈的交响乐。不知为什么,我怎么都听不进去,两耳嗡嗡嗡嗡响个不停。于是,我慢慢向门口移动,准备到外面透透气。拿起桌子上的水,咕噜咕噜喝不停。渴倒是不渴,就是口干得要命。
果然,耳朵里的嗡嗡声在逐渐散去。听到了忧伤悲痛的琴声,我笑自己,竟然出现这样的幻觉,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可琴声却声声入耳,我想,即使就是真有人在拉二胡,那世间也不只有他会拉,说不准是其他人在拉呢?我也多次问过自己,他就是个路人,何必如此挂念?社会上这样的人多了,就算这辈子什么事不干,专门帮扶也帮扶不过来。这时同伴站在门口喊我,说,在想什么呢?我喊你那么多声,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不想解释,直接说,怎么了?同伴说,那个重量级人物要出来,我们得去搀扶。我赶紧跟着进去,小心翼翼地扶起老人家,问去哪里?秘书也跟着。他嚅动着嘴,音乐声太大,干扰得听不清楚。只好扶着出了门再听。
出了门,我又听到了那熟悉的琴声。老头立住,推开我们,依靠在护栏上,闭上眼睛,头仰向天空。像是在享受着什么东西的浸润,沉醉不已。我们迷惑不解,站在边上反复思索眼前人的意思。老头说,听到没?秘书说,什么?胡老。同伴跟着发出相同的疑问。我猜测地说,琴声?老头得意地点点头。示意我们搀扶他到琴声的发源处。我心里嘀咕,难道不是幻觉?琴声是真切的?那就是说他回来了?我满心期望。琴声离我们越来越清晰,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他盘腿而坐,胡筒搁在膝盖上,眼睛闭着,忘乎所以地拉着曲子。就在墙后面。我们往前走,试图从前面的出口出去。忽然琴声消失了,我们几个立在出口,四处张望。老头说,肯定在,就在不远处,仔细找。我前后左右仔细搜寻,并没有发现我所想见的那个人。左边是排门面店,前面是马路,边上坐着些斗鸟下棋玩牌的老人,我挨个看过去,没有。后面是工地。右边是修车洗车的地方。许是我们出现了幻觉。但对于一个大师级的音乐家来说,应该分得出什么是幻觉。
秘书看久久没有琴声响起,只有无数的嘈杂声,就说,胡老,我们回去吧。老头严肃地说,用心听,这是真正的高手。同伴对我笑,我明白其中的意思,是对胡老执着无奈。我听到了,胡老抬起手指着前面,说,就在前面的某个角落。我们往前走,在两百多米的一个巷道里,有个避风的拐角,阳光正好照上。是他。他坐在石头上,腿撑着地,胡筒搁在膝盖上,身子绷直,眼睛闭着,入情地拉着。秘书想上前问候,老头快速拦挡住,差点摔倒。边摇着头,边示意千万不可,坐在边上废弃的水桶上认真地倾听。这才多长时间没见,他却憔悴了不少。几簇头发飘荡在眼前,干枯的双手灵活地使着,身子随琴声而动。琴声如山涧的清流,从高处悄声流下,和花草的嫩芽亲吻,和树根盘绕缠绵,和光润的石头交心。慢中有快,快中有慢,琴在手中又似手在琴中。太阳从林间照下,投下斑斑点点的光芒。鸟儿叫,虫儿鸣,兔儿跑,猴儿蹿。琴声止,胡老起,上去恭敬地鞠躬,口中言语着,好一派自然景象。琴即是人,人即是琴,人琴合一,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才是真正的音乐。绝也绝也。高人也高人也。他睁开眼睛,看到胡老给自己鞠着躬,立即起身去扶,连说不敢不敢。
胡老说,大可使得。
他看到我,笑着说,那天走得急,没顾上告别。
我说,不要紧不要紧。从他的话语及笑容里,我看到了天上的云彩,不再郁结不再沉重。他拾掇东西,准备离开。
胡老说,老师,能否邀请您到里面演奏一曲。
他背上二胡,拉起皮箱,真诚地说,我该回去了。
我说,去哪里?
他说,去该去的地方。
胡老没强留,望着远去的背影,走到他坐过的地方坐下,闭目不言。恍然想到什么,惊得合不拢嘴,口里念叨着,原来他那只按弦的手是坏死的。后来从音乐厅出来好多人,胡老忘却了所有,静静地享受着那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