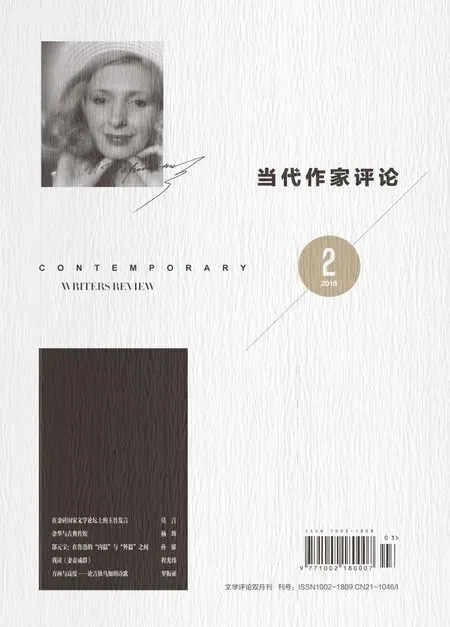近十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的传播
郑英魁
随着中国与俄罗斯往来的日趋深入,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经贸、文化和教育各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尤其是近十年来,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兴趣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饮食、服装、丝绸、工艺品、中医、武术、戏剧上,逐渐扩大到政治、文学、文化等方面上来。他们开始研究中国所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因素,并十分渴望走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潜入其心灵深处,了解其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教育文化、社会政治、外交政策等多个层面。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就是明证。近些年来,有不少中国当代作家名字为俄罗斯人所熟知,如王蒙、冯骥才、刘心武、莫言、余华、贾平凹、金庸、毕飞宇、格非、马原等。他们部分作品被译成俄语,在图书市场上销售。喜欢中国当代作家的人群增大,阅读和欣赏其作品渐已成为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对文化底蕴深厚的俄罗斯民族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一、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传播受关注的原因
摆脱信仰危机。俄罗斯是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它人口最多,土地面积最大,是原苏联的主体和代表。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不景气、物资上的缺乏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更大的困惑是信仰危机、思想迷茫、精神萎靡。已经实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制度和马克斯列宁主义思想及各种思想道德行为规范一夜之间都被废弃,这像锥子般地刺痛了每个俄罗斯人的心。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会解体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埋怨、示威、游行都无济于事,甚至俄罗斯人开始去祈求上帝。然而,宗教信仰并没有真正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此,很多俄罗斯人开始怀念原有的社会制度。自然而然,也开始关注他们的邻邦中国。中国的社会制度没有变,可人民精神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些对于热爱读书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极力地想从中国当代文学中得到启示。
了解中国现实社会。是什么让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什么中国在世界各国有那么多朋友?为什么中国的反腐败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中国改革开放有哪些经验可以值得借鉴?诸如此类的中国现实问题,俄罗斯人都渴望从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找到答案,从而挖掘中国人的思想根源。俄罗斯心理学博士研究生亚库波夫(Якупов П.В.)2016年12月14日在网络杂志《科学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俄罗斯和中国民族心理特征、公共文化特点及公务文化中的相同与差异》的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首次提出了“公务文化”和“社交文化”的新概念,并详细阐述了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不同民族在参加公务和社交活动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思维方式和道德理念。他说:“中国人的道德观是热爱劳动、谦虚谨慎、服从领导、有获得感、有忍耐性、懂得珍惜、尊重和报答。‘友善’是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它体现在他们参加社会活动,甚至经商活动中。中国人的意志坚强在于他们的理想是‘人定胜天’,也就是说,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目标,而不相信命运、天命、上帝。”这是一个年轻学者对中国人先进思想、道德理念的接受。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同时,传递着人们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观,这是中国当代文学送给俄罗斯人的精神食粮。
莫言获诺奖的影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和传播在俄罗斯开始不断升温的原因还来自多数普通人的好奇心,这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不无关系。虽然俄罗斯人对诺贝尔奖并不陌生,在其历史上先后有20多人获此殊荣,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有5人,但他们依然对每位获诺奖者十分关注,其中也包括中国人。这并非是俄罗斯人都喜欢上了莫言,而是想通过对其作品的阅读,了解他所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中国社会。2012年莫言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在俄罗斯引起了极大轰动,特别是对于那些喜欢研究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但又徘徊不定,不知道从哪儿入手的人来说,其兴奋的心情,好比是意外地找到了一把能够打开中国人内心世界大门的“金钥匙”。所以,就在莫言获奖公布的当天,所有俄罗斯书店里有关莫言的书籍便被一抢而空。一时间,莫言在俄罗斯变得家喻户晓,同时也在俄罗斯掀起了一股大众对中国当代作家感兴趣的热潮。阅读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观看中国当代电影和戏剧的人骤然增多,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的译介和传播开始盛行,其声誉也日渐攀升。所以,在俄罗斯本来已经开始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热的基础上,莫言获诺奖又助推了这股热潮的提升,可谓火上加柴,又添新燃。
二、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的传播途径
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俄译纸质版本。纸制版本译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是中苏有计划传播阶段。苏联未解体前,中苏双方按照合同有计划地在俄罗斯和中国出版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俄译本,最早版本是1983年由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以刘宾雁的小说《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为书名的选集,其中有王蒙的《蝴蝶》、刘心武的《如意》。1985年由俄罗斯虹出版社出版了汉学家李福清主编的、以谌容的《人到中年》为书名的小说集,其中有王蒙的《杂色》、冯骥才的《啊!》、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1986年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路遥的小说《人生》。1987年俄罗斯虹出版社出版了李福清的《冯骥才小说选》,其中有《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和《神鞭》。1988年该出版社出版了《王蒙小说选》,其中有《活动变人形》、古华的小说《芙蓉镇》。这些是中国早期当代作家为俄罗斯人所熟悉的作品。1988年《王蒙小说集》和《中短篇小说集》俄译本在中国问世,其中王蒙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冬雨》,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这里有黄金》《班主任》等,是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并推介到苏联。
第二是中俄无计划传播阶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再履行前苏联的合同。所以,从苏联解体后至2005年大约15年里,几乎没有中国当代作家的新作被译成俄语在俄罗斯出版。即使有,也是前苏联时期的再版。我们在阿姆法拉出版社只找到两部与中国有关的长篇小说:一部为《高兴与成功的俱乐部》(2007年),作者是美籍华裔,女职业作家,真名唐艾米(Тан Эми,1952年在美国出生),她就是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山楂树之恋》小说的作者艾米。另一部小说名为《女皇传》(2008年),作者俄语音译名字为Мин Анчи,从汉语音译而成,有关作者的信息书中和出版社均未提供。
第三是中俄有计划和自主传播阶段。2003年普京执政以后,中俄文化交往开始步入正轨,特别是从2006年至2008的八年间,两国互办国家语言年。据俄罗斯青年汉学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副主任,孔子学院院长罗季奥诺夫(Родионов 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副教授2014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俄文学名著翻译国际研讨会”上介绍,在此其间共有12部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俄语在俄罗斯出版。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两部长篇小说《酒国》和《丰乳肥臀》的俄文译本先后在俄罗斯阿姆法拉出版社出版。不久,中国一些其他当代作家作品开始在俄罗斯逐渐传播,如:2014年俄罗斯文本出版社出版了余华的《十个词里的中国》,其另外三部长篇小说《兄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在该出版社出版。之后,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生死疲劳》《师傅越来越幽默》,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也相继在俄罗斯出版。2016年俄罗斯文本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隐喻类型:当代中国散文和随笔》文集,并在该出版社网站上发布。
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传播的次要途径是网上电子版本。从2006年中俄两国开始互办国家语言年始,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的传播量明显增加,主要是以网络传播。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开办了一个学术互联网,在这个网上可以获取在俄罗斯的各类学术信息,其中也包括中国当代作家方面的。俄罗斯人在网上读到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如:苏童的小说《米》《妻妾成群》;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浮躁》《秦腔》和《废都》;金庸的《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李敖的《李敖大全集》;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马原的《纠缠》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据该网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俄罗斯各大书店里出售的有关中国的俄文版各类图书至少有300多种,中国当代文学的俄译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2017年5月16日中国“沪江俄语网”从俄罗斯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网上转载了陈应松的小说《巨兽》和以韩少功的短篇小说《第43页》为名的小说集,该书共收入26部21世纪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并都获过中国文学奖项,所写作题材与中国传统文学有所不同,作者的年龄都在35-40岁之间。在俄罗斯人看来,这些年轻作家的世界观和创造力的形成刚好与中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相吻合,是全球新思维化进程的组成部分。
三、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传播的感兴趣焦点
俄罗斯人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兴趣焦点是以年龄为界线,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经历的人,关注点不同:
俄罗斯老年人的兴趣焦点。俄罗斯老年人,特别是那些出生和生活在原苏联的老年人,十分推崇和喜爱中国当代文学中直接描写爱国主义、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和爱憎分明题材的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及张艺谋根据该小说导演的同名电影(该电影于1988年获第1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王蒙的《青春万岁》和黄蜀芹根据同名小说导演的电影(该电影于1984年获苏联塔什干国际电影节纪念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从中找到了与苏联文学和电影作品中的很多相同之处,就如同高尔基(А.М.Горький 1868-1936)的《海燕之歌》,奥斯托洛夫斯基(А.Н.Островский 1823-1886)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在激励和鼓舞着他们前进一样。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留给俄罗斯人的记忆是无法抹掉的,就像他们所相信的西方宗教那样:“人虽然死了,可是灵魂还在”,这样比喻他们对苏联的怀念,再恰当不过了。
俄罗斯中年人的兴趣焦点。俄罗斯中年人,那些生长在后苏联时代的人,似乎不像长辈那样生活,愿意过比较安逸平和、悠闲自在的平淡生活,说到阅读,喜欢读休闲娱乐性的书籍,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尽情地欣赏男主人公郭靖背负着家恨国仇闯入江湖,并在红颜知己黄蓉的帮助下,通过无数艰难困苦的历练,终于成为“侠之大者”的民族英雄的武林故事。他们还特别喜欢温键键的言情小说《成龙传》(200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获金马特别奖),这源于他们看过很多成龙主演的香港武打片,因为这些电影为他们消除疲劳、减轻工作和心理压力,快乐健康地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俄罗斯年轻人的兴趣焦点。俄罗斯年轻人,多是苏联解体后出生的,喜欢阅读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流派文学,如:格非的《山河入梦》,是其《江南三部曲》(2015年获第9届矛盾文学奖)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马原的长篇小说《纠缠》(2013年出版)。余华的小说《活着》(张艺谋根据该小说导演的同名电影于1984年在47届嘎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此外,俄罗斯人还通过读余华的小说《十个词里的中国》,从十个主题词中捕捉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信息。总之,当今俄罗斯的年轻人,比较喜欢读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他们认为,这些文学很“接地气”。
四、中国当代作家被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热点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有的作家已经成为俄罗斯学者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研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有人研究莫言,主要是研究他的文学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人物描写手法等。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被俄罗斯文学家认可,源于他的小说《酒国》,正如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酒国》的译者叶果罗夫(Игорь Александр Егоров)在他2014年出版的学术专著《诺贝尔获奖作家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一书中所说:“应该指出,在中国文学中,尤其是在莫言的文学中,自然主义流派很常见,甚至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也把莫言的写作方法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如果让我翻译,我就译成‘令人震惊的现实主义’或‘非同寻常的现实主义’,总而言之,它是十分接近自然主义流派的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
俄罗斯作家帕谢奇尼克(Е.Пасечник)于2013年在《文学问题》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莫言:初次艺术手法的认识》,谈到莫言小说《酒国》和《丰乳肥臀》时说:“莫言的《酒国》的艺术手法的确是魔幻现实主义(маг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说到汉字,他风趣地说:“我看了《酒国》后,才知道汉字可以做游戏,汉字‘美’可以与‘酒’搭配成‘美酒’(мэйцзю),还可以和‘元’搭配成‘美元’(мэйюань),通过翻译我们知道了‘美’的意思是‘漂亮’(прекрасный)。”说到莫言文学对世界的意义时,他引用了基普林(Редьярд Киплинг)的话说:“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就是东方,他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合二而一。”这表明了他对东西方文学的态度。说到对小说《丰乳肥臀》的读后感,他颇有感慨地说:“中国妇女,真善良,真纯朴,真勤劳!”
研究余华所代表的中国“先锋派”。有人研究余华,是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最新创作手法,捕捉中国现实社会的真相,了解中国“先锋派”作家的命运。莫斯科大学女汉学家徳列伊兹涅(Ю.А.Дрейзне)教授从2006年开始系统研究余华,她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学报》和《圣·彼得堡大学学报》《远东科学院杂志》上发表过有关余华的研究论文7篇:《余华小说:命运三部曲》《余华小说:叙述结构》《中国当代作家余华的暴力观》《余华长篇小说〈兄弟〉中的可笑世界》《余华创作中的先锋文化基本点》《余华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死亡主题》《余华和索罗金(Владимир Сорокин)的后现代主义之导体成份》。她的博士论文题为《余华的散文艺术概念》。这些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对俄罗斯人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思想意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西方哲学体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等。总之,要寻找某些存在主义的真理,历史的真实性,尝试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观念,构建作者本人的文艺世界核心。”
文学研究者泼楚兰(Поцулан Окса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在《俄罗斯远东研究院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中余华长篇小说〈兄弟〉文艺特色》中说:“余华的艺术创作手法是从一种社会环境脱离开后,但又尚未适应另一种社会环境,与现实相对抗,但又不接受过去文化格局的过渡时期的文学创作。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出版以后,很长时间无人问津,是作者典型的过渡时期作品。余华小说的主要问题是破坏了‘文革’时期的价值体系,这种破坏性创作手法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精神危机的原因。余华利用文化狂欢的现象反射当时中国社会被颠覆的道德准则,遏制不住的淫欲和道德败坏。在这个狂欢现象里‘光头李’和‘流氓宋’恰好扮演了被取乐者和骗子的角色。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发生在一个小镇‘刘镇’,这个小镇的外貌是对当时中国社会认识的窗口。毫无疑问,‘文革’时期发生的事与中国现时社会产生了冲突,并通过所发生的事情,将两个时代连在了一起。余华小说《兄弟》明确表明,人已经到了失去理智和自身毁灭的境地。”
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群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一部分人普遍研究中国当代作家,是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找到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与人交往、语言交际和行为表现的方式,总结俄罗斯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构建各个领域中俄罗斯与中国最合理的人文交往和外交策略。正如中俄关系研究者亚库泼夫(Якупов П.В)所说:“目前中俄关系进入了新水平,在世界上最近发生了很多社会政治事件,这些事件都是俄罗斯自己要单独面对的很复杂、很新、很尖锐的地理政治问题。俄罗斯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需要寻找与合作伙伴合作的新途径,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来说是利益共赢的,这不仅体现在物资和原材料的贸易方面,还体现在相互技术交流及合资企业的建立等方面。今后俄中双方还应该重视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研究。”
还有一部分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目的是了解中国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新观念的产生、变化和形成。研究者齐比科娃(Цыбикова Валенти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在学术专著《中国诗人海子的浪慢主义创作成分》一书中说:“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很多著名天才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80年代有大量作品出版,年轻诗人海子(真名查海生1964-1989)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中国传统诗歌作品带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色彩和异国风情情调。”
五、结束语
以上概述了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传播的现状,尽管近十年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译介不容乐观,还存在诸多问题。
传播数量少。笔者查阅了俄罗斯国家级文学专业双月刊《文学问题》(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3-2017年)的全部内容,在每期都有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专栏中,没找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作,所刊登的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及其他语言的译作都比较常见。只找到了5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克拉斯诺娃(Г.Краснова)的《托斯托耶夫斯基与中国》(1999年第1期);戈尔拉诺娃(Н.Горланова)的《两个中国手提包》(2001年第3期);Чжэн Ян(汉俄音译)的《士兵的长篇小说和战争的真理》(2011年第6期);帕谢奇尼克(Е.Пасечник)的《莫言:初次艺术手法的认识》(2013年第5期);张建华(Чжан Цзяньхуа)的《颇有争议的后苏俄散文美学》(2015年第4期)。笔者还查阅了2014—2017年间同为俄罗斯国家级文学专业月刊《星》(Звезда)、月刊《旗帜》(Знамя)、月刊《人民杂志:长篇小说报》(Народный журнал:Роман газета)、《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月刊《中小学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школе)、双月刊《新文学评论》(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月刊《俄罗斯言语》(Русская речь)的全部内容,均未找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作,所刊登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的译作居多,也有少量爱沙尼亚语译作。只找到3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娃罗金娜(А.Володина)的译文《俄罗斯中国移民的价值体系》(从作者Mark Gamza的英语译成俄语;2014年《新文学评论》第127期);Ван Лие(汉俄音译)的《М. Ю. 莱蒙托夫在中国的翻译:传统、学派和方法》(2015年“俄罗斯文学”第3期);鲍里斯·科雷马金(Борис Колымагин)的《具有广泛传播和影响力的中国长篇诗歌主题》(2015年“新文学评论”第135期)。可见,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大众文学刊物上还没有立足之地。
传播速度慢。说到中国当代作家对外传播的速度,与西方相比,俄罗斯人接触中国当代文学的速度还相对缓慢,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的出版者和翻译者对中国当代作家缺乏了解。正如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叶果罗夫(Игорь Александр Егоров)所说:“前些年,中国当代文学被译成俄语数量有限,主要是满足少数业内人士的兴趣需要。现在情形有了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专业翻译家翻译后,再经过商业出版。相应而言,是满足市场需求和保证卖钱额。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多数是先被译成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欧语言后,再译成俄语出版。职业翻译者和出版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大体上是相同的。因为出版者不了解中国作者,不想去冒险。如果一旦他们的书被出版,按照常规,还怕遭到双方批评家的批评。除此以外,在俄罗斯主要出版来自西欧语言的翻译作品。出版者认为,翻译汉语成本高,甚至有人建议,将中国文学,从已翻译的英语中再翻译成俄语。”
叶果罗夫所说的情况属实,给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传播造成了时间上的滞后。如果一本书在中国出版后,被译成英语再出版至少需要2-3年时间,如果再译成俄语还需要2-3年时间。
传播质量差。中国当代作家在俄罗斯传播不但数量少,速度慢,质量也较差。主要是俄罗斯从事汉语翻译工作的人手不足。在俄罗斯从事汉语翻译的人多是老汉学家,他们多数年事已高。懂汉语的年轻人数并不少,但是他们大多不愿意当汉语教师或做职业文化翻译工作,因为收入偏低,不如做贸易翻译或自己开设公司赚钱多。中国国内的俄语工作者数量也不少,但是他们中大多也不愿意从事俄语翻译,尤其是文化类的翻译,赚钱少。在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翻译作品不被重视,有的单位还不把其视为重要科研成果。目前所翻译的中国当代小说俄译本,大多比较粗糙,质量欠佳,在译作中出现的问题很多:有的是错译,有的是意译,有的是注释译,有的是编译,其结果都会使读者不能完全了解作品的真实内容、真实艺术风格和修辞手段。这也是中俄两国翻译标准应该进一步规范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原因都是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传播的客观因素。因此,要使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入俄罗斯,并使其快速得到传播,必须在中俄文化交流中建立一种合理、合法、切实可行的机制,如建立中俄当代作家交流平台,定期召开中俄当代作家学术研讨会,成立中俄翻译联合会,制定俄汉和汉俄翻译标准,制定译审制度,将翻译工作纳入国家对俄文化交流计划等,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中所存在的困难,从而保证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快速和有效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