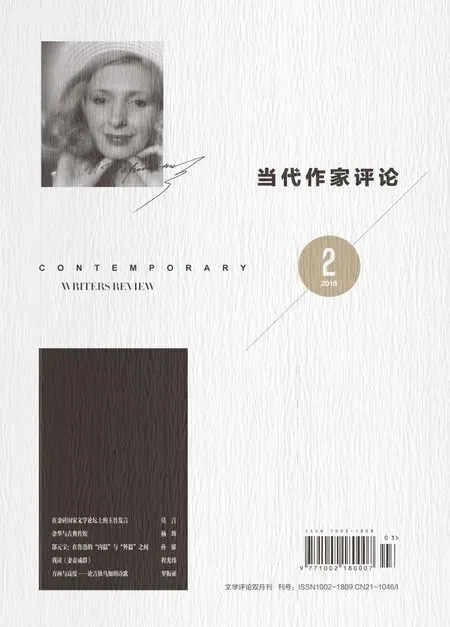跨界诗歌:逾越后存在的问题
——兼谈消费语境下诗歌的姿态
邱志武
近年来,跨界诗歌成为一种新的诗歌现象。跨界诗歌,简言之,就是诗歌跨越自身的边界与其他艺术元素进行融合而衍生出一种新的艺术。也就是说,诗歌的跨界使诗歌“混搭”了其他艺术元素,诗歌变得不“纯”了。就目前来看,诗歌与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融合主要有四种方式:一、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众多摇滚乐和民谣歌手将诗歌进行弹唱,演奏出新的“艺”境。如海子的很多诗歌被民谣音乐家谱成曲子进行诵唱,周云蓬是近年来在诗歌和音乐两个领域“跨界”最为活跃的实践者,他的《不会说话的爱情》把“诗”演奏成了“歌”。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并非为中国所独享,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发广泛影响,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音乐人鲍勃·迪伦,对诗歌与音乐的结合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答案在风中飘荡》广受欢迎。二、诗歌与戏剧的结合。假以戏剧的形式,灌装诗歌的内容和精神,如1990年代于坚的《O档案》由牟森导演进行操盘,在海外公开演出,又如瓢虫剧社以吕约的诗歌《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为蓝本创作出了《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三、诗歌与电影的结合。这种结合形式很灵活,一方面,通过“众筹”方式在影院上线,前段时间一度热播的《我的诗篇》即属此种;另一方面,影视传媒公司将经典的中国现代诗歌拍成微电影,在电视屏幕、视频网站进行播出。四、诗歌与音乐、舞蹈、戏剧的结合。从容是跨界诗歌的积极实践者,她在深圳创办的“第一朗读者”是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其融原创演诗、原创唱诗、原创写诗为一体,向社会大众尽情地展示‘诗悦读、诗剧场、诗现场、诗聚焦’。”
不可否认,在一个消费和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跨界诗歌的出现,确实使清寂寥落的诗歌变得热热闹闹,吸引了众多的眼球,给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增强了诗歌的“收视率”,众多批评家对跨界诗歌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的还称之为“新世纪诗歌的新范式”。然而,在我看来,诗歌的跨界在热闹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重点讨论诗歌跨界后与舞台艺术的结合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引发的对消费语境下诗歌姿态的思考。
一、诗歌跨界中的误读
诗歌跨界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以诗文本为依托,对诗文本的内容进行再创作,融以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元素,实现诗歌的跨界。譬如,“第一朗读者”的诗歌沙龙,其活动的内容就涵盖了“小剧团对于所选诗歌作品的诠释性主题演出”,以及“音乐人对于主题性诗歌作品的现场演唱”;又如2010年创立于北京的民间独立戏剧团体——瓢虫剧社以诗人吕约的诗歌《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为底本,结合诗歌、戏剧、现代舞、音乐等,创作出第一部诗歌剧场作品《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这部作品在舞台上对诗歌进行了全新的演绎,堪称一部典型的跨界诗歌。跨界诗歌必须要具有诗的因素,跨界是手段,诗歌才是目的,这样才能称之为跨界诗歌。郭小川创作的《一个和八个》,由第五代导演张军钊根据其诗文本拍摄成了同名电影,这种情况已经脱离了跨界诗歌的本体意义,不能称其为跨界诗歌。跨界诗歌本质应该还是诗,其他的元素与媒介只是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嵌入诗歌中,也就是说,跨界诗歌是有一定边界的,一旦完全跨越,那么诗则变成非诗了。
在探讨跨界诗歌的误读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同一文本基础上生成的阅读体验能否产生“共识”?不同的读者由于人生历练和文学体验不同,面对同一文本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但是,这种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是建立在物质性“文本”基础之上的。对读者来说,从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体验到的那种沉抑顿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徐志摩飘逸空灵的《雪花的快乐》中产生同样的感觉。这样看来,文本传递的内容存在一个“定量”的问题。“一个比喻往往有许多可能的意旨,特别是在诗里。我们解释比喻,不但要顾到当句当篇的文义和背景,还要顾到那比喻本身的背景,才能得着它的确切的意旨。见仁见智的说法,到底是不足为训的。”朱自清从解诗角度强调诗是有其确切的意旨的,必须尊重作品的客观意义,不能随意解释。
但是,这种“定量”在读者那里发挥作用时会发生变化,这也就是接受美学所主张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这里面存在不存在误读呢?有人认为,文学无所谓误读不误读,如果读者能够结合自身的阅读体验带来审美愉悦,那么文学就完成了其艺术使命。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也存在一定问题。文学是创作者呕心沥血凝练而成的,其中隐匿着创作者的智力、情感、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传播过程中既传递着创作者的审美感受与审美体验,也传递着创作者的审美理念和审美价值。实际上,诗歌在与世界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其能指的空间十分广阔,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如果读者不解“其味”,就会造成误读。李轻松在一次研讨会中说:“我不想看到朗诵者面无表情地拿着诗稿说出来,包括一些著名的朗诵家,都是装腔作势的,几乎不用去看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想象出这个样子来。”她表达的是自己的诗歌没有被朗读者领悟而遭际误读的无奈。对于朗读者来说,由于理解不到位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会存在该悲伤的时候没有眼泪而该喜悦的时候没有微笑的状况。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诗歌批评逐渐出现了缺席的境况。有些批评家倾向于用惯性思维和国外的诗歌理论,甚至用国外滞后的诗歌理论做指导来进行诗歌批评,导致诗歌批评变得有些僵化,存在着误读和隔靴搔痒的情况,而不能深入诗歌的灵魂进行解读,为此很多诗人自己站出来做诗歌批评。那么,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既然诗评家对诗歌都存在着误读,何况普通读者呢?
对文本的误读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夸大了诗歌表现的内容,二是缩小了诗歌表现的内容,三是发生了“错位”,该扩大的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该缩小的没有缩小反而进行了延伸。无论是哪种可能,其结果都是造成了诗歌的误读。由此可见,诗歌从“文本—读者”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理解,正可谓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所言:“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诗歌的理解,原本应该存在“原点”的解释,但是由于读者的理解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
跨界诗歌在实现跨越的过程中,由“文本—读者”的二维链条变成了“文本—跨界诗歌—读者”的三维链条,事实上,由“文本—读者”存在着一次误读的可能,而由“文本—跨界诗歌—读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二次误读。在这一过程中,“量能”的传递必然会发生相应地变化,或者是丰富了或者是缩减了,很难实现“原汁原味”的传递。西川在接受马铃薯兄弟访谈时指出:“一年前我还看过另一位年轻导演导的海子的《弑》,也让我觉得其中有很多问题——有些是海子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导演和演员的问题,甚至是舞美的问题。”西川这里所说的“海子本身的问题”,是指《弑》这部诗剧自身的问题,西川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看到了这种“转换”过程中“导演和演员的问题”,甚至是“舞美”也存在着问题,虽然说西川没有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问题,事实上什么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西川指出了《弑》这首诗剧由文本搬上舞台所带来的二次误读,导演和演员对《弑》的理解与《弑》本身的具体所指出现了偏差。那么,舞台上的《弑》带给观众的审美体验,还是海子的《弑》所要彰显的吗?可想而知,《弑》这部本身带“伤”的诗剧,搬上舞台后给观众所带来的审美感受和体验与原作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
诗剧《向日葵》的导演张旭说:“在三个小时之内,要把这一切表现出来,是有很大难度的。我们的音乐其实是和诗剧密切相关的,要在尊重观众的观赏心理和观赏极限的前提之下将这些东西很好地整合,就必须有必要的调整。”导演把诗文本搬上舞台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演出时间、还要考虑到观众的观赏心理,受此种种条件的限制,搬上舞台的诗剧怎能不出现对诗文本有意或无意的错位“误读”呢?更为重要的是搬上舞台演绎的诗歌,可能只是导演“眼”中的诗歌,无论导演的技巧多么高妙,水平多么高超,境界多么高深,可能仅仅展露出作者所表之冰山一角,而冰山下巨大的冰体却被掩盖了。
二、跨界诗歌的代价
诗歌跨界的另一种方式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融合其他艺术元素,实现诗歌与其他艺术的有机结合。下面我们来探讨诗歌创作中的跨界,或者说原创的跨界诗歌。所谓原创跨界诗歌,就是作者不经诗文本改编,而直接进入跨界诗歌的创作,像“第一朗读者”创办者从容曾经尝试的:“(每场活动)推出原创‘唱诗’音乐作品70多首”,原创的跨界诗歌关键在于“原创”。
海德格尔说过:诗与哲学是近邻。哲学以其深邃的思想性著称,诗歌虽然不像哲学那样去探索真理,但是诗歌是以诗的方式与灵魂进行深层次的对话,这种对话体现着人类对于宇宙奥秘的探知。“诗歌是一种神圣的宗教,是诗人的精神家园,它要求诗人付出绝对的虔诚。那些坚守的诗人都视诗为生命意义的寄托形式,把诗供奉在心灵的殿堂,不让世俗的尘埃玷污;他们用生命和心血去写作,对每字每句都一丝不苟,绝不敷衍,生怕因一丝的粗心草率而损害了诗歌的健康和尊严;他们虽然置身于物质欲望的潮流中而又能拒绝其精神掠夺,置身于日常生活的诸多琐事之后又能以脱俗的勇气出乎其外,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致力于日常性的生活的提升。”庄严而肃穆、谨小而慎微,这是诗人在面对诗歌时应有的情怀和姿态。但是,跨界诗歌的出发点却与此不同,作者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重点是以舞台的演出效果为指归,将观众在剧场内的赏心悦目作为落脚点,这样一来,诗歌的重心不再是对自身本体进行哲思,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对诗歌造成一定的戕害。
诗歌是一种个人化、私语化的冥思和体验,其最高境界在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王家新所言:“诗歌要达到的,却是某种不可诠释的境界,是写只有诗歌才能写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句式和装饰上的复杂,而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可说;而在语言的要求上,是把生命集中到眼睛中最明亮的那部分,生命的强度与纯粹度由此而生……”诗歌本质上所追求的“境界”是一种不可诠释和不可言说,诗歌拒绝“众声喧哗”的混杂,而诗歌跨界之后出现的“狂欢”效果与诗歌本体是相悖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跨界诗歌存在的面目就十分可疑,既然诗歌是不可诠释和不可言说的,那还有“跨界”的必要吗?
廖伟棠在谈到跨界诗歌给诗歌带来的影响时说:“诗歌本身是语言的艺术,和其他艺术进行跨界的时候,还是要重视本体——语言文字本身。不能说一首诗变成一幅画的图解或注释,或者让一幅画成为一首诗的图解,这都是不恰当的。”廖伟堂的这番话着重强调诗歌不能因为跨界而忽视其语言的重要性。显然,他看到了诗歌跨界后,对语言所进行的粗暴处理。诗歌的语言一旦兑换成舞台上人物的语言和场景的时候,哪怕是成为舞台人物诗一般的语言的时候,诗人在创作过程中那种对“物与词”的追求、体验就会遗失殆尽,因为此时此刻诗歌已经发生了变异。
诗歌是一种想象力的艺术,是心灵的自由翱翔。但是诗歌跨界之后,由于混杂了其他艺术元素,调动了其他器官的参与,结果诗歌对想象力固有的强烈诉求变淡了,诗歌成了“扁平”的艺术。洪子诚指出:“多媒体的视觉诗歌,当然扩大了诗的表现力,开掘被掩盖的潜能;事实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存在互通和互补的可能性。因而艺术门类之间的交往、渗透,总是新锐探索者的着力点之一。艺术分类自然是历史现象,它总是处在变动之中。但这种分类也仍有其根据;设想诗过于倚重视觉图像的支撑,会否动摇我们对语言、文字的信心,削弱、降低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诗歌跨界后,使得对语言、文字的直观感触消失了,对语言、文字的想象力也变异了。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诗歌跨界后表达的内容还是诗意的吗?或者退而言之,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表达出诗意?
诗歌跨界后,对诗歌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或者说,诗歌要为跨界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方面,从诗歌跨界的过程来看,跨界诗歌对于诗歌的表现,有能表现的,有不能表现的,那么不能表现的该如何处理呢?诗歌作为想象力的艺术,在文本中可以纵横驰骋,像庄子的《逍遥游》一样,在神逸、灵动间展示出壮阔波澜,诗歌一旦转换成视觉艺术或空间艺术显现时,诗歌本身的丰富性不可避免地出现遗失,这是诗歌在跨界过程中对诗歌本体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从诗歌跨界的后果来看,一个原本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文学作品经过“跨界”搬上舞台,一经演绎之后,变成一个“固化”的文学形象。这样一来,诗歌跨界造成了对自身想象力的束缚。黑格尔曾经指出:“造型艺术主要通过建筑的雕刻或绘画的外在形象,音乐家则通过集中的情感和情欲的内在灵魂以及其迸发于旋律的音调……诗人所要深入体验的事物在范围上却远较广阔,他不仅要掌握心情和自觉的观念这一内心世界,而且还要替这种内心世界找到一种适合的外在显现,通过这种外在显现,诗比其他艺术表现方式能更充分、更圆满地表现出上述理想的完整体。”黑格尔将诗歌与造型艺术和音乐进行比较,由于诗人要发挥充分的想象力,并将想象力诉诸“适合的外在显现”,得出诗歌是比其他艺术能够表现得更充分、更完整的“理想完整体”。而跨界诗歌则打破了诗歌的这种“理想完整体”,给诗歌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影响了诗歌作为一种“理想完整体”的可能。廖伟棠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诗歌为什么能成为独立并且重要的艺术门类,是因为诗歌永远能说出别的艺术说不出来的东西。诗歌能表达的,音乐都未必能表达出来。”诗歌是最具想象力的、最敏感的,能够将不可言之的东西通过诗的方式呈现出来,能够突破造型艺术的具象局限。即便现代的声、光、电高科技手段如何发达,都不可能对诗文本进行传神的“真实”演绎。对于创作者而言,在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聚焦于跨界后的诗歌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诗歌跨界后如何“大马力”地吸引观众上面,事实上,跨界诗歌在吸引观众的路上走的越近,疏离于诗的本质就越远,如此而言,并非说诗歌与大众是矛盾的,而是说诗歌目前的边缘位置决定了诗歌不可能和大众“亲密接触”,跨界诗歌利用其他艺术元素的这种“吸睛”效果必然会以牺牲诗歌深度为代价,一味地在诗歌上聚集消费、时尚、前卫的信息和元素,一味地在舞台上的造型、声音、光线等上面下功夫,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对诗歌自身造成机械地拆解,这是诗歌跨界给诗歌自身带来的最大危险。
有人认为跨界诗歌和诗歌所追求的跨文体写作具有一致性。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混淆了跨界诗歌和跨文体写作的本质区别。跨界诗歌是用一种外力将诗与其他艺术强行进行捏合,而跨文体写作则是诗歌对于自我综合技艺的提高。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复杂的社会现实,诗人为了在诗歌文本中容纳更多的可能性,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诗人追慕“混合体写作”,诗歌敞开胸怀,面对一切可能。敞开的诗歌无疑拥有了一个好胃口,增强了吞食纳物的能力。王家新说:“一种能够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中,不断地吸收、转化,将各种话语引向自身、转化为自身的写作”。陈东东的《喜剧》将神话、梦幻、现实、独白等混于一起,西川的《致敬》《厄运》等都是诗歌文本复杂化的典型。但需要看到的是,诗歌文本内容的复杂化为诗歌的跨界提供了可能。可以想象,单薄的抒情诗和充满对抗主题的诗歌相比,撑起鸿篇巨制是有一定难度的,即使实现了跨界,可能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吗?
三、诗歌要走向何方
诗歌跨界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提倡者自身的经历、教育背景使然。比如,“第一朗读者”的发起人从容曾是一位戏剧工作者,制作音画诗剧《面朝大海》的屈轶曾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诗话剧《向日葵》的作者李轻松曾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这些经历和艺术功底对创作者的审美趣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廖伟堂所指出的“出于生计的考虑”的原因,“因为一首诗不能卖”,但是跨界诗歌可以走向剧场,走向票房。诗歌跨界的出现可能缘于种种原因,但是吸引大众、摆脱诗歌边缘化位置也是其发生原因之一。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跨界诗歌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诗歌跨界走上舞台,是谋求大众对诗歌进行消费的一种新形式。应该看到,现在批评界对于跨界诗歌的认同或肯定大多是从跨界诗歌与公众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吴思敬认为:“诗剧场这种形式为我们探讨如何结合诗与戏剧开辟了一个很好的途径,诗歌面临着如何走向公众,而一些诗人进行私人化写作,把自己放到一个边缘状态。诗剧场则借助剧场,借助重大题材,让诗面向社会公众,从形式上来说,非常有意义。”敬文东说:“‘第一朗读者’有着神奇的魔力,每个人都是剧中人、都是参与者。在这里,诗歌也好、戏剧也罢,都能使观众获得艺术享受。”冷霜则主张:“‘第一朗读者’是在诗歌与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间实现的跨界,而跨界的结果便是营造一个活生生的‘诗现场’……‘第一朗读者’这种跨界艺术形式,不仅有利于提升诗歌戏剧的传播面、大众认可度,也在培育诗歌戏剧爱好者和基础观众方面做着有意的探索。”这些批评家都着眼于诗歌目前的窘境来进行分析,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诗歌极力想提高“收视率”,摆脱“小众”状态,因此在某种程度而言,诗歌跨界的使命在于寻找丢失的大众。那么,诗歌跨界后就能找到丢失的大众么?鲁迅有段话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鲁迅对国人给予深刻讽刺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人具有爱看“热闹”的奢好。凡是只要出现“热闹”,总会不缺人围观。所以,诗歌通过跨界变得热闹了,于是乎围观的人也就多了,诗歌自然也就逐步走向“大众”了。这是跨界诗歌的发生学逻辑。
从跨界诗歌作者的角度来讲,其心理趋向在于改变诗歌边缘地位的窘境,使诗歌回归曾经显豁的影响力。在他们看来,当今消费压倒一切的语境中,音乐可以商业化、市场化,雕像、绘画和电影也可以商业化、市场化,难道诗歌不可以沿此路向趋近商业化、市场化?于是,诗歌与其他艺术元素进行联袂实现跨界,尔后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让·波德里亚认为:“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流行以前的一切艺术都是建立在某种‘深刻’世界观基础上的,而流行,则希望自己与符号的这种内在秩序同质:与它们的工业性和系列性生产同质,因而与周围一切人造事物的特点同质、与广延上的完备性同质、同时与这一新的事物秩序的文化修养抽象作用同质。”这段话一方面很好地揭示出消费对跨界诗歌的催生作用,另一方面则说明了由于消费逻辑的指引使诗歌在走向跨界的过程中变得平庸。但是,应该看到诗歌与音乐、电影等其他艺术的结合,并非是诗歌本身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对商业化、市场化的一种迎合。这样,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任何诗人在写作过程中,“就会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自己的‘产品’能更多的占有市场份额,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的受众群体而非文学艺术品的审美价值,这是在市场经济下文学家、艺术家优先考虑的问题”,为此,诗人不再以追求诗歌的“理想完整体”为指归,而必然是以如何赢得市场、如何吸引读者的眼球为着眼点,诗歌创作者开始集中于观众的耳朵和眼睛上下功夫,造成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诗歌自身的迷失,甚至于让人担心诗歌是否还能进行自身本体意义的探讨?
既然诗歌的跨界带来如此诸多的问题,那么跨界诗歌能否可以回避当下的消费语境呢?事实上,诗歌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一定会与历史、时代、现实发生复杂的关系。应该看到,诗歌与消费联结起来与市场经济的出现关系密切。1950到1970年代,诗歌是带有政治使命的,而这种使命是为了使政权更加稳定,随后,朦胧诗也好,第三代诗歌也好,诗歌的生发语境都不是建立在消费基础之上的。诗歌开始与消费建立联系应该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的。诗歌的消费性不是以换取经济效益为目的,而更多地体现出对大众“眼球”的吸引,一些诗人开始用商业性的思维来“经营”诗歌,在市场经济的包围下,固然存在“饿死诗人”的可能,但也有很多诗人能够在商品大潮中自由地游弋和纵横捭阖,使诗歌在消费语境中如鱼得水,畅快淋漓。
跨界诗歌的问题,说到底在于诗歌在消费语境中不甘于目前的“小众”状况而做出的搏击,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存在的问题很多。那么,诗歌在消费语境中应该如何自处呢?诗歌该走向何方呢?对于诗歌在消费语境中的姿态必须要有理性的考量。诗歌一味地迎合消费,终会因为围着消费“旋转”而迷失自身,从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现实的消费语境中,诗歌又不能回避消费、拒绝消费,同时诗歌也不能迎合消费,显然,迎合消费的后果和诗歌成为政治工具的后果是一样的。诗歌不能让消费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必须在消费语境中保持自身的“矜持”。王家新对诗歌在消费社会中的角色有着精辟的见解,“我们不可能生活在消费社会之外,但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我们的写作,拒绝成为消费的对象,或者说,让消费社会不那么好消费你。”在他看来,诗歌要在消费的张力和空隙中,保持自我的底色。诗歌如若一旦成为消费的俘虏,那么诗歌自身就会成为消费的一部分。诗人在消费时代的使命就在于抵制和拒绝消费的侵蚀和围剿。王家新有一首诗《牡蛎》,“聚会结束了,海边的餐桌上/留下了几只硕大的/未掰开的牡蛎。//其实,掰不开的牡蛎/才好吃,在回来的车上//有人说道。没有人笑,//也不会有人去想这其中的含义。//夜晚的涛声听起来更重了,/我们的车绕行在//黑暗的松林间。”对于这首诗,王家新自己曾颇为得意。在他看来,诗歌最主要的就是对“大时代”的抵制,表现出一种孤绝、傲然的姿态。诗歌不能跟着时代潮流走,要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情怀,而一旦这种潮流无法阻挡不得不迎头面对的时候,要表现出对潮流的拒斥、阻绝和抗议,而决不能成为这种时代潮流的推手。也就是说,在消费语境中,诗人要坚守自己,在时尚潮流面前要反应迟钝一些,不要在追求潮流中迷失自己。诗歌不要轻易地去跨界,而要葆有自己的姿态和品格。正如周瓒所指出的:“诗人中不乏头脑聪明的人,不乏搬弄各种知识进行的发声练习和在纯思辨中获得的取巧回报,可我倒是宁愿写作的人笨拙一点,与随大流的愤怒、怨恨保持距离,更多一些身体力行的执拗。”这是跨界诗歌在逾越后带来的问题给予我们的启示。
诗歌在消费语境中应该展示出何种姿态,罗振亚对新世纪诗歌的期待性评述为我们带来了启发性思考。“我认为新世纪的诗歌如果能够扬长避短,在时尚和市场的逼迫面前拒绝媚俗,能够继续关怀生命、生存的处境和灵魂的质量,坚守时代和社会的良心;同时注意张扬艺术个性,提升写作特别是底层写作表现对象、抽象生活的技术层次,避免在题材乃至手法上的盲从现象,那么目前的困惑与沉寂,就会成为跋涉途中的暂时停滞与必要调整,重建诗歌的理想便会在不久的将来化成现实。”说到底,诗歌不能为取悦市场、迎合市场而失却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应该着眼于人类命运和灵魂的关怀,挖掘自身的艺术特长,并适度合理地融合、吸收、升华其他艺术特质,最终构建出一种新的诗歌姿态和诗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