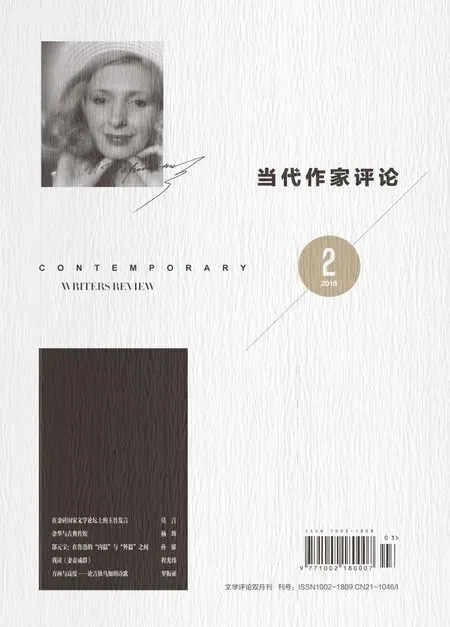自然,人,文学:竞争、疏远还是和谐?
〔俄〕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巴尔梅托娃
(Ир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Барметова)
张 曦 译(海南三亚热带海洋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对这一严肃话题进行简单论述,我只能借用著名哲学家、人道主义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的话来作为我演讲的主题:“我是想活在生命中的生命,我是想活下去的生命。”
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以显而易见的不稳定而著称,而不稳定的自然,即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灾难和其他异常现象,它们正急剧地改变着我们这个星球的形态。
要想不陷入一知半解的神秘论,就应该指出,这种双重的不稳定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可以稍带嘲讽地说,这两种不稳定倒是形成了某种“和谐”,自然和人正携手而行。
当下,作为科学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之结果,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个世界之发展的各种基本走向的反思正在进行。
如今,自然开始被视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诸如生物多样性这样的概念也获得了政治内涵。
当今世界的重要现象之一可以被合理地视为文明和环境的冲突和融合。
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然会出现:文明何时转变为对于自然而言的野蛮?对于新世纪的人而言,创造的能力和意志的自由究竟是一种禀赋还是一种惩罚?物质的增长是否存在边界?
文化逐渐把对自然的态度变成自己的客体,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种人的能动性的文化,或像人们更常说的那样,即生态文化。它的职责是把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评价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并将其纳入文化价值体系。在已经到来的第三个千年,美学和哲学思想以及往日的种种公设是否也会发生变化?文学和作家将在这种变化中占据何种位置?当代俄国文学能否对时代的挑战做出回应?
500年前,意大利人乔尔丹诺·布鲁诺坚信:“艺术可以弥补自然的不足。”
其次,实行物物交换。在上一轮美对伊制裁过程中,伊朗官方也曾表示愿意接受黄金交易,还可采用小麦、大豆以及消费品实现与伊朗石油贸易结算印度就曾经以黄金换伊朗石油。
我们的同时代人、伟大的中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也认为:真正的美是通过对丑的矫正而实现的。
如果以俄国文学为例,我就有理由断言,近10年来所有那些令人不安的事件都“不由自主地”证明着,俄国经典文学仍具有高度的现代性。俄国经典文学展现了恶产生的道德机制,恶在众目睽睽之下占据着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精神领域)。俄国经典文学正绝望地、无望地把我们引向光明的源头。
当代俄国文学也有这种引领愿望吗?
近20年来的文学处于全新的历史和心理环境之中。我们的文学首度被挤出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区域,它不再是民族意识的主导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似乎处在大众文化的边缘,而大众文化宽容地接纳了文学的相对效用。文学的社会潜能急剧降低,自然与传统价值体系的崩塌、统一国家(苏联)的覆灭和帝国意识的危机紧密相连。今天,文学环境由评论家决定,而危机就在于,作家们完全不参与当下的现实生活。
详尽地描写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非常罕见,作家们千方百计地回避当下。俄国当代小说家的研究对象通常要么是历史,要么是未来,即反乌托邦体裁,而且作者还经常陷入危言耸听,即为未来担忧。
一些作家由于无法创造性地指出社会的发展道路,便主动放弃与社会的直接关联,逃往互联网空间。在这个空间,作家们试图用篇幅不大的争论、随笔和杂文来弥补创造性地改变现实的作家义务。但是,互联网空间能提出一个关于现实的文学公式吗?我想,不可能。
这便构成了当代作家与19世纪俄国文学代表之间的一个可悲差别。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除了文学之外,还致力于那些一位作家似乎不必去做的事情,即他们想在艺术和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他们致力于将日常生活与其理想意义联为一体,并把这一意义变成世界性的行为准则。
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变存在的构成,创建新的生活范式。
正因为如此,俄国文学的社会潜能非常之高。在一个国家,在俄国,当公民自由、议会辩论、出版自由、公开的哲学争论、党派斗争等等被取缔时,文学就不得不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所有潜能。
正是文学成了精神的舞台,在这里提出并讨论那些激动全民族的问题。因此便出现了那个著名的诗歌公式:“在俄国诗人大于诗人。”这与我们19-20世纪的文化现实完全相符。而如今,这个公式被改为:“在俄国诗人小于诗人。”
俄国文学先前的地位,亦即它作为民族意识之代表的存在方式,还能“失而复得”吗?抑或说它的这一特征已一去不返,成了当代“进步”文化界里的老古董?
无论多么悲伤,我们还是应当意识到,尽管我们装腔作势地千呼万唤,却离我们民族的源头越来越远。俄国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作家伊戈尔·沃尔金认为,如今我们有很多机会变成第三个千年的希腊人,我们可以为了微薄的报酬带领那些好奇的旅游者,去参观我们曾经辉煌的文化所留下的废墟,参观我们那些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形而上的帕特农神庙,参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遗迹……
这一切取决于社会自身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社会最终选取的价值体系……也许,作家如今已不可能再做出全知全能的言说。
也许,作家如今已不可能再以真理的名义作证。也许,当代人的怀疑精神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他想要他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他得到的却是他不想要的东西。”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作家对这样的人感兴趣吗?这样的人对作家感兴趣吗?
与此相关,我们的社会对作为文学现象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对这一局势产生了糟糕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影响。俄国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单词,之后成为一个概念,指俄国社会中一大批致力于严肃思考生活意义的人,如今,这一概念却被“脑力劳动者”一词所取代,这完全不能表示那个真实存在的社会阶层,之后,“脑力劳动者”这个词又被赋予某种值得同情的意味。
这些问题在世界图景的背景下产生,世界图景中出现了需要深刻思考的新的思想迷雾和不确定性。而在文学中则产生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临界状况:一方面,生活需要并促成对真理的探寻,因为人不可能在完全缺乏真理意义的情况下生活;另一方面,作家们却完全没有做好准备,也不情愿投身这项艰难的工作。
其结果,作家面临一种诱惑,即步入一个隐秘的角落,一个超越历史的纯净思想空间。不同流派的当代文学正在寻觅这类隐秘的角落。
作者和主人公与世隔绝的方法之一,就是自然主义的半乌托邦:奔向自然,为了社会而消失。有一大批作家,对于他们来说,孤独的主题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他们的作品中,主人公孤零零地生活在世界上被遗忘的角落,在那里寻求灵魂的救赎……而恰好在这里,却有陷阱在窥伺着作家和他的主人公。
关于陷阱,莫言警告我们:在混乱和分崩离析的时代,人像鸟一样自由,但事实上,四处等待着他的却是陷阱和网,是猎人的箭和子弹。
当今世界正在巧妙地布下罗网,想捕捉作家,不让他完全沉浸于自然,不让他歌颂自然,歌颂自己的孤独。透过作品的内容,世界的不稳定性、混乱和杂交性无意地、却清晰地表露出来。而读者自己也立即觉察到,自然的生命力、人与环境和谐融合的自然法则、田园诗均不会再出现,也许永远不会再有。
自然对人的激情和灾难态度冷漠,它会给生命教训的总结过程带来益处吗?人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自然是无法“超越”的。要给人类的可能性画上一个清晰的边界,当代作家能够在这一方面给人类以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