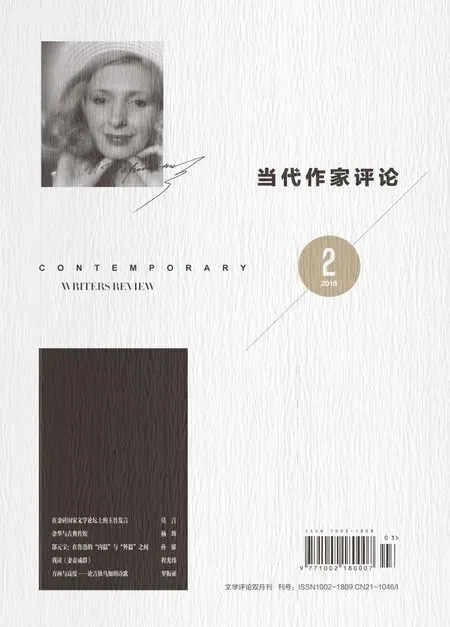你的时代,我的故事
苏 童
各位下午好,为了准备今天的发言,我很认真地写了一个稿子,结果因为太认真,发现写得太长了,所以抛砖引玉,我决定把我文章当中最精华、最好的那部分删掉。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著名的电影《八又二分之一》。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值得我们一再讲述,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导演的故事,也是人生的故事,又似乎是创作的故事。我主观地认为,就连片名也酷,不是装酷,是真的酷,一个艺术家竟然用数字模拟了大的绝望,和小的希望。我这么理解,八是焦虑和混乱,二分之一是诊疗,加起来,八又二分之一是一个人的境遇。这境遇好不好,看数字本身就不言而喻,焦虑和混乱很强大,而诊疗机会小而又小,几乎是可以忽略的。这个数字有悬念,目标似乎是九,对于中国人是完美的数字,又缺了二分之一,这二分之一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或许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
如果我没记错,《八又二分之一》应该是费里尼60年代的作品,电影的开始就充满暗示,有人驾车在公路上遭遇严重的交通堵塞,被堵在路上,不能动弹,结果驾车者从车窗里腾空而起,开始飞行。这是对一个梦的交代,也是典型的费里尼式的对现实生活的应对方式。走不了,我就飞。当然,我也想过,如果60年代的中国观众恰巧看到了那部电影,他们大概不会懂得费里尼的暗示,第一种可能,中国观众们会认为那是胡编乱造,吹牛吧,意大利那种小小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汽车?小汽车与小汽车怎么都不一样?还堵车?第二种可能是,他们羡慕嫉妒恨,那些开车的人都是普通人吗?要是让我开着汽车上下班,那天天堵车也行,慢慢地出发,慢慢地到达,多么幸福啊。
无独有偶,大概是在90年代初期,我看了一部好莱坞电影,请原谅我不记得电影的名字了,只记得电影的主演是小道格拉斯,开始也是堵车,是高速公路上的堵车。电影的镜头与道格拉斯的表演,都非常好莱坞,很直接,很明晰。要知道小道格拉斯与他扮演过斯巴达克斯的父亲老道格拉斯一样,有一个让我们亚洲人过目难忘的下巴,那下巴上一条深深的沟壑,在我看来代表着男子气或者英雄气概,但我很快发现,那深深的沟壑里,流淌的英雄气概有点令人不安,准确地说,那只是一种越烧越旺的惊人的怒火。与费里尼的电影不一样,好莱坞的导演只让蝙蝠侠飞,不会让小道格拉斯飞,他只让小道格拉斯下了车。与好莱坞电影大致一样,小道格拉斯在高速公路附近遭遇更多的愤怒之后,最后拿起了枪,杀了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路怒症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我也还没去过美国,而中国的城市里已经有了很多汽车,我偶尔也会经历堵车事故,已经认为堵车肯定不是什么幸福的事情,尤其是你急着赶飞机赶火车的时候。但我作为一个电影观众的主要反应是:至于吗?堵个车要杀人?杀了人坐了牢,还怎么开车?而我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一方面懂得愤怒的美感,另一方面更习惯于探究愤怒的价值,所以疑惑也不少,这是反映美国现实生活的电影吗?这是一个真实的美国故事吗?这是在控诉汽车,还是在控诉交通?这是在批判物质,还是批判现代文明,或者是在批判被现代文明绑架的人性?但这样的问题,即使我遇见导演,也不会问,因为导演可能会跟我说,随你怎么想,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因为堵车引发的故事。
我再说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电影,不是故事,是真事。恰好发生在我认识的一个意大利朋友身上。我们几个作家朋友在罗马的时候,他的妻子开车接送我们,他从不开车,到哪儿都骑自行车。我们问他妻子,他是不是不会开车?答,会,是老司机了。又问,他是环保主义者?答:不是什么环保主义,因为有一次堵车堵在路上,极其焦躁,极其愤怒,又不想焦躁,不想愤怒,因此他忽然觉醒,就把汽车扔在路边,不要它了,自己徒步回家,从此再也没有开过汽车。
我很抱歉,我自己其实不会开车,却一直在说开车堵车的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文学,我想说,开车开不了,就从驾驶座上飞起来,飞离公路,像费里尼那样解决问题,这其实是文学。开车开不了,气得杀人,像小道格拉斯一样,那是一种好莱坞电影的解决方式,虽然逻辑通顺,但没有人愿意赞同那是高尚的文学,更多的人会像我一样,认为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恰好相反,那就是,我愤怒得想杀人,但我是如何做到不杀人的。而像我的那位意大利朋友,开车开不了,弃车而走,永不开车,这当然更是文学,具有弹性,因为我至今不知道,那样一种觉醒,究竟是幸福的还是哀伤的,是属于抵抗还是属于逃遁,是某种希望还是绝望,当我想象那位意大利朋友骑着自行车在罗马街头的滚滚车流中缓缓而行,我会看见他的T恤衫上的字,也许仍然在为他的同胞,电影大师费里尼60年代的杰作打广告:八又二分之一。当然,也可能,他的T恤衫上出现了更加意味深长的新广告:八又三分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八又二分之一的时代,或者,这已经是八又三分之一的时代。堵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与人,要处置惊慌、疲惫与厌倦,要在愤怒时远离枪支,要在八的后面看见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这更像是当今世界的基本影像,描摹人们的主要处境。文学,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在探讨某种飞行的可行性,以及逃遁的方法。
只不过,飞行的可行性越来越小,逃遁的工具也并不多。请允许我再说一下《八又二分之一》,也透露一下我对这部电影强烈的移情的原因,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移情于电影主人公圭多,他始终对付不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电影中的电影完工后,圭多是被架到记者招待会上去的,人人都在向他提问,他却无话可说,在被别人一再的逼迫下,圭多干脆钻到了桌子下面去。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生活,这一钻钻得观众怜悯心大发,几乎要潸然泪下,在桌子底下,可怜的圭多终于获得了安全。
圭多最后的表白听上去形而上学,其实是形而上学的混乱,他说:“一生的困惑,是我生命的写照。我就是我,但从来不是我想做的我。”
我明明知道圭多式的表白真诚而混乱,钻到桌子底下也是不好的,但我还是热爱这样的表白,甚至热爱钻桌子的行为。是的,也许真是这样的,很多的你和我,从来不是你想做的你,我想成为的我,我们钻到桌子底下才可以坦诚一些,成功太少,失败太多,希望太小,绝望太大。一辆汽车被堵在高速公路上,迟早还可以再走,一个人被困惑和愤怒淹没,应付不了自己的生活,他走不了,飞不了,逃不了,他该怎么办?
我想象这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病症。八又二分之一,我想象那二分之一,才是时代赐予我们的主要故事。当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题目有点自以为是,你的时代,何以成为我的故事?二分之一?谁的二分之一?谁要二分之一?那个八呢,八是怎么处置的,八究竟去哪儿了?是的,我的困惑与所有人一样,甚至我的时代,也不一定成为我的故事。我不知道二分之一将会如何演变,这数字会变小,还是会变大。我们只能尝试。我们尝试叙述,叙述那剩余的二分之一。我们唯一的信念是,当对于二分之一的叙述成功了,我们就找回了那个八,或者,能触及那个完美的九。
我们因此写作。
我始终相信,因为写作,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