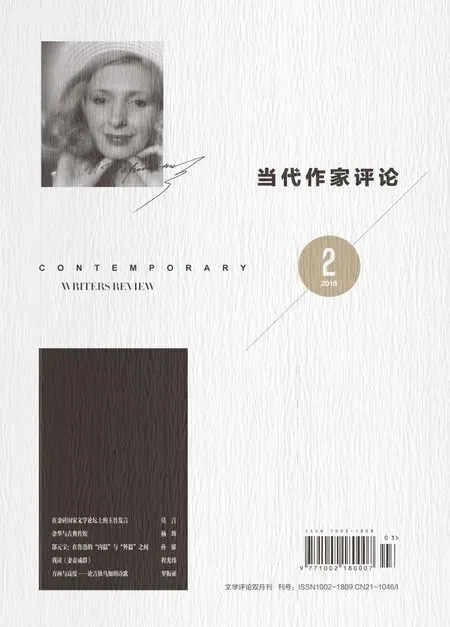在金砖国家文学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韩少功
中国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孔子,在其代表作《论语》第1页,说到他人生中最高兴的两件事:一是温习和运用自己的知识,二是接待来自远方的同道好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在这里参加金砖五国文学论坛,既有学习之乐,又是交友之乐,享受着双重快乐的一个周末。
跨国的文学对话其实很难,比微笑、握手、碰杯、合影留念要困难太多。我们坐在一起,首先有语言翻译的障碍。即便我们都是多语种天才,能用同一种语言直接交流,但受制于不同的知识训练和文化传统、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有时也很难避免隔膜,如同鸡见到鸭时不知该如何说。我们以为讲通了,但实际上可能远未讲通。我们以为没有讲通,但实际上可能早已心领神会。
尽管这样,我们这些鸡啊、鸭啊、猫啊、狗啊今天仍然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有什么理由吗?当然有。我想至少有以下两条:
一、我们都来自新兴国家,都处于一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动荡时代。说到“现代”,欧美发达国家曾是现代化的典范和老师,而新兴国家不过是好学生,最用功的一批学生。我们曾一心一意地学老师们如何吃饭,如何穿衣,如何说话,如何谈恋爱,如何嚼着苞米花看电影和穿上晚礼服看歌剧。但是学生学习,总有毕业的一天,我们除了学习先进的老师,是否还可以相互学习、创新学习?
二、我们都来自艰苦的文学实践,都关切人类最基本、最普遍、最恒久的精神难题。这个世界可以分成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巴西人和俄罗斯人,如此等等,但可能还有一种重要的分类:亲近文学的人和远离文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前者已组成了一个隐形的文学“共和国”,其公民遍布全球各地,以小说和诗歌为特殊护照,无论走到哪里都可找到自己的同胞,找到自己的家园。在这个“共和国”里,时间差异并不重要,比如古人用长矛杀人,现代人用无人机杀人,但杀人就是杀人。在这个“共和国”里,空间差异也并不重要,比如南非人曾用舞蹈表达爱情,中国人曾用绣球表达爱情,但爱情就是爱情。文学这种超级护照上总是显现人们最容易辨认的容貌特征,大大过滤掉时代、地域、宗教、种族、政治、语言等诸多差异,让心灵跨越千山万水,与更多心灵永远地相聚和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