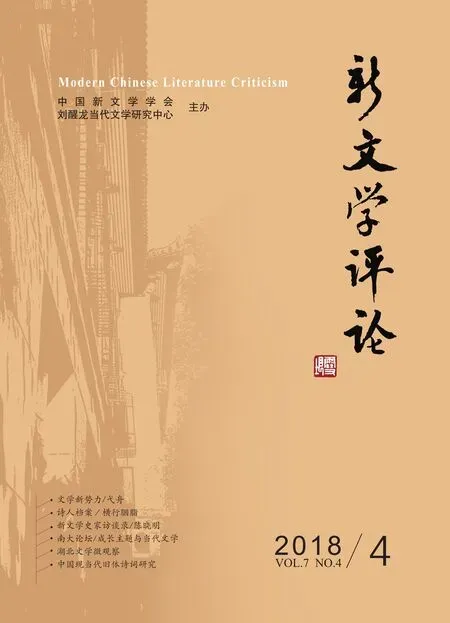架空的畸形成长
———对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的一种反思
◆ 田青艳
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在表现大学生成长问题时,着力描述在校学生畸形成长的状态,却往往因近乎猎奇和模式化的叙写而丢失了真正的现实批判力度。塑造模式化的大学生形象,叙述重点是学生在校期间跌宕起伏的情感经历,结局落在其成长的必然失败上,这已然成为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表现大学生成长问题的固有方式。众多作者在通过这一表达方式显示在校大学生的成长问题时,往往用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夸大、扭曲笔下人物的形象,力图批判现实,反与现实渐行渐远。
从二十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大学的叙事作品(小说、随笔、校史等)应运而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有钱钟书的《围城》、鹿桥的《未央歌》、沈从文的《八骏图》、老舍的《赵子曰》等。陈平原在《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一文中论述了对大学的文学想象与中国大学发展的关系,认为“构建现代中国的‘大学史’,引入五彩缤纷的‘大学叙事’,不只可能,而且必须”。而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进步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大学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必备的人生经历,大学叙事小说从数量上也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由此可见,探讨大学叙事小说的现实意义,是研究大学叙事小说的重中之重。更进一步,我们必须重视其中对在校大学生校园生活的表述,因为“日渐增加的大学生,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终将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
新世纪以来的大学叙事长篇小说,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大学生视角出发叙述在校学生成长,关涉师生关系、校园文化、高校发展的校园青春小说,如李师江的《中文系》(2010年),江南的《此间的少年》(2002年),孙睿的《草样年华 北X大的故事》(2004年)、《草样年华Ⅱ 后大学时代》(2005年)、《草样年华Ⅲ 跑调的青春》(2009年)等;另一类是从高校知识分子的视角展开,透视学术与政治、校园管理、人际关系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如邱华栋的《教授》(2008年),张者的《桃李》(2002年)、《桃花》(2007年)、《桃夭》(2015年),史生荣的《所谓大学》(2009年)、《所谓教授》(2010年)、《大学潜规则》(2010年),朱晓琳的《大学之林》(2007年),汤吉夫的《大学纪事》(2007年),阎连科的《风雅颂》(2008年)等。
本文论及的“大学叙事长篇小说”以大学师生的情感、学术、日常生活为主要叙写对象,展现大学校园众生百态,重视群像而非单纯的个体化书写。因此,许多以大学生个人奋斗历程、情感经历为主线的校园青春小说,以知识分子个人奋斗、情感生活为主线的高校知识分子小说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在从不同角度展现大学面貌时,新世纪大学叙事小说的作者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高校知识分子的权力斗争、拜金风潮、道德败坏等种种令人扼腕叹息的问题,更表现了象牙塔的崩塌,将在校学生的堕落作为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品在描述大学生的畸形成长时,在人物塑造上趋于模式化,更大篇幅描述其情感经历,最后宣告成长的失败。这使得在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中,大学生的畸形成长愈来愈呈现“架空”的状态,鲜有作者真正深入了解了当下学生的生活,其距离感和刻意突出的批判性导致小说流于表面,作者未能找到大学生在当下校园回归正常成长轨迹的方法。
一、 学生形象的模式化
不论是从学生视角出发的青春校园小说还是从知识分子视角出发的高校知识分子小说,其对大学生形象的塑造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已趋同质化。校园青春小说的主角大多都是颓废、“垮掉的一代”的样子,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进入大学后面对学业、情感、事业问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随心随性而行,《中文系》中的“我”,《草样年华》系列中的邱飞同属此类。而在以大学知识分子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小说中,学生虽是配角却仍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符合作者批判大学阴暗面的目的,其行为表现出格之处多令人大跌眼镜,似乎只有将学生形象塑造得愈夸张、愈离奇,才能体现出问题的严重性。
总结来看,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在表现学生的畸形成长时,往往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其一为突出学生颓废迷茫、丢失生活目标的一面,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中文系》中的“我”、《草样年华》系列中的邱飞。其二则突出学生追求个人利益、丧失道德底线的一面,《大学之林》《桃花》《桃李》《桃夭》《风雅颂》《大学纪事》……中都存在这类描写。
在李师江的小说《中文系》中,主角“我”入校不久就发现自己不喜欢学校的教学模式,开始了以逃课、谈恋爱为主题的大学生活。小说中的“我”不能算厌学,作者笔下的“我”对诗歌、小说都有独到的见解,认为“现实中无法找到的自尊,在文字(中)会魔术般变出来;想要逃避无奈,文学为你编个茧子”。但在反抗所谓权威时,他的勇气却没有足够坚实的思想支撑:
“我想要学的是真理,或者如何找到真理,这是老师该启发我们的。但是书上的那些理论不是真理,是迎合,我们学了一学期,即便考了个高分,又有什么用,跟真理一点都没关系。”我豁出去了,说出了心底考虑已久的东西。当然这些话不是我的原创,你在图书馆的许多学者名言上可以找到,只不过我深以为然。
此处,颓废者除了“看上去很酷”之外,尚没有过硬的能力与他自己都不甚了解的大学的权威对抗。更何况“我”也知道反复逃课的自己“不论我讲得多么有道理,多么精彩,此刻都不可能是英雄。我走上前去,然后在同学的惊诧中,昂首挺胸向门外走去,一口气跑回宿舍”。在后续的叙述中,主角虽然了解了青年讲师李向阳苦于职称评定的困难,实际上也只是窥到大学问题的一角。
而在孙睿的《草样年华》系列中,主角邱飞及好哥们杨阳的自我放逐与颓废则更令人瞠目结舌。在邱飞眼中,“学习成绩能证明什么呢,什么也证明不了,它仅仅是一个与你被现行教育制度压迫、同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参数而已”。不喜欢不愿接受自己的专业却毫无作为地继续逃课,期末考试以通过为标准,还以勇敢反抗的姿态为自己寻找借口,作者在此准确揭露了自甘颓废的学生对自我不负责任的特点。但在后续的《草样年华Ⅱ 后大学时代》中,邱飞在“毕业即失业”的状态下继续着不负责任的态度,人物的成长转变十分缓慢,标签化的“颓废”就显得不合逻辑了。
不能否认,校园青春小说中以颓废之姿反抗大学日常生活的学生,确有反抗僵化死板的授课制度、自以为是的思想权威的倾向,但在作家笔下他们并未更进一步对大学制度有何深入的反思和抵抗。虽然,这类小说中颓废者“我”的经历都带有自叙传的意味:《中文系》的作者名为李师江,而文中的“我”在他人口中被称呼为“师师”;孙睿《草样年华》第一部的副标题为“北×大的故事”,而他本科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可简称“北工大”。作者虽试图用零零碎碎的逃课装病、研究试题、代写论文、打工兼职等生活细节构建出更为个体化的大学回忆,主角的生活状态却仍停留在“为颓废而颓废”的模式中。
而在大学叙事小说研究中被更广泛讨论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作者为了表现大学现状,批判当代在校学生道德滑坡、追逐个人利益的状况,往往因已经与当下校园生活脱节,而极力扭曲学生行为。
举例来说,为表现学生对老师、对非实用性知识的不屑,小说中往往会出现学生们逃课或当场顶撞老师的行为。比如阎连科的《风雅颂》中,主角杨科的《诗经》解读课上,“竟有十几个学生联名写信给学校要求取消这门课”,而且“在我把课讲到一半时,学生走了一半,在我快要把课讲完时,学生也差不多就要走完了”。更夸张的是,留下的十几个学生中,竟有人提议“你看所有的学生都走了,这里只有我们十几个留下给你撑面子,你不掏钱请我们看一场电影吗?”此刻,施教者与受教者的传统关系被彻底颠覆了,人称“教授”的知识分子因为“无用”而被学生轻视。
在《大学纪事》中,为突出“道德滑坡的学生”与“坚守立场的教师”之间的对立,作者设置了一场围绕“考试诚信”展开的风波。学生为通过考试,先是异口同声地说考试内容上课未讲授过——“我们都不记得您讲过”。后有人试图借上厕所的名义作弊,不愿意在老师陪同下去洗手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该学生甚至直接在考场中尿裤子引起骚乱,“考生间的‘交流’便紧张地开始”。坚持考场纪律的阿满老师抓出作弊严重的学生,却遭到投诉。事后,学校为平息风波便安排学生补考,保证每个人合格。从这场风波的结局来看,不尊重知识与师长的学生在学校粉饰太平的遮遮掩掩中占强势地位,而坚持原则、决不妥协的老师成了无奈的弱者。
在此,通过颠覆传统大学叙事中的学生形象,突出其以“通过考试”“获得文凭”为目的,却对知识本身毫不在意的特点,确实能显示出作者对当下大学本末倒置、大学生道德滑坡的批判。而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此类小说叙写学生与教师对抗的部分时,其共有的缺点就是,作者完全是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展开叙述的。学生表现得愈乖张暴戾、愈不合常理,教师愈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似乎愈能体现小说的批判性。当学生的飞扬跋扈成为此类小说必备的元素时,作者其实已经将问题学生的行为模式化了。
总之,大部分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作者在塑造大学生形象时对当下大学生的真实面貌不够了解,以单纯批判大学阴暗面为目的,使其脸谱化与模式化。无论是以讲述亲身经历的口吻,展现在大学中经历的迷茫与颓废,还是站在教师的角度,以夸张行为突出学生道德水平的下降,都已有固定的模式。当问题学生的形象千人一面时,读者很难有代入感,学生的畸形成长自然也难真正引发读者对大学教育问题的思考。
二、 情感经历的离奇性
叙述男女生如何在象牙塔中经历青涩爱情与在懵懂中完成性启蒙、学会爱与被爱,是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讲述在校学生成长时必备的部分。与异性的暧昧纠缠在从学生视角出发的校园青春小说中是大学生活的重中之重,所占篇幅极大。作者在以情感经历为主线串联全文的时候,往往会给读者造成“谈恋爱是大学最重要的经历”的错觉。而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大学叙事长篇小说中,作者对大学生情感经历的叙述,往往为表现其在现实诱惑面前的挣扎或堕落。通过叙述畸形的情爱经历,进行道德批判才是此类小说的目的。
在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中,一类学生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心思单纯,坚守爱情的纯洁性,表现出草率与脆弱的特点,《草样年华》系列、《中文系》、《大学之林》……中均有对此类学生的描述。另一类学生的目的则已在情感之外,玩弄感情、以身体为筹码进行利益交换,作者往往通过类似叙写表现其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挑战。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在校学生情感经历之跌宕起伏、复杂纠缠在作者笔下被放大,其离奇性和激烈程度已经超过了艺术夸张的必要程度。
初通人事的大学生,在与异性交往时并无经验,面对感情问题往往表现出草率与脆弱的一面,易走极端。无论是《大学之林》中因男友出轨而跳楼的姜小艳,还是《中文系》中为情自杀未遂的左堤,以及《草样年华》系列中分分合合的邱飞和周舟、《大学纪事》中为作家麦子花言巧语所骗而最终精神崩溃的小伊……小说中的在校学生往往会轻易付出深情,又因一腔热情的错付走向崩溃。为了表现大学生在情感方面的稚嫩与冲动,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常描述学生将生死、正常生活置之度外的激烈举动。
常见于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另一类学生成长中的情感问题,则是在校学生以感情、以身体为筹码的堕落。这种堕落常见于因经济困窘出卖身体的女生中,几乎是每一部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的必备。前文提到的《大学纪事》中的小伊,在被作家麦子欺骗怀孕后,不得不生下孩子离开校园,因家庭窘迫,为了生活她无奈选择被台商包养。同样为改变经济状况以身体为筹码的还有《教授》中的代孕学生乌梅,但她最终觉醒,没有将腹中孩子作为交易资本,选择离开北京自力更生。作者在叙述这类学生的遭遇时,往往语带同情,目的是反思学生为何被迫走上出卖身体的道路。
与受生存压力逼迫走上堕落之路的学生不同,许多新世纪大学叙事小说中的问题学生,已在有意识地利用身体、情感来获取利益了,成为与之相对的另一极端。比如《大学之林》中抛弃原配女友的夏中骏,在老师戈新元问起他是否爱大他十几岁的法国教师诺爱米时,他直言不知道自己爱不爱诺爱米,和对方在一起是为了得到她的帮助,进入欧盟企业工作并留在法国。他充满理智、毫无感情的回答,赤裸裸表达自己的目的,与上文中为爱痴狂的学生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中,类似试图以情感关系获取利益的还有《桃李》中的刘唱和《桃夭》中的胡丽。刘唱刚认识博士生老孟,就言辞暧昧地诱惑他,摆出自己的目的:找老孟帮自己代考法律系研究生,以便留在北京工作生活。她甚至露骨地说:“你想,如果在你的帮助下我读了研,我就成了你名副其实的师妹,将来还不就是你的人了”,“如果你愿意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我那个小天地,今天我可以把一切都给你”。后来,刘唱诱骗好友蓝娜,致其被宋总侮辱,最终被好友记恨,被公安局拘留,导致精神失常。
与夏中骏、刘唱类似,《桃花》中的胡丽是试图通过“干爹”教授梁石秋学生的关系请歌舞团团长吃饭,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在小说中,这类学生的诉求十分直接——夏中骏想留在法国,刘唱想留在北京,胡丽想找到适合的工作。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将情感、身体作为交易的筹码,试图走捷径来避开同龄人必须承担的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类学生彻底贯彻消费文化的精神,摒除道德限制和个人情感,将自己作为商品推向社会。
小说对两类学生行为的呈现,从显示批判力度的角度来看十分有效,学生对待感情、处理两性关系的方法如此极端,确实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但在单纯呈现问题之外,作者并未进一步探讨其成因。夏中骏、刘唱、胡丽的情感观念如何形成,类似小伊、乌梅这样的学生又为何无法在生存问题上保全自己,这些都不能用简单一句“社会道德滑坡”来解释。而他们是如何通过一次次抉择、积累生存经验走向畸形的,则不得而知,其成长状况背后复杂的成因仍然模糊不清。
而当学生作为主角出现在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中时,其情感经历往往会作为主导人物行为的线索出现,情感生活的波动成为推动其学习、生活、思想变化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桃花》中的姚从新,在与钟情、邸颖、刘曦曦三个女生的恋爱过程中,或神魂颠倒试图用不明药剂延续爱情,或为了已经失踪的女方出国寻访,一片痴情。从他因钟情父亲被股市套牢,而一步步加深对股市的关注,到与刘曦曦产生感情,而延续了整个师门与宋总公司的利益纠缠,再到为追寻怀孕的刘曦曦迫不及待出国来不及准备论文,导师将自己的论文交给他发表,最终招来大祸……姚从新读博期间行为转折的重要节点,都与其感情生活密切相关。
至于校园青春小说的主角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中文系》中,“我”为了心爱的姑娘与同学闹翻,逃课追到姑娘的家乡表白心迹,争取每一次机会与她谈心,帮她做作业……直到毕业。《草样年华》系列中的主人公邱飞与周舟经历热恋、争执、分离、复合……其间还夹杂着邱飞和韩露、乔巧等女性角色的情感支线。作者刻意为主人公设置复杂的感情线,将在校学生的生活和感情捆绑为一体,成长也好,堕落也好,似乎都必须通过与异性的纠缠不休才能完成。
当复杂甚至离奇的情感经历成为小说人物成长的主旋律时,生活的其他部分因之被弱化了,以此出发对其成长问题进行反思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小说深陷千回百转、高潮迭起的情欲故事,不仅偏离了叙事的目的,更降低了小说的格调,有用俗套情节吸引读者之嫌。可以说,许多作品并不能通过在校学生情感经历真正说明其畸形成长的原因,实际上只是增加小说的可读性罢了。
三、 成长的必然失败
新世纪大学叙事长篇小说中的大学生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并没有成长为传统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们或与礼崩乐坏的世界同流合污,或与世界脱节在狭隘的个人世界中徘徊,更有早早陨落、用生命撞击现实者。“成长”对于这类小说中的学生来说,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伪命题。但众多作品中,大学生的成长失败往往被作为大学乱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被反复展演,鲜有小说真正达到反思大学教育现状的目的。
校园青春小说中以颓废生活“反抗”校园陈规的主角,临近毕业及毕业后即面临无法融入社会的问题。《中文系》的主角感叹自己找到工作的瞬间“就像个肚子被人搞大的女人,侥幸找了个男人领了结婚证”。《草样年华》的主角邱飞则连毕业设计都是找人代笔,最终请老师吃饭通过。因缺乏社会经验,毕业后邱飞在第一次独自承包项目时就因缺乏经验,在骗子卷款离开之后只能痛哭一场。
其他在大学早有个人规划的学生,要么如《中文系》中的凯歌早早进入社会脱离课堂;要么如《大学之林》中的洪俊花、《桃李》《桃花》中的众弟子,或无奈服从导师意见,或与老师一同为巨额利益蒙蔽了双眼。总之,无论是投身社会浪潮追逐利益,还是在已经被金钱权力污染的大学校园里努力攀升,小说中学生在接受高校教育后没有建立起独立的人格,更缺乏自我决断的行动力,其未来总是一片灰暗。
从社会现实来看,新世纪以来整个社会对大学的定位已经变更,大学所代表的知识的神圣性在与经济利益至上的社会价值观的交战中已落下风。大学精神旁落的原因是大学教育目的的错乱——大学成为培训学生进入社会后迅速掌握生存技能的场所,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已不是传承自由与理性的精神。可进入市场交易视野内、创造经济价值的专业受人吹捧,如张者“大学三部曲”中法律系的众师生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既惧怕又对令人咂舌的利益欲罢不能;而无法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专业,则只能通过建立博士点、硕士点获得国家资金支持,来显示其存在感,如《大学纪事》中的何季洲为建立中文系博士点、提高其知名度绞尽脑汁。从此角度出发,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小说中人文专业学生(多为中文系学生)往往陷入精神迷茫和与社会脱节的恐惧,而经管法专业学生往往难逃利益旋涡与精神世界的撕扯。
由此,大学叙事长篇小说中大学生成长的必然失败获得了其合理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结合前述小说中学生形象的模式化、以情感经历离奇性为生活主调的叙述方法,大学生成长失败的结局只能是作者展示大学全貌中一个必要的元素。在反思成长失败的原因时,我们只能大而化之用“社会道德滑坡”“教学与行政的倒置”寥寥几语带过。
叙写以成长失败告终的大学生活是批判大学现状的重要手段,尤其在从大学知识分子的角度批判现今大学生成长的小说中,由学生反抗师长、钻营人际关系、唯独无心向学的状况,往往可联系到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对学生的侵染及教师对教学重要性的忽视、师生关系的变迁等方面。但是,当成长的失败作为功能性元素存在时,不仅不能体现现实批判的全面性,而且显得生硬和单薄。
四、 结语

注释
:①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③李师江:《中文系》,《当代》2010年第5期。
④李师江:《中文系》,《当代》2010年第5期。
⑤李师江:《中文系》,《当代》2010年第5期。
⑥孙睿:《草样年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⑦阎连科:《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⑧汤吉夫:《大学纪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⑨张者:《桃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⑩李师江:《中文系》,《当代》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