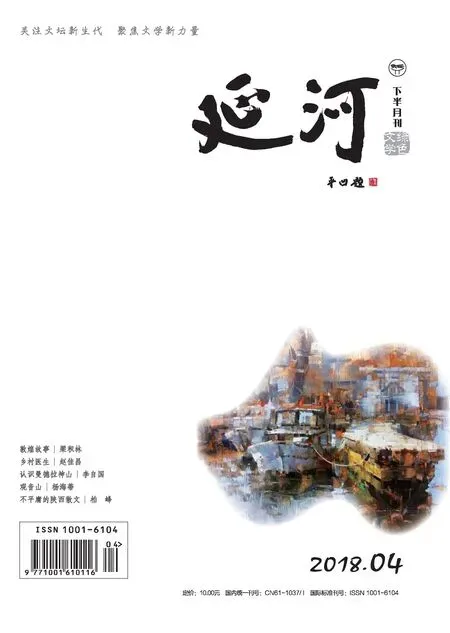普陀潮
雨 凡
站在陆地,依然觉得身在海中,就是指舟山群岛这样的地方吧。
从陆路去,先要一口气过完下述跨海大桥:金塘、西堠门、桃夭门、响礁门……有人造桥像抛缆,甩手一条又一条,缆绳那头系着舟山这条船。
下桥,已近五十公里之外。
占据群岛面积一小半的舟山本岛五百多平方公里,有新区与非新区之分。新区就是一切都是新的,这种现代、流畅、明丽、活力感一路延伸到朱家尖一带。抬头,普陀山隔海在望。
再也没有了桥,就是个渡口,单是人渡。相信这是个特例,含有掩饰不住的设意。风驰电掣赶来的人们被一脚急刹,顿挫之感很明显。接下去无论渡船如何的先进高效,古老与传统在此已经显露无遗。
以这种方式过到普陀,像是一种预热又像是一种冷却。
普陀山岛总共三十公里长的海岸线,内部容纳了大大小小几十座庙(庵),史上最多的时候有四大寺、一百零六庵、一百三十九茅蓬。这些千年古刹,看上去一律少见建筑的客观性和固定性,而像植物,在岛上随处生根,缓慢自然地生长,日久形成特别庞大的群落。它有自己的吐纳,兴衰是它的四季。
岛上更大的群落当属真正的植物,尤其是各种树木,有一长上千年,很多一长几百年,数不清的正往百年里赶。海边人的常识,海岛风大、土薄、咸涩之气重,植被脆弱,成林成材尤难。普陀之木,仿佛不在影响之列,生来高大、茂密、葱郁,占据了岛上70%以上地盘。当我站在一棵古樟前,看它千年之后的不空、不枯、不疏,一开始也想借它的幸运之光。但我知道人心念头的威力,任何一次妄念都可以引来一柄利刃,将历史砍断。而一腔善意与一缕惜念,可以让它从种子开始,安然无恙地一直长,最终借年轮的形式存录千年而不泯灭。当树千棵万棵地自由立身立命,那就不再是偶然,若论幸运,至少整个岛的树林包含在内。
古木和古刹,此丛林和彼丛林,千百年下来合为一体,普陀山留给人类的地方确实有限。民居相比前面的两者,反倒需要刻意找寻,居民,也需要留心甄别。大概,这就是普陀山的做派。
到底是在人海中翻出了几个常住者,当然他们包括其祖上的历史都比不上古刹和古木悠久。这些少数派做着与旅游相关的一切行当:餐饮、民宿、百货……跟一般旅游胜地并无两样,唯一不同的还是做派:家常、随缘,比如邀客的时候,开场白不外是,饭吃过了吗?住下了没有?淡淡然的口气,好像是纯粹找人寒暄。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太清楚,吸引和留住这些客人的首先不是他们,所以不急切。同时,他们的胃口也一般,私家提供的服务大都属平价,使得普陀山看上去无论拥有多传奇的过去,往后想要达到怎样高蹈的境界,它从来都是平民之岛,出自自然与内心始终是立岛法则。当然,进入之前,来人自有来人的各色面目各种身份,但当他们同船渡海、同登彼岸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称呼——游客,更确切地说是过客。在此,芸芸众生再未显示出众生相,体现在表情、想法、行为都趋同。必定在离岛之后,才又各奔前程。
在我这里,普陀山首先是行走的天堂。为了加深这种印象,一场叫黄蜂的台风路过东海海面,将绝大部分游客刮回了大陆。随之而来的断航,类似断却念想,空静下来的普陀山,安心留下的人,美景良辰,都到眼前。很有脚感的木质游步道蜿蜒于岛之内,沿途一侧是海,不离不弃,动荡喧哗,另一侧是不间断的黄墙黛瓦碧树,游人在其间如静水流深,多的时候想必会蓄积成池塘,泛起阵阵涟漪。
无处不在的私家车终于在此绝迹,只保留了有限度的公共交通。公路狭窄、通畅,鸡犬不闻,与游步道一起穿越老枝新叶交织而成的绿色长廊,在永恒的海与旧迹古物之间侧身而过。这种时候,稳坐在现代交通工具上,往往有一些地老天荒,有一些历久弥新……
其实,这仍旧属于表象。普陀山的实质,要在入夜露出端倪,就像水墨印上夜的底色,能持有,不走样,融通而非迷失,终至纯粹、如一。因此夜晚只是夜晚,黑暗只是黑暗,不丛生其他。游人也只是游人,虽然成为了岛上的活动主体,但已提前放下生活中的武器,诸如眼中的戾气,刀锋般的言辞,冲撞式的肢体交流。这样的夜色里遇见这样的人群,越不明来历,越南腔北调,越觉无挂无碍。
除树木和建筑,普陀山上的群落,细分之下还有游人、居民、方外之人、管理者……居民不断地进货出货,方外之人只做自己的功课,游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管理者不动声色地掂量调度。从来没能在一个地方见过这样自成一体却又互相依存的群落关系。以其不足十三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难免大容量之下的高密度。这里所做的不过是让它流动起来,直到构成密不透风的内循环体系,从此再多外力的踏入,最终归化于循环本身,像洋流,幅宽有限,却浩荡无止境。
以历史的长度和节奏感看,树木噌噌地长大,建筑物转眼间兴衰交替。以眼下看来,普陀山最不缺乏最值得一提的还数游客。一年数百万人进出,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岛上空出来的每一条缝隙都注满,之后又像潮水一样退得干干净净。周而复始,始终停留在进行的状态,就像山脚下的沙滩,每天潮来潮去,从来没有完成的时刻。
一座岛,历经人潮与海潮千百年的冲刷,我曾经以为会留下很多,却只发现普陀山。当我认为什么也没有留下的时候,再回首发现普陀山的笃定就来自这两股潮水的积淀,看得见的是沙滩,看不见的是氤氲。
岛上制高点佛顶山,山下有座宝陀讲寺。以进岛的渡口为起点,它已经在远端,临近小村庄,特别嵌进深深的山坳,就像住进世界的底部。风从大片建筑物上空翻卷过去,夜晚,听得出极强的质感,浑似狂涛排空。海岸线近在咫尺,涌上来的涛声在崖壁绝处无尽应和。双方同等强大同时发力,小岛唯有被猛烈摇撼。凌晨,风声与涛声最紧,岛上的世界也最沉静。有早课的人声传出来了,加入自然成为第三种声音。谛听无抗衡、争锋之意,甚至不辨内容,漫无目的,只有一团柔和的存在,但的确会在每一次风声、涛声的间隙里宏大鲜明起来。可以想象,风最终会在树木的姿势里留下用力的方向,波浪也会在海岸留下蚀刻的痕,而人声仿佛一边在消解,一边不着痕迹地留下安详。
有座宝塔在不远处耸立,入夜亮起一大柱暖色调的光,与天上的星光,人家的灯光,共同映照这方天地。记得先前走过塔下的村庄,彼时进入了人气最旺的晚餐时间,煎炸烹煮,生活的滋味正浓。
上佛顶山的路多达三条,一为捷径,即索道,直上直下;一为平路,缓坡盘旋而上;最后一条坎坷曲折,需要爬过每一级台阶。便利游人的前提下,此举是否另有深意,不敢妄猜。
此山高程二百八十六点三米,当然不代表舟山的高度。这个千岛集结之地,一支极其庞大的船队,承载着上百万人民,单本岛上的定海城就有几十万,他们累积出的才是文明的最高海拔。但普陀山无疑是舟山扎入海底至深的锚,锚链的长度等同于千百年的时光,是舟山一块致密的压舱石,约等于每一个来普陀、去普陀的人体重相加之和——这相当于东海之海舟山之舟的一份独特定力,也可以理解成磁力与魅力。
最后的问题是,当年普陀山无人的时候,是落寞,还是自在?就像在百步沙观潮,浊浪滔天的是人心还是海?我唯一能确认的,是起程去舟山,从一路摇曳,进入摇曳的世界,总归随潮来,随潮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