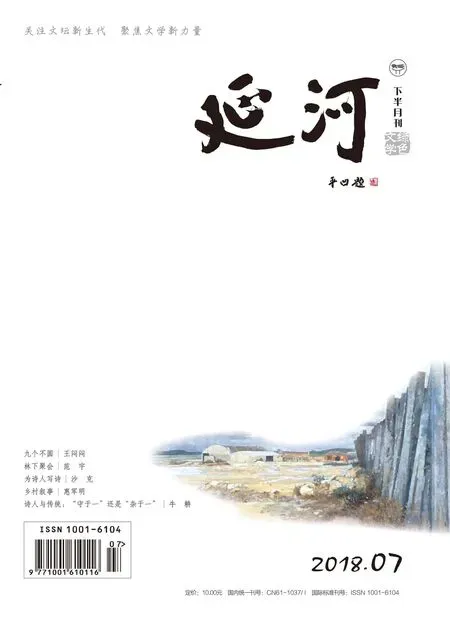隋朝走来的银杏树
杜文涛
仁者喜山,寿者亦喜山。
深秋时节的一个早晨,我和一棵一千四百多年的寿者银杏树相见在岚皋县木马河畔的山坡上。寿者多喜幽处独栖,朝觐的路需耐烦地逆岚河,溯支河,踅木马河,当河流分支再分叉,溪水喧嚷而柔婉时,攀上一面缓坡,我和银杏树觏面了。
树叶正黄,浮光曜金,涨满了亲昵。脚步移动着,一树金黄从季节的烂漫景色里,从悠悠的希冀里,摇曳而至,飘然而起,诗意地萦绕进了这绛红色的日子中。黄叶灿亮了人的眼睛,亦悸动出了人的叫声。我抓起一把厚厚坠落的树叶,在鼻息里深深地嗅了嗅,抬手抛向天空。每一片树叶,都在旋转中翩飞,每一枚叶子,都在舞动中舒卷着各异的姿态,飘拂成一叶叶晕黄的眷恋,念想着时光的经往,缠绵着美奂的景象。
树身伟拔,高过了树后的山峰。树身离开地面后一分有二,似开未开,若合若离,我抱着你,你抱着我,缠绵着挺向天空。树干高过人头处,挂着块当地政府名木古树保护牌,仰头细瞅,啧啧得知,树围十五米,树高三十七米,树龄一千四百年。默言自忖,回退一千四百年,银杏树最初萌芽立身时,那是隋朝的时光,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一统王朝。大树暴芽初生时,也初生了三省六部制,初生了开科取士。楔地挺起的银杏树,洇染着“开皇之治” 的欣欣气,远汲着大运河的脉脉水,也难怪根劲树茂十四个世纪了。
树干粗阔,和树下一间土屋近乎一般模样。有人说树得十个人牵手合围,有人说要十二个人伸臂相量。树下不远处一放羊老人闻听此言走近说:“这树早年间有人量过,八搂九拃一姑娘,现在恐怕还不止呢。”我问咋是八搂九拃一姑娘?老人挥了挥手中放羊竹棍说,说是慈禧太后老佛爷在世的时候,一位赶考秀才路过此地到树下躲雨,见树奇粗,有心想量一下,便搂抱了八搂。搂动时发现树后站着个大姑娘也在躲雨,不好再搂,只好收臂改用手量,量了九拃到姑娘身边。雨停秀才赶路,遇到同道人闲谝,说木马河边的银杏树搂了八搂拃了九拃还剩有一个姑娘站立的宽度。这话后来被传回到木马河,“八搂九拃一姑娘”就成了这古树粗大的形象说法了。
树下土屋的院里,卧着座古墓。墓碑拙朴,文字漶漫。残存的文字透出这是清代中叶甘姓夫妇的合葬墓,让人不由得想起树旁甘家坪出生长大的清末画家甘棠。甘棠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原名甘大霖,号醉霞。幼时读过两年私塾,从小喜爱绘画,因家贫买不起纸笔,放牛、砍柴时用树枝在地上比画山水、树木、鸟兽、虫鱼。一天一位农民请甘棠画画,现场却没笔纸颜料。甘棠看见旁边地上有一块灰白色的大石板,笑了笑,兴趣盎然地让和一盆黄泥巴水来,大家虽感到奇怪却照办了。甘棠挽起袖子,就势把眼前坐着的一个光屁股娃娃提起来,放在黄泥巴水里蘸蘸,屁股沾满泥水,又把娃娃提到石板上轻轻蹭了蹭,一个红黄色的南瓜雏形立刻现出来了。顺手扯了几把青草、绿叶,揉搓一阵,挤出绿汁,在石板上点点画画,一幅活生生的南瓜画跃然于石板上,妙趣横生,引的围观人捧腹大笑。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避难,陕西巡抚鹿传霖召甘棠为太后的行宫作画。甘棠先是在墙壁上依据“万绿丛中一点红” 画题,先画出郁葱的桑林,继而又画出一位背着背篓的采桑女。只见采桑女左手爬树,右手摘叶,左脚隐于林间,而右脚则在树缝间露出红色绣花鞋的一点尖部,赢得了众人对其点题之妙的叹服。随后甘棠又受命为太后内室画了葡萄图。画面上葡萄藤杆蜿蜒,绿叶掩映,疏密相间,葡萄串串,似伸手可及。偷吃葡萄的老鼠,有的瞪着警惕的小眼,有的竖起灵敏的耳朵,好像稍有响动即可逃遁。又有二鼠争食,似有吱吱叫声,惟妙惟肖。慈裕太后见后叹为“神品”,留甘棠到京供职紫光阁绘画,自此名播京师,其画作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树下出画家也出文士。树下木马河畔有座清乾隆五十五年留存下的叶仁安夫妇合葬墓,碑文七言诗体,新颖且别致,收录进了《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安康碑石》和《安康碑版钩沉》典籍。我们慕名去看,荒草萋萋,苔藓茂密,扯把草叶拂拭碑面,碑文楷体左行竖书,文字依稀显现。“盖闻初生太平世,福寿康宁人人钦。生于楚北通山邑,欢欣移居至秦境。惟望光阴百岁寿,古稀余四登天庭。□□□□□□□,严君慈母厚德情。略表寸心之薄意,稍酹劭沥一片心。生于康帝伍十伍,殁于乾王庚戊春。安葬此处平利境,木马河尾小地名。坐定西北平安稳,正向东南水秀清。兰桂腾芳垂万世,荫佑儿孙发千金。父母恩深如海报,刊碑不朽永留名。”碑诗无撰写人姓名,想来应是墓主人的一位文字颇渊的子嗣。孔子曾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位写诗的叶氏后裔不知是否做到了“事君”,但却真切地做到了“事父”。碑诗渗透了丰富的史料价值,佐证了明清两朝陕南移民的重大历史事件,从诗中也明晰地知道岚皋置县前此地隶于平利县境。墓碑前的拜台上横陈着块镌刻精美的硕大方石棋盘,只是如洗的流光濯去了棋盘上最初的石质棋子。子承父好,子悉父好,墓主人生前许是谙熟文墨的,也是极喜象棋的。两百多年前的碑诗几近完好地存立于今,是叶氏后裔的幸运,也是木马河的幸运。树下的事总会受寿者的庇佑的,千载的银杏树鸟瞰着树下的万物。
嗜文痴棋的叶仁安早已成为古人,画艺卓绝的甘棠也已成为古人。但这棵银杏树仍不急不缓地行走在时间的山道上,一岁岁的发芽,一载载的结果,不疾不燥,不卑不亢,矢志不移的走着,行过了唐宋,步过了明清,穿过了无常,迎讶着穿越。
“叶长千年茂,根扎大地深。不思登大雅,惟愿送温馨。”年年岁岁叶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康熙乾隆王朝时的叶仁安曾漫步树下把玩银杏口诵诗文,道光咸丰皇帝时的甘棠也许身蹴树下手捋树叶枝画白云,慈禧太后时的赶考秀才曾在树下搂量树身雨邂村女。今天,我们来了,为了千年的一晤,遁着冥冥之意的高远,在一枚枚金黄叶片的轮回里,探索树的秘笈,抚摸树的蠹节莓苔,凝望前人背影,踏觅历史轴心上移动的道场,跟着季节的脚步,将红尘烟雨和对生命伟力的敬畏,系上树的枝枝杈杈。
树下曾有过学堂,有过村落,也有过繁华。如今大多的人下山去向往高楼,去寻找远行。但这棵银杏树依旧牵着岁月的巨手,不弃初心契定,盘紧春秋,在岩石里涅磐,在阳光里掘立,看热闹褪去后的阒寂,阅风雨游梭中的人往。
树旁一户人家依树而筑起数间土房,屋内地面上树根悠游伸没。一丝炊烟从屋内飘出,女主人正在给她的孩子烧火做饭。主人家的一双儿女吃完饭后便需要乘车前往二十余里外镇上的学校,他们和母亲再次见面便已是下周末的光景了。她的丈夫在山下的石板厂里务工而数周才回家一次。平日里的这座山头上,只有她一人独自生活,陪伴她的除了春耕为稼秋收为穑的农活,便只有存在于电视机里的光鲜世界了。她家的邻居早已迁出而搬至山下的高山移民安置房,而她自己却不太清楚何时会离去,毕竟丈夫和孩子终是要回家的。
屋旁的银杏树,许是已经看惯了千年间的“春花秋月何时了”。人世的场场离别重逢在它眼下哭笑交替着,多少往事也无需细心铭记,而身处时间长河之中的它早已不悲不喜。
回望那棵银杏,树下炽色的树叶上睡着屋主人的家狗,它的眼睛闭着,睡得沉沉的。银杏树叶辉煌的黄,家狗看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