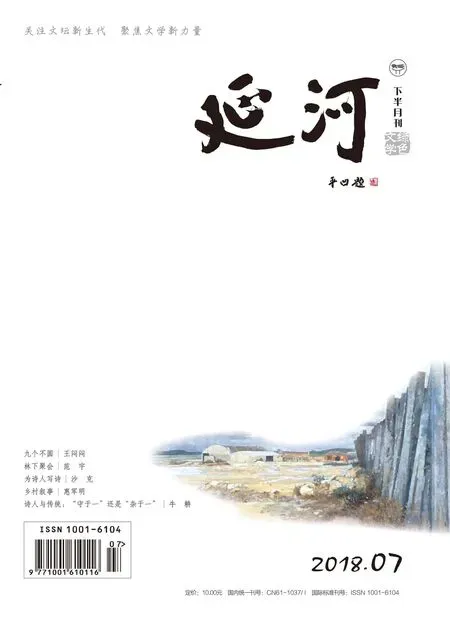一声鸡啼,打开村庄根部的寓意
——读范宇散文所直观与猜测
杨小愿
清晨的鸡鸣,是最村庄的显著特征,声情并茂,景象鲜活,总会勾起在乡下生活过的人无边遐想。它惊扰清梦、随地粪便遭人厌烦;它打鸣下蛋、滋润口福让人赏悦。它的种种好处坏处都会与村庄连成一体,烙刻在记忆深处。
唐人崔道融诗中“欲近晓天啼一声”的“晨鸡”,想必曾经吵醒少年范宇的许多春眠夏梦,以至于多年后还在《鸡事》中详尽描述杀鸡去毛的情形。当然,范宇用笔的心机是引出村庄另一大特征物——柴禾。
点燃散失的秸秆茅草,火苗腾起,将开水淋烫后扯掉羽毛的鸡体放上去,烧掉剩下的绒毛,这样去毛的鸡肉真比“脱毛机器”打理干净的鸡肉更香?我觉得这不是味蕾的判断,而是意识里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乡村风物的念想。因此,无论青椒爆炒还是红油凉拌,抑或萝卜清炖,那原生的鸡味,其实是柴火的纯香,是时光留给范宇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味觉村庄。他曾在《柴禾》一文中写到:“没有了柴禾,也就没有了村庄,一切都先入为主地打了大折扣。”他还拟人化地与“躲在角落里暗自神伤”的柴禾对话,信誓旦旦地表示“至少我会永远记得你!”
是的,范宇永远记得的,不仅仅是柴禾,而是一个村庄所蕴含的全部况味。在范宇笔下,村庄不仅是时代背景,还是一种借喻。通过锄头扁担、竹林枯井、田埂泥坝、鸡鸭柴禾等等典型物什,把村庄的骨骼、纹理、血脉、表情形象刻画,并将一个懵懂少年与成长环境之间的情感牵绊灌注其间,让人从中领略到村庄丰富的根部寓意和精神实质。
纵观范宇这一系列作品,不难看出,“村庄”出自他一以贯之的“故乡情怀”。他凝望着渐行渐远的村庄背影,对那些旧光景的顾盼眷恋,比所谓的“乡愁”多了一份超越他人生历练的沧桑,以及对故乡神形分离的反思,更有“夕拾落花”的时代感。尽管村庄的鸡鸣狗吠、夜籁晨晖无不显示出安宁心神、极目静美的超凡脱尘,但升格成范宇自成一体的文本昭示,依然掩映着几分亲历之后的哀婉轻叹,含有一种负气的追忆和牵恋。基于现实的逃离和根系的死结,作者把他破土绽放的村庄,在意识里纠结成一个象征符号,并缘此构成满腔复杂的情愫,既是对出生境遇的隐讳悲悯,又有天道酬勤的低调欣慰,甚而还有一些不忘初心的志向宣示。总体来说,他对村庄满怀感恩之心的回望,乃至把离乡求学谋生贬斥为“背叛”,但事实上,村庄绝非他人生宏愿的实践天空,而更多是他饮水思源的一个自我安慰式的念想。
不少卓有成就的作家,都有一个生发灵性的“精神家园”,这是作家作品的特定背景,往往指向作家生活过的故乡。静水深流,沃土深耕,源出一撤。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晓苏的油菜坡……范宇笔下那个叫作“野猫”的村庄,概莫能外。这个特定背景,可以是某个真实地域,也可以是作家艺术性虚构的一块土壤,但它必定实在存活于作家的文学构思中,是作家艺术创作的精神源泉和文学形象的表演舞台。同系列题材的不同作品,都可以共享这个固有的背景,聚合成根植一处、繁花四放的同质化集群。当主旨朝向归一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量,就会衍生知行交织、纵横联想的规模效应,构成文学“这一个”的鲜明特征。
当然,对一个作家的选材心理及作文取向,读者只能猜测,但范宇作品中不乏对时代变迁、人生波折、命运多舛的思虑纠缠,总能从文字背面跃然纸上。诚如文中写到——
多年之后,远行的父辈们相继归来了,而我们却漂泊在陌生的城市不愿回去,或许这其中夹杂着几分现实的无奈,亦或是对命运的不甘;
所有后辈对村庄的“背叛”几乎是不可挽回的,没有人会再回到村庄重拾他们的信念;
成为村庄遥远的念想,又是怎样的命运安排;
……
凡此种种,皆出自范宇“故乡情怀”的历史沉吟和思想宣泄。人们与故乡的关系,是大树与泥土的关系、花絮与根须的关系;是一种冥冥中的地气牵连,是母亲与子女那种融于骨髓的血脉传承,是生命对水土的存续依赖。“故乡”就像插在人们最柔软心底的一根针。我不解的是,一个90后青年,在心智逐渐成熟期间,需要怎样敏感的人文思考,才能胸藏如此深邃旷远的故土村庄,并萦系脑海,牵肠挂肚,几多梦回。北岛说: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源于对时势的顺从和对命运的放任,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重返故乡。范宇也只能在作品中实现对故乡的精神重返,这种重返其实更多是不能重返的无奈之举。即便时光倒流,能重返的也只有物是人非的地理定位,少年范宇刻骨铭心的村庄,唯有魂牵梦萦时浮现思绪,再现文字,最终实现行为“背叛”,精神“重返”。
故乡的变异,无疑令人情伤,但故乡的浸润和滋养,不会随远离故乡而中断。
记住乡愁是不够的。把故乡村庄设为背景,用时代色彩描绘出厚重的乡村史志,那些过往的人情物事都会散发出慰藉漂泊灵魂的温情,让时下日渐冷漠的心性回暖。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宇的故乡情怀和村庄散文,更具有难得的文学价值和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