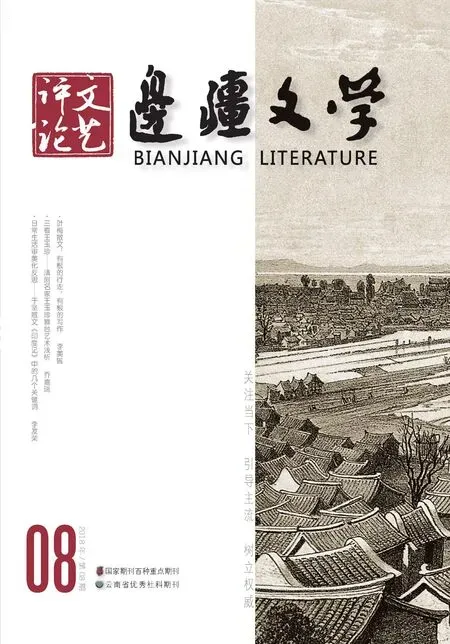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仓央嘉措诗歌赏析
吴金洪
他说:他信人世轮回,永坠地狱也不怕,既然伸不出抚摸天空的双手,宁愿足踏莲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回归深海或者没入尘土……
在历代的达赖中,他不是最有作为的一位,但却是人们最难忘记的一位,他用诗歌表达着宗教情怀,传递着人生感悟,他的名字,随着那一首首优美的诗歌,已流传了三百多年,他就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仓央嘉措的一生充满戏剧性,他出身贫寒,却登上了尊贵显赫的宝座;他无意政治角逐,却被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他渴望爱情,却是一个不准结婚的喇嘛身份;他热爱生活,却被高墙大寺摧折着青春,如同他自己控诉:“岩石伙同风暴,散乱了鹰的羽毛。”这样一系列矛盾结合于一身的仓央嘉措,使得感情丰富、细腻、热烈的他,留下六十多首流传至今的《仓央嘉措诗集》。本文试从仓央嘉措诗歌创作的风格,汉译仓央嘉措诗集的版本进行比较,继而与大家一同领略其诗歌之美。
一、在阳春白雪里感受清新自然
了解仓央嘉措的诗歌,我们得从《诗境》这部著作开始,在有关仓央嘉措的文献中,记载了他从小学习这本著作的经历。《诗境》是古印度的一部梵语作品,为檀丁所作,13世纪初期,藏族学者贡嘎坚赞将其译介到藏地,经过数代藏族学者的翻译和创作,《诗境》最终成为藏族自己的重要美学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大致可以分为诗的形体、修饰和克服诗病等三个基本内容。因此,它不仅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本诗歌创作指南,尤其是在诗歌写作方法的修辞学方面有极大的实用功能,可以说,它是藏族诗学体系的根,也是藏族诗歌创作技法与风格的源头。此前,藏族诗歌领域流行的是“道歌体”和“格言体”,受《诗境》理论体系的影响,此后形成了“年阿体”诗歌,“年阿体”讲究修辞、喜用辞藻,比较注重形式。
那么仓央嘉措为什么要学习写诗呢?是他从小就想做一名诗人吗?不是的,这是藏传佛教的传统,是对僧人的要求,属于佛家“五明”中的“声明”。在西藏历史上,活佛作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比如米拉日巴写了五百多首诗,号称“十万道歌”;萨迦班智达的格言体诗歌,形成了萨迦格言,而宗喀巴、五世达赖等都写过诗歌,但为什么仓央嘉措的诗歌得以流传下来,并经久传唱呢?这是因为仓央嘉措用他的创作实践改变了藏族诗歌的文风。
仓央嘉措的诗歌,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诗境》的影响,但与“年阿体”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诗歌运用一般口语,采取“谐体”的民歌形式,基本上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音节三顿”,这样的诗歌节奏明快、语调清新,朗朗上口,还可以用民歌曲调来演唱,极富于音乐感,将文艺从阳春白雪走向朴素自然,所以仓央嘉措的诗歌得以广泛流传,而且个别诗歌还逐渐演化为民歌传唱。
二、在学术中呈现仓央嘉措诗歌的知音
仓央嘉措的诗歌,虽然在民间流传了许久,却一直没有刊印本,而是以手抄本和口口相传的形式进行的,直到1930年,由我国藏学藏语研究的前辈于道泉先生出版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才开创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先河,此后还有1939年曾缄译本和刘希武译本等,这几个版本也有互相影响的痕迹,这些刊印本的发行,使得仓央嘉措的诗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影响力更深远,但这几个译本中,谁是仓央嘉措诗歌的知音呢?
于道泉(1901-1992),我国著名的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刘希武(1901-1956),四川人,曾投身军界、教育界,是进步的爱国革命诗人。曾缄(1892-1968),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黄侃先生的弟子。我们试以《东山上的月亮》来看他们的译本,于道泉译本为:“从东边的山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未生娘'的脸儿,在心中已渐渐显现。”曾缄译本为:“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刘希武译本为:“明月何玲珑,初出东山上。少女面庞儿,油然萦怀想。”于道泉先生的译法,是逐字逐句的“直译法”,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诗歌的原意,但是要照顾到文字的原汁原味,在今天看来,这一译本没有诗意,甚至还有很多粗陋之处,但却是比较客观的汉文资料,其价值与意义非凡,即使没有藏文原本,也可以帮助很多学者研究仓央嘉措的诗歌。刘希武的译本,文字艳丽,内容缠绵,他的诗“其事奇,其词丽,其意哀,其旨远”,少了民歌的风味,这可能是他译作的蓝本为英译本的文字风格所致。曾缄的译本仿古意,用词考察,意象丰富,讲究押韵、格律、用典等,这样一来,也就束缚了自由活泼的灵气。
总体来看,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本中,比较常见的为两种:一种是绝句体,代表版本主要为曾缄的七言本和刘希武的五言本,另一种是自由体,也就是白话诗,这一版本以于道泉的译本为代表,目前学界倾向认定于道泉先生的译本比较忠实于藏文原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风貌,基于这一因素,本文在第三部分的诗歌赏析中主要参考于道泉先生的译本。
三、在诗歌里,遇见仓央嘉措的心灵
从于道泉先生的译本来看,仓央嘉措的诗歌饱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摒弃了严谨的格律,将真挚的情感用清新的语言表达,记载了一个民族最质朴、最纯真的爱情心理和经历,不管是青春少年,痴男信女,还是历经风霜的老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皈依之处,随着历史的沉淀,愈发彰显其独特的雪域光芒。
(一)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
月亮是这个世界上的唯美之物,而爱情,则是超脱于人生繁杂的唯美精灵;月亮还是诗的化身,温柔、深情、宁静,这样的美也正是仓央嘉措所追求的。
“从东边的山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未生娘’的脸儿/在心中已渐渐显现”(《东山上的月亮》),相见不如怀念,诗人此刻想念的滋味如同一条小溪,曲折蜿蜒,涓涓细流注入心底,这个夜晚是如此的漫长,起身仰望,云雾缭绕的山峰上,圣洁的月亮冉冉升起,映射出少女白皙的脸庞,心上的人儿,这个夜晚,她也一样难以入眠吗?这是仓央嘉措诗歌开篇的一首,语言清新,意境优美。再如“初三的新月啊/没有什么比它更白/请你对我发一个/十五的夜色一样的誓约”(《初三的新月》),诗人遥看着这轮新月,她像天幕里的珍珠,深远、清亮,朵朵洁白的纤云在夜风中摇曳多姿,那高高悬挂的,不只是一弯新月,还有诗人的心,只要心上的人儿微微点头,他的世界就会银光闪耀,堪比那十五的月亮一样圆满,不管时光如何轮回,光阴如何流逝,他始终保留着对爱情的向往和不舍的追求。
在诗里,我们能感受到仓央嘉措的独特气质和隐忍的爱情,当月亮出现的时候,这样的情感强烈爆发,让整个天空为之充满光辉,让每一个望月的人痴痴地迷醉。“白”,是仓央嘉措诗歌的色调,从性情上说,仓央嘉措诗歌淳朴天真,可谓为“白”;从写法上说,描刻简洁,笔触轻盈,可谓为“白”,这样的“白”,和其金碧辉煌的达赖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初六到十五/月亮终于丰盈/有谁知道,那月中的兔儿/寿命已消磨尽了”(《从初六到十五》),我们常说,时间可以抚平忧伤,却无法让伤口痊愈,所以在仓央嘉措的诗中,弯月总是伴随着时间的长河,时隐时现。这样的意境,总让人想起嫦娥,轻漫的脚步踏碎了天上那池盈盈的忧伤,虽有玉兔相伴,还是凋谢了如花的娇颜。诗人朴实的吟唱,却透露出不一样的味道。“这个月亮已经过去/下个月亮还会到来/等到吉祥白月来临/那时我们就能相见”(《这个月亮已经过去》),有一种爱,叫相依相守,繁华落尽后,依然一起看那弦月的阴晴圆缺,夜空中,顽皮的星星向诗人眨眼,仿佛在说,思念虽然是如此的煎熬,但不要心急,下月上旬,月亮的女神就会来到他的窗前。在仓央嘉措诗歌中,月亮是一个出现较多的意象,“吉祥白月”是藏族人对满月的亲切称呼,月圆之夜,是自然馈赠人类的美好时光,在半明半暗的诗句中,你尽可以发挥想象和萦绕的思绪,诗歌的美学空间就这样在诗人与我们的共同创造中建立起来了。
(二)春在枝头已十分,炽热情感的真切流淌
爱是涤荡人内心惶惑的甘泉,佛家心中的爱是对有情众生的大爱,是从一个人的爱推及芸芸众生普遍的慈悲之心,仓央嘉措以“婴儿观佛殿”的境界在爱的殿堂里目迷神往,不掩饰,不隐藏,大胆坦露着自己的心扉,勇敢地表白着自己一个又一个唯美的情结……
“自己的意中人儿/若能成为终身的伴侣/犹如从茫茫大海/得到了一件珍宝”(《大海中的珍宝》),在诗人眼中,爱情是无法解释的情缘,从朝思暮想的爱恋到天天相对的婚姻,正如“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当是寻常”这样的生活弥足珍贵,用心的人才能体会,在人生的大海里,心爱的人就是其要寻找的宝贝,愿从此天长地久。大海在藏族人的心中,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是一个虚幻的天外美景,从神圣的美景中得到宝贝,诗人这样的爱情是如此的震撼人心。“我默想上师的面容/怎么也不能看清/我不想爱人的脸/却时时入我心中”(《我默想上师的面容》),作为六世达赖的仓央嘉措,尽管每天面对着四面的高墙,诵经烧香,朗夜星空洗去了铅华,却掩饰不住他内心的冥想,新月上的绰约身影是其心上人儿在凭栏远望,那样的杏眼,仿佛在与诗人对话,美丽的脸庞,在佛殿上慢慢晕开,这样的诗歌与汉族《诗经》中的《关雎》和古诗《明月何皎皎》如出一辙,相隔千里,却在感情点上发出了同样真诚的独白。
“渡船无心停留/码头却依依不舍/那负心的爱人/一次也不回头看我”(《负心人》),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爱却故意置之不理。都说渡口是无情的,却承载了多少人的离别哀愁,都说船上的木马是没有心肠的,但尚且对诗人回头告别,看着心上的人儿渐行渐远,却不肯回头,他的心像掏空了似的,守着空荡荡的渡口,独自惆怅。“柳树爱上了小鸟/小鸟爱上了柳树/若两人爱情和谐/鹰也无隙可乘”(《柳树恋上了小鸟》),人类的爱情也需要这样的心心相印,在外界的干扰来临时为爱情搭一个窝,在爱情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意外,什么样的阻隔,请记住这坚如磐石的爱,只要手牵手,心连心,他们的爱情就会海枯石烂。“后面凶恶的龙魔/不论怎样厉害/前面树上的苹果/我必须摘一个吃”(《凶恶的龙魔》),这样的诗让人想起狄金森有着同样纯真的《篱笆那边》,在这两首诗里同样跳跃着两颗单纯童稚的心灵,那心跳是源于对香甜苹果的渴望,这样渴望的美好也许在现实里找不到,但诗人却没顾虑这些,而在是自己的灵魂里超越现实的阻隔,率性地追求自己心中美好的东西。
仓央嘉措的这一首首饱含炽热情感的诗,写尽了人生的爱情百态,写尽了爱情的酸甜苦辣,可算得上是一部藏族风情的爱情百科全书,在这座用诗垒成的玲珑塔中,诗人用的每一块砖,都散发着青稞的麦香,白雪的清凉,寺庙的铃声,给这座藏族风情的文学宝塔增添着独特的神韵。
(三)不舍众生月重圆,睿智的佛心禅意
从仓央嘉措的诗歌来看,诗人本着一种放下、看淡、忘记自我的境界,追寻着生命的快乐,如月亮一般,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周而往复,在心灵的世界里,寻找其生命轮回的意义。
“随了心上人的心意/今生就与佛法无缘/到那空寂的山间云游/又怎能和她相见”(《不负如来不负卿》),如果为了爱情,那就失去了佛缘,但是爱情的力量却是如此的强大,让诗人又难以忍受离别之苦,“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又全法,不负如来不如卿。”曾缄先生作了如此精妙的解读。“若不常想到无常和死/虽有绝顶的聪明/照理说也和呆子一样”(《无常与死》),人既生亦死,千人千般苦,苦苦不相同,每个人都会在无垠的宇宙中化为一料尘埃,人生无常,但如果我们不能参透世间的纷纷扰扰,不去领悟生命的真谛,到头来不过只是空有躯壳而已。“洁白的野鹤啊/请将飞的本领借我一用/我不到远处去耽搁/到理塘去一遭就回来”(《洁白的野鹤》),诗人向野鹤的呼唤象征着他渴望自由的心灵,那念念不忘的地方,是其一直没有抵达的彼岸,借一双洁白的翅膀,飞过高山,飞过雪域,在人生的轮回中选择停留,诗歌里带着淡淡的忧伤,带着一种看透后的宁静,安静里的一份执著。这也是一首影响历史进程的诗,聪明的僧侣们从这首诗中悟出了轮回的真谛,从而找到了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
“在极短的今生之中/邀得了这些宠幸/在来生童年的时候/看是否能再相逢”(《短短的今生》),诗人这样吟唱,是你给我今生这样的圆满,让其在现实和精神里得到了莫大的幸福,感谢命运的恩赐,让我的今生如此精彩,聚散两依依,爱与恨都要道别离,只是这爱太浓太真,让人无法割舍,只是现实太多的残忍,让爱情无法相守到永远,剩下那颗痴情的心,任宿命的味道模糊诗人的视线。“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可不至相恋/第二最好是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用相思”(《最好不相见》),诗人在历经爱恨情仇之后,他想,如果没有开始,也就不会有现在的痛苦,甚至最好都不要遇见。《短短的今生》和《最好不相见》形成了仓央嘉措最后的绝笔,前一首眷恋人生,期盼来生能与其再相见;而后一首则显得悲凉凄绝,对世界的无尽失望,他们有着共同的情感底色,因为爱得深,所以伤得重,没有受尽命运的捉弄,是吟唱不出如此刻骨铭心的决绝之词。
综观仓央嘉措的诗,他的诗好像一组丰富的交响乐,每一首诗歌如这交响乐中的一件不可或缺的乐器,发出着自己和美的音调,直至《最好不相见》,达到整个乐曲的高潮,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只有真爱才会真痛,只有真痛才会真悟,仓央嘉措的每一次挫折、悲伤和痛苦,都是为了唤醒芸芸众生。他的大智、大勇、大悲,使得他的诗歌溢满真情,他在艰辛的世事中、最深的忧伤里吟唱着佛法的智慧,让我们调伏着在浮光幻影的尘世中愁苦的内心。他的诗是自然而然地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这些诗真情真性,直指人心,让人易懂,容易产生共鸣,一听就想传唱。这些诗歌又如一盘盘珍珠,一枝枝柳叶,一朵朵莲花,盛开在这美妙的凡尘世界,而那一段段痛苦的吟唱,却是这珍珠上的光泽,柳叶上的脉络,莲花上的露珠,让我们每一个有缘人都爱不释手,梦绕魂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