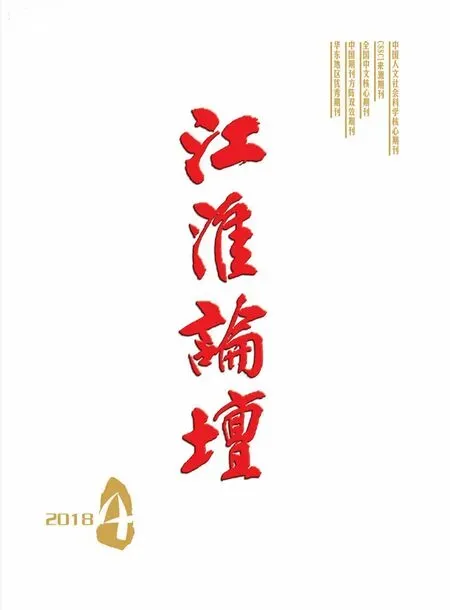平实醇正:“韩门弟子”传记文理论与创作述论*
谢志勇
(江西省宜春学院韩愈研究所,江西宜春 336000)
唐代李肇云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这是史见“韩门弟子”的最早记载。欧阳修亦云韩愈“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可见,“韩门弟子”不能完全等同于韩愈的受业门生,指称范围要广得多,“韩门弟子”与韩愈可亦师亦友,因仰慕韩愈而有着大致相似的文学旨趣。囿于主旨,本文所论“韩门弟子”专指与韩愈关系亲近、在文学创作上自觉接受韩愈影响且受之影响最深的李翱、皇甫湜和沈亚之三人。钱基博云:“韩门弟子众矣!尤著闻者:李翱皇甫湜雄于文。”李翱和皇甫湜都不满朝政,愤世嫉俗,政治上无大作为,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文“同出韩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 沈亚之“以文辞得名……尝游韩吏部门”,为文受韩愈影响,他自己曾云:“昔者余尝得诸吏部昌黎公,凡游门下十有余年。”韩门三人都以文名世,古文创作成就较高,有论者认为,他们“延续了韩愈散文反映现实、不平则鸣的传统……创作成就虽赶不上韩愈,但能各具特色,别具风貌。”但就传记文的创作而言,李翱、皇甫湜和沈亚之受韩愈之影响,总体呈现出平实醇正的风格特点,具体表现在文辞上的朴实无华、笔墨简省、直叙平易,内容上的关注史实、直面现实、淳厚端正。
一、温厚平和中见妩媚
李翱在唐代文坛上地位颇高。《新唐书》本传云:“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 ”欧阳修云:“唐文之善,则曰韩李。 ”李翱自己亦云:“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欧阳修把李翱和韩愈相提并论,李翱也自认当时文章盟主,可见李翱文重于时。李翱是韩愈的侄婿,他在《与陆傪书》中称韩愈为“我友”,称韩愈文为“古之文”,称韩愈为“古之人”,李翱视韩愈为同道,他们年相若、道相似。李翱深受韩愈影响,但其为人为文自有不同于韩愈的个性,其传记文理论和创作亦有特色。
李翱在《百官行状奏》中对行状的撰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史官的职责在于“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这和司马迁、韩愈、柳宗元的传记文创作一脉相承。其次,强调修史之必要。他认为:“自元和以来,未著《实录》,盛德大功,史氏未纪,忠臣贤士名德,甚有可为法者,逆臣贼人丑行,亦有可为诫者,史氏皆阙而未书。”极为肯定修史的重要性。第三,李翱直陈当时行状创作的现状:“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或言盛德大业,远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恶混然不可明。”第四,指出行状作者之史才不足:“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辞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记事则非史迁之实录”。第五,对行状写作提出要求:“指事书实,不饰虚言……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李翱在《答皇甫湜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其为人、为史传之思想:
仆窃不自度,无位于朝,幸有余暇,而词句足以称赞明盛,纪一代功臣贤士行迹,灼然可传于后代,自以为能不灭者,不敢为让。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群党之所谓为是者,仆未必以为是;群党之所谓为非者,仆未必以为非。使仆书成而传,则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无穷。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
这是李翱任史馆修撰时写给皇甫湜的书信,他自言“性不解谄佞,生不能曲事权贵”,且“议论无所避”,因而不得志于朝廷,转而穷愁著书。并表示其志向不在文而在史,欲“纪一代功臣贤士行迹,灼然可传于后代”,心慕韩愈“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欲在史传修撰上有一番作为。李翱对史传和文章的看法透露出其传记创作的观点。从李翱的《答皇甫湜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当时所见国史极为不满,立志“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因此,李翱认为,欲成一代良史,一要注重史传的实际内容,只有道德充积的著作,才能“假空言,是非一代,以传无穷,而自光耀于后”;二要有一颗公正之心,“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三要坚持史官的正直立场,做到“群党之所谓是者,仆未必以为是;群党之所谓非者,仆未必以为非”;四是史传创作需有文采。李翱云:“近写得《唐书》,史官才薄,言词鄙浅,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德,使后之观者,文采不及周、汉之书……唐有天下,圣明继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晔、陈寿所为,况足拟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文哉!”他把辞采和史传的流传、唐之有天下相联系,可见辞采对于史传的创作、流传作用重大。
李翱现存传记文有行状三篇:《韩吏部行状》《岭南节度徐公行状》《皇祖实录》,碑传四篇:《欧阳詹传》(佚)《高愍女碑》《杨烈妇传》《东川节度使卢公传》,墓志铭十一篇:《杨公仆射墓志》《故检校工部员外郎任君墓志铭》《独孤常侍墓志》《故处士侯君墓志》《叔氏墓志》《武侍郎墓志》《马少监墓志》《李长史墓志》《卢司录墓志》《武录事妻墓志》《故朔方节度使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碑述三篇:《平原郡王栢公碑》《仆射传公碑》《陆歙州述》。李翱的传记文创作真正做到了文理相兼、文史并重。他对其传记文的文辞非常自信,对其史才更是自视甚高:“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憨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意思很明确,李翱自诩其《高愍女碑》《杨烈妇传》两篇传记文就史才来讲不比班固、蔡邕逊色。《杨烈妇传》记叙县令李侃的妻子,在李希烈叛军兵临城下、举县不知所措之时,挺身而出,发动胥吏百姓进行抵抗,最后以弱胜强,击退叛军,保住城池。杨氏以一女子的身份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勇于抵抗,“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廪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其胆识仁勇超出须眉男子。对这样一个惊险的故事,李翱却以平实的笔墨来叙写,故事显得平淡无奇,而在平铺直叙的过程中杨氏的刚烈形象益加凸显出来。文章于叙事之后的议论,相对于韩柳的借题发挥来说,也要实在得多。其云:“厥自兵兴,朝廷宠旌守御之臣,凭坚城深池之险,储蓄山积,货财自若;冠胄服甲负弓矢而驰者,不知几人。其勇不能战,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弃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杨氏者,妇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 ’杨氏当之矣。 ”《高愍女碑》的创作也大体如此,这或许就是李翱自负之所在。李翱为史强调“指事书实,不饰虚言”、“直载其词”,这两篇传记文是其史传观点的直接反映,也是李翱史笔、文辞的集中体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李翱“才与学虽皆逊愈,不能熔铸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温厚和平,俯仰中度”。 总体来看,李翱为文确有“温厚和平,俯仰中度”的一面,且超越了韩愈的“醇”,使文章显得平易畅达。现将韩愈的《试评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和李翱的《故处士侯君墓志》作一比较,以见李翱为文之醇正。韩愈的《试评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记述的是“天下奇男子王适”的事迹,在文末韩愈补叙了侯高嫁女于王适之事,以突出王适之“奇”的形象,也写出了侯高的滑稽可笑。而李翱的《故处士侯君墓志》记侯高生平事迹,却绝口不提“侯高嫁女”之事,侯高作为韩愈、李翱共同的朋友,在李翱的笔下俨然一个高风亮节的隐士,和韩愈笔下的那个滑稽可笑的老者判若两人。李翱为文直叙平易,得愈之“醇”,却缺少了韩愈为文的生动活泼,其传记就不免给人以生涩板滞、艺术魅力不够之感。难怪欧阳修云:“韩之文传布世间者,不啻家传人诵;李文则落落然而后学有终身不得见焉者,兹非一大欠事欤?”欧阳修是针对李翱文流传太少而发,但其原因恐怕和李翱文太“醇”不无关系。李翱的《叔氏墓志铭》典型地代表了李翱传记创作平实醇正的风格,全文先以小段文字叙写立墓志的过程,续以大段铭文记述叔氏的事迹,哀婉之情蕴含其间。李翱为其岳母韦氏写的墓志铭亦是如此,先直叙其立碑之缘由,后以铭文“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苍苍兮不回,生几时兮终日哀。”唱出哀绝之歌,全文于温厚平实的记叙之中见出妩媚动人之情。
二、尚奇求新中寓深情
皇甫湜在唐代颇负盛名,李贺称颂他和韩愈为:“东京才子,文章巨公。 ”皇甫湜为人“辨急使酒”,敢于放言,发而为文,直言谠论。 《新唐书》本传载其为裴度撰《福先寺碑文》一事,可见其人性情孤傲、躁急。皇甫湜对韩愈的为人为文极为推崇,其《送王胶序》称韩愈 “余之旧知”,在《韩文公神道碑》中称韩愈为“先生”,其《韩文公墓志铭》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 ”皇甫湜为文很是自负,极少称许他人,竟称韩文“后人无以加之”,足见其对韩文的推崇备至。皇甫湜为文强调“意新”、“语奇”,其《答李生第一书》云:“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奇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 ”对皇甫湜为文之“奇”,后人多有评论。纪昀说皇甫湜得韩愈之“奇崛”,章学诚亦云:“世称学于韩者,翱得其正,湜得其奇。”实际上,皇甫湜所谓的“意新”,是指内容上的新意,“词高”是指形式上的出众。可见,皇甫湜为文尚“奇”本质是在追求创新。皇甫湜在内容上所标榜的 “奇”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他云:“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也。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当之亦可也。”皇甫湜清晰地描绘出了“奇”的发展逻辑:奇—非常—不如常—出常—无伤于正,他为文尚“奇”是要达到“正”,“正”即儒家的思想正道。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尚“奇”,皇甫湜解释说:“夫文者非他,言之华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夫言亦可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 ”很显然, 他强调的是 “理正”,要使“正之理”不朽,就必须文“奇”。如何做到文“奇”呢?皇甫湜提出要向“其文皆奇”的屈原、宋玉、司马迁及燕公、许公、韩吏部等人学习,做到“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文不百代,不可以语变”,才能写出“奇”文来。
皇甫湜的传记文不多,其中碑志文三篇:《韩文公神道碑》《韩文公墓志铭并序》和《护国寺威师碣》,另有《祭柳子厚文》《悲汝南子桑文》及《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共六篇。《悲汝南子桑文》《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是皇甫湜“有意为奇”之作。《悲汝南子桑文》借题发挥,讽刺社会现实的锋芒极为尖锐。他先以简短的散体之文记述周子桑之死,然后以大段骈体之文悲之:“浑沌无端,谁开辟之?善恶未形,谁分白之?善其福之,恶其祸之。谓善之福,夷死何饥?谓恶之祸,跖死何肥?何阖闾之死,金玉其基?何黔娄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张其事,而颠倒其数?天且高,地且辽。鬼神之形幽,敢问何故?”一气呵成,连续发问,再以“巫咸招日”云云借骚体之文抒写心中不平之气。一篇简短的祭文融合了散体、骈体、骚体之语,可谓“语奇”,文章悲的是友人子桑,讽刺的是深广的社会现实,意亦奇。《新唐书》本传记载皇甫湜一事云:“(裴)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 《顾况集序》,未常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今其《福先寺碑文》不存,而《顾况诗集序》尚在。这是皇甫湜为他的前辈诗人顾况所写的诗集序,名为序,实乃一篇不错的传记文。作者对此文颇为自负,当时也广为传诵。其文不长,兹录于下:
吴中山泉气状,英淑怪丽,太湖异石,洞庭朱实,华亭清唳,与虎丘、天竺诸佛寺,钧号秀绝。君出其中间,翕清轻以为性,结泠汰以为质,煦鲜荣以为词。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君字逋翁,讳况,以文入仕,其为人类其词章。尝从韩晋公于江南为判官,骤成其磊落大绩。入佐著作,不能慕顺,为众所排,为江南郡丞。累岁脱縻,无复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飘然,若将续古三仙,以寿九十卒。湜以童子,见君扬州孝感寺。君披黄衫,白绢鞳头,眸子了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鹭也。既接欢然,以我为扬雄、孟轲,顾恨不及见。三十年于兹矣,知音之厚,曷尝忘诸?去年,从丞相凉公襄阳,有曰顾非熊生者在门,讯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诗集二十卷,泣请余发之。凉公适移莅宣武军,余装归洛阳,诺而未副,今又稔矣。生来速文,乃题其集之首为序。
文章开篇写吴中的山水灵美秀绝,为文似有意求奇,却不难懂,意在引出生长其间的顾况。接着,写其为学和仕宦经历,结合山水景物的描绘突出顾况的风流俊爽、禀性不凡。更令人叫绝的是,作者在简单叙述顾况的人生困顿、失意之后,插入一段作者三十年前所见顾况:“君披黄衫,白绢鞳头,眸子了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鹭也。”诗人的清高绝俗、自然风流跃然纸上;山水美景与诗人风神融合一体,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此序以其语言之简洁平易、形象之鲜明生动在唐代传记文中别具一格。
而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韩文公墓志铭并序》二文中以平实之笔墨记述韩愈的生平事迹,对韩愈为人为文予以高度赞誉,字里行间饱含深情。《韩文公墓志铭并序》写韩愈:“先生与人洞朗轩辟,不施戟级。族姻友旧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后衣食嫁娶丧葬。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巨人长者矣。”叙述了韩愈的性情行宜,描绘出一个乐易君子的“长者”形象,深情贯注其间。《韩文公神道碑》相对来说要平易醇正一些,与李翱碑志文更为接近。现将李翱《韩文公行状》和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略作比较,即可见出其共同的醇正特点。李翱《韩文公行状》云: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马。祖浚素,皇任桂州长史。父仲卿,皇任秘书郎,赠尚书左仆射。公韩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岁,父殁,养于兄会舍。及长,读书能记他生之所习。年二十五,上进士第。汴州乱,诏以旧相东都留守董晋为平章事、宣武军节度使,以平汴州。晋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观察推官。晋卒,公从晋丧以出,四日而汴州乱,凡从事之居者皆杀死。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奏为节度推官,得试太常寺协律郎。选授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为幸臣所恶,出守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李翱用极为平易的语言记叙了韩愈的家世和其初期仕任。高步瀛评云:“详而不冗,简而不略,淡而弥永,朴而弥真,此种境界,非宋贤所能及。 ”钱基博亦云:“《韩愈行状》,为集中第一篇文字;只是从幼到老,顺次叙去,而提挈顿挫,自然起伏。归震川谓:‘《史记》如平地忽见高山;如地高高下下相因,乃去得长;如水平平流去,忽然遇石激起来。’此文乃臻此妙。”李翱记叙韩愈生平行迹于淡朴中见醇正,达致高妙境界。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对韩愈一生事迹的记述亦是如此,其文有云:
先生讳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郑氏异而恩鞠之。七岁属文,意语天出。长悦古学,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秀人伟生多以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为唐之章。贞元十四年,用进士从军,宰相董晋,平汴州之乱。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于四门,先生实师之。擢为御史。十九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缗民傜,而免田租之敝。专政者恶之,行为涟州阳山令。阳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孙。
两段文字放在一起,读来尤如出自一人之手。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云:“皇甫湜《韩文公墓志》、李翱《行状》不必同,亦互见之也。”皇甫湜、李翱叙韩愈事各有侧重,互有不同,但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叙事简朴而真挚,醇正之中寓深挚情感,与李翱《行状》相似。
三、平正质实中显神气
沈亚之曾“游韩吏部门”,不仅思想上受过韩愈影响,而且其为文也曾得到韩愈传授。沈亚之曾云:“闻之韩祭酒之言曰:善艺树者,必雍以美壤,以时沃濯。其柯萌之锋,由是而锐也。夫经史百家之学,于心沃灌而已。”沈亚之为文虽受韩愈影响,但却有自己的主张,对其文章造诣也很是自负,其《答冯兄书》云:“奉策应对之日,操意张谋,唯恐不远;刻文励语,唯恐不工。思欲不肩于俗,以为世之大宠。”《答学文僧请益书》云:“陶器速售而易败,煅金难售而经久。”说自己文乃“黄金锻”,故不易得售。沈亚之以其文工自许,但他最为自负的是其“史笔”,这在《与京兆试官书》中表露出来,其书有云: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升堂者十辈。然皆不能周其德,故各以其所长出人者称之,名曰四科。百世之下,皆言孔子圣,是知无全能者也。今亚之虽不肖,其著之文,亦思有继于言,而得名光裔。裔不灭于后,由是旨《春秋》而法太史。虽未得陈其笔,于君臣废兴之际,如有义烈端节之事,辄书之。善恶无所回,虽日受摧辱,然其志不死。
从上述文字看,沈亚之颇有史志,尽管他非史官,却留心于 “君臣废兴之际”、“义烈端节之事”,而且他还提出为文要遵循“旨《春秋》而法太史”的原则,这表明沈亚之和韩柳等古文大家一样具有一颗关注社会现实的忧世之心。
沈亚之于文章最为用力、成就也最为突出的是人物传记。其现存传记作品有《喜子传》《李绅传》《冯燕传》《郭常传》《表刘熏兰》《旌故平卢军节士文》《歌者叶记》等七篇。沈亚之为人立传常能于简短的形貌叙述中摄取人物的精气神,凸显人物性格和心理。《喜子传》写一个“饥年女子”喜子的“义烈端节”,其赞曰:“吾闻程生云:喜子之事,至死不变,亦可为烈。”作者以简短的语言,突出喜子的“义”和“烈”,人物形象生动而鲜明。《郭常传》写以医为业的郭常为人治病,见利而思仁。文章以对话成篇,主要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凸显人物的思想性格,语言直叙平白。作者的愤激之情在篇末发出:“沈亚之曰:仲尼盖言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而后学之徒,未闻明好恶也。岂其言之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邦有土之臣,专心聚敛,残割饥民之食,以资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无耻,是亦不仁甚矣。终无有恶者,若郭常之贱而行之,又焉得不称于当时哉! ”沈亚之仿“太史公曰”借郭常之事发表议论,以微贱如郭常的仁义之言行和某些“有邦有土之臣”之“专心聚敛,残割饥民”的行为相比较,不仅对郭常的仁义予以赞许,更是对“有邦有土”者的强烈讽刺。《冯燕传》叙写魏人冯燕平素好任侠,后与滑州将张婴妻有私情,为张婴所知,张婴屡殴其妻。一日,冯燕杀张婴妻而去,张被诬为凶手。将就戮,冯燕挺身出,自白其事,得免死。此文笔虽较简质,然情节曲折生动,近于小说家言。沈亚之在文末云:“予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谊事。其宾党耳目之所闻见,而为予道。元和中,外郎刘元鼎语予,贞元中有冯燕事,得传焉。呜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 ”作者称赞冯燕是“真古豪”,并透露了其写作初衷乃在史传。《李绅传》是沈亚之传记文的代表作品,重点记述的是李绅的“义烈”直言。节度使李锜不奉朝廷诏召,没有一个门客敢于劝说,而李绅“坚为言”,只是李锜听不进去,李绅又无法离开。等到中贵人叫书记官起草文书以向皇上“复锜位”,李绅躲避不书,李锜极为恼怒,急切召来李绅,让他起草奏章,“绅坐锜前,佯惴怖,战管摇纸,下札皆不能字,辄涂去。累数十行,又如是,几尽纸。”接着,李锜以死威胁李绅,李绅毫不畏惧:“绅不敢恶生,直以少养长儒家,未尝闻金革鸣,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 诚得死,生若前,幸耳! ”作者认为李绅敢于进言,不肯附逆,乃是“义烈端节之事”,李云抗节之事有刘腾为之记载,而李绅“临大节而不可夺”之迹更甚于李云,尚未及称。因之,沈亚之为之立传。传文不假任何虚饰,给人以平正质实之感,却凸显出传主李绅刚直忠勇之神气。
综上所论,李翱、皇甫湜和沈亚之在传记文的创作上有着不同的艺术追求,李翱强调文理相兼、文史并重,其传记文于平易畅达的行文中见出妩媚;皇甫湜论文尚奇、求新,其传记文有意为奇,借题发挥,讽刺现实,寓含情感;沈亚之颇有史志,留心史实,注重史笔,于简洁平实的语言中凸显人物的精气神。“韩门弟子”三人的传记文各具特点,但总体上呈现出平实醇正的艺术风格,这种大致相似的创作实践反映出他们对韩愈散文创作理论的自觉承袭。他们通过传记文的创作实践拓展了古文的题材领域,丰富了散文的表现技巧,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