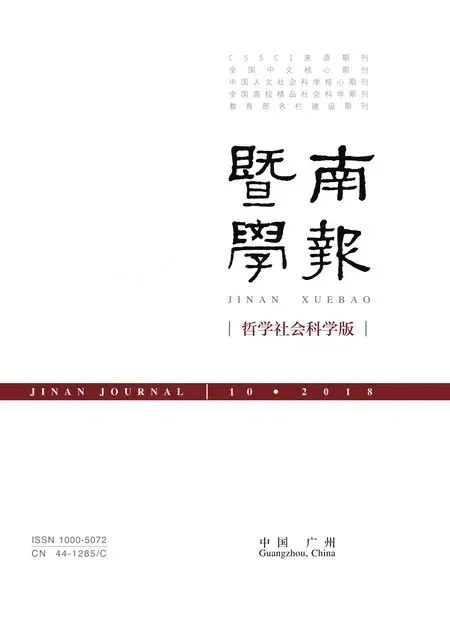静嘉堂所藏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的文献价值
陈广恩
《松乡先生文集》是元代文人任士林的别集。任士林(1253—1309),字叔实,号松乡,其先绵竹(治今四川绵竹)人,后徙居奉化(治今浙江奉化)。元成宗大德后期出任上虞教谕,武宗至大元年(1308),中书左丞郝天挺荐授其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不就任而卒。任士林“籍籍有文名”,倡导古文,被时人誉为柳宗元,而他自己也以“平生韩退之”自况。赵孟頫称其文“沈厚正大,一以理为主,不作廋语棘人喉舌,而含蓄顿挫,使人读之而有余味”。与任士林交游者,多为元中期著名文人,如赵孟頫、杨载、袁桷、邓文原、刘汶等,因此任士林在元中期文人群体中颇有声望。对此任士林自己也说:“自予得杨仲弘,人方翕然从予后;后得师鲁,而人益信予。”杨仲弘即杨载,师鲁即刘汶。清乾隆时期,四库馆臣评价任士林“有振衰起废之功”。清人王家振在《松乡文集后序》中也称誉说:“松乡当大德、至大间,有盛名于浙,为文力追先正,理足而意厚,不为时风众势所移,可谓豪杰之士。……松乡以山林一老儒,独能齐帅初之芳躅,而振牧庵、道园之先声,至使海内嗜古之子,皆若以不及见任山长之文之为憾事,则岂非树本固者历岁久,用功深者收名远也欤。”帅初指戴表元,牧庵指姚燧,道园指虞集,三人均为元时名儒、文章大家。在王家振看来,能与戴表元齐名,开启姚燧、虞集先声的人,正是任士林。于此可见,任士林亦元中期一名儒。他一生著有《松乡先生文集》《中庸论语指要》《中易》等作品。《新元史》有传。
作为任士林的别集,《松乡先生文集》自然是研究任士林最为重要的资料,同时也是了解元代中期文人群体比较重要的史料之一。关于该文集版本,国内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一卷本和十卷本两种。一卷本为清顾嗣立所选《元诗选》本。十卷本则有8种,分别是明初刻本,题为“元松乡先生文集”,藏国图;明泰昌元年(1620)刻本,藏重庆图书馆;光绪十六年(1890)孙锵明泰昌元年刊本修补本(以下简称修补本),国图、北大图书馆等均有收藏;《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清刻本,国图、上海图书馆收藏;清抄本,国图、北大图书馆亦有收藏;秦更年抄本,藏南开大学图书馆;抄本,藏北大图书馆。可见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初刻本。
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松乡先生文集》有三种版本,一种是元代刊本,还有两种是明刻本和旧写本。明刻本共两册,原陆心源十万卷楼旧藏。旧写本也是两册,系明泰昌元年(1620)刊本的影写本。有清同治四年(1865)徐时栋手识文及朱墨笔校与校语附笺。卷中有“朱彝尊”“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柳泉书画”“兼牧堂书画记”“徐时栋秘籍”等藏书印。综上可知,静嘉堂文库所藏元刊本,是《松乡先生文集》存世最早也是最好的版本,因故复旦大学黄仁生先生称这个版本是“现存最早的元刻元印本,堪称稀世之珍”。
目前学界尚无研究任士林及其文集的专门论著,相关研究成果也十分匮乏。笔者所见,仅有石勖言《元代杭州宗阳宫文人群体考述》一文,在针对元代大德、至大年间活跃于杭州宗阳宫的文人群体进行探讨时,涉及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任士林的文学创作等活动。由此可见,关于任士林及其文集的研究,尚属比较新颖的课题。有鉴于此,本文拟针对静嘉堂文库所藏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的文献价值进行分析探讨。
一
静嘉堂文库是由日本三菱财团的第二任社长岩崎弥之助创立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的著名私家藏书机构,以收藏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典籍珍本为主。其中所藏汉籍最为珍贵者,当属陆心源旧藏宋元珍本。陆心源是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尤以收藏宋元旧椠著称,其藏书与著作成就,晚清藏书家无出其右者。1907年,在陆心源去世之后,其子陆树藩因经商失败,家道衰落,于是将其父苦心经营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所藏珍本文献大半售予静嘉堂文库。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所言,这次收购,使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元版的数量,可与明治以前日本全国所藏宋元版的数量相匹敌。当年促成静嘉堂和陆树藩这桩买卖的日本汉学家岛田翰,曾感慨说:日本藏书之能事始毕,“而吾平生之素望尽于此……不亦人世之大快事乎?”静嘉堂文库也正是因为收购了以珍藏宋元旧刻精钞而最负盛名的皕宋楼藏书,从而使其成为国外所藏宋元汉籍之翘楚、国际汉学之重镇。2015年4月,笔者在日本访学期间,曾前往静嘉堂文库查阅了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
元刊本共3册,编号231/3/5 37。每半页13行,行23字。卷首半页9行,行18字。有栏,四周双边。板框18.8厘米×12.1厘米。版心粗黑口,双黑鱼尾,中间刻书名“松乡集”及卷数。书中个别页面有残缺者,则手抄补录,如卷四第14、17页。抄写用小楷,亦工整精美,笔力遒劲,不失上乘之作。整书保存完整,版面清晰,可称善本。
文集卷首有三篇文章,分别是赵孟頫所撰《任村实墓志铭并序》、陆文圭所作《任叔实遗稿序》和杜本的序文。卷首之后是目录,详列文集所收诗文的具体篇名,标明各卷的体裁依次为:卷一记、碑,卷二记,卷三墓志,卷四传、叙,卷五说、引,卷六赋,卷七后,卷八卷九诗,卷十表、疏、杂述。各卷头、卷尾均题“元松乡先生文集卷之几”,有的卷数于书名下署名“句章任士林叔实”。
卷首墓志铭之前的副页上,钤藏书印四枚,自上而下分别是“结社溪山”朱文方印、“家在黄山白冈之间”白文方印、“金星轺藏书记”朱文长印、“秋夏读书冬春射猎”白文方印。这四枚藏书印的主人应该是金檀。金檀,清浙江桐乡人。字星轺,诸生。“博学好古,经史图籍,靡不遍览。好聚书,遇一善本,虽重价不吝,期于必得。即不得,必假归手钞。积数十年,收藏之富,甲于一邑。”著有《文瑞楼集》《销署偶录》等。
墓志铭首页钤印九枚,分为两行,第一行自上而下分别是“元本”朱文腰圆印、“田耕堂藏”朱文方印、“平阳汪氏藏书印”朱文长印、“文琛”白文方印、“太原叔子藏书记”白文长印、“莲泾”朱文方印。第二行自上而下是“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朱文方印、“民部尚书郎”朱文方印、“汪士钟印”白文回文方印。“元本”藏书印表示该藏本是元代刻本。“田耕堂藏”朱文方印,与文集目录首页右下方所钤“郁松年印”白文回文方印和“泰峰”朱文方印,均是郁松年的藏书印。郁松年,清上海人。字万枝,号泰峰。恩贡生。家道殷实,喜好读书,尤其热衷于收购宋人典籍,所藏古书数十万卷,其中多元明旧本,并手自校雠。编有《宜稼堂丛书》。“平阳汪氏藏书印”“文琛”“民部尚书郎”“汪士钟印”,是汪文琛、汪士钟父子的藏书印。汪文琛,清江苏长洲(治今江苏吴县)人,祖籍平阳(今属山西临汾)。他“设‘益美’字号于吴阊,巧为居奇……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是以布匹生意致富的江苏大家,但喜好藏书。其子汪士钟,字春霆,号阆源,曾为观察使,官至户部侍郎。民部是户部的旧称,因故其有“民部尚书郎”藏书印。他继承父亲实业,更喜收藏古书,且仇对精审,举世珍之。著有《艺芸精舍宋元本书目》等。同治十二年(1873),吴县潘祖荫为《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作序称:“吾郡藏书家……后嘉庆时,以黄荛圃百宋一廛、周锡瓒香严书屋、袁寿阶五砚楼、顾抱冲小读书堆为最,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士钟。”可见汪士钟的藏书主要来自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砚楼和顾之逵小读书堆,尤其是黄丕烈旧藏善本多归他收藏。因其祖籍平阳,故又有“平阳汪氏藏书印”。“太原叔子藏书记”和“莲泾”是王闻远的藏书印。王闻远,清苏州人,字声宏,一字叔子,号莲泾居士、灌稼村翁。藏书颇多,著有《孝燕堂书目传世》。
“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是陆心源之子陆树声的藏书印。陆树声(1882—1933),字叔同,号遹轩,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之弟。邑庠生。陆心源藏书加盖陆树声藏书印,并不是说这些书又经过陆树声收藏,而是在日本汉学家岛田翰煽动陆树藩出售其父藏书给日本三菱财团时,事先与陆家管家李延达合作,在陆心源收藏的所有秘本书上均盖上“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臣陆树声”“陆树声印”“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等藏书印,其目的是标明这些秘本是陆心源旧藏。所以任士林文集加盖“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藏书印,正说明此本就是陆心源皕宋楼旧藏。陆心源(1834—1894),字子稼,一字刚父(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咸丰间举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其藏书先得自郁松年宜稼堂,又得周星诒等江浙旧家所藏,而皕宋楼尤以收藏宋元旧椠著称。著有《仪顾堂文集》《皕宋楼藏书志》等著作,合署为《潜园总集》。以上藏书印说明该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曾经王闻远、金檀、汪文琛和汪士钟父子、郁松年、陆心源等著名藏书家收藏。
卷十末有摹刊“任勉私印”阳文方印、“任氏近思”阴文方印。任勉,字近思,明松江府华亭县(今属上海)人。正德《松江府志》载:“其先四明人。元松乡先生士林子耜为两浙盐运照磨,始占籍华亭。勉之(即任勉——引者)登洪武甲戌进士,岀知饶州府鄱阳县。”由此来看,任勉可能是任士林的后人。他出仕后曾任鄱阳县令,累官福建右参政。“永乐、正统之间,论文章政事,必以勉之为称首云。所著有《薇庵集》若干卷”,说明“任勉私印”和“任氏近思”都是任勉的印章。此外,书中还有“静嘉堂珍藏”朱文长印。如此之多的藏书家和藏书机构辗转收藏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正是该版本弥足珍贵之体现。
二
前述国内现存《松乡先生文集》,最为流行的版本是四库本。近年影印出版的杨讷先生主编的《元史研究资料汇编》,收录有任士林的文集,乃光绪十六年的修补本。《全元文》所录任士林文,则以万历刻本为底本。因此这三个版本是已经公开的本子,其他各版本则均未公开。三本中修补本和《全元文》收录了赵孟頫所撰墓志铭,而四库本卷首三文无一收录。《全元文》另据陆文圭《墙东类稿》,收有陆文圭所作序文,所录杜本文章共15篇,却没有《松乡集》的序文。而元刊本卷首的三篇文章,无疑是研究《松乡先生文集》以及任士林生平十分重要的资料。鉴于此,笔者先将杜本的序文全文转录如下:
右《松乡集》者,四明任叔实甫所制诗、赋、记、序、碑、铭、传、赞、杂著之文,总若干卷。其嗣子良为江浙行中书省理所案牍官,今杭州路太守任公欲其文之传于世也,就子良求其稿而刻之。子良谓其先人著述甚广,而掇拾于散亡残脱之余者,未能毕见,其仅存者此尔。赵君仲德素与先人游旧,故用意裒集,缮写如此。因拓以遗余,且抆泣言曰:“先人与子夙有文字之契,欢愉忧戚,未尝不相与莫逆也,而先人墓上之木拱矣。始克粗成,是集子宜叙其颠末,以考其成,庶几先人之志也。”
惟叔实甫始自四明山中来杭,倡为古作者文辞,一时惊猜疑愕、怪笑非讪者,往往喧杂,独赵公子昂、邓公善之、袁公伯长、周公景远、张君锡、杨仲弘、薛宗海、吾子行、刘师鲁交相推誉,以为柳河东其人也。由是近远求文著金石者,户外之屦相接矣。往时怪笑非讪者,亦随以服。余时喜从故都遗老承问往昔文献,尤与叔实亲善,又尝从受《中易》之旨。盖叔实粹美质直,爱好人伦,有志于当世,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尝见其意于《送邓善之赴史馆序》矣。中书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见其文之典则淳雅,而制行端实,荐为安定书院山长,庶使讲道以淑来学,而竟以疾终。若赵公子昂、袁公伯长、邓公善之继登词垣,使叔实而犹存,岂不能与时翕张,日昌其制作之思,而相与为高下耶?是其所谓浑厚博大、温润清扬者,抑又有非人之所能为者矣,而不使之鸣夫国家之盛,乃独多见于宫祠塔寺琬琰之间,其亦幸托斯文以为世隽永。又若谢翱、胡烈妇传,能使秉彝好德之心千载著明,是岂徒作者哉?赵公之铭之辞,所谓“木折于山,玉碎于璞”,尤知德之士所以深嗟而痛惜也。京兆杜本序。
杜本(1276—1350),元清江(今属江西)人,字伯原,号清碧。其先居京兆,后徙天台,再迁清江,故其序文自称京兆杜本。杜本是元朝有名的隐士,《元史·隐逸传》为其立传,称其“湛静寡欲,无疾言遽色”。他与吴澄、范德机等人友善。博学善属文,工篆隶。朝廷多次征召,终皆不就。著有《清江碧嶂集》一卷,《元诗选》有录。另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著作,学者称其为清碧先生。杜本比任士林小23岁。从序文来看,他是任士林的门生,曾跟随任士林研习《中易》。《中易》是任士林的易学著作,惜今已不传。杜本跟随任士林不仅仅学习《中易》,而且研习诗歌创作。元末崇安人蓝仁、蓝智兄弟,曾拜隐居于武夷山的杜本为师,杜本“授以四明任士林诗法”,兄弟二人“遂谢科举,一意为诗”。可见杜本的诗法传自任士林。杜本为《松乡集》作序,是受任士林之子任耜(字子良)之托。在任耜看来,杜本与其父“夙有文字之契”,可算是“莫逆”之交。而杜本自己也说他与任士林“亲善”,称赞任士林“粹美质直,爱好人伦,有志于当世”。加之任士林与他有师生之谊,故而为《松乡集》作序。
大德七年(1303)七月,位于上虞县(治今浙江上虞东南丰惠)西北二十里的兰芎山福仙禅院重修竣工,任士林为禅院撰写碑记,此时他已51岁。大约这一年,他开始“职教上虞”。其后“讲道会稽,授徒钱唐”,开始在杭州生活。可见他晚年的行踪轨迹是从庆元路,经上虞、会稽,然后抵达杭州。至武宗至大二年离世,任士林在杭州生活了大概四五年,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他在杭州的讲学及学术交游活动,受到了时任杭州路道录、主持杭州宗阳宫的杜道坚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赵孟頫的大力支持,因故形成了以他们三人为核心的宗阳宫文人群体。据杜本的序言,除了杜道坚、赵孟頫之外,比较推崇任士林的还有邓文原、袁桷、周驰、张君锡、杨载、薛汉、吾丘衍、刘汶等人,他们称誉任士林为柳河东,这与任士林倡导古文辞有关,也是对任士林文学成就的认可。而赵孟頫、邓文原、杨载、袁桷等人,均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由此可见,任士林在当时文人士大夫群体中的声誉是很高的。
三
杜本的序文,除了为我们研究任士林及元代中期文人士大夫的活动提供了相关资料之外,也为我们考察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的刊刻时间提供了信息。目前关于《松乡先生文集》的元代刊刻时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周清澍先生所说的元至正四年(1344)浙江行中书省刊刻,并且周先生指出此刊本原为缪荃孙所藏。一种是黄仁生先生所说的元泰定间刊刻。大概黄先生的观点依据的是陆文圭序文的写作时间,因为该序作于“丁卯孟夏”,即泰定四年(1327)。而严绍璗先生则仅注明该元刊本为“静嘉堂文库藏本”,没有指出具体刊刻时间。那么哪一种观点正确呢?
明代宁波人孙能传为我们提供了元刊本《松乡集》的刊刻时间。他在应试期间,发现秘阁中藏有元刊本《松乡集》,欣喜之余,题识如下:“万历乙巳春,予校阁中藏书,有《任松乡先生文集》四帙,乃元至正四年浙江行中书省旧刻……先生为予乡先喆,今其集多亡阙不可得,幸藏在秘阁,岿然若鲁灵光之独存,亦予邑文虬之光也。”这说明元刊本《松乡集》刊刻于至正四年。今存元刊本无刊刻时间信息,孙能传在万历乙巳(1605)年见到的元刊本是否刻有刊刻时间,已不得而知,但孙能传应该自己不会也没有必要杜撰该本的刊刻时间,很可能是他看到的元刊本还保留有刊刻的时间信息,而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元人的相关记载以及任士林之子任耜刊刻其父文集的前后经过,可以佐证孙能传的说法是可信的。
静嘉堂藏本于陆文圭序文之后,还有杜本的序文,显然该本是刻于杜本序文写成之后。杜本的序文并没有注明作序的时间,但据序文可知,任士林之子任耜是在担任江浙行中书省理问所案牍官期间请序于杜本的,而其父文集《句章集》,也是任耜“在理问所时,命儒师锓梓行于世”。泰定年间,任耜在澄川(即澄江,指今江苏江阴)任职,这与贝琼所谓任耜“初辟松江府史,历江阴、铅山二州”正相符合。陆文圭序中也说,“泰定间,公之嗣子良吏于澄川,因出先人手泽示余,将摹而传之”,也没有显示出泰定时期任耜要刊刻其父文集的信息。任耜出任江浙行中书省理问所提控案牍的具体时间,尚不得而知,但明初刊刻的《松乡先生文集》所保留的另一篇序文,为我们又提供了一条线索。我们先看看这篇序文:
四明山川为越中诸郡冠,钟奇孕秀,宜当辈出。夷考传纪,则唐之贺季真以风流称,宋之二史以富贵显,外是寥寥然。季真不免有狂客之讥,二史相业,容有可议,山川奇秀,二三公能尽当否?余来东吴,获睹《松乡集》,则四明任叔实先生所作也。先生才裕而学博,理足而词胜,无奇奇怪怪之习,有浑浑浩浩之气。凡勒诸金石,形诸题咏,率得体制,名重于当时,可传于后世。山川奇秀,于是乎发。呜呼!苏之峨眉,欧之庐陵,始焉赖山川以生,终焉为山川之重,文章何负于山川哉!今四明以《松乡集》重,无疑也。陆子方名世具眼,向已订正而序之,且即世矣。叔实之子子良来为江浙司理官,欲锓诸梓,以广其传。余喜其不私于家也,亦为之书。至元后丁丑三月初吉,阆苑邢泰谨书。
这篇序文的作者是元人邢泰。该序文静嘉堂所藏元刊本中并没有收录,《全元文》也未收邢泰的任何文章,因此这篇序文仅见于明初刻本。邢泰其人,文献中鲜有记载。据元人王逢《菜亭四咏》所载,他是阆中人,曾为王逢之父所建菜亭写过记文,但这篇记文也未能流传下来,写记文时邢泰为江阴儒学教授。邢泰的序文写于后至元三年(丁丑年,1337),序中提到“叔实之子子良来为江浙司理官”,说明其时任耜已到任江浙理问所,即杜本序中所谓理所案牍官,亦即贝琼为任耜所撰《元故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照磨任公墓志铭》中提到的“江浙理问所提控案牍”。这说明任耜刊刻《松乡集》,至少在后至元三年之后。浙江行中书省刊本,应该就是任耜在浙江行中书省任职时的刻本。杜本的序也提到,任耜任江浙行中书省理问所提控案牍时,“杭州路太守任公欲其(指任士林——引者)文之传于世也,就子良求其稿而刻之”。杭州路太守任公,可能是任处一。至正三年(1343)九月,元代钱塘(今浙江杭州)文人张雨(又名张天雨)撰有《吴山承天灵应观记》一文,此文当时刻碑由亚中大夫、杭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知渠堰事任处一书石。而元代担任杭州路总管府总管的任姓官员,仅有任处一一人,则他应该就是杜本所谓的太守任公。至正三年,任处一在杭州路任总管。他在任期内支持任耜汇集其父诗文,于至正四年刊梓,时间上正相吻合。这样看来,杜本的序文大概作于至正初年,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刊刻于杜本作序后不久,即至正四年。
四
任士林一生主要活动在江浙地区,晚年生活在杭州。他在郝天挺荐授安定书院山长之前,曾担任过上虞教谕,而书院山长,任士林也是未及赴任而卒,说明任士林在元朝没有仕途可言。他的交游对象,几乎是清一色的南人,没有蒙古和色目人。文集卷一《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卷二《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讲的是赛典赤之孙乌马儿的生平事迹及其奉命春运粮食至大都之事,似乎任士林与乌马儿有交集。其实这两篇文章的真正作者并不是任士林(详见下文),而应是他人的托名之作。从碑文也能看出,即便是托名者本人,对乌马儿家族的历史也不是很清楚。赛典赤赡思丁是成吉思汗西征时归附蒙古的,其后追随太祖、太宗、世祖等大汗,屡立功勋,尤以治理云南成就最为显著。赛典赤是回回贵族之意,赡思丁才是他的名字,因故成吉思汗以赛典赤称之,而不用赡思丁之名。赡思丁之父苦鲁马丁、之子纳速剌丁、之孙伯颜,也因此被称为赛典赤。但碑文在叙述赡思丁事迹时,却说“皇帝嘉之,赐姓赛典赤”“乃锡宗姓,曰赛典赤”,“赐宗姓”的说法不够准确。
另一篇涉及蒙古色目人的文章是《杭州路三教人士送监郡叙》,是大德十二年(亦即至大元年,1308)二月杭州路达鲁花赤任满北归之际,任士林写的送别之文。文中对即将卸任的达鲁花赤充满赞誉和感激之情,但文中却只字未提达鲁花赤的名字。任士林写这篇叙文,与其说是为达鲁花赤而写,倒不如说是为杜道坚而作,因为送别达鲁花赤的主人公是“三教人士”的代表杜道坚。大概任士林是跟随其师杜道坚送别达鲁花赤,而任士林很可能也是受杜道坚之命而作叙文,正如他在文中所说:“遂述其辞,以遗采风者得焉。”任士林与这位达鲁花赤应该并无交集。
从文集中我们也能看出,以南人为交游对象的任士林,以及与其交游的一些江南士大夫,仍有比较浓重的宋遗民情结。任士林所写的人物传记,排在文集传叙类第一、二篇的分别是《谢翱传》和《吴思齐传》,而谢翱和吴思齐均是宋遗民。谢翱曾跟随文天祥参加了抗元活动,宋亡后隐居不仕,游玩山水,“问遗事故迹”,所作歌诗“其辞隐,其义显”。又“善哭如唐衢”。吴思齐于宋亡后隐居浦阳,自号全归子。家贫,有人劝他出仕元朝,他回答说:“譬犹处子,业已嫁矣!虽冻饿不能更二夫也。”与方凤、谢翱等友善,相与放游山水之间。他曾与谢翱等登严陵山,恸哭西台,凭吊文天祥。此二人是典型的宋遗民,任士林为他们立传,传文中歌颂其忠义之举,且置于传文之首,显然这是任士林本人遗民情结的一种显露。
为文集作序的杜本,武宗、文宗、顺帝时多次征召,皆不就任,“与人交尤笃于义”。“喜从故都遗老承问往昔文献”,留意于文天祥、谢翱抗元事迹。上文提到的追随任士林的杨载和刘汶,在与任士林交往期间,均是一介布衣。杨载诗歌悲壮慷慨,歌颂宋末抗元的谢枋得等人的忠义事迹,如《题谢叠山遗墨》诗二首:
荆南失守见亡形,太岁徒闻忌丙丁。羸老扣心天藐藐,鬼神号哭夜冥冥。忠臣效死招乌合,烈妇捐生报雉经。辞气凛然遗墨在,再三寻绎泪双零。
故宫愁见黍离离,大厦元非一木支。义士忠臣徒走死,寡妻弱子谩伤悲。五经文字宁虚设,一代人才颇中衰。慷慨杀身犹易事,似公方可正民彝。
刘汶是南宋中兴名将刘錡后裔,与任士林年龄相差较大,任士林去世之前他也未出仕。他是元朝建立后才出生的文人,自然不是宋遗民,但他致力于古学,隐居不出,所撰诗文豪迈激昂,深得任士林赏识。其诗中即有“乾坤又元统,人物少咸淳”“栖迟唯故辙,无梦到飞腾”“东南诸老尽凋零”等句。这种对宋遗民的依依惜别之情,正是他遗民情结的一种流露。任士林的交游圈中,新朝的文人士大夫开始成长起来,其与旧朝文人间的交游,亦表现出一种历史的过渡特征,也体现出政权变易之后,江南士大夫的复杂情感与心态。《松乡先生文集》中任士林与这些士大夫们的往来酬唱,正为我们考察他们这种复杂的心态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任士林与道教的关系十分密切。文集中收录任士林与道教有关的诗文,计有《老子祠碑》《武夷山天游道院记》《杭州承天灵应观记》《大护持杭州路宗阳宫碑》《杭州佑圣观玄武殿碑》《杭州路开元宫碑铭》《杭州路纯真观记》《上虞县明德观记》《通玄观记》《天清宫记》《婺州路浦江县真常道院记》《四圣延祥观碑铭》《庆元路道录陈君墓志铭》《杭州路三教人士送监郡叙》《南谷原旨发挥叙》《重阳王真人悯化图叙》《三十八代天师广微真人小像赞》《题叶天师奉化镇海图》《题大涤洞天》《顾道士松岩图》《谢广微真人假以自然处士之号》《留别沈介石尊师》《寿杜南谷席上得寒字》《用韵酬陈渭叟林伯清》《重游昇元归寄陈道士》《寄题终南山甘河遇仙宫》《吕道录保安醮疏意》《谢恩醮疏意》《宗阳宫三清殿上梁文》《四圣延祥观上梁文》《宗阳宫讲堂上梁文》《四圣延祥观塑三清圣像请疏》《代道录司贺天师寿》《代四圣观贺宗师寿》《开元宫钟铭》《代贺天师生日呈子》《赵蒙斋入道疏》近40篇。
任士林与道教的密切关系,除了有古代文人往往与佛道二教多有交集的传统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杜道坚对他的器重与支持。成宗时期,道教茅山派领袖杜道坚受到重用,“提点道教,主持杭州宗阳宫”。大德七年(1303),“复被旨授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不仅在杭州的宗阳宫、纯真观,“若湖之昇元、报德,实护持之”。在他受到重用期间,宗阳宫的地位或许在开元宫之上。而开元宫是由南宋宁宗的潜邸改建而成的宫观,有元一代,在浙西道各道派中,作为胜朝的御前宫观,开元宫(也被称为大开元宫)地位十分尊荣。这说明成宗时期,茅山派在江浙一带的势力呈上升之势。据杜本序可知,任士林初到杭州之时,曾受到当地文人的质疑,“惊猜疑愕、怪笑非讪者,往往喧杂”,表明他在当时文人士大夫中并没有威望可言,甚至招人议论。但在杜道坚、赵孟頫等人的支持下,任士林得以在宗阳宫开坛讲学,授徒钱塘。宗阳宫给任士林提供讲学的场所,赵孟頫甚至亲自写信督促彦明等人“疾早择日收拾生徒为佳,想吾弟必不迟迟也”,为任士林开讲召集生徒。正是在杜道坚和赵孟頫的鼎力支持下,任士林得以在杭州士人圈内站稳脚跟,得到了施展才华、提升他在文人群体中的声望和地位的机遇。一时间“近远求文著金石者,户外之屦相接矣。往时怪笑非讪者,亦随以服”。因故,任士林对杜道坚自然心怀感激,并以师事之。而杜、赵、任三人的互相支持,无论是对任士林社会地位的提升、杭州乃至江浙地区茅山派势力的扩张,还是宗阳宫文人群体影响的扩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任士林本人,在其诗文中也因此体现出对道教的倾慕与向往之情。其《谢恩醮疏意》中即云:“伏念臣早涉世机,幸依道域,委心冲寂,岂曰渊宗”;《用韵酬陈渭叟林伯清》亦云:“我本厌尘市,志在栖幽清。还听客城雨,深夜愁寒更。山中两道士,孤铛煮雷鸣。漱沐得清谣,久却世上名。何用王子乔,相从学长生”。在这种背景下,任士林与道教的关系亲密自然顺理成章。
五
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具有较高的文献校勘价值。清末藏书家陆心源在《元椠松乡集跋》中指出:“是书有明泰昌时刊本,脱误甚多,此则其祖本也。”指出静嘉堂所藏元刊本,是明泰昌刻本的祖本,而泰昌刻本脱误甚多。不仅对泰昌刻本如此,元刊本《松乡集》也是其他明清诸刻本和抄本之祖本,自然可以校订其后各个版本之讹误。如《元诗选》所录一卷本,所收任士林五言诗有《寄陈宣慰帖》,核对元刊本卷八,可知该诗名中“帖”为“祜”之讹。陈祜是人名,宣慰是官职,即宣慰使。不仅如此,元刊本诗名中陈祜之名,也为我们校改元代文献以及学界研究成果中误将陈祜当作陈祐,又提供了一条佐证。
陈祜(1222—1277),一名陈天祐,字庆甫(父),号节斋。赵州宁晋(今属河北)人。《元史》有传。元人王恽《秋涧集》中提到的陈祜,均作“陈祐”,张养浩《张文忠公文集》卷18《陈天祥神道碑铭》亦作“陈祐”,《元史·高兴传》同。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陈祐传》,点校者根据上述文献,将底本中的“陈祜”均为“陈祐”。除此之外,清雍正《畿辅通志》、清道光二十年《河南府志》、1929年《宁晋县志》等文献,亦均作“陈祐”。《全元文》亦作“陈祐”,收其文《三本书》一篇。《元代人名大辞典》也作“陈祐”。《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于收录的《陈祜诗刻并跋》拓片之下,题识曰:“祜安庆甫……其名或作‘祐’。”认为陈祜一名是陈祐,且将“字庆甫”误作“安庆甫”。可见,历代文献以及今人研究成果中,仍有将“陈祜”作“陈祐”者。
对陈祐之名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台湾蒙元史专家洪金富先生。洪先生对《秋涧集·乌台笔补·论陈提刑改除不宜取解由事状》中提到的“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陈祐”进行订正,他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石拓《元单父道中琴堂书事诗》和《元陈祜过德州书老农诗》两份石刻资料,加上马祖常《石田集·章疏·论加恩典》,认为“祜”正“祐”误。但洪先生并没有展示碑刻的具体内容。其后南京大学博士生朱春悦又在洪先生论证的基础上,从古人“名”和“字”的对应关系入手,对“陈祐”乃“陈祜”之误又做了进一步讨论,并且补充了元明善《清河集》卷六《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以及《蒙兀儿史记》卷88《陈祜传》的资料。
洪先生和朱春悦的质疑是对的,“陈祐”的确是“陈祜”之误。任士林所作《寄陈宣慰祜》云:
客从昆仑来,遗我一寸胶。投之东海中,浊浪生青涛。世人饮泾水,沦浃如村醪。醉久与俱化,复恶醒者劳。客笑予亦休,泾水方滔滔。
从诗名来看,任士林作此诗时,陈祜已经出任宣慰使了。陈祜出任浙东道宣慰使是在至元十四年春,时年陈祜56岁,该年九月陈祜遇害。陈祜长任士林31岁,陈祜遇害时任士林25岁。诗名曰“寄”,诗中又有“客笑予亦休”之语,表明该诗当是陈祜在世时任士林所作,则任士林此诗当作于至元十四年春至九月间。陈祜、任士林为同时代人,全诗表达了任士林对陈祜的景仰和赞赏,以情理推之,任士林当不会搞错陈祜的名字,因故,这是订正陈祐为陈祜之误的又一条有力证据。
我们再来看看洪先生提到的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两份碑刻的具体内容。这两份碑刻均是陈祜的诗歌,并且是陈祜本人题写的。第一份碑刻是《单父琴堂诗》,包括《单父道中》和《琴堂书事》共四首(《全元诗》有录),兹仅录诗后陈祜按语如下:
予按部东鲁,及于此州,作是四诗,以实所见云。嘉议大夫、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赵郡陈祜庆父题于此城之琴堂。偕行者,历下士人李衎侃甫、张斯立可与。至元六年夏五月十有三日也。
可见,这四首诗是陈祜在任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按部山东单县期间,题刻于单县之琴堂的,时间是至元六年(1269)五月,且有同行证人李衎和张斯立。
第二份碑刻是《老农诗刻并跋》,包括《老农》诗两首(《全元诗》有录),以及宋景祁的跋文一篇(《全元文》有录),此外还有道光二十六年(1846)浙江桐乡人沈淮的识语。两首诗题写的背景是:“至元七载冬十一月二日,节斋陈祜按部过此,乃书《老农》二诗于平原之廨舍。”宋景祁作于至元八年(1271)三月的跋文中说:“公行按,因书此诗于公馆,州牧黄侯彦文、同知德州事金台阎侯巨川、德州判官古兖马侯颐之暨长史渤海马君国宝聚而言曰:‘公之忠爱,乃见于诗,诗之质厚,有章其化,而楮墨不可以恒久。’于是召匠刊石,庶永其传。”可见这两首诗也是陈祜自己题写的。两份碑刻中的几首诗,均是陈祜自己题写,自然陈祜不会写错自己的名字,因故陈祐乃陈祜之误当无疑。
六
元刊本对《松乡集》其他版本的校勘价值很高,因为其后的版本,往往是根据较早的版本刊刻或誊抄的,正所谓元刊本是最早的祖本。我们可以以元刊本与《全元文》所录任士林文(以明万历刻本为底本)、四库本、明初刻本、修补本、清抄本以及《元诗选》所录一卷本等版本进行对校,通过一些具体的例证来体现元刊本的校勘价值。
《全元文》是元代文献汇编整理的一项大工程,为学界利用元人之文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其中所录任士林文,编排顺序与底本及其他各版本均不同,是按照全书统一格式编排的,共分为六个部分,并且用四库本做了校勘。其中第二部分所录《玄经原旨发挥序》,是从《正德道藏》中辑录的集外佚文。第一部分所录《刘思鲁侍父之浏阳叙》,“思”乃“师”之误。刘师鲁乃刘汶(前文已提及),杜本的序中就提到他很推崇任士林。任士林该序伊始即云:“鄜川刘汶侍父之浏阳”,且文中两处均提到“师鲁”。元人蒋易所辑《皇元风雅》,即作“刘师鲁鄜川刘汶”;王沂亦云,元蜀人林彦立,“其游如弘农杨载仲宏、鄜刘汶师鲁,皆敬畏之”。第二部分《考亭先生聚星屏后题》,“然尝观太史公《天宫书》”,“《天宫书》”乃“《天官书》”之误。第六部分《定光寺立经藏吉语》,“八万四毋陀罗尼”,“毋”乃“母”之讹。
在《全元文》出版之前,四库本是《松乡集》最为通用的版本。如前所述,四库本卷首仅有提要,无元刊本卷首的三篇文章以及目录,各卷之下亦未列该卷之体裁。四库本正文中的讹误情况十分严重,如卷一《平章政事赛音迪延齐荣禄公世美之碑》、卷二《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题名和文中的“赛音迪延齐”之名,均是“赛典赤”之误改。卷一碑铭中的“乃锡宗姓,俾恢先烈”,元刊本作“乃锡宗姓,曰赛典赤”,亦将“赛典赤”之名进行窜改。碑铭中“迫四月二十有一日”,“迫”乃“迨”之误;“尝间公行事”,“间”乃“闻”之误;“连粜财赋府米一十万石”,“连”乃“运”之误。卷三《郑氏夫人墓志铭》,“密缝手熨”,“手”乃“平”之误;“且从事府帅家间”,“间”乃“问”之讹;“归来有日矣”,“来”乃“未”之讹;“思曾六岁”,“思”乃“师”之误;“或曰:‘南戍远’”,“或”乃“戒”之讹。《汴张府君墓志代赵子昂作》“故交终不以游”,“交”乃“来”之误。卷四《谢翱传》, “往桐庐”,“往”下脱“来”字。《吴思齐传》,“谷其怜之免女欲弃者”,“怜”乃“邻”之讹;“谋庶兄者再”,“谋”乃“让”之误;“常逢其故也”,“故”乃“固”之误。《刘思鲁侍父之浏阳序》,其讹误情况同《全元文》。卷八《寄陈宣慰帖》,同《元诗选》一样,误“祜”为“帖”。《过华亭留别吴山诸友》,其中“吴”,元刊本、明初刻本、修补本、清抄本、《全元诗》均作“湖”,而任士林所作诗中,正有《湖山堂》一诗,因此四库本作“吴”误,《元诗选》同四库本,亦误。
国图所藏明初刻本,是国内现存《松乡集》最早的版本,也是除元刊本之外最早的版本,国图将其列为善本,可见其版本价值亦很高。卷三《故奉直大夫赵公墓志铭》一文中,从“鲁事。凌州西迫御河”以下,至《经历阮公墓志铭》中“且赀奉嬉游”,整页缺失,元刊本存,可补该页之缺。卷十自《开元宫钟铭》“皇风驾,祝”之下,至《赵蒙斋入道疏》“三教并立天地间”,亦缺整页,中间还包括《佑圣观牛鼎铭》《肃堂铭》《代贺天师生日呈子》三文,元刊本同样可补明初刻本之缺失。
修补本是光绪十六年,孙锵在明泰昌刊本的基础上进行补刊的修补本,被杨讷先生选入《元史研究资料汇编》之中,因此也是《松乡集》较好的版本之一。该版本中赵孟頫所撰《任叔实墓志铭》,“得湖州安定书院”前脱“仅”字,目录卷一下“记”后脱“碑”字,目录卷三墓志中,“临淮府君墓志铭”,“府君”后脱“王公”二字,目录卷八“海扇”诗名下,元刊本有“海中有甲物如扇,文如瓦屋,三月三日,潮尽乃出”双行小字,修补本无,可补;目录卷九“侍家君行雷公山中谒大父墓因知渊明韵”诗名中,“知”乃“和”之误(修补本正文诗名即作“和”),卷三《承事郎柳惠考妣墓志铭》中,“尔父年来四十”,“来”乃“未”之误。元刊本也可补修补本残缺之处,如目录卷七“题刘忠公谏草后”,修补本“题刘忠”三字漫漶不清。
国图藏清抄本,亦属善本。卷首依次为洪武时期江陵熊钊的序文、陆文圭序文、杜本序文、《任叔实墓志铭》及目录。正文之后附有永乐三年(1405)冬十一月胡俨《题任松乡先生文集后》。抄本依据的应当是元刊本,或者是以元刊本为底本的明刻本,尽管抄本无板框,但每半页行数、字数,与元刊本完全相同,可见抄本忠实于底本。即便如此,抄本的讹脱倒衍等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如《任叔实墓志铭》中,抄本于“是四明任叔实”之下,脱“之文也。余始闻叔实,梦寐思见之。数年,叔实”共17字,“止于斯”后脱“也”字。目录卷七《又华国如此山二师诗卷后题》,“又”乃“文”之讹(抄本正文中即作“文”)。目录卷八《寄陈宣慰祐》,同《元诗选》一样,误“祜”为“祐”(抄本正文中即作“祜”)。目录和正文卷八《荒村市》,“市”乃“布”之讹。卷三《承事郎柳惠考妣墓志铭》中,“俾尔有事进”,“事”乃“仕”之讹(抄本于“事”旁有小字“仕”字,概为藏书者或读者之批校);“既辟门南江浙省掾”,“门南”二字为衍文;“皇天寔存”,“存”乃“闻”之误;“宗妬之奉”,“妬”乃“祏”之误。《郑氏夫人墓志铭》中,“蜜缝平熨”,“蜜”乃“密”之讹;“附姑之兆也”,“附”乃“祔”之讹;“独何由乎”,“由”乃“尤”之误;“子读兮书”,“读”乃“诗”之讹,且“兮书”乃“书兮”之倒文。卷四《谢翱传》,“所知论没”,“论”乃“沦”之讹;“往来洞庐”,“洞”乃“桐”之误;“翔自若也”,“翔”乃“翱”之讹;“品居仁”,“品”乃“吕”之讹。
《元诗选》是从元刊本卷八、卷九两卷诗中摘录34首汇为一卷而成。前文已提到其中的个别讹误,再如《寄陈宣慰祜》,“浊浪生清涛”,“清”乃“青”之误;《海扇》“对天摇动不如烹”,“天”,元本作“人”,当是;《四雁图》“孤咮双翎睡古香”,“古”乃“舌”之讹。
此类例子,在各个版本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四库本讹误、窜改之处,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以上仅选取《全元文》、四库本等六种版本进行比对,并通过各版本的一些具体例子来体现元刊本的文献校勘价值。唯主旨于此,故于六种版本之全文,则未及一一校对。
七
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存在误收他人冒名之作。上文提到的卷一《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卷二《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即是如此。卷一碑文中提到的“赛典赤荣禄公”,并不是赛典赤赡思丁,而是赡思丁之孙、纳速剌丁之子乌马儿。据碑文,乌马儿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事是在“既莅政之岁冬十有一月”。这里的莅政之岁,碑文中没有名言,查其他史料,可知是英宗至治元年(1321)。任士林卒于武宗至大二年(1309),他怎么可能为其死后12年才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乌马儿撰写碑铭呢?无独有偶,《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提到赛典赤荣禄公春运粮食至大都一事,与碑文中提到的“春运五十八万,以四月到京”,是指同一事而言,赛典赤荣禄公也是指乌马儿,因此这篇记文和碑文一样,也不可能是任士林所作。窃以为,应该是任耜在编纂刊刻其父文集时,收入了任耜自己或者是其他人托名其父所作之文。余大钧先生在撰写乌马儿词条时,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正是《松乡先生文集》中的这两篇文章。而元刊本这种误收他人托名之作的情况,被其后的《松乡集》各个版本全部继承下来。如此看来,我们对《松乡先生文集》中的诗文,使用时还需持比较慎重的态度,首先需要判断文章是否是任士林本人的作品。
此外元刊本也存在一些校勘方面的问题,我们以目录为例。卷四《正一先生传》,正文中“正”作“真”,《全元文》、四库本等亦作“真”,可知“正”乃“真”之误;《张仲宽教授宜兴叙》,正文及《全元文》、四库本“宽”均作“实”,元人仇远、戴表元、方回、傅若金、龚璛、陆文圭、杨载、袁桷、袁易、赵孟頫等诗文中也均作“实”,可知“张仲宽”乃“张仲实”之误;卷六《宝鹿赋》篇名,据正文、《全元文》、四库本,可知“鹿”乃“麓”之误;卷七《跋史文静公遗黄司户襄阃书后》,据正文、《全元文》、四库本,可知“静”乃“靖”之讹;《题叶天师凤化镇海图》,“凤化”乃“奉化”之误;《题吴子行瘗猫文后》,“吴”乃“吾”之误,吾子行即吾丘衍,杜本的序中也提到他与任士林友善;卷九《荅初阳台》,据正文及四库本、《全元诗》,“荅”乃“登”之误。再据元刊本正文、《全元文》、四库本等,可知卷六《蟠松赋》之后,脱《凤花赋》篇名,卷七《题方白云山蔬谱》之后,脱《陪杜南谷踏雪上白石洞天赋返招仙辞》篇名。元刊本的这种不足,在古籍中比较普遍,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文献本身的价值及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