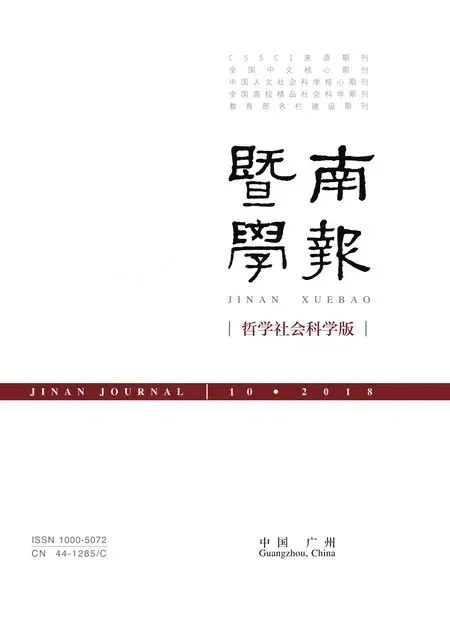文天祥的“自述”与“他述”
——以文天祥全集的编纂为中心
[日]近藤一成 撰, 尤东进 译
为宋王朝殉节而死的状元宰相文天祥,其生命价值取向被后人广泛称赞,甚至有人认为文天祥的客观存在是宋代士大夫政策的最后的绚丽篇章。此前,笔者曾撰文探讨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对文天祥能够作出怎样的评价,同时一并指出作为今后课题之一的便是文天祥全集的编纂问题。
获悉文天祥言行等信息的最基本的史料,无疑是收录在其文集中的本人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指南录》《指南后录》《纪年录》《集杜诗》等。上述著作详细记录了从南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二日,文天祥前往驻屯在临安城郊外皋亭山的伯颜军营起,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九日,文天祥在大都受刑处死这一期间他的言行。显而易见,上述这些著作都不是在正常情况下写就的。《指南录》收录有“是年夏五(月)改元景炎”的准确纪年的后序,内容是文天祥从皋亭山被裹挟北行,途中在京口脱身,再从通州出海,由海路至台州登陆,其后再经陆路从温州至福州福安这一行程的具体描述,这篇后序极有可能是在福建福州写成的。此外,记录文天祥成为元军俘虏之后,截至投入大都牢狱这一期间事迹的《指南后录》,以及在狱中写成的《纪年录》《集杜诗》等,它们是如何从大都的牢狱之中传出,并最终被收入一般认为是在江西庐陵刊刻的《文山先生文集》之中的呢?其不明之处甚多。
本文首先简单地介绍迄今为止的关于文天祥文集版本的研究成果,接着探讨文天祥大都狱中之书的编纂与流传。中国的相关基础性研究多利用在日本很难见到的珍稀版本以及各种族谱等,故在具体细节的考证方面,供笔者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几乎没有。
一、文天祥文集的版本与流传
最新的文天祥传记研究当为俞兆鹏、俞晖合著的《文天祥研究》。在该书第十章第一节“著作流传”中,作者列举了现存文天祥文集二十四种,以及包括单刊在内的文天祥著作近六十部。关于现存《文山先生文集》的版本系统,前人研究成果甚多,其中最简单明了的是由刘德清先生执笔的《宋集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明景泰刻本《文山先生文集》(17卷,别集6卷,附录3卷)之解题,姑引其文如下:
文天祥全集在宋代未及刊行,入元,始由其孙文富编为五十卷,刻板传世(清同治版《富田文氏族谱》引乾隆《文氏通谱信国公遗翰》),但传本极少,亦未见他书著录。元贞二年,文天祥故里刻《文山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大德元年又刻《后集》七卷,世称道体堂本。元人刘壎《隐居通议》卷十二详载其事。道体堂原刻虽在明清之际散佚,但其跋语九条却赖后世刻本得以传存,道体堂本亦为后世各《文山集》之祖本。据《绣谷亭薰习录》载,明、清两代,世人敬慕文天祥忠义气节,其诗文刊本多达二十余种。又据邓碧清《文山集版本考》(《宋代文化研究》第二集)考证,明、清刻本尽管版帙繁多,追遡其渊源,可谓“一个源头,两个系统”,即诸刻同源于‘道体堂本’,又大体分成景泰本、家刻本两个系统。景泰本系统有景泰本、正德张祥本、嘉靖鄢懋卿本、张元谕本、万历胡应皋本、崇祯钟越本、崇祯间张起鹏刻本等。家刻本系统由文氏家族翻刻,盖发端于文承荫刻本,现存有嘉靖间无名氏刻本、万历二十八年萧大亨刻本、万历崇祯间无名氏刻本,家刻本系统普遍存在编次欠审、校勘不精的缺点,其价值低于景泰系刻本。清代刻本虽多,但都是明刻的翻版,而以家刻本为主,其中雍正三年文氏五桂堂刻本影响最大,一再翻刻,但该本仍然沿袭着明家刻本之误。究观《文山集》诸刻,其初衷本为表彰忠义气节,往往致力于文集之编刻与附录资料之累积,而忽视遗文搜集及版本比勘。可以说,《文山集》迄今尚无一完善之本。
此本由韩雍、陈价刊于景泰六年,前有韩雍、韩阳、钱习礼、李奎序,又有道体堂本二序。据韩阳等序,知此刻所据为尹凤岐居馆阁日钞本,经转运使陈价校勘、编次,又呈正于江西巡抚韩雍,遂得锓梓传世。又据卷首道体堂本序后所载跋语:“《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予合而为一,姑存二序于此。”则系合道体堂本前、后集为《文集》十七卷。同时,又“访求遗稿,编次成帙”,为《别集》六卷;又辑“名公所述传记哀挽”,为附录三卷(李奎《文山先生别集序》)。则此本系据道体堂本重编,并有所增补。道体堂刻板于明初失传,其本亦于明清之际散佚,景泰刻本遂为现存《文山集》最早之版本,亦是后世诸刻之祖本。
目前,日本最容易阅读、利用的是以明嘉靖三十九年张元谕刻本《文山先生全集》为底本,并参考各种版本而进行了校勘的熊飞等编集、校点的《文天祥全集》,这是目前最好的整理本,本文所引《文山集》之原文即依据此整理本。
如上所述,现存文天祥文集的祖本即已经散佚了的道体堂本;同时可知有助于考察道体堂本的主要线索为:景泰本所收录的道体堂本之两篇序文,以及从卷三“御试策一道”至卷十二“大使司回”中标注为“道体堂谨书”的九条或长或短的按语。而且,上述按语被以《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为主的各种现存文天祥文集所承袭和收录。
二、关于道体堂本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道体堂本两篇序文的主要内容。首先,标注有“元贞二年(1296)太岁丙申冬至日道体堂谨书”之具体日期的第一篇序文,其文如下:
先生平日著述,有《文山随笔》凡数十大册,常与累奉御札,及告身,及先太师革斋先生手泽,共载行橐。丁丑岁,犹挟以自随,一旦委之草莽,可为太息。今百方捜访,仅仅有此。因自宝祐乙卯后,至咸淳甲戌止,随门类略谱其先后,以成此编。虽首尾粗备,而遗佚者众矣。如诗一门,先生所作甚富,中年选体更多,今诸体所存无几,而选几绝响,更可浩叹。至如场屋举子之业,自有旧子黄册板行。又如《年谱》、《集杜》、《指南录》,则甲戌以后之笔,不在此编。其曰《吟啸》者,乃书肆自为之名,于义无取,其实则《指南》别集耳。因著其说于集端,以谂观者云。
此序文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文天祥常常随身携带著作原稿、文书的相关记述。当时的一般官员常常随身携带表明自己身份、地位的官文书如告身、敕黄、印纸历子等。“累奉御札”“告身”是上述所谓的官文书。文天祥其他随身携带的还有包括诗文在内的十数册《文山随笔》,这些后来成为文集中的重要著作。第二,道体堂本中有确切纪年的篇帙只收到咸淳十年为止,其后的则没有收录。由此可知,道体堂本相当于景泰本的卷一之“诗”至卷十七之“乐府”“上梁文”“公牍”“文判”等,别集卷一之《指南录》至卷六之《纪年录》则在道体堂本之外。第三,序文表明文天祥随身携带的行李曾在“丁丑岁”即1277年散失,其事恐怕发生于元军猛烈进攻的该年八月之后。
且来看看文天祥的具体行踪:1277年的上半年,文天祥与江西各地蜂拥而起的义军互相配合、策应,收复了赣州会昌县,随即北上,在雩都县打败元军,遂进入兴国县。然而,兵锋在此受挫,且在赣州和吉州的攻城战中败北,后向吉州东北方向的永丰县转移,又与南下蒙古大军遭遇,被迫转移至离吉州与赣州交界处不远的空坑村,在这里文天祥一侧一败涂地、溃不成军。由于失散的妻子被元军俘获、部下的不断牺牲以及身边人的机智,使文天祥孤身一人得以脱逃。将行李“委之草莽”,恐怕就在这个时候。从现在的地图上看,空坑村直线距离文天祥的故乡吉安市富田镇仅四十公里。虽然其间有几座山岭,不能作简单的对比,但庐陵县城距离富田镇也只不过大约五十公里。对道体堂本的编纂者而言,文天祥的手稿并不是遥远且行踪不明之所在。
接着,考察大德元年丁酉(1297)中秋日之第二篇序文,其文曰:
文山先生文集既绣诸梓矣,然散佚尚多,其为人所什袭者,间复出焉。今随所得编类如前,为后集。更当访求,陆续入集云。
由上可见,距离前集刊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后集即得以编纂、刊行。
此外,景泰本在采录了道体堂本《文山先生文集》两篇序文之后,空两字记云:“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子(予)合而为一,姑存二序于此。”之后又附加双行小注云:“以上俱旧集所载。”如果没有此双行小注,似可简单地认为景泰本首次将道体堂本前、后集合为一集而刊刻、印行。但“旧集”究竟指何本?而“俱”字是否包含道体堂序和“合而为一”云云之注记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呢?关于景泰以前的刊本,除了事实上尚不能确认的文富编五十卷本外,其他则不存在。
从上节刘德清的景泰本解题中,可知韩阳的序文中提及《文山集》的抄本。其抄本有两个。第一,在韩阳父亲韩经的藏书中,存在韩阳祖父的手抄本二帙,但这个抄本不是完本,且在第二次的火灾中付之一炬,化为灰烬。附带说一下,韩经是绍兴人,乃韩琦的十二世孙。另外一个是以景泰本为底本、翰林侍读尹凤岐的抄本。尹凤岐在馆阁任职时抄录了馆藏的完本,后按察副使陈价在吉州从尹凤岐处借出并刊刻。如果尹凤岐抄本是汇合道体堂本前、后集而抄录,那么这个抄本就是所谓的“旧集”,这与双行小注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且从逻辑上来看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上述也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至于道体堂的名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一《文山集》条云:“……世称道体堂刻本。考天祥有文山道体堂观大水记,称自文山门入,过障东桥,为道体堂云云,则是堂本其里中名胜,而乡人以为刊版之地者也。”作为文天祥之号由来的文山是咸淳七年(1271)文天祥建立新家之处,位于“庐陵南百里”。文天祥拟在四十三岁时辞退,从而过上退隐山林之舒适生活,但当获知“江上有变”(襄阳危急、蒙古大军南下)之际,立即中断工程,故新家仅仅建成了厅堂。综上可知,道体堂是作为《文山先生文集》的刊刻之地而使用的,目前尚无记载表明其间的具体人物关系,且以往的研究中也未涉及。下面,笔者对此作出一些推测,以供参考。
如前所述,文天祥文集中存在数条“道体堂谨书”的按语,在最初的卷三“御试策一道”中,该按语用简短的文字,描述了殿试时的文天祥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他因吃河鱼而饱受食物中毒之苦的情景。同卷《己未上皇帝书》,是文天祥结束父亲守孝期满后刚出仕的上奏文,其中小注记述了得到状元及第的恩典后,如何补行“门谢”;最终得到恩典,文天祥被授予秘书正字。文中引用了授予秘书正字之诰辞中的部分文字。这表明,道体堂也回收了行踪不明的、原在文天祥行李之中的“累奉御札”“告身”等官文书。而在身边亲眼目睹文天祥被授予秘书正字的人,正是文天祥的弟弟文璧。如前稿所论,与兄长文天祥一起参加宝祐四年殿试的文璧,为了看护父亲的病体,不得不中断考试,最后没有进士及第。因此,守孝结束后的开庆元年,文璧与兄长一起进京,兄长积极谋求补行“门谢”,而他则积极准备殿试,并最终成功进士及第。
总而言之,可以说道体堂本与文璧的关系非常紧密。如下文所述,辛未(至元十八年,1281)之夏,前一年已滞留在大都的文璧,与狱中之兄文天祥所托付的著作一起南归,其时收到文天祥的一封遗书:死后墓所的位置、形制以及请求邓光荐撰写墓志铭等。文璧于大德二年(1298)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即后集刊行的第二年。刘岳申在《文璧墓志铭》中写道:“又求丞相遗文而传之梓”,由此可基本肯定文璧主导了道体堂本的刊行。在文璧周边理解其出仕元朝的人士非常多,但以自己的名字来编纂为大义殉难而死的兄长的文集,则多少有些踌躇。
那么,德祐以后的著作又如何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江西副使陈价、庐陵处士张祥先后刻之,附以《指南前录》一卷、《后录》二卷,则自德祐丙子天祥奉使入元营,间道浮海,誓师闽粤,羁留燕都,患难中手自编定者。《吟啸集》则当时书肆所刊行,与《指南录》颇相复出。《纪年录》一卷,亦天祥在狱中所自述,后又复集众说以益之。惟《集杜诗》以世久单行,未经收入。”关于最后的《集杜诗》,陈价景泰本之别集卷五为集杜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乃指张祥刻本,关于此点,邓碧清《文山集版本考》一文已详述。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道体堂本确实没有收录《指南录》以下诸书,此问题容下节进一步探讨。
三、狱中书的南传
本节主要探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等是如何写成的?其间又经历了什么?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能够读到它。首先,对下面一条关于狱中书的记载加以考察。
《纪年录》(《文天祥全集》卷十七)辛巳(至元十八年,1281)之注文云:
正月元日,公为书付男陞。公在缧绁中,放意文墨,北人争传之。公手编其诗,尽辛巳岁为五卷。自谱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为绝句二百首,且为之叙。其诗自五羊至金陵为一卷;自吴门归临安、走淮、至闽,诗三卷;号《指南录》,以付弟璧归。
在文天祥写了一封书信给养子文陞的记述之后,接着写道:文天祥狱中的诗文在北人中争传,同时文天祥将这些篇帙托付给其南归的弟弟文璧。此外,据上文可知文天祥曾自编自己辛巳之年为止的诗文为五卷。稻垣裕史先生认为,“公手编其诗,尽辛巳岁为五卷”,其五卷即为《指南后录》,主要旁证史料为刘岳申《文丞相传》中所云“自是囚兵马司四年。其为诗,有《指南前后》三卷,《后录》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顺带说一下,管见所及,现代通行本的《指南后录》从卷一(上、下)至卷三,只有三卷。如果文天祥自编之五卷者为《指南后录》,而其后文中所云“自五羊至金陵为一卷”之一卷,显然是《指南后录》之卷一(《文天祥全集》为卷一下),因此相关表述显得重复、累赘。同时,根据文天祥庚辰年正月十二日的自注(见《指南后录》卷一末尾),可知在文天祥《指南录》以后的诗文中,《过零丁洋》以下曾在惠州与后录本合为一卷。此外,《指南后录》的内容因刊刻时间、版本的不同而差别较大,将上述记载与现行诸本详细地一一对应,加以比对、分析,则非常困难。与“文”相对的是“诗”,笔者认为《集杜诗》二百首一卷、《指南后录》一卷、《指南录》三卷,故可笼统地记为全“诗”五卷。但是,在文璧南归的辛巳之夏,《指南后录》卷二已经存在,这与《指南后录》仅有一卷的记载明显存在冲突,容后日详考。不管怎么说,即使不是狱中书的全部,依然可以确定:在文天祥受刑的前一年,狱中书随着文璧的南归而南传。
俞兆鹏、俞晖的《文天祥研究》一书,在论述文天祥著作的流传时,呈现了上述之外的、与众不同的狱中书的流传,可资参考。首先,严格地说《指南录》并不是狱中之书。关于此书,在文天祥从广州押往大都之际,将如前所述相当于现在通行本《指南后录》卷一上的文稿在惠州交给其弟弟文璧,同时也将不完整的《指南录》交给了文璧。除此之外,“将亲手书写的《指南录》两册,一册赠予邓光荐,一册送给另一位友人宋行朝兵部官员曾宗甫”。又,《指南后录》卷一上在文天祥离开广州北上之时,已赠送给惠州教授谢崔老。此外,龚开的《文丞相传》中有文字云:“仆见青原邓木之(榆)藏文公手书《纪年》,皆小草,首尾备具。因求得誊本,取其首末为传”,详细介绍了《纪年录》的相关情况。阅读龚开的《文丞相传》之后,可以发现其的确是《纪年录》的节录,可见龚开并没有读到现行《纪年录》所付之注文。
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一书在探讨狱中书之时,还对文天祥受刑牺牲之后,搜集其骸骨、须发等使之归葬故里的张弘毅展开了论述。张弘毅,字毅甫、千载或千载心,文天祥挚友,与文天祥一起北行至大都。文天祥认为食元朝之官饭为不洁,所以张弘毅天天为文天祥送饭。在《集杜诗》壬午(至元十九年,1282)文天祥的自注中云:“是编作于前年,不自意流落余生,至今不得死。斯文固存,天将谁属?呜呼,非千载心,不足以语此。”后世史料亦有将张弘毅的字写作“千载”,而《文天祥全集》卷二有“拜罗氏百岁母之明日,主人举酒,客张千载心赋诗。某喜,赞不自已,见之趂韵”之小序的诗歌,可见其字为“千载心”。张弘毅搜集文天祥骸骨、须发等南归的记载,《宋史》本传以及早期的文天祥传均未记载。例如,刘岳申《文丞相传》云:“尝裹所脱爪齿须发寄弟璧。始终未尝一食官饭”,未见张弘毅之名。《纪年录》的各条注文中亦未提及此事。但是,同时代的王炎午在文天祥的祭文中写道:“庐陵张千载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这篇祭文具有特别的意义,容后文详述之。在后代,将此逸闻推而广之的则是陶宗仪《辍耕录》卷五“隆道友”,并进一步在遗骸、遗发等基础上,添加了《集杜诗》等遗文,使之一起南归。此外,明杨士奇《书集杜诗前》《题文山集杜句》两文,最早指出《集杜诗》文天祥自注中的“千载心”即“张弘毅”。杨士奇是庐陵的南邻、吉安府泰和县人,可能获得了《辍耕录》等之外的独家资料。
诚如前引《文天祥研究》一书中所言:“还在文天祥生前,他的著作就已被人收藏并逐渐流传”。除上文所引《纪年录》辛巳之注文外,壬午之注文中亦有“公囚系久,翰墨满燕市。时与吏士讲前史忠义传,无不倾听,感动其长李指挥、魏千户”云云,可以想象文天祥的诗文正是通过他们之手而得以流传。
四、关于《指南录》
严格来说不算狱中书的《指南录》在1227年的吉州空坑曾一度遗失,在文天祥的手里只有残本。其后,在大都狱中,如何对其增补,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记载。但如前所述,在文璧受托之书中存在《指南录》三卷。与其他狱中书不同,显示其独特的流传方式的刊本目前仍然存在。
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有被认为是南宋刻、元初印的《新刊指南录》四卷(其中附录一卷,共两册)。该本据说是陆心源的皕宋楼和毛晋汲古阁旧藏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记载其版本信息如下:
版式:左右双边(15×10.7厘米),有界。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六字。版心线黑口, 黑鱼尾,重叠字处用“又”。遇宋讳字及宋朝处,顶头空一格,备考。其书为入元后刊行,故北兵、文天祥等字眼均被挖空。本书被列入史部,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众书目均将其列入集部别集类。藏书印:竹坞真赏、毛晋、毛氏小晋、毛晋私印、汲古主人、宋本、汪文琛印、平阳汪氏藏书印、三十五峰园主人、汪士钟印、民部尚书郎、鹪安校勘秘籍、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秘籍志》卷一〇之四五)。
同时,从内容上来看,有些现象值得注意:一是重叠处使用“又”字,以及挖去“贼”等字眼。二是自序中文天祥的名字也被删去。三是存在墨斑涂去的情况,如将标题“纪事”两字墨斑涂去。至于为何有墨斑,原因尚不明。此外,有几处“圣旨”之前部分有两字空格,且“虏酋”“大酋”“虏”等字眼被删去;“胡”“逆”等字以及人名“吕师孟”之“吕”字被删除。但是,上述字眼有时也被保留下来。静嘉堂解题中的南宋刊、元初印之说,显然是沿袭了陆心源“当是景炎元年宋未亡时所刻,入元后将版挖空耳”之见解,但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版本目录学家尾崎康先生在《日本现在宋元版解题·史部(上)》中指出:“其字体是元末至明初的风格,再从自序之德祐二年来看,不管如何地推崇文天祥,在没几年就灭亡了的、苟延残喘的南宋时期内可能刊刻么。再进一步说,即使删除、挖空了上述众多字眼,在元朝的鼎盛期它被容许刊行么。因此,我们不妨推测其是以在元朝的衰退期或明初加入墨斑的本子为底本而刊印的。无论如何,应是‘元末明初’刊刻的。”这就否定了南宋末刊、元初印之说,并推断其为元末或明初刊刻而印行的。我们理应尊重多次实地调查宋元刊本的尾崎先生的见解,但他判断的依据仅仅是感性认识的“字体”而已。因此,在思考静嘉堂藏《指南录》的刊行时间这一问题时,考察从南宋起至元末明初为止的吉州版刻本书影,便显得十分有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南宋前半期同为庐陵的周必大文集的家刻本。
静嘉堂文库藏《周益文忠公集》,存七十卷,皕宋楼本,有开禧二年(1206)中秋之序文。国家图书馆亦藏有该文集,且与静嘉堂藏本为同一版本,但仅存二卷(书稿)。《中国版刻图录》认为其为嘉泰四年(1204)周必大去世后的家刻本,且刻工是嘉泰前后、吉州地区的名匠,与同为家刻本的《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合称“庐陵三绝”。在《中国版刻图录》中收录了后两部书的书影。
《中国版刻图录》的编者认为,家刻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即为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家刻《欧阳文忠公集》的原刻吉州本(存一百三十三卷),同时指出,在这之后南宋江西地区产生了行款版式与其完全相同的翻刻本,而一般学者误以为其翻刻本就是吉州本。然而,日本的欧阳修研究者东英寿先生通过对日本、中国以及台湾地区现存宋版《欧阳文忠公集》的比较,认为家刻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并不是原刻本,而只是后来的翻刻本。原刻本据说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刊本十种之一,即现存四卷的“邓邦述跋本”。东英寿先生的考证及其结论正确与否,容另文探讨,这里再介绍他的另一种见解。一般认为很早即流入日本的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欧阳文忠公集》(存一百二十七卷),与家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为同一版本,均是庆元二年刊刻。但东先生已论证并指出天理本并不是周必大的原刻本,而应属于周必大的儿子周伦修订后的版本系统。再进一步,在前引《周必大原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百五十三巻について》一文中,他比较了天理本和国家图书馆藏本之《居士集》卷一中的刻工姓名,它们完全不同,可见两者不是同一版本,但存在着翻刻的关系。
周必大家刻《欧阳文忠公集》的原刻本,究竟是现存南宋诸刊本中的哪一种,姑且不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前人所述,在南宋孝宗、宁宗朝所刊刻的诸本中,其间刻工的姓名存在很多重复,由此可见其时刻书业的中心之一便是吉州。周必大家刻本以及其多种翻刻本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当时吉州刻书业的繁荣。再者,庐陵本《东坡先生诗》显示了迄止元代,吉州依然继承了其繁荣的刻书传统。
关于静嘉堂本《新刊指南录》何时、何地刊行,如上所述有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两种意见。鉴于存在以南宋周必大家刻本为代表的吉州本传统,因而一味否定宋末元初说似欠妥。下面,对此问题再略加探讨。
稻垣裕史先生以现存最早的版本——静嘉堂《新刊指南录》为基础,比较了卷首之序与后序(《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所收《指南录》作自序和后序)这两篇序文的内容,从其不同处入手论证了《指南录》的编纂、成书过程。不仅仅内容,语法和遣词造句等相同之处甚多的两篇序文,经过仔细研究,从中可以看出文天祥编撰《指南录》前后意图的变化。
原本,《指南录》卷首收录同一作者的两篇序文,这一体例本身就显得十分特别。首先,介绍一下稻垣先生的结论。两篇序文中,各自有“德祐二年(1276)闰(三)月日”和“是年夏五(月)改元景炎”的纪年。从后序的记载来看,《指南录》四卷的构成为:卷一为至伯颜军营交涉止;卷二为被裹挟北行起,至京口止;卷三为在京口脱身,至通州止。以上三卷是文天祥滞留通州期间,或者在去台州的船上编辑,与此同时并写成第一篇自序。脱离虎口的安稳感,以及欣闻二王在永嘉建立元帅府,迫切希望与二王合流,成为该篇自序的基调。但是,经海、陆两路长途跋涉,终于与已登基的端宗政权合流,这一期间的诗作被编辑成第四卷,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后序。虽然多次虎口脱险,但后序非常纠结并自问至今为何还活着。与前一自序不同的是,后序中极力表明自己是为了保全君、亲之义而苟且偷生的,应“誓不与贼俱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其后当从容就义,从中可以发现论调的前后变化。
稻垣先生进一步指出,作为被裹挟北行投降使团中的一员,脱险而出的文天祥有被认为是北方间谍的极大嫌疑,并推测在面对端宗政权冷淡的态度时,在与自序完全不同的后序中,必然有浓厚的自我辩解的味道。而事实上,从京口脱身,行至真州,正因为有北敌间谍之嫌疑而没有使文天祥入城,同样也不允许其接近扬州城门。进而稻垣先生更认为,从上述历史背景出发,文天祥在编辑卷四的过程中,萌生了为取代先前写就的自序,而重新撰写后序,并以后序为正序的意图。正如笔者前稿中所指出的那样,谢太皇太后集团要投降的意愿,其实在德祐元年十二月已经确定,即派遣文天祥出使伯颜兵营时的第二年正月十二日,早已决定投降。甚至可以认为,此时文天祥作为投降的障碍,朝廷给其和谈使节的身份从而排挤他。果真如此,文天祥为何不拥戴二王、从都城脱险而与主战派共同行动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主战派内部存在分头行动、各担其任的意图,而仅仅是文天祥与其他主战派之间的关系不睦,所以自己单独行动而已。文天祥的这种处境在端宗朝仍然没有改观,原本指望在二王的直接领导下抗击蒙古的文天祥,结果却不能在行朝内立身、活动,有所作为,而不得不离开二王,孤身转战福建和江西。
《指南录》是纪实性文字,是端宗政权建立后,以参加政府为目标的文天祥为自己脱险而辩解的文字,并以现在之“后序”作为正序而重新作序的。上述稻垣先生的解释虽然只是推测,但极富有可能性。但是,《指南录》并不是作为最终定稿而编纂的,因而其自序与后序两篇序文的原稿都流传至今。再者,作为《新刊指南录》附录卷之五,收录了被认为是在从福州前往南剑州、汀州途中吟咏的《和自山》及其自注等,而在通行本《四部丛刊》收录的嘉靖本《文山先生全集》之《指南录》中却被收录在卷四之中;由此可见,《新刊指南录》是文天祥本人在生命最后阶段所持有的原稿,以其最初的形态而刊行的。
那么,这种刊行是在何时、何地完成的呢?非常遗憾尚未发现与其相关的直接史料。但稻垣先生的论文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线索,即对《文山先生全集》附录王炎午《生祭文丞相》一文的解释。吉州安福人王炎午(1252—1324),是咸淳十年太学上舍生。临安献城时,丁父忧,返回安福。听闻文天祥起兵,遂投其幕下从军,但因父亲没有安葬,老母有病而再次返乡。文天祥被元军俘虏,王炎午认为“仆于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为报”,随即写成《生祭文丞相》一文。文章以“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开篇,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叙述文天祥可从速殉难就义的理由。有感于时势的同乡、建康军判签刘应凤读完之后,非常感慨,于是一连复写了数十本,并抢先到达从赣州至洪州的、文天祥被押行至大都的必经之地,将其张贴在驿站、渡口、山中小店等处,希望文天祥看到后早日自决。其后,文天祥被处决,王炎午又立刻写下了《望祭文丞相》一文,以示悼念。字数是《望祭文丞相》数倍的长文《生祭文丞相》非常脍炙人口,流传很广,连元朝人也十分关注。
稻垣先生认为王炎午《生祭文丞相》一文中,反复强调文天祥“可死”,是意识到《指南录》后序的存在而写成的。从文中“华元踉蹡,子胥脱走,丞相自叙几死者矣。诚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等可知其读过《指南录》。如上述观点正确,与景炎二年(1277)在战乱中遗失的文天祥的其他著作不同,《指南录》则很好地保留了原貌,其抄本极有可能正是由去过汀州的王炎午带回吉州的。如此,可以确切地认为《新刊指南录》正是在元初有着浓厚刻书传统的吉州而被刊行的。一般认为王炎午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高宗、孝宗朝都十分活跃的王庭珪的族孙。王炎午出身于吉州非常有影响力的家族,同时作为南宋末年激烈批判政府的据点——太学的上舍生,其言论可谓当时舆论界的代表。吉州地域社会士人的动向、言行不仅给文天祥本人,还给文氏一族施加了巨大影响。
代结语——以《纪年录》为中心
作为狱中书之一的《纪年录》是文天祥的自编年谱。《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等基本上是诗集,都附有文天祥自身所作的注,《纪年录》与上述诸书最大的不同是,该书中附加了众多的同时代的史料。《纪年录》卷首详细列举了其注文的出典,其文曰:“正文乃公狱中手书。附归全文集注,杂取宋礼部侍郎邓光荐中甫所撰《丞相传》《附传》《海上录》《宋太史氏管发国实》《至元间经进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庆安刊行《伯颜丞相平宋录》,参之公所著《指南前后录》《集杜句诗》前后卷,旁采先友遗老话旧事迹,列疏各年之下。”由此可见采录了邓光荐所撰的《丞相传》《附传》《海上录》《宋太史氏管发国实》《四年野史》、伯颜丞相《平宋录》等书,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指南前后录》《集杜句诗》前后卷以及“先友遗老话旧事迹”。
管见所及,目前尚无资料表明现行《纪年录》由谁、何时编纂而成。但是,在正文的最后之年壬午(1282)年的注文中,记述了大德九年(1305)文天祥妻子欧阳夫人之死与埋葬之事,并以至正元年(1341)在河州养老的文天祥之女文环的一些情况作为结语,此时离文天祥去世已达六十年之久。听闻“先友遗老话旧事迹”不需要经过太长的时间,且可在注文中按照年月连续地记录下去。《平宋录》在大德八年(1304)刊行,由此可以推断《纪年录》卷首所谓的出典,经过了后人的增补。关于邓光荐的《文丞相传》,景泰本附录卷三除了收录其“论”与“诗”之外,可能现已不存,因而这篇散佚之文显得非常珍贵。而《附传》很可能就是现在各种文集中作为附录而收录的《文丞相督府忠义传》。《海上录》容下文述之,《宋太史氏管发国实》和《四年野史》,则不详。
戊寅之岁(1278)的注文中有“四月十六日,大行皇帝遗诏曰”云云,全文载录了因遭遇暴风雨而驾崩的景炎帝的遗诏;紧接着上文,十七日征引了卫王昺祥兴帝的登基诏书;以下注文简短地记载了赠景炎帝庙号为端宗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上述记载均不见于它书,极有可能是从邓光荐的《海上录》中转引的。崖山之战时,邓光荐与陆秀夫在同一条船上。走投无路的陆秀夫在背负幼帝昺投水之前,曾将二王的记录亲手交给邓光荐,并临终嘱咐使其传之后世。这些记录恐怕就是所谓的宰相的《日录》。《宋史》卷四五一《陆秀夫传》云:“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邓光荐的《海上录》有可能就是陆秀夫所嘱托的《日录》,南宋亡命政权的遗诏与登基诏书被《纪年录》所收录,其理由十分容易理解,而元代《宋史·陆秀夫传》的编者对上述情况浑然不知。
《纪年录》庚辰、辛巳年的正文,只有“是岁囚”。最后壬午年的正文,记载了文天祥受刑被处死后,藏在衣服中作为文天祥绝笔的“叙”与“赞”,这显然是出于后来编纂者之手。庚辰之岁的注文中还记述了如下一则逸事:五月,弟(文)璧自惠州入觐,右丞相帖木儿不花奏其略曰:“此人是文天祥弟。”上曰:“那(哪)个是文天祥?”博罗对曰:“即文丞相。”上叹嗟久之,曰:“是好人也。”如前所述,辛巳之岁的注文中,记述了将狱中之书托付给文璧、身后的墓地以及请求邓光荐撰写墓志铭等。此外,还有至元二十年(1283)文天祥的灵柩回归庐陵故里、翌年得以安葬以及以后种种逸闻,再以文天祥妻子欧阳夫人、两位女儿文柳、文环的相关情况描述而煞尾。
最后,对本文题目“文天祥的‘自述’与‘他述’”作一简短的补充说明。一般而言,作为士大夫著作集——文集的刊行,都有将本人的言行(“自述”)流传后世的目的。但在编纂文集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他述”的因素。就文天祥而言之,在搜集、编纂曾一时失散的著作之际,数量虽然不多,但编者通过“道体堂谨书”的形式,直接添加了各种解说;然而更进一步,《纪年录》中不仅仅注文的分量非常大,而且在最后的三年中特别强调与选择出仕元朝的弟弟文璧之间的紧密关系,从中或许可以读出其独特的“他述”方式,亦可认为其是编者对自身所处境遇的反映。
关于乾隆三十年纂修的《文氏通谱·信国公遗翰》中所载之文富编五十卷的《文山集》,前引邓碧清一文指出:此刻本在《文氏通谱》以外,未见著录。因《文氏通谱》代代相传,其记载或有所本。但此本因内容、刊行册数以及政治上触犯禁忌等,传世甚少,元代已失传。然而,本文认为有一种可能性,即景泰本与文富本关系甚大。诚然,景泰本的四人的序文中均没有提及文富本。同时,只有李奎之序附在《别集》之前,且从景泰本中可以发现其首次将道体堂本中没有收录的《指南录》以下之诸书合刻为一帙,但李奎的序文丝毫没有谈及此事。此外,根据许有壬的序文,可知文璧之次子、文天祥养子文陞的儿子文富,刊刻刘岳申《文丞相传》的时间为元统元年(1333),而《纪年录》最后的注文中记述了至正元年(1341)文天祥女儿文环的相关情况,元统元年在至正元年之前七年。文富生卒年不详,但从时间上来看,并不存在冲突。又,如前所述,景泰本之序文中有注文云:“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予合而为一,姑存二序于此。”(以上俱旧集所载)如果认为此“旧集”即为五十卷之文富本,则道体堂本共三十九卷、《指南录》四卷、《指南后录》四卷(卷一有上、下)、《吟啸集》一卷、《纪年录》一卷、附传一卷,总共正好五十卷,那么无论如何,将狱中书合刻为一帙的正是在文富之时,从而景泰本才能够以现在的卷帙而编纂。邓碧清根据《富田文氏族谱》,记述了文富曾于至顺初担任兴文署丞,后累官至湖广省检校、延平守、嘉议大夫、温州路总管。从情理上来看,不可否认上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可以认为《文山先生全集》正因文璧、文富的“他述”而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