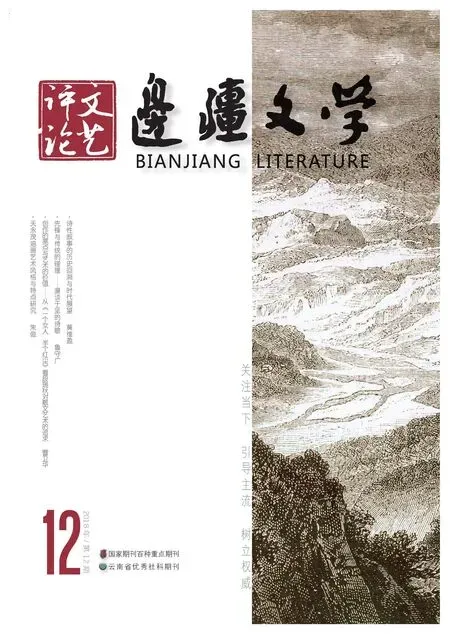本期摘录
黄维盈 诗性叙事的历史回溯与时代展望
所以,把诗性叙事重新提到“议事日程”,除了解决诗歌的思想境界、艺术水准等问题,同时也面临“写什么”的问题。比如,信手拈来的吃喝拉撤、家长里短等生活场景到底承载了什么?如何让私人生活与现实社会发生关联,如何让个人生活的特殊性关涉到大众的普遍性,确实是诗人必须正视的问题。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一定都具有诗学价值,我们当然不是在倡导一种简单的诗歌强行介入,但诗人对自己的日常叙事总得有一些“先知先觉”式的诗性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多寡,应当与文学常识构成审美对应。
鲁守广 先锋与传统的碰撞——漫谈于坚的诗歌
20世纪80年代之后,于坚便走向自己的诗歌之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主张和诗歌语言,开始引领起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于坚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代表作《尚义街六号》。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当时有很多人都怀疑“野怪黑乱”的它到底是不是诗?尽管从“五四”时期白话诗就产生并发展,但中国古诗千年来的传统使大多数中国人只能接受四言、五言、七言这样的诗,这是中国新诗合法性的问题。到“朦胧诗”阶段,学术界虽然有对其疑惑不解的地方,但还是承认“朦胧诗”是诗,而“第三代诗人”诗歌的境遇就不同了。
曹卫华 创作的亮点与艺术的价值——从《一个女人 半个红尘》看段瑞秋对散文艺术的追求
段瑞秋善于把这些作品的内容与自己书写的内容联系起来,让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分浸透到自己的内容中来,润泽、提升自己书写的艺术水准,同时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照、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关照、不同心理状态下的关照。这种关照,使一些琐碎的事物、平凡的人物都成为审美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符号。并且,这种文化符号是多元的,打上了鲜明的艺术烙印。
朱 俊 夭永茂油画艺术风格与特点研究
他并不着力于表现山川外在雄阔壮丽、奇绝险峻令人心潮澎湃的感觉,而是着力于从那些日常围绕着人们更有亲切感的,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山川、大地、河流、树木中,将他所经验到的同时也是某种具普遍意义的谦和、质朴、坚毅的内在生命品质,通过具象元素在画布上呈现出来。画面整体感觉浑朴平实、自然清新,或如一支轻轻吟唱的田园牧歌,曲调悠扬而意境深远,给人一种本然状态的原初复归。或如引入一个静谧空灵的宇宙世界,带给人类灵魂安居的栖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