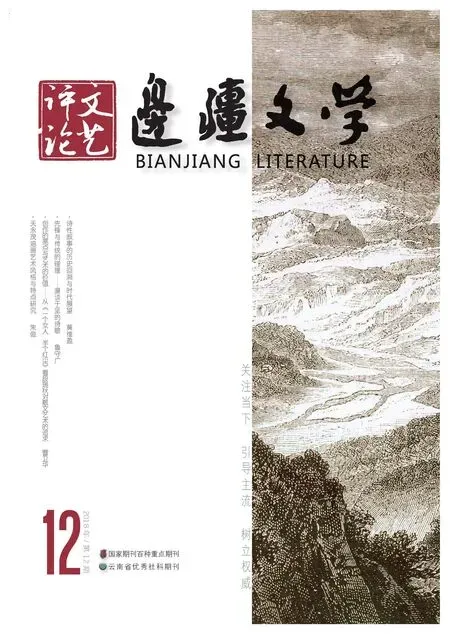黑蝴蝶
——孙禹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集序
孙国庆
一
岁月的白云苍狗,时代的嬗变更迭,人生的跌宕浮沉,对仼何一个人生历程的审判,生存意志的磨砺,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拷问,从来都是极其锋利和残酷无情的。而正是这种铁律般的锋利与残酷无情,才愈能彰显那些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与身俱来的贝多芬精神,以及悲剧英雄的人格特征。
这些人,在升斗小民的眼里,不是“轴”的沒治,就是“二”到沒根。不是浑身“戏剧化型人格障碍”的基因,就是似患有家族“宰廷亨舞蹈症”病史的“涝头巴吱”,活的极累又不接地气。因为这些人不懂什么叫“放下”。然,“鸟雀安知鸿鹄之志”。其实,他们活的痛快淋漓,心灵自由,透明扎实。只是常人看不穿而巳。因为他们心中,永远供奉着一盏从不熄灭的神灯。远比那些尸位素餐的人活得单纯干净。一个人,只有活的干净单纯,才能痛快过瘾,善良的彻底,洒脱到极致。这即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超脱。在当下这个娱乐致死,五音乱耳,七色迷目,巧取豪夺的生死场上,有这般信仰和定力的人,不是“怪物”,就是极品。因为他们早已“出世”。
二
而我眼中的孙禹,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涝子”(合肥方言“傻帽”),更是一个铜碗豆似的“极品”。即有“好奇害死猫”的机警与愚钝,又有着“咬住青山不松口”,倔驴似的敏感和呆痴,即有知恩图报的良心,又有对命运煎熬的无所畏惧,更有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的忧患意识。这些优良的基因,正是其歌唱为文的基本特质,大凡具有如此特质的人,多是好人。因为他们沒有精力尔虞我诈,更不耻投机钻营。倘若这样的好人,终生移山不止的文化愚公,最终不能得志,不是天妒英才,必是时运不济。
三
从弱冠之年就才华横溢的孙禹,虽历尽了一生的文化苦旅,20年欧美漂泊的歌剧炼狱,直至一路走进“天命”的年轮之后,生命“如歌的慢板”之际,仍能在歌唱上宝刀不老,又以小说散文见长,报告文学和剧本创作上破壁,艺术评论及歌剧导演中灵意,如此通天接地,天马行空的行者,就不得不让我临渊羡魚了。而这种将文化的跨界,各种艺术门类复合交溶的大雪无痕,融汇贯通游刃有余的人,不是奇人,当为何物?但,奇人之所以神奇,不下大功夫者,不吃苦中苦,何以称奇?因此孙禹常说:“天才,是个最靠不住的东西。一个再天赋异禀的人,终日躺在昨日的阳光下,享受着微风的轻拂,鲜花的芳香,那温柔的灵感绝不会光顾。”
四
作为一个在德国和美国,一呆就是20多年的歌剧人,孙禹主演过的西洋歌剧岂止70余部?足迹所至,又何止国家百余?仅与多明哥同台演出的歌剧就有5部。但他自视的扛鼎之作,却只有中国歌剧《原野》。这是一部被中外同道共识为中国歌剧的颠峰之作,唯一走进世界经典歌剧系列的民族歌剧。今天,他又作为一个导演,被其反复执导而视为最爱。这部足以见证孙禹全部文化积淀,又常常革故鼎新的生命活剧。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其漫长的文化准备,国际歌剧的辽阔视野,厚重的戏剧和文学底蕴,决不可能使他在民族歌剧美学上高屋建瓴,中国歌剧体系上独树一帜。而他在海归之后领衔主唱的大型交响史诗《成吉思汗》,更是让他常常在“一代天骄”灵魂附体的须臾之间,又使他将这位被“长生天”及“腾格里”吻过灵肉的万汗之汗,演绎的神似形似卓而不群。
作为话剧演员出身,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科班毕业的高材生,又获得美国世界著名音乐学院Peabody歌剧艺术家的文凭者,国际瓦格纳歌剧大赛金奖得主,比利时皇家“伊丽莎白”声乐比赛,一人独得三项大奖的歌者,他的出类拔萃似在逻辑之中。但他与各种文体的文学创作,就风牛马不相及了。但朋友们有目共睹,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硕果累累,长中短篇小说多管齐下,散文报告文学恣意汪洋,评论及剧本的写作鸾翔凤集,风声水起,不仅渐成气象,且势头了得,更使我蜂目豺声,人贵语迟。无怪一位吃皇粮的知名作家曾说:“一个唱歌的写的东西,不过城狐社鼠而已!”而已?我这位在美国已几年之后,竟连皮鞋都舍不得买一双的亲哥,突一日,竟以小说《残阳如血》,斩获台湾笫二届《联合文学》新人首奖时,竟不满28岁!城狐社鼠乎?曾被美国核心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级的男中音歌唱家孙禹,刚海归不到一年,竟以他的首部50余万字的非虚构小说《悲剧英雄》,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与煤矿作协联袂举办的长篇小说“乌金奖”、中国散文协会年度奖等。只是,这样的人凤毛鳞角,在常人的眼里匪夷所思,太不真实。
如今,集歌唱大家,歌剧导演,小说散文剧作家,文艺评论及报告文学作家等多重身份的孙禹,又有近50万字,冠名为“《黑蝴蝶》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集”即将问世之际,他竟突发奇想,要我来为他作序?于是,几推不掉,我只有济河焚舟,赶鸭子上架,因为我们血浓于水。
五
关于爱情,一位西方哲学家说的诡异:“爱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爱情’的证据。”而好莱坞的一位大导演却说的悖论:“在我的电影中,如果没有爱情,将如何面对观众?”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倘若剔除了人性和爱情,那么庄子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幉之梦为周与”这磨棱两可,又深不可测的辩证哲思,及有关“爱情”的“二律备反”,究竟还有多少妙不可言的玄机,几成生命的禅意和空灵的诗性?
而孙禹的长中短篇小说集,却以在德国的天主教小城维尔斯堡中,那间不足10平米的袖珍公寓里,与一位原部队文工团舞蹈演员的留学生,名叫“诗蝶”的妙龄少女,那段颠鸾倒凤的隔代爱情故事《黑蝴蝶》冠名,又处心积虑地在卷首,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诗经》绝句:“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题跋,并以德国与北京和成都三地的时空穿梭为背景,歌剧人及舞蹈者灵肉的撕裂与缝合,绝妙而细腻的心理述说为独特语境,详尽而坦白地讲述了这段让他刻骨铭心的生死恋。该书在多年之前,就被台湾大名鼎鼎的《联合文学》出版社一眼看中,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段里以繁体字出版,近日,又在作者现身台北时,再度大受读者青睐,这说明此作品,随着时间的沉淀,定会越来越俏,更是当时台湾出版界的一大趣闻。
六
擅长以“我”为主线的心理描写,非虚构叙事的孙禹,却机关算尽,欲盖弥彰,用貌似男欢女爱的物种本能,人性使然的灵肉交媾去取悦读者,去误导各种男神女神的小鲜肉们。更不惜用麻辣的肉欲猛料,赤裸裸的荷尔蒙喧啸,隔代男女那种既血脉贲张,又划地为牢的盛大情欲仪式,去梆架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消费的无意识。但这一切却在高人眼里,那种蓄意的情欲误导,“伪命题”的爱情表征,无一不在其媚俗腥膻的表皮下,蠕动着深刻的思想钩沉,复调似的内蕴格局,和声织体般庞大的情感细腻,复杂多变又直白坦荡的自我审判,血泪俱下的人性剖析。这自然是逃不出智者那洞若观火的穿透与内醒的。可见,弄纯文学的作家多么悲摧,不浪得虚名,不使障眼法,不用摧情散,不服食激活“市场勃起”的摇头丸,不吞嚥救赎“良心阳萎”的伟哥,你的呕心沥血之作,还真不如那些用“内分泌”写作的“萠萌达”们色香肉艳。这种逼良为娼的文化市场扭曲,常使用生命写作的作家首鼠两端,惩忿窒欲。
如果依那位西方哲学家:“在这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爱情,有的只是‘爱情’的证据”的逻辑,那么,当一轮大若金盘似的满月,盈满“我”那从袖珍公寓顶端的墙上斜劈下来的天窗时,豆蒄年华的诗蝶,何以义无返顾地脱去上衣,心无旁鹜地委身给了一个不惑之年的男子?这仅仅是一种身处异国,两个独孤的灵魂和肉体,相互的满足和基本慰藉吗?骨子里当然不是。那时,在徳国南部那个著名的天主教的小城里,她的身边,既有潘安之貌,睥睨一切的医学博士“旗人”,又有虽相貌丑陋,一如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且银行存款达六位数以上,油画了得的结巴“幌子”,以及我这个终日有背不完的谱子,苦行僧似的歌者。在这三个“饿坏了”的光棍大男人谗涎欲滴的围猎之下,诗蝶这个黑发浓密飘逸,风情万种,身材肤色一如巴西“桑巴”舞孃,性格舞姿恰似一匹母马驹“在阳光下狂奔不息”的花际少女,仅是为了排遣寂寞,宣泄情欲,寻求生理刺激,大可不必为“我”一人守身如玉?
如果,《桃花扇》中的勾栏女子,若不是为情触柱而死,血溅纸扇,撞出孔尚任笔下的一派桃花灿烂,那么,这部明未清初的传世之作,何以焚琴煮鹤历演不衰?
倘若,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绝唱还不够惊世骇俗,何以被孙禹以《黑蝴蝶》冠名的长篇书写中,作为神性的乐感,贯穿旋律的反复穿梭?而那部由拉赫玛尼诺夫在19岁时,根据普希金著名爱情长诗《吉普赛人》改编的独幕歌剧《阿列冠》的律动,也绝不可在构成对《梁祝》音乐的对应契合之后,又以男女主人翁每临灵肉媾合的颠狂之际,巨大的心理危机不期而至,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前夕,在他们眼前陡地幻化成黑蝶的方阵,飘逸着溢散开去,不仅浸满了那轮金色满月,而且缔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魔幻景致,这就不得不让我惊呼孙禹那拨新领异的想象力,唯美的电影画面感,深厚的音乐贮备,以及将所有的艺术元素,大雪无痕地糅进了其作品的谋篇布局,故事的气氛渲染,人物刻划另辟蹊径的奇思妙想中。这样的,充盈着丰润多样艺术品质的艺术小说,当属我对所有文艺和音乐小说阅读的视野中,最别开生面和最罕见的一部。
最终,诗蝶为报答因经济罪将锒铛入狱的父母,竟卖淫还债而歿于世纪的黑死病,破茧成蛹羽化成蝶。而旗人因医学试验不慎,导致贵重仪器毁于一旦,酒后乱性竟强暴了美好的诗蝶。而幌子因长期“葛朗台”似的吝啬无以复加,多种沉重的打工劳作,导致他的健康全毁身陷绝症。但他却在死前,苦苦哀求诗蝶,终于画就了他梦寐以求,并以诗蝶为裸体模特儿的大型油画《蝶欲》。而“我”这个至始至终虽与诗蝶爱得颠鸾倒凤,却终不知该与少女的亡灵如何定位,至始至终焦虑着彼此的爱情该如何了结的所谓男子汉,却只有久久地仰望着从焚尸炉的烟囱里,悠悠飘出被“蝶化”了的缕缕白烟,泪流满面痛哭不止。除了心里充满了对诗蝶永恒的感念之外,剩下的唯有锥心的沉痛,刻骨的思恋,窒息的无奈与无尽的悔恨。
至此,《黑蝴蝶》这部典型爱情悲剧小说的密码已被破解,作者隐藏极深的思想内核已浮出水面,其音乐复调式的文学化,电影画面感唯美空灵的阅读化,一路将黑蝴蝶为宿命的暗喻符号,象征着命运不可知的意识,以及作者以自身深切的愧疚,连同其复合丰沛的艺术积淀,所运用的各种艺术手段刻划人物的终极意义,到这,已全部揭晓。那就是:男欢女爱起源于异性相吸,升华于精神的默契,铭刻于相濡以沫的记忆,深刻于彼此无尽的感恩,不朽于阴阳两隔此恨绵绵无绝期。
倘若,这个世上根本沒有爱情,只有证据,那么长篇小说《黑蝴蝶》和汗牛充栋的世界名著皆属多余,也决不会感动两岸那数以万计的读者和文学编辑。更不可能使庄周在梦蝶之后,写出那千古传唱的锦绣绝句。而长篇小说《黑蝴蝶》,也绝不可成为作者与诗蝶,那爱情与哲思的血泪证据。
七
在孙禹这部以《黑蝴蝶》冠名的长中篇小说集中,收录了作者长达数10年(海外20年搁笔不算)文学创作的部分作品:一部长篇,三部中篇,七个短篇,加上附篇的散文和随笔,洋洋洒洒近50万字。其中,被他扩充为中篇小说的《残阳如血》,不啻是他的“镇书之作”。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在“黄祸的瘟疫”肆虐神州大地,文化大颠覆的丧心病狂,人性大扭曲的时代洪流中,挣扎沉浮在人兽之间的一个普通知青的故事。这个性格羞涩内向,举止女性化,有着仕女一般雪肤玉貌,开合有度的“假丫头”,在留学德国并获医学博士之后,毅然回国任省医学院专家院长的父亲,不堪轮番批斗割腕自杀后的性格裂变,竟让他变成了一个冷血无情,心狠手辣的人。
这部小说以《水浒》似的文字老辣和简洁,人物刻划的风骨峻峭,文学宏大叙事的游刃有余,作品谋篇布局上的老道从容,读者理性阅读之下的视觉冲击,不经意之中的悲剧张力,无一不彰显着作者:“对‘文革’书写特殊的语境下,那庞大而沉稳的才气,以及前途不可预估前瞻性,使该篇对那个灭绝人性时代的表述,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奖。”(《残阳如血》荣获台湾《联合文学》笫二届新人首奖评委会总结语。)
当小说中的“我”和一干知青,在老牛倌和村民,面对吃了铁钉行将痛死的牛,却不忍下手的节点,假丫头却挺身而出,在已被青皮将刀刃深深插进牛的脖子后,却仍不肯气绝的当儿,假丫头拚尽瞬间的蛮荒之力,举起碌碡将牛的脑袋砸的五官爆裂,脑浆四溅的这段文字描写,直着叫我浑身觳觫,不忍卒读。而孙禹在该篇结尾之处,更是以唯美的神来之笔,空灵的魔幻呈现,将假丫头和“我”,在潮水一般的牛群,前赴后继地将那滩被抬走的同类之血,密密匝匝地围牢之后,冲着远处兀立的我们,发出了倾天塌地的怒吼,至此,作者那力透纸背的文字发力,对人性残忍的泣血控诉,振聋发聩的馨竹难书。以及这种对“暴力美学”早已在骨子里长期的渗透,一旦井喷,逐使他的文字,在这一瞬间里,便爆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震撼力。
《残阳如血》在台湾的蟾宫折桂,丰厚可观的奖金,给刚到美国不足一年,经济上卑以自牧,英语的诘屈聱牙,文化差异大尴尬中的孙禹,带来了他在文学苦旅上最高级别的奖掖和肯定,一扫其灵魂孤独,身处异乡的雾霾,甚至使他对后一年的学资,声乐比赛,试唱角色等诸方面的经济掣肘不再发愁。但更要紧的是,《残阳如血》荣获台湾文学大奖对其生命的意义,对其“路漫漫其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文学人格建立,以及写作信心与尊严的再度确认,将是一种何等的激励?随后,荣获此奖的还有孙禹的发小严歌芩,以及后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
八
人生有三苦:一是得不到。二是付出了也得到了,却发现不过如此。三是轻易放弃了,后来发现它在你的生命中如此重要。在这一点上,孙禹是幸福的。关于文学,他从18岁一路写来,除去赴美深造,旅德主演歌剧的20年间几乎封笔之外,他笔耕不掇,对文字的锤炼和写作的自觉从未忘情。以至他的文字到了今日,巳方纳圆凿,履险如夷了。这些如同裸露在阳光下,荒原上的沟壑与石砾般的显著,如同一条激情汹涌的暗流,始终贯穿在他对各种的题材,风格语言,形式品相,以及不拘一格的尝试之中。
如果说在孙禹的小说集中,那部以交响乐4个乐章为结构,音乐术语为章节写就的中篇小说《诞生交响乐》,生动传神的刻划了舒天野,这个音乐学院指挥系天才型的学生,在青春期中的狷狂自恋,孤独反叛,偏执敏感,即自卑又傲慢的分裂性格,准确细腻地彰显了艺术天才的特质与典型性,不如说他在另一部写音乐学院生活的中篇小说《三桅船》中,以素颜及直白的文字驾驭与节制,第一人称的心理深度挖掘,写活了藐似自卑无为的声乐系学生吴秋泓,虽无声乐天赋,却对名誉和政治地位的贪婪,巧取豪夺的不择手段,以及虚伪狡诈的双重人格。并突显出另一位声乐天才,容貌出众,天性落拓不羁,性格透明直白,出身优越的裴燕莎,那种不谙世事的率真与单纯,以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无辜与幼稚,竟让我读的风声水起,一气呵成。这种久违了的纸质阅读的快感,并不是我对这两部中篇情有独钟,而是缘于我和作者同一年考上的中央音乐学院。
九
诗人泰戈尔在总结人生时,曾用诗性的语言如是说:“旅客在每一个生人的门口敲叩,最终才能敲响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流浪,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而孙禹经历了中外数十年文化的苦旅,心灵与肉体双重的流浪之后,现已叩响了自己的家门,但他是否已经走到了最深的内殿?我不得而知。但从他已出版的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中,读者不难感到他离“内殿”并不遥远。他那些以悲悯的情怀,忧患的意识,正直的胆气,对蚁民凡人命运的书写与深情的文学关照,人性壮美与丑陋的纵情呕歌与冷酷的鞭笞,竟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就显露无疑了。例如他在《抖抖老太》中,以沉重的赎罪心情贯穿全篇,将专在他家院口摆摊卖瓜子,且每次都以手抖为由,将瓜子从量器中洒出而被视为狡诈。而“我”又在一个全城停电的夜晚,伙同玩伴牛牛,对她的瓜子摊实施了吹灯拔蜡毁灭性的打击之后,方才得知患有早期“美尼尔氏斯综合症”的抖抖老太,不仅在中越自卫还击战中刚刚失去独生儿子,又因他们的顽劣住进医院后,作者那种无尽的悔恨及悲悯,不得不让人热泪盈眶,思绪万千,回味无穷。而作者无论是对《财迷老妪》中,市井“滚刀肉”似的餐馆主老财迷,那先恶后善的人性转折与剖析,还是在《无言》中那“茨威格式”的少女,让人终生抱憾的单恋,那种何等潮起潮涌的书写,抑或是《船从雾城启航》中,那位对亲生儿子几近绝望的父亲,将对“我”的“角色转换”和移情,在彼此邂逅与长江的轮渡上,用泪水倾诉的是那般的无助,直至《都是笑话》中,因“我”竟与全国声乐大赛秘书长的同名同姓,而在人性中所引发的价值重估,色诱贿赂,虚妄愚昧的同时,又充斥着果戈里《钦差大臣》似的喜剧深刻,仍有深刻的现实比照意义。足见作者早期的作品,不仅是以小人物的命运,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为主体关怀的,更能彰显其喜剧才华的社会性批判,以及在笑声中完成其思想深度的开掘。除此之外,更让我意外的却是,作者在他的《远去的旋律》中,竟以尝试性的前瞻,换一种“写法”的手段,用“非戏剧不小说”的交叉构架,完成了他生平笫一部的爱情小说。以至我在后来读到他的一篇准“意识流”,而且不可复制的作品《被公审的大儿童》后,给我的全方位震撼,绝不亚于第一次读到卡夫卡的《城堡》和《变形记》。
十
人生是一种隐喻,是关于人生脆弱和不安的隐喻。而这种隐喻越是神秘,就越能激起勇者探索的激情,自决能力的检验及迎接挑战的斗志。
在孙禹小说集的附篇中,有几篇大散文和数篇艺术美学与理论功底深厚的随笔。不仅足以证明作者,对人生这种神秘隐喻大彻大悟的通透和借力,而且对赋于他生命和领悟力的人和事,那种剥肤锥髄的感恩与追思。
当我读到孙禹借用余光中的《乡愁》为文眼,又以诗人那数行诗句为引子,分别溶解展开去写去的《温故乡愁》之后,我在惊叹他构思奇绝的同时,更为他散文的角度切入怀瑾握瑜。就在我读到他写道:“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之后,那大段怀念母亲的锥心刺骨的文字时,眼前突然出现他在案前数度失声痛哭的样子。于是,我泪流满面难以自持。这篇曾感动过无数读者,悼念我生母的散文,怎能不叫我锥心刺骨?不仅如此,在我读到小说集中写我的邻居,孙禹的恩人,煤矿文工团的老团长瞿弦和的散文《大象无形》时,一方面为作者以《麻衣相术》的气韵,去刻划人物而匪夷所思,一方面又为孙禹笔下宅心仁厚,视才如命的伯乐瞿弦和大为感动,以及对他人格人品的高山仰止。
十一
灵性,不用则封。少用少成,多用则通神……
几年前,孙禹应《散文选刊》之约,随中国一线散文作家去了趟新疆喀什。回来后竟用时数月,翻阅考证所带回的书藉和资料逾百万余字,最后竟写出3万余字的超大型散文《喀什,我丟失了什么?》,现作为附篇一并选入他的这本集子。作者在这篇超大型的散文中,以记实性的文字,全景式的视野,翔实的史料索引,旁征博引又择句精确的学术态度,激情汹涌的文学辅陈,纵横辽阔的宏大叙事,将香妃的身世之迷,高台民居的危机,十二木卡姆的来历,阿尼曼莎的传奇,斯文·赫定大漠腹地,楼兰古国的冒死探险,刀郎族的独舟漁猎,连同叶尔羌河流域的诗韵绿地,和阗玉的起源与史记,唐玄奘,法显,甘英,张骞与马可波罗过罗布泊荒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那极目荒凉的文存价值写透。继而又是对维吾尓族的文化神器《突厥大词典》《福乐智慧》等史诗般的详细介绍,活活将这篇典型的文化大散文,推向了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献美学高度的文学书写层面。
十二
要想成为艺术贵族,必须逃离上流社会。
孙禹的歌唱修为和文学执着,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但他却戏称自已仍在“边缘上”。他虽至今孑然一身,仍是我母亲撒手人寰时的一块心病,但他却自嘲的更加锋利:“歌唱是我的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尽管他论“歌剧思维”的随笔《美学高度救戏招魂》《人就活一回》《现实题材的集结号》等,已是寸木岑楼,桴鼓相应。纵然他的导演阐述《人性的变脸,狼性的救赎》,已形成了别人夺不去,并对“中国歌剧体系”在理论和美学观念上的清晰与认定。但你沒有圈子背后没人,你还得像你计划写的下一部长篇小说《熬鹰部落》那样,继续熬着。尽管你的老院长乔羽逢人便说:“孙禹,就是歌剧树上那个虫!”,纵然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邓友梅,你的中国作家协会入会介绍人如是说:孙禹的长篇非虚构音乐小说《悲剧英雄》,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列斯朵夫》的中国版。”但海归艺术家哪个不“轴”?哪个不“二”?都用你们,别人还怎么过?你们呵,先得治病。你们的病根就是不懂国情不接地气!但,什么是“国情”?什么又是“地气”?那就得看我喜不喜你!
但愿我的这个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用尽洪荒之力的序,千万别是个:“吴王爱剑客,百姓多疮斑。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拨楞”(合肥方言:二货)。我想孙禹懂:要想成为不朽,其代价就是生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走的是一条别人都无法走的路。
因为,我们是骨肉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