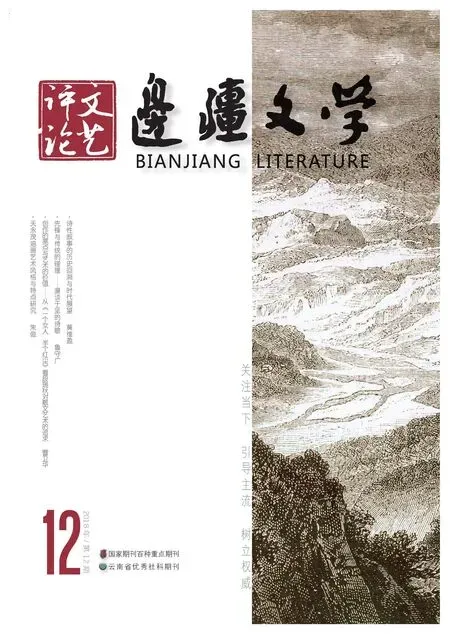先锋与传统的碰撞
——漫谈于坚的诗歌
鲁守广
新世纪以来,于坚往往给人这样一种假象:于坚这个当年的先锋诗人回归传统,趋于保守。表面上看,于坚确实不再“先锋”,甚至站在了与“先锋”对立的一面。于坚在《新诗应当正视它的成熟,不能总是一场青春期的胡闹》一文中提出“如何说”是无限的,而“说什么”是有限的。他不会与诸神绝交,而要为天地立心。于坚的骨子里存在着很强的颠覆性和叛逆性,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感觉和道德是冲突的,我宁可冒犯道德。”但是他并没有舍弃传统,因为他知道若是没有传统和传统隔绝的话,他将只是一棵长在墙头上的无根芦苇,或者只是一个摆在阳台上的盆景,而无法成长为参天耸立的合抱之木。于坚有效地吸收了传统的文化因子,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也越来越显著。正如我们在于坚身上所看到的,他在与中国诗歌传统的探索结合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给了那些在某些向度上一味先锋的诗人很好的启示:只有与传统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诗歌才能获得读者,才能获得生命力。任何地域或民族的诗人和作家,若是没有传承自身的文化传统,都难免有一种写作上的无根的轻浮。真正的“先锋”诗人和“先锋性”写作和古典诗人以及古典诗歌写作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先锋”产生于传统,“先锋”是衍生在传统里的新芽儿。他赞同“天地国亲师”,仰慕孔子、屈原、颜真卿、李白、杜甫、辛弃疾、陆游、陈与义,开始更多地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从他在《南方周末》上的《固执于见》专栏来看,他的思想甚至是“倒退”的,在近些年出版的《印度记》和《昆明记》中更能看出他的“保守”,以及他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的忧虑:“道可道,非常道”。若把“非/常道”比作先锋,那么“非常/道”便是传统。而不论“非/常道”,还是“非常/道”,都是“非常道”。作为于坚思想中的一组二律背反,“先锋”与“传统”好比太极图中的阴阳两极,阴是阴的同时,也可以是阳。于坚对于现代文明的态度是“拿来主义”,而在个人情感和审美层面上,他对于古典与传统又是那么难以割舍。
“先锋”与“传统”在于坚的诗歌之路中是一对共生关系,有些阶段此消彼长,但其中一方从没有把另一方消解掉。大多数当代诗人的诗风多年来并没有什么改变,开始便已僵化,进而定格,而于坚在否定之否定中有过多次的自我超越。于坚成名之前,主要受古典诗歌、新格律诗派和尚处于潜在写作层面的“朦胧诗”的影响。其实任何写作者早年都不可避免地向自己民族的传统学习,这一道坎是无法逾越的。于坚在《棕皮手记:诗如何在》中这样说道:“没有比诗歌写作更困难的事了,每个诗人都知道,他不是在白纸上写作,他是在语言的历史中写作,你写每一行,都有已经写下的几千行在睥睨着你呢。诗人永远不可能从第一行写起,他总是从过去已经开始的第某行继续写下去。因此你的写作总是与过去的写作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通顺的关系。”1971年,于坚去他父亲的流放地探望父亲。在父亲住的一个乡村破庙里发现60年代印给机关干部内部参考的古体诗词时,大喜过望,便开始沉迷于古体诗词的写作,并创作了古体诗集《野草集》。于坚最早接触的中国传统古典诗歌是王维的《辋川集》。一个人早年所接触的东西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于坚在后来的写作中多次提到王维对他的影响,说王维融进了其生命之中,成为其精神世界中众多圣灵之一。我们也可以从于坚的许多诗歌创作中看到王维诗歌意境的影子,像《滇池月夜》:
当滇池的水上
流过幽蓝的月光
乘一叶小小的木舟
一摇桨离开了水岸……
漫游在夜的天空
披着温柔的山风
睡美人躺在我的船头
她的头发浮在银波浪中
鱼儿跃出灰色的水面
月光照见金色的鱼鳞
鱼鳞被波浪们捏碎
散作了天上的星星……
还有《有一回,我漫步林中……》:
有一回 我漫步在林中
阴暗的树林 空无一人
突然 从高处落下几束阳光
几片金黄的树叶 掉在林中空地
停住不动 感觉有一头美丽的小鹿
马上就会跑来 舔这些叶子
没有鹿 只有几片阳光 掉在林中空地
我忽然明白 那正是我此刻的心境
仿佛只要一伸手
就能永远将它捕获
这两首流动空灵渗透着禅意的诗和王维的《山居秋暝》《竹里馆》及《鹿柴》何等相似。于坚多次谈到王维的《山居秋暝》,认为这首诗是存在之诗,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对象,不是主体与客体,而是在世界之中。于坚此处的观点和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如出一辙。于坚还说这首诗吟唱的是世界赖以存在的基本事物、与生俱来的事物,人和世界不言自明的关系。笔者认为《山居秋暝》这首诗没有故弄玄虚的典故,没有生僻难解的字词,可以说是白话诗,甚至是高雅的“口语诗”。1000年前的口语对于今人来讲,自然是古典高雅的。所以1000年之后的后人若是读到于坚的《横渡怒江》《山里人的歌》《南高原》等现代口语诗作,自然也认为是古朴淡雅的,“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 王维对于坚的影响是至深的。到2006年春创作《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时,于坚写诗已经整整30年:
春天中我们在渤海上
说着诗 往事和其中的含意
云向北去 船向南开
有一条出现于落日的左侧
谁指了一下
转身去看时
只有大海满面黄昏
苍茫如幕
从这首诗里可以清晰地看出王维的影子。《只有大海苍茫如幕》的境界和氛围不需要任何言语来阐释,诗和大海一样自在,自知、自明,其中的禅意顿时使人洗去内心的蝇营狗苟,澄澈清明起来。于坚这一时期的诗歌还带有很重的新格律诗派和当时朦胧诗派的风格。像这首《梦幻曲》中的一段:
我躺在灰色的窗下,
虚度着人生的年华。
我听见苍凉的天空,
谁在敲古老的巨钟。
钟声在宇宙里回荡,
天国的歌一样嘹亮。
仿佛是旷野的呼唤,
穿过了神秘的黑暗。
这首诗的节奏和谐、格式整齐,注意音节在造成诗歌音乐感中的作用以及押韵和声调抑扬的交错,貌似闻一多的“豆腐块”,属新月派的格律诗风格。这一年,于坚还接触到地下流传的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他这一时期的《新堂吉诃德之歌》《我愿意》等诗作和食指的诗风相类似。还有写于这一时期的《不要相信……》,会使人联想到北岛的《回答》,摘录一段如下:
不要相信我的骄傲,
不会在生活中的阴影中沮丧;
不要相信我的智慧,
不会被命运的黑手暗算;
但你要相信我的沉默,
永远的沉默只为爱你一人;
决不是反复无常的命运,
决不是漂泊不定的人生。
20世纪80年代之后,于坚便走向自己的诗歌之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主张和诗歌语言,开始引领起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于坚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代表作《尚义街六号》。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当时有很多人都怀疑“野怪黑乱”的它到底是不是诗?尽管从“五四”时期白话诗就产生并发展,但中国古诗千年来的传统使大多数中国人只能接受四言、五言、七言这样的诗,这是中国新诗合法性的问题。到“朦胧诗”阶段,学术界虽然有对其疑惑不解的地方,但还是承认“朦胧诗”是诗,而“第三代诗人”诗歌的境遇就不同了。其实,这正是“先锋”诗人于坚的先锋性的表现。在全国一片“朦胧”的英雄式抒情之下,于坚率先把视角从英雄转向了平民,转向了世俗生活,转向了普遍性的正常的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歌。于坚本人认为《尚义街六号》受到了杜甫《饮中八仙歌》的影响,通过诗歌这一途径把一般平民升华为仙人,把日常的普通生活通过诗的语言神圣化,进而通过诗歌的命名使日常生活恒久长存,这一点是于坚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先锋性所在。1986年10月,于坚在《诗六十首·自序》中这样写道:“如果我在诗歌中使用了一种语言,那么,绝不是因为它是口语或因为它大巧若拙或别的什么。这仅仅因为它是我于坚的语言,是我的生命灌注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尚义街六号》便是于坚当时的生命灌注其中的有意味的生活方式。《作品39号》中同样可见于坚的“生命灌注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摘录一段如下:
我们一辈子的奋斗
就是想装得像个人
面对某些美丽的女性
我们永远不知所措
不明白自己——究竟有多憨
于坚在《彼何人斯》里写道:“是否知道我藏在镜子后面的秘密/知道我/刚刚从幕后出来/阳奉阴违的一日”;在《拉拉》中也说了一句与“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类似的话:“我们一生都在/准备着/时来运转”。还有《给小杏的诗》:
小杏 在人群中
我找了你好多年
那是多么孤独的日子
我像人们赞赏的那样生活
作为一个男子汉
昂首挺胸 对一切满不在乎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才能拉开窗帘
对着寒冷的星星
显示我心灵最温柔的部份
有时候 我真想惨叫
我喜欢秋天 喜欢黄昏时分的树林
我喜欢在下雪的晚上 拥着小火炉
读阿赫玛托娃的诗篇
我想对心爱的女人 流一会眼泪
这是我心灵的隐私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理解
人们望着我宽宽的肩膀
又欣佩 又嫉妒
他们不知道
我是多么累 多么累
小杏 当那一天
你轻轻对我说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唱只歌给你听听
我忽然低下头去
许多年过去了
你看 我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金应圭在《词选》后序中曾批评那些无心的写作:“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欢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而在于坚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颗颤动着的心,看出于坚在日常生活中的压抑以及对于他人对其认同的渴望,可谓内足以摅己,外足以感人。
于坚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诗人,是一个内心极为强大的有自己写作信仰的诗人,他的创造性写作天马行空、狂放不羁。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纽带已经严重断裂,“天地国亲师”不在,“仁义礼智信”式微,“不学诗,无以言”的诗教传统更是灰飞烟灭,于坚诗中的先锋性或者说叛逆性也滋生到了极致的程度。这个时期,于坚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是被称为“非诗”的《零档案》。笔者认为在写作《零档案》时,于坚的思想里面很可能在进行着一场斗争:一场中国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诗歌影响之间的碰撞与博弈。中国诗歌传统对于坚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因为他是读着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的诗歌成长起来的,这也是为什么《零档案》写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于坚不敢再翻看的原因。这场碰撞与博弈的结果是于坚走向了他的“中庸之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之间的中庸,先锋与传统的中庸。此时的于坚虽然“叛道”,但并未“离道”。于坚深知传统诗歌描写现代生活的局限性,所以一直想要找到一条诗歌的“中庸之路”,把中国传统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糅合在一起,尝试着找到一条新的诗歌之路,为中国诗歌注入新的生命。《零档案》便是于坚诗歌“中庸之路”上的一次创造。这首诗由《档案室》《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青春期)》《正文(恋爱期)》《日常生活》《表格》《卷末(此页无正文)》8个部分组成,描述了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的存在与感知。于坚的诗歌是用眼睛写的,他的观察极为仔细,注重每一个细节,像是拿着显微镜一样。于坚曾这样说道“你比如说,‘枯藤老树昏鸦’六个字完成一个意境。这是古典诗歌。换成当代诗歌,完全可以写:那个枯藤是怎么样的枯?一点钟的枯藤和两点钟的枯藤、三点钟的枯藤是不一样的,秋天的老树和春天的老树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传统写作里面,这些都是被忽略的。中国传统写作很强调一气呵成,把握一个整体的氛围,在混沌方面非常有力量,但是在清晰的方面就显得非常的微弱。”从这里可以看出于坚的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及其变异。古代诗歌重在感觉。所以讲“气”。现代诗重在“思”的细节展开,也要讲气,气之贯穿才有思绪。现代诗是语词场,古代诗是意场,得意忘言。现代诗也许得言,倒不在乎意。“意”在现代诗里成了局部、细节,整体的力度来自“场”而不是意,《零档案》构筑起的便是一个任何人都难以逃脱的场。对于这首诗,许多人直言看不懂。而看不懂的原因其实是于坚太过前卫或者说太过“原始”,因而不能为这个到处充斥着“隐喻”的世界所理解。《零档案》是于坚的又一次神灵附体,是对当代新诗的拯救,它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定。其实《零档案》的很多句式都是源自元散曲式的“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一类,而许多于坚的其他诗作也可以说是发端于隋唐时期“长短句”即宋词的一种变体。从这一点来说,于坚的诗不像某些诗人的诗那样无根的轻浮,而是植根于中国文脉的千年一系。这种单纯的排列词语,在我们当代很多人看来,或许缺少古典诗歌的那种诗意或者说是意境,但是当这首诗越过时光的长河,辗转至数百年乃至千年后,它的诗意或许便会显现。时间可以产生诗意,可以使真正的诗歌水落石出。
王国维曾回顾中国思想发展史,赞扬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灿然放万丈光芒,认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以抱残守缺为事,造成思想僵化停滞,从而主张输入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断言:“异日发明广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把这句话借用在诗歌领域是多么熨帖,于坚的诗歌之路与王国维寄予希望的“学术之路”也存在着某种契合。在于坚这一时期的许多诗歌中,都可以看到他想要把中西诗歌杂糅为一体的雄心,写于1996年12月至2000年2月的《飞行》最具代表性。在《飞行》这首诗里,到处都是象征着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专有名词和语句:大麻、天使、老子、尤利西斯、西伯利亚、顿河、西斯廷教堂、卡夫卡、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金斯堡、白居易、颜真卿、达达主义、平平仄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段落是直接引用中西方古典的或者是现代的诗歌:苏轼、屈原、岳飞、范成大、王勃、郭沫若、闻一多、艾略特……,这样一种“混搭”的写作态势一直持续发展着,到诗集《彼何人斯》,已趋成熟。《彼何人斯》的诗名出自《诗经》,古韵绵绵,而这首诗给人的感觉更是余韵悠然,有戏曲的味道:
我一唱歌你就应和 我卑鄙你尾随而至
我下流你顺水推舟 我胁肩谄笑 为大王
涂白自己的左腮 你递上一面小圆镜
照出我藏在眉宇间的弥天大谎 雾 雪光和火焰
唯与你 我敢一丝不挂 袒露私处 素面朝天
80年代以来的几次诗歌事件称为“青春期的胡闹”,提出来新诗应当正视它的成熟,而不能只是一场青春期的胡闹。他在《还乡的可能性》中说道:“自我,个性、乖戾、极端固然是有助革命。但是,文明不能总是破旧、总是跳梁之辈在表演。时间到了,文明在呼唤守成,呼唤高僧大德。写作其实是为世界守成。”于坚在2013年出版的《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很好的验证他的“中庸式”写作。其中的《拉拉》《下山》《火锅行》《喍戈布丁》等等,或是夹杂古今中外诗歌的原文,或是化用它们。如《拉拉》的一个片段:其实,如何说是无限的,说什么是有限的。福柯也曾说过:“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样说。”于坚说:“我的非诗,非历史,一直只是在如何说上。在说什么上,我一向很保守,我可不敢与诸神绝交。”2010年夏,笔者和于坚一起去潘家湾的一家旧书店,见他挑出了一本《东坡乐府》。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于坚确是未与诸神绝交。无论哪个民族的诗人,无视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是愚蠢的,真正的前卫与先锋也产生于传统。
于坚诗歌的调和方式事实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诗歌道路走入歧途的规劝和引导。他把20世纪
杏花疏影里 吹笛到天明 哦 拉拉 你带来了春色 跟着你
就是跟着爱情 窈窕淑女 谁热恋过你 谁曾经寤寐思服
谁就是幸福的麋鹿 幸运儿 你英俊
于坚的诗歌写作是加法,是打乱逻辑不按照线性发展的拼接蒙太奇,是碎片化的循环整合。又如《火锅行》的一段摘录:
辣就是辣 咸就是咸 酸就是酸 醒就是醒 醉就是醉
硬就是硬 软就是软 闷楼十日心将死 好酒三杯我欲飞
岑夫子 丹丘生 长风白日君开眼 堂堂吾辈高七尺!
樽前曼吟三百曲 才比唐初人未识 大道已废食为天
弥勒佛 挺大肚 腹中自有千秋业 吃起 捞得很麻利
很熟练 很准确 很直白 很露骨 很果断 手疾眼快
莫再欲擒故纵 阳奉阴违 装神弄鬼 看中哪块拈那块
但总是 稀烂的脑花 失去了眼仁的目 瘪掉的腰子
破碎的肾 黑透的胆 糊掉的蹄子和舌尖 过度萎缩的牛鞭
杯盘狼藉时 好风把大街吹得森凉 又可以睡了
晓看红湿处 花重五华区
其实,于坚现今的诗歌写作方式是一种“中庸”式的“鸡尾酒”式的“混搭”写作方式,把西方、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下杂糅在一起,重新组合,为“我”所用,由“大乱”到“大治”。“第三代”诗人之后,中国当代诗歌便走向了“一场胡闹”,而于坚抱着一块石头沉到了底。虽然于坚是以“口语诗”和“非诗”著称,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古典主义者,认为尽管“道在屎溺”,但“道”不是屎溺,而主张“道成肉身”。于坚的回归传统异于白嘉轩的跪倒在祠堂里。于坚是在诗歌这座祠堂中添加了新的东西,使祠堂中所供奉的东西有了新的生命,从而使诗歌重返人间,重返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接地气,臣服于大地,使诗有了人间烟火气,使人间烟火有了诗意。这种“臣服”从“于坚”这个名字上便可以看出来。于坚小时候的名字是“于长风”,出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由于他比较爱哭,所以他的父亲把他的名字改为“于坚”。而“坚”这个字的繁体写作“堅”,“堅”中有“臣”,又有“土”。于坚的诗歌方向就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方向,是中国当代诗歌自我救赎的方向。
于坚的这一“中庸”式的“鸡尾酒”式的“混搭”写作方式为中国当代诗歌输入了生命的元气、日常生活之气和大地之气,使诗歌走向了新生。“混搭”原本是指一种穿衣风格,用在此处借以形象地指称于坚近年来的诗歌特点。于坚近年来一直在寻求着一种融通,游刃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歌之间,甚至还加上了哲学、音乐、戏剧、纪录片、摄影,打破了文体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域之间的隔膜,破除了它们之间的执障,为诗歌融进了新的生命和活力。他的写于世纪之交的长诗《飞行》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飞行》中,康德、孔子、老子、屈原、陆游、郭沫若、苏轼、范成大、岳飞、金斯堡、颜真卿、闻一多……融在了一起。这首诗分开了,或许就什么也不是,但作为一个整体,有它独特的蕴意。从这里来看,于坚实现了他刚“出道”时的宣言:“不是口语,而是‘于坚语’。”其实,于坚的诗,一直都是“于坚的语言”。于坚在诗歌上是个先知,将今天的众多诗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于坚不光是诗人,同时也是诗论家、摄影家、纪录片导演、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提出了自己关于诗、关于社会与人生的看法。
在“先锋”与“ 传统”的碰撞过程中,于坚的诗歌还呈现出特质:越来越有担当以及诗中的巫性。自2009年开始,云南持续干旱。于坚,作为传统文人,担负起了传统文人的使命,念天下苍生,怀人间疾苦,重拾诗歌最原始、最本质的功能,意译了屈原的《大司命》:
大开天门吧 雨神
乘着我的乌云
令大风在前面开路
把暴雨洒向大地
你在天空上下翱翔
跟着你越过了高山
九州大地纷纷扬扬
生死一旦都在你的手掌
你高高在上那么安翔
乘着清气掌握阴阳
紧紧地跟着你啊
请你降雨于九冈
长长的灵衣在飘扬
美丽的玉佩闪着光
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
不知道你要降雨还是不降
桑麻和花朵就要夭折
就要被遗弃离居
衰竭苍老接近死亡
没有水啊大地疏荒
你乘着龙车辚辚飞行
高高在上啊飞在长天
像月亮上的桂枝不肯下降
我们苦苦思念心中哀愁
哀愁之人无可奈何
唯愿你今天行善
生命固然有限啊
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对于当下的社会,于坚也开始发出更大的声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集体怀旧的时代,因为几乎每一代人都没有了曾经存在过的痕迹。由于城市化的狂飙突进,蕴蓄着传统文化的建筑实体大都被拆,陈寅恪说过:“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痛苦亦愈甚。”于坚在一腔悲愤中写下了《喍戈布丁》:
扬着长鼻子穿着黄制服就像来自德国的野蛮人
推土机一冒烟就拆埋下嘴就挖抬起头就吐它们早上拆
中午拆下午拆夜里拆不分青红皂白这些机器只会拆
戴着安全帽一吹口哨就变出一朵朵灰沉沉的蘑菇云
它们昨天拆它们现在拆它们明天也要拆它们后天还要拆
拆个不停它们拆个不停就像青铜鼎里逃出来的老饕餮
拆个不停拆掉了祖母的老棺材拆掉了父亲的旧钉子
拆个不停拆掉了妹妹的玩具箱拆掉了哥哥的臭鞋子
拆个不停拆掉了老铁匠的五角星拆掉了乌衣巷的水井
拆个不停拆掉了母亲的春花秋月拆掉了故园的芷岸兰汀
拆个不停拆掉了白头偕老的邻里拆掉了大佛寺的晚凉鸦背
拆个不停拆掉了夜晚的黑丝被姐姐要投奔金发的玛格丽特
拆个不停拆个不停滚开铁履带张着钢嘴巴咔嚓咔嚓 戈布丁
拆个不停喍戈布丁挖出许多大坑坑大窟窿埋掉了大地的遗骸
拆个不停隔壁卖花的真 一掀被窝逃上屋顶变成了火天鹅
拆个不停喍戈布丁我们睡不安稳它们挖出来一个个失眠者
拆个不停喍戈布丁故乡土崩瓦解它们闭着眼大吃大喝加满油
戈布丁刨根究底多快好省分秒必争拆个不停喍戈布丁
戈布丁拆个不停拆出一堆堆废墟一张张白纸真干净拆个不停
死神是一位住在电视机里玩骨牌的灰大师他把世界视为灰尘一团
戈布丁烟灰骨灰粉笔灰水泥灰垃圾灰汽车灰燕子灰水仙灰
戈布丁槐树灰爱情灰牙刷床单灰邮票灰像册灰丝袜灰童年灰
拆个不停雕梁灰窗花灰落日灰雪灰死灰我们搬家搬家不停地搬家
戈布丁扶老携幼捂着鼻子跟着灰搬家人生无根蒂呵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呵此已非常身喍戈布丁去终古之所居兮遵江夏以流亡
戈布丁心婵媛而伤怀兮 戈布丁眇不知其所跖兮戈布丁
戈布丁 戈布丁 戈布丁 戈布丁观乎四荒兮唯有文章
投奔屈原呵 戈布丁投奔李白呵 戈布丁投奔杜甫呵 戈布丁
投奔王维呵 戈布丁归我故乡呵 戈布丁高吟九章呵 戈布丁
日月安属 戈布丁列星安陈 戈布丁遂古之初 戈布丁
谁传道之 戈布丁上下未形 戈布丁何由考之 戈布丁
冥昭瞢 戈布丁谁能极之 戈布丁 戈布丁
沧浪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喍戈布丁
“终古之所居”被现代化连根拔起,每时每刻都在破旧立新。但是,一个社会不讲“守成”只讲破旧立新,便永远不会有安全感,诗意栖居也就无从说起。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即使身处故乡,生活世界也被流放了,存在感的丧失使众生成了被流放的无家可归的尤利西斯。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招魂。祛魅的现代化摧毁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没有温度的钢筋水泥组合而成的模式化的西式小区中没有教堂,也没有庙会。为了抵御彼此隔绝,需要为自己重建独立的文化空间,招魂之意即在于此。中国诗起源于卜巫,巫事在原始时代,是非常实用的,兹事体大,并非后来那样只是抒情言志、吟风弄月。诗首先是通灵,与神灵对话的,是神韵,神话,通灵而文之,才成为文明。这绝不是某些混迹于诗歌的人所说的“装神弄鬼”,或者“美”其名曰:东方复古主义,原始复古主义,这些被超大城市的霓虹灯闪的眩晕的人,这些没有用自己的脚掌深入过滇地,没有做过田野调查的人,自然是无法理解于坚诗中的巫性。他们被所谓的现代文明异化,已经退化到无法逃脱城市进而回归大地。他们无所谓灵魂,而只是一个皮囊,一个躯壳。于坚是当代的屈原,他与众生一同体验着这片土地上的荒诞和疯狂,美好与丑陋,快乐和痛苦,荣耀和卑劣,并且为我们这个时代招魂。于坚所招的魂是众生在杂乱庸碌的生活中所遗忘所忽视的最基本的人生之常,人生之常道。试看他的《故乡》:
从未离开 我已不认识故乡
穿过这新生之城 就像流亡者归来
就像幽灵回到祠堂 我依旧知道
何处是李家水井 何处是张家花园
何处是外祖母的藤椅 何处是她的碧玉耳环
何处是低垂在黑暗里的窗帘 我依旧知道
何处是母亲的菜市场 何处是城隍庙的飞檐
我依旧听见风铃在响 看见蝙蝠穿着灰衣衫
落日在老桉树的湖上晃动着金鱼群 我依旧记得那条
月光大匠铺设的回家路 哦 它最辉煌的日子是八月十五
就像后天的盲者 我总是不由自主在虚无中
摸索故乡的骨节 像是在扮演从前那些美丽的死者
文人政治终结了百余年,于坚这样的文人无缘于政治,却可以引领众生,普度众生。故乡已经不再,这首《故乡》便是招故乡之魂,为我们所有人招故乡之魂,唤醒我们对故乡尘封的记忆,使我们还记得从哪里来以及来时的路并且意识到未来的虚无。在这个上帝已死的年代,真正能够让灵魂出窍的人物,恐怕就是于坚这样的诗之巫者了。
云南是众神狂欢的世界,还有许多无法言说的东西,还有净土,还有大地之美,滇者,有水有真,而水意味着生命,真代表着人生之常。正是这一块遍地高山大河奇潭险谷的巫地成就了于坚。于坚少年时代在父亲的一本日记本的插图看到徐悲鸿根据屈原诗歌创作的彩绘——披着树叶缠着藤条的女妖骑着豹子在山中走,并不以为怪。当时于坚虽住在城里,但要看见一头豹子并不困难。有一天,他的一位邻居就从山里捉到一头小豹子。于坚20岁在农场时,整日谈论的就是豹子和关于豹子的传说。土著人经常来农场里玩,豹子的种种传说就是他们在火塘边说起的,骑在豹子背上的人,就是他们的祖先。豹子们就住在于坚的宿舍附近,最多隔着几里路,有时候就在农场的壕沟里躺着,于坚看见过它们凸出黑夜表面的绿色眼睛。于坚用自己的脚掌慢节奏的丈量了云南无数的高山、峡谷、河流、溶洞、湖泊,在这个过程中,巫性或者说灵性浸染在他的身上。《在深夜 云南遥远的一角》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深夜 云南遥远的一角
黑暗中的国家公路 忽然被汽车的光
照亮 一只野兔或者松鼠
在雪地上仓惶而过 像是逃犯
越过了柏林墙 或者
停下来 张开红嘴巴 诡秘地一笑
长耳朵 像是刚刚长出来
内心灵光一闪 以为有些意思
可以借此说出 但总是无话
直到另一回 另一只兔子
在公路边 幽灵般地一晃
从此便没有下文
为什么“总是无话”?为什么“从此便没有下文”?既然“无话”,为什么又“以为有些意思” ?这中间有太多的无法言说的疑问。“没有下文”就是“无”。 “无”不是虚无,而是巫,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意会也只能“在场”中才能意会。
于坚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一直以写出传世作品、成为经典作家来要求自己。可以传世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诗歌作品,总是可以找到它们与过去、与当下、与未来的息息相关之处,而诗人便是把传统、当下和未来通过诗歌和自己的体验联系起来,在不同时空中跳跃飞行,在不同的时空中寻觅到一个渡口,一个可以普度众生的渡口。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道:“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于坚也一直在强调,中国没有宗教,但有“诗教”,只有诗可以使人们安居在大地之上,只有诗能担当人类的厄运,只有诗能拯救人的沉沦之心。于坚主张通过诗引领世人的日常生活,在无意义已然成为意义本身的当下,他通过诗传达出真正的生活之美。诗性的魅力并不会因为多数人的淡漠而飘逝,历史是减法,吹尽黄沙,在日常语言枯竭之后,如骆驼般踟蹰跋涉于文化荒漠许久的人类整体,必能重新回归诗性和哲思之途,诗歌语言将重新奏响黄钟大吕。
在黑暗中坚守大道的于坚知而能行,知行合一,他不是抒一己之情的小诗人,而是不舍众生的摆渡者,其诗歌的“大乘”性也体现于此。诗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遗世独立者,而恰恰应当与这个时代发生深刻关系。歌德说伟大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而在当今的中国,能够引领着我们上升而不是堕落的,引领着我们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唯有像于坚这样伟大的诗人。于坚是真正有使命感的人,在价值混乱的年代,他始终追问诗歌的社会意义和终极意义。在世界趋于单一化和平面化的今天,他重提“神灵”对我们的注视,认为诗人就是巫师,诗人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接媒介。于坚是当代少数有自由灵魂的诗人,是最明白诗人何为的诗人,用文字搭建了一个伟大的充满创造力和生命感的场。虽然这个时代诗性枯竭,价值跌落,时空的碎片化也使得个体沦为丧失面孔代以面具的犬儒,但只要伟大的诗歌存在,其独特的召唤必将带我们重回家园。
【注释】
[1]于坚:《还乡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第1版,161页。
[2]沙少海 徐子宏:《老子全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1页。
[3]于坚:《还乡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第1版,89页。
[4]于坚:《于坚集·卷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12页。
[5]于坚:《诗六十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102页。
[6]袁梅注释:《古文观止今译》,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5月第1版,518页。
[7]于坚:《只有大海苍茫如幕》,北京:长征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1页。
[8]于坚:《于坚集·卷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2页。
[9]于坚:《于坚集·卷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14页。
[10]于坚:《诗六十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2页。
[11]于坚:《于坚集·卷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66页。
[12]于坚:《彼何人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33页。
[13]于坚:《彼何人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107—108页。
[14]于坚:《诗六十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63页。
[15]张惠言:《词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109页.
[16]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499页。
[17]石岩:《何谓诗?于坚:如果不是工匠式写作,你会被淘汰》,南方周末,2013-11-7。
[18]傅傑:《王国维论学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117页。
[19]于坚:《彼何人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33页。
[20]乔姆斯基、福柯:《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漓江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37页。
[21]于坚:《还乡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第1版,298页。
[22]于坚:《还乡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第1版,304页。
[23]于坚:《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106页。
[24]于坚:《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71页。
[25]于坚在《诗六十首·自序》中说道:“如果我在诗歌中使用了一种语言,那么,决不是因为它是口语或因为它大巧若拙或别的什么。这仅仅因为它是我于坚的语言,是我的生命灌注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见《诗六十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2页。
[26]于坚:秭归祭屈原记,大家,2011年第13期。
[27]陈寅恪:《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第1版,1037页。
[28]于坚:《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85页。
[29]于坚:《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15页。
[30]于坚:《于坚集·卷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342页。
[3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