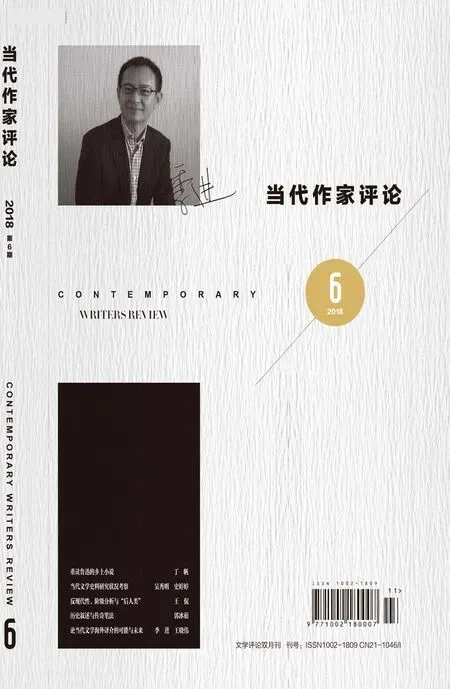民族记忆的另类建构
——以长篇小说《南京不哭》的大屠杀叙事为中心
王冬梅
作为震惊世人的民族浩劫,南京大屠杀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惨烈创伤,赤裸呈现出现代文明时期的人性在战争机器碾压下所遭遇的凌迟与屠戮。自1938年的小说《干妈》(黄谷柳)起,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即开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并在不同的作家手中历经了话语形态、艺术风格、道德担当等诸多层面的叙事变迁。这类作品一方面控诉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则鼓舞国人追求民族解放、实现国家进步的信心。新世纪以来,海外华裔作家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加入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叙事行列,凭借跨越中西的文化身份重启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新一轮文学建构。《金陵十三钗》(严歌苓)与《南京安魂曲》(哈金)被视为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屠杀书写的典范之作,前者颂扬了秦淮歌女代替女学生舍生赴死的历史功绩,而后者则礼赞了明妮·魏特琳等西方人士博爱众生的人道情怀。这类为妓女或传教士树碑立传的拯救叙事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及电影中南京大屠杀叙事的主导潮流。2017年2月,由美籍华人作家郑洪创作的长篇小说《南京不哭》(中文版)在国内面世。这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于惯常所见的拯救叙事之外开辟了不同以往的叙事路径,以大历史时空、解构他救模式及具有超越色彩的人性探源等方式实现了对民族记忆的另类建构。
一、大历史时空中的日常美学
在以往的南京大屠杀文学叙事中,创作者大多倾向于对南京大屠杀作镜头特写式呈现,或者将其视为抗战洪流中一脉支流,而这于无形之中规约着文本的叙事时空和内容生产。简言之,1937年12月或整个抗战时期成为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叙事时间,教堂、国际安全区、医院等极具南京标识的特殊场所则成为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叙事空间,不少文本即在此时空坐标中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话语生产。在这一趋于封闭化的时空规约下,血淋淋的大屠杀本身无疑成为各类文本的题中之义,而杀戮和强奸则成为揭露日军暴行、反思民族悲剧的两大叙事支点。在以受难或拯救为主导的南京大屠杀书写类型中,文本风格大多表现得沉郁悲戚、哀婉凄清。
不过,《南京不哭》似乎有意规避了这种写作模式。南京大屠杀是小说不能回避的叙事背景,不管是人物的成长、情节的推进还是价值的再现都以此为基本前提。然而,在重返历史现场时,小说又有意将南京大屠杀处理成故事远景,试图对历史事件本身作远距离审视及模糊化处理。作者郑洪如是写道:“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这本小说写的是两对男女在七十年前大时代中的悲欢离合。”较之同类题材,《南京不哭》无疑更加注重“长时段、多空间”的整体叙事布局,与之相应的是,长时段的大历史观念使得南京大屠杀被处理成现代历史长链中的一个节点,而空间的多元转移则令孤城中的大屠杀所造成的压抑和焦虑得到了部分转移和舒缓。
小说以1919年陈梅的出生为叙事起点,细致描摹了她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长达18年的成长史。与此交替推进的另一线索则是约翰和任克文在美国求学生涯的点点滴滴。两条线索独立运行,却又在文本形式上通过南京和波士顿的空间切换而呈现交互之势。随着约翰应任克文之邀远赴南京共振中国航天事业,两条线索在南京这一地理空间之上合二为一,而两对男女主人公也开始了战乱年代的人生沉浮、情感碰撞及命运交错。小说对1937年之前的南京日常生活进行了精雕细琢式的呈现。与全景式、理念化的历史再现有所区别的是,《南京不哭》通过更为鲜活具体、细腻纷繁的个体记忆来再现日常图景,复原历史气息。它借由品茶、观景、交游、狎妓、寻求古董等细节场景来构筑日常生活空间,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美学中探求普通民众的人生价值。
然而,大屠杀的发生使得波澜不惊的日常突然遭遇撕裂,以情感为主要表征的一切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一一遭到贬抑直至轰然倒塌。洪水猛兽般涌入南京城的“乞丐一样的士兵”成为个体命运塌方的血色符号,言说着生活的断裂和记忆的转向。“他们穿着满是泥浆的黄布制服,手中的步枪上了刺刀,匕首在裤袋上晃来晃去,神情凶狠,像丛林冒出的野人。”而这一历史镜像让被裹挟进难民潮的少女陈梅“发怔”且无措。平静、庸常而纷杂的日常生活格局随之全盘瓦解,所有人被抛到历史风浪的潮头被迫面对战争的残酷和屠杀的暴虐。捷克哲学家科西克曾说过:日常断裂处,历史呈现。不过,革命或战争往往始于变动,却又不可避免地终于恒常,在破除了一种生活常态之后迫使重建后的所谓新生活逐步凝固成新的常态。就本质而言,日常生活在历经革命风云或战争炮火之后复归日常生活的缓流之中。正如米兰·昆德拉借卡莱尔之后所说的那一句“坦克是易朽的,而梨子是永恒的”。
在《南京不哭》里,爱情被置放到大屠杀之上成为真正的叙事重心。作者郑洪如是坦言:“贯彻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小说即是以“情”为叙事内核,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幕布上勾连人物命运,喷绘浮世图景。早在1939年,张恨水即在长篇小说《大江东去》中做出了“抗战+言情”的文学探索。这部小说在一女两男的架构下倡导了舍弃爱情、保卫国家的价值诉求。就身份特点而论,《大江东去》的主人公们均为中国人,即是说抵御外寇的时代使命主要在民族国家的圈定范畴内实现。随着明妮·魏特琳、拉贝等日记文本的公之于众,南京沦陷期间西方人士的人道义举得到越来越多的宣扬和歌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书写。《南京不哭》的两对男女主人公均为“中国+美国”式的身份组合,都因死亡或离别导致身份组合的最终破裂。
较之宏大历史的全息图景,《南京不哭》着力开掘的是宏大历史中的个体命运,将个体成长轨迹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审视。主人公陈梅既是悲剧的亲历者又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小说以这个南京女孩的视角目睹了一个家庭的毁灭,以一个家庭的毁灭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创痛。作家逐步以“这一个——这一群——这个国”的潜在线索追求窥斑知豹的叙事效果,以更为细致入微的个体生命史折射出民族国家的灾难史。
二、他救式叙事模式的解构
就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叙事而言,拯救模式的铺展往往离不开这样一个话语情境:在狼烟遍起的南京,日本兵是无恶不作的施暴者,守城难民(含缴械战俘)是毫无反抗之力的受难者,而国际安全区的西方人道主义人士则是不畏强权的拯救者。就历史情形而论,拉贝、明妮、威尔逊、马吉等西方人道主义人士在南京沦陷之际不顾个人性命安危,积极筹建国际安全区,设法为大量难民提供安全保护和人道援助。这令世人所敬仰,为历史所铭记,同时也昭示着人道主义的超越性和宗教情怀的普世性。
不过,《南京不哭》在颂扬他救的同时,也更为充分地探究了自救问题。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主人公陈梅的命运起伏暗示了一条潜在成长线索,即“受难——反抗——拒绝怜悯——个体自决”。与外求于人的他救不同,自救更强调内求于己。小说前半部分的叙事布局没有突破以往的拯救设定,然而在最终的叙事走向上却质疑了借西救中的历史局限,也强力戳破了拯救神话的虚幻泡沫。小说中,任克文以振兴航天事业、抵抗他国侵略的神圣使命对美国教授约翰进行了各种劝说、挽留、激将乃至道德绑架,将其视为增强国力、扭转国运的关键人物。而垂危之际他却忽然意识到约翰有权利追求个人幸福和生命自由进而实现了对约翰的道德松绑。这无疑消解了文本前半部分所强力植入的拯救情结。与此类似,陈梅在挚爱之人约翰返美时同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痛悟。无论是任克文的歉疚还是陈梅的痛悟,都在无形之中扭转了文本的话语流动及潜于其内的价值指向,使得个体自决的实现有了更多可能。随着美国英雄的全面隐退,侵华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必须独立面对、全面承担和浴血抵抗的历史劫难,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则为国人提供了重新反思民族境遇,追求民族自立的重要契机。
作为点题之笔,小说两次出现的“南京不哭”极具隐喻色彩。第一处“南京不哭”出现在故事之初的“楔子”,第二处出现在故事结尾的“最后胜利”,皆以陈梅为表达视角。在第一处,甫经杀父之痛的陈梅犹如负伤困兽令人疼惜。面对美国教授约翰的劝慰,陈梅却语词坚定地答以“我不哭”继而道出“南京不哭”。就话语隐喻而言,亲历暴行的女孩与惨遭屠城的南京完成了符号同构与话语转喻,同时也实现了意义重叠——同样饱受欺凌却鼻息仍存,同样遍体鳞伤却不需要怜悯,同样因复仇的烈焰而引发生命灼痛。然而,在第二处,暂逃日军魔掌的陈梅却化身为被“美国英雄”弃之不顾的南京女孩。陈梅以拒绝怜悯的姿态撕碎了约翰留下的美国地址,并以此表达了自己的倔强和自立自强的决心,同时也寻求到实现自我拯救的唯一路途。结合人物命运来看,任克文死在战火纷飞的故国,约翰和珠迪于葬礼后返回美国,而陈梅携弟弟流落到重庆躲避战祸直至日本战败南京解放。中国人的苦难归根结底还是要由中国人自己来面对和承担。随着美国英雄的出走,拯救神话开始悄然破灭,而拯救力量实现了由外部向内部的转移,受难者和拯救者进而在国人身上实现了主体统一。
西方形象的优越性常常借由大屠杀期间西方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诉诸笔端,但这却丝毫无助于民族悲剧根源的深掘与反思。在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叙事中,拯救模式的解构所引发的是深层次的文本革命——西方中心主义的瓦解。当然,西方中心主义的瓦解不是一蹴而就的,作者借助绵密的叙述、缓慢的节奏不动声色地将其逐步拆解。长久以来,血性和反抗的双重缺席成为国人反思南京大屠杀时的心灵隐痛。尤其当300000这样一个惊人数字还原为国人群像时,我们几乎没有勇气直视无数冤死魂灵背后的那些沉默和软弱。而在《南京不哭》里,一幅布满血腥肉搏却又让人热血沸腾的反抗图景出现了:身陷时代碾压的南京少女在目睹了父母兄弟惨死敌手后,以自己的不屈和抗争杀死了一个对自己施暴的日本兵。陈梅已不单单是一个南京浩劫的受害者、见证者和复仇者,而成为超越了个体创伤、家国仇恨的文化符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梅便是惨遭蹂躏的南京,更是久浴战火的中国,而陈梅的觉醒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复活,更隐喻着一个民族的崛起。
三、超越民族的善恶之辨
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时,每个作家都试图寻求出悲剧发生的缘由及人性畸变的根源。与纳粹时期的屠犹暴行一样,南京大屠杀并非发生在南京的地方性事件,它们均赤裸呈现出人性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危机和挑战,同是人类学层面上值得现代人反思的人性失落悲剧。“在大乱离、大屠杀中,入侵的外寇、作乱的内寇,都会以突破伦理底线、践踏人性禁忌为大欢乐。”由此,对历史事件尤其是反人道暴力事件开展叙述不仅是对历史真实的复原,对施暴罪行的控诉,也囊括了对人性尤其是人性恶的反思。
在以往的文本叙事中,嗜血如魔的日本兵无疑是处处施暴的恶性代表,而明妮·魏特琳、拉贝、美国医生、传教士等外籍人士则往往被看作积极扬“善”的人道主义者。如《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南京大屠杀》等莫不在善恶分明的二元对立式架构下再现历史。然而,在《南京不哭》《紫金草》等新近的小说中,这种善恶设定显然开始无声消解,以往那种过于绝对化的善恶布局被逐步打破。作家们虽然仍在人性善恶的博弈中叩问悲剧根源,却开始对“善”有了不同以往的诠释。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即为西方外籍人士逐步隐匿在历史远景中,中国女性或日本老兵逐步被托举到叙事中心,开始成为新一轮的“性善”代言者。
相较于以往“妓女救国”“传教士救国”的类型叙事,《南京不哭》更关注的是普通民众见证民族悲剧、历经民族创痛之后的主体觉醒,尤其对以往二元对立式的善恶格局做了两个方面的叙事改变。第一重改变为在受难者群像中增加了美国战俘,第二重改变为在道德审判席上增加了越南战场上的中国兵。小说结尾借中国兵孙起之口补充陈述了日本兵在越南战场上虐杀美国战俘的事实,也坦白了中国兵在越南战场上充当杀人机器的无奈。这番陈述的话语前提为南京民众并非日本兵施暴泄愤的唯一对象,同时中国兵在别国战场上同样屠人性命。而这番陈述的价值后果则是南京民众所遭遇的悲剧随着受难者群体的扩大而有所冲淡,日本兵所背负的道德压力随着施暴者力量的补充而有所缓解。
小说潜在的善恶观主要依托任克文这一角色传达,由“人是善与恶的两栖动物”和“勿念旧恶,与人为善”两种价值理念共同建构而成。恶不再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类人群的专有属性,它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人性结构中,藏匿于每个人的人性深处,成为包括灾难受害者在内的所有小说人物共同面对的话题。就像任克文反复对陈梅所说的那样:“人是善与恶之中的两栖动物”,“我们所有的人,你和我都不例外,身体里面都有一个邪恶的种子和一个善良的种子。我们可以成长为其中之一。”与其说依托战争语境而集中爆发的恶性是现代文明时期的反动潮流,不如说它就是现代文明发展意想不到的直接产物。面对南京大屠杀,不少作家往往致力于寻求人性畸变尤其是恶性爆发的根本缘由,试图厘清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或为人父或为人子或为人夫的现代人如何强盗般闯入别人家中并摇身变成一个杀人父子、奸人妻女的嗜血恶魔。此外,还有不少作家倾向于超越民族仇恨和民族矛盾,而把对历史灾难的深掘指向人类学层面的现代性反思。在《南京不哭》中,依靠复仇来苦撑生命的陈梅最终选择了对日本战俘的宽容与和解,而“勿念旧恶,与人为善”是她反复咀嚼的价值准则。这意味着作家对大屠杀的反思已不再局限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抉择,而试图在超越民族仇恨的前提下复原善恶缠绕的人性情状并通过人物的内心转变来传递抑恶扬善的价值旨归。
作为二战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南京大屠杀不仅是发生在亚洲战场的特殊事件,也真实记录了人性理想在现代文明时期的坍塌。故而,以文学或历史的方式对其进行书写,既关乎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也关乎人类集体记忆的文化建构。在现有的南京大屠杀叙事中,基于人类层面的文学反思逐步成为主导潮流。这与华裔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有关,也显示了他们将民族事件置放到世界价值序列中所做出的叙事努力。不过,我们仍需充分顾虑到民族国家叙事之于南京大屠杀记忆建构的重要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南京大屠杀作为民族的灾难史,必经‘民族国家叙事’阶段,经过这一阶段的成功写作后,再有大范围地进入‘人类层面’的书写,方是真正对死难者和民族历史负责。”
在那个由历史暴行层层构筑的话语场中,无论是造恶者抑或者在恶行面前紧闭双眼的“平庸之恶”者均难辞其咎,因此被共同钉上“南京恶魔”的历史耻辱柱。鲍曼在研究大屠杀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即是说,大屠杀悲剧固然该由战争的制造者承担实际责任,而道德感的缺失和无所作为则应成为放逐人性者自觉肩负起的道德责任。
结
语
在跨越中西文化的双重身份下,张纯如、哈金、严歌苓、郑洪等华裔作家本着对真理、正义、人道的不懈追求去书写南京大屠杀,同时也试图突破西方文化霸权的规约进而为中华民族“发声”。“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正是基于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主流话语中的被“遮蔽”状态,“对世界发声”鼓舞了作家们为民族历史“去蔽”的决心,也被他们视为铭记民族悲剧、恢复民族尊严、提升民族地位的重要途径。作为回顾民族历史的重要记忆手段,文学则致力于复原、建构、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包括民族创伤在内的一切人性景观。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忘却以往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战胜造成这种苦难的力量。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
在《南京大屠杀》的扉页上,张纯如以“遗忘大屠杀是第二次屠杀”警示世人,而大多数作家正是从还原真相或抵抗遗忘的诉求中寻求到创作内驱力,以或文或史的书写方式进行民族记忆复原。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进入文学创作视域时,作家们在宏大的场景和惨烈的悲剧之外愈加注重考量历史灾难情境中纷繁复杂的个体经验,即余华在《我们的安魂曲》中所说的“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就创作立场而言,“重审国民性”作为第三股叙述流,与镌刻民族记忆、疗治文化创伤共同肩负起南京大屠杀文学叙事的艺术道德。何建明在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之际先后发表了《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时,我们该想些什么?》《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纪实〉:发现与反思比历史本身更重要》等系列文章,以“十问国人”的方式呼吁我们反思南京大屠杀时不仅要控诉日本罪行更应深度清理国民劣根性的余毒。其实,不少涉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作家们在重审国殇之时都不免升腾起“书成国恨心犹烈、唱罢梅花意未休”的心灵隐痛。就民族历史而言,死亡或墓碑在某种意义上绝非悲剧的终点,倘若忽略了“抉心自食”般的“本味”探究,似乎很难彻底实现国民根性的洁净、提纯和升华,而以重审国民根性为起点的民族内省则为民族国家的文化更新和长足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话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