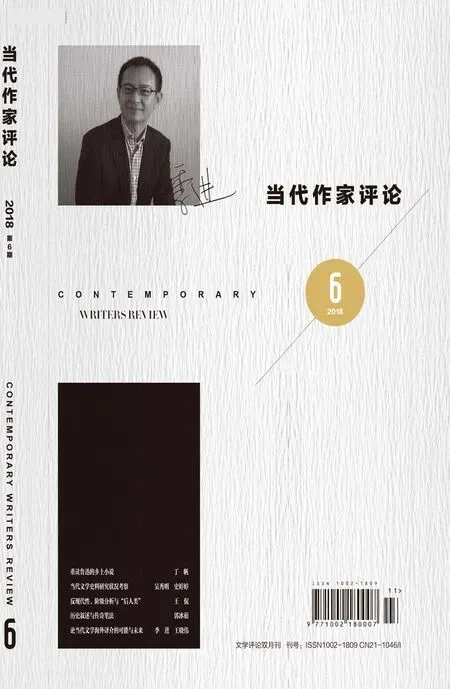一篇《锦瑟》解人难:《风声》的游牧诗学、重复叙事和物之抒情
余夏云
麦家的小说有心对话历史,这早已为识者所见。不过,其流利的文字和特殊的题材,似乎一再妨碍我们对此议题做出深耕。尤其是放置在80年代以来,苏童、莫言、王安忆诸位在写家史、家事的背景下,麦家介入历史、调停古今的动作,未免失之单薄,甚至过于主流、娱乐。与前述几位魔幻、缛丽、荡气回肠的民间叙事不同,麦家的小说不单语言清浅,而且故事常常徘徊在正史周围,查漏补缺,难以见出有“发愤著书”的迹象,更遑论嘲弄或者瓦解大写历史的决心。而且更甚者还在于,他非但不以大写为忤,反而一再暗示稗官野史其实存有自爆的可能。他苦心孤诣地调用各种技术(如访谈、实录)来铭刻证言、完备讲述,却也无法阻止故事中的叙事者常为各种质询、怀疑所干扰,从而自我折磨、苦不堪言。
在这一点上,他与王朔玩世不恭式的叙事拆解,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在《动物凶猛》里,王朔也同样让他的叙事者骤然意识到记忆的虚妄和讲述的暧昧,从而引出了“元叙事”的问题,但毫无疑问,这位叙事者远比麦家笔下的“我”来得更为主动。无疑,王朔笔下的叙述者也带有鲁迅式的高自标置,呈现了一种积极的介入姿态。
而相较于王朔而言,麦家的叙事者无疑显得被动。故事既没有被拦腰阻断,叙事也未能挑起对任一陈规的协商或改写。“我”老老实实地复述完一个故事,又被逼无奈地去聆听另一个版本——这样耳闻式的接力叙事,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自然保守有余而批判不足,而且还有重蹈晚清谴责小说步履的嫌疑——叙事者随波逐流,不够高瞻远瞩。
在本文里,笔者将追问这种拖延叙事的方法,是否真的只是暴露了叙事的平庸和被动?或者说,遏抑叙事高潮到来的做法,真的仅是通俗小说所预设的一种消费伎俩吗?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处理,是否可以放在一个新的观察脉络里来讨论?如果有,这个线索是什么?再进一步,如果我们非要强作解人,将麦家对话历史的冲动,和莫言、苏童等人的先锋实践等量齐观,那么,他又在什么意义上得以进入这一叙事序列,并提供了哪些新的特质值得我们为之瞩目、赋能?我将试以《风声》为例来展开讨论,并分辨这个故事极有可能回应或者说“引用”了李商隐最难索解的作品《锦瑟》。因为这首七律同样触及了时间以及对时间的认知问题。
重复美学
《风声》有着复杂的身世,这一点麦家已经做过夫子自道。他坦言故事的主核其实来自中篇小说《密码》,而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十万余字的版本《密密码码》。这部书稿曾经因为和《密码》过度雷同,而被出版社拒收,认为是扩充之作,新意阙如。《风声》的诞生,应该说,是得益于对这两部作品的大幅改写,尤其是叙事方式的调整,更为之带来了关键性的转变。熟知现代文学的读者,自然不会忘记祖师奶奶张爱玲所进行过的一系列类似操作。通过不断地征引、改写、翻译早期作品,张爱玲既显示了她难以割舍的上海情结,也暴露了童年的创伤是如何历久弥新,难于超越。王德威说,她转记忆为技艺,一面是有意挑战革命、启蒙的直线史观,用重复与回旋来自我消耗,同时也指正了历史粘滞、衍生的层次;另一方面,借着对旧事节外生枝式的再叙事,她也毫无疑问地瓦解过去是独一无二的假设,提供了一个以虚击实的批评界面来窥看历史、记忆与书写的辩证法。
张爱玲的再生论述,横跨语言、时代乃至文化的鸿沟,步入晚年,这样的尝试更趋激烈,就表面而言,我们不难指正其中包蕴的题材症结和文化乡愁,但更进一步,我们似乎还要理解“重复”,其实也指涉第三世界的文化困境。张爱玲以寓言化的方式,集中展演了伴随20世纪中国的重生热望。以文学为例,从清末的“新民”论述,到五四的“凤凰涅槃”,再到世纪中期的“时间开始了”,均历历可见其对脱胎换骨的革命经验的迷恋。在此,“重生”当有断裂、超拔,另起炉灶的意味。但是,于张爱玲而言,这样的再生缘,恐怕无法寄托她意犹未尽的折返之意。换言之,“重”的意思,当然隐隐指涉了一个晦暗不明的前文本,如何念兹在兹、幽魂不散,而且更甚者在于,其极致处恐怕不是“新”的可能盖过“旧”的面目,而是旧的面目始终停滞不前,令意义悬置(aporia)搁浅。
当然我们注意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张爱玲,其实已经来到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也因此,她的重复势必让我们提出这样一种假想:即为了检验那些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故事同样会拥有国际市场,或者反过来,为了试探所谓的世界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包容了异质的地方经验和民族记忆,张爱玲重写了她心目中的“全球本土”(glocalization)经验,构造了一种全球格局里的文学“异乡记”。王德威以为,张爱玲晚年有心发展“易”的哲学,当中包含变易、不易和简易等相反相成的面相,足以显示其人重复美学的错综复杂。在一定意义上,重复是变异,但毋宁也是对“异”的警觉。无论是事易时移,还是人地两疏,凭借张爱玲对历史的慧敏判断,她当感到一种“惘惘”的文化威胁,以及对自我根源的反省。也因此,她的“易经”似乎也就指向了《色戒》中那个似有若无的易先生,以及由其所代表的背叛诗学(a lyricism of betrayal)——她离开了懂她的上海读者,却不愿意背弃对他们的文字承诺,愿意在一个变更的时空里,持续讨好他们,证明他们的选择和目光如何毫厘不谬。同时,她用对世界读者的包容和博爱,毫不保留地将原本只馈赠给上海读者的故事和盘托出,慰藉其人的日常苦痛,从而为自己的去国离家,做了最崇高、抒情的粉饰和寄托。
借着张爱玲的例子,我们要讨论麦家的重写叙事,其实未必抱持那么深重的家国伦理或读者视野。麦家的小说尽管同样炙手可热,但是一路走来却磕磕碰碰。换句话说,他并没张爱玲式的对题材或读者的一贯期许,抑或负累。也因此,其人在谍战题材上的重复,其实应该是幽怀别抱。过去的讨论指出,《风声》与《罗生门》在叙事上存在类同。同芥川龙之介相比,《风声》应该更接近限制叙事的本意。说到底,这个故事虽然也触及黑暗世界里的人心起落问题,但用意却并不是要借此揭开语言的诡术,来探求道德本真。恰恰相反,它不断激励语言来发挥它智识的一面,放大理性运思的能量,来使讲述者脱险。换言之,叙述在芥川龙之介那里,是一种卷入行为,而麦家则视其为“逸术”,一种逃离的方法。故事里的人物(读者也同样如此)将就着十分有限的生存(阅读)资源,来最大化叙事的能量,讲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也因此,《风声》往往被视作新智力小说的代表。
但是,吴金李顾的斗智,毕竟只是故事的一个层次,跳出了“东风”,另有“西风”“静风”。尤其是“东风”“西风”之间所形成的“重复”关系,更预示小说所要处理的问题,其实不唯是历史的,更是史学的。照专业的知识来看,历史“所要探寻的是客观历史过程的目标、意义、规律、动力等问题”,而史学“则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历史认识和历史揭示的特性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探讨”。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史学的发展在西方世界经历了至为著名的“语言学转向”,或者说修辞/叙事转向。也因此,在目前的情势里,史学所要重点分析的问题,乃是要厘清它与文学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或者说,某种重复性构造。这种形式主义的思路,无形中指明了“东风”和“西风”的关系,无论是互补,还是对立,其实都只是我们思辨历史的角度之一。由它们所组成的叙事整体,其实还另有一个潜在的对话文本,即其他类型的历史叙事方案。我们可以称之为复调对单音。
表面上,麦家的史观消极虚无,但考虑到这样的认知,其实得自他反复操演叙事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该憬悟:他实际上是要把叙事的困境作为一个问题,一次性地呈现出来,而不是像张爱玲那样透过多次重复的方式来消磨、遮蔽这种困境,甚至暗示重复有可能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即她可以讲出一个完美的故事,来终结这种重复。相形之下,麦家对书写的看法,吊诡而暧昧,他试图通过讲述来讲出所谓的“不可讲”。或者退一步说,借由讲述来推敲讲述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重复的进程,描画了话语逐渐产出、立定的思想图谱。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过程是张爱玲探究用英文来讲述/翻译中国的合法性的一个镜像。它们均涉及了如何跨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区隔,来达成对话的问题。尽管各自的答案殊异,但两位都追问了如何呈现中国的问题,并且还表明:所谓的差异多是意识形态的后果,而过分强调差异更会模糊事物之间的互动关联。易言之,重复美学的要义是互动,而非对立。这就好比《风声》马赛克式的拼图叙事,内部自有一条姻亲血脉的线索加以联系、维持,令不同政党以及民间的声音彼此流动、充实,成为一个复调型的整体。
“风”作为一种史观
在麦家看来,“风”所代表的自是叙事中最晦暗不明的层次,也因此它和芥川龙之介式的幽暗意识大有瓜葛,但是,就史学的认知而言,风未必不能展示历史的体貌,甚至表征某种体量化的趋势(如学风、政风、时风)。而在此视域下,“捕风捉影”当是把握历史的重要手段之一。“刘咸炘认为‘史’不应该有定体,应该根据所要描述的‘风’而创设新的史体。他认为能捕捉‘风’的史体要能兼顾‘上下’和‘左右’。所谓‘上下’,就是要贯穿……但他同时也讲‘左右’,讲‘横’观。”换句话说,察势观风的本质乃是“汇聚”和“综合”。它反对那种定于一尊的单音独奏或一时一地的狭小视域,讲求通观全览,“宇宙如网”。
而在一般的论述里面,主流的历史讲述往往要替单音受过。其体例上的完备与行文上的流畅,均被看成是设定意图过于明显的表现。严丝合缝、从善如流的讲述,自然也少不了要操刀裁剪许多无用的“边角料”和“怪兽性”。也因此,万状无形的“风”,在大写的意念里,最终要被划归到公律、科学、思想等言之凿凿的概念范畴里去,坐实历史的可感可知。一方面,大写历史姿态高蹈,备受挞伐反思,自在情理之中,但另一方面,那些假个人、家族之名而出之的小写历史,其实未必没有需要检讨的层次。陈思和早在他处指明:民间讲述生机勃发,却也藏污纳垢、泥沙俱下。言外之意,这些起于对抗大写历史的叙事,在分庭抗礼之际,其实掺杂许多自由主义的思维,将个体的经验和家族的活动看成理所当然,不受质疑的存在。而实际上,在此二元的构造里面,“对抗”才是最为大型的书写符码。通过占据道德上的高位——代言民间、尊重个体、多元发声——“小写历史”因此一跃成为比“大写历史”更为崇高的意象。在一定意义上,小写反而是一种更为隐晦的意识形态。
当所谓的新历史主义,本着解构、反讽的初心进入到文学场域之际,它应该早已料想到,有朝一日经过层层的试炼和重复,它终究会成为一种书写的技术和常态,性质由新而旧,或者说,逐渐抹平自身的先锋性和批评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到民间讲述其实也不过是在“大写”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单音而已。而与这种对抗的构造不同,我以为麦家的叙事,有意打开大小历史之间更为复杂的分歧和互动。透过并置东风、西风、静风,他等于取消或者说至少令那个总能在危机时刻能火速驰援、解决难题的机械神(deus ex machina),徒劳无功。传统叙事里面,一旦故事进入僵局,总有一个神从天而降,令一切困难迎刃而解。但在麦家这里,叙事开裂、前后对立,他均不加施救,甚至还扬言“我所了解的其实还没有被蒙蔽的多”。讲完东风、西风,他本可见好就收,却又枝枝节节地牵出一些本该前置的背景材料,令叙事更趋漫漶无形。
但也正是在这种无法定形、收拢的叙事里面,我们读出了一种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所谓的“游牧”之意。借镜这种以混沌和有限经验为观察要点的思路,我们不难说,麦家正是那个做“修修补补零活儿”的匠人。他当然知道,甚至深谙写好一本(历史)小说所需的各种技巧,“东风”就是一例。但是他说:“卡夫卡靠做梦写小说,博尔赫斯靠读哲学书写小说,写小说的门道看来不止一个。我收集各个年代的地图、旅游册子、地方编年史,然后把胡思乱想种在合适的时间、地图上。我就是这样做小说的。”熟读麦家的读者,当然还知道他笔下的叙事者常去采风、访谈,复印各种机密档案、私人日记,甚或留影存照,俨然要将整个写作的过程搬进小说,使之成为小说最重要的部分。“他”捕风、听风,看似目标明确,但又常常为材料所限,诉讼质询缠身。东风、西风、静风三足鼎立,看似兼听则明,可其实,他不妨已经暴露:偏听才是令人昭昭的最佳方案。如若我们要巨细靡遗地展示历史,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得叙事变得一筹莫展,永远盘旋在所谓的“真实”外围。
这令人想起茅盾,他也曾受困于写实的限制。乍看之下,他和麦家毫无相通之处,至少在追求所谓的“时代性”上,他的执念无人能及。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执念,他遭遇了叙事上的背反。为了能够容纳时代的全景细节,展示历史的必然,同时也为了维持艺术上必要的水准,茅盾避开了清末小说流水账式的记述方法,转而在巴尔扎克式的“科学”布局观中找寻灵感,但很快,茅盾发现:这种强烈的分类意识,使得本该客观的历史,全都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破坏了观察与阐释之间的平衡。茅盾的本意是藉由文内的整饬来理顺文外的乱象与失败,却不想首先遭遇观念和形式上的矛盾,导致历史被越描越“黑”,越写越暴露个人的无力和悲观。
而既然见证了前辈言多必失的无奈,同时,也无心为历史的目地论背书,麦家自然可以好整以暇地重新布局茅盾的“布局欲望”(desire for plot),变废为宝,将写实的限制反转为一种关于修补的技艺或诗学,“游牧”地呈现出来。这样的“优游”,当然得益于麦家的处境,他从现在回望过去,而不似茅盾需从今日推敲未来,也因此,双方所持论或展示的其实是“诗学正义”与“正义诗学”的对话。对麦家来讲,大国肇造,当然要跳出一己政党的局限,转从民族国家的层次来再行理解,重新肯定各方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并为今时今日定义“全民”的概念提供参考。破裂、多歧的叙事形式,既代表历史本身的偶然多发,也揭示历史目前被接受、呈现的状态。诗的正义,恰恰不是去缝合裂罅,而是将这种裂罅症候式地展示出来,让“历史”乱象有一种非规训化的存现形态。简言之,以“风”的形式出现。
如上所言,“风”毕竟暗示“介面之间的永不间断地,‘不能以一瞬’的交互作用(reciprocal)”,所以,它不必固化为一种二元的结构。这种交互的作用,既见诸文本之间(inter-textual),如与大写历史、民间叙事的对话关系,也可表现为文本内部(intra-textual)的“多重渡引”关系。“多重渡引”乃是作家兼艺术史家李渝在探讨小说技巧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观念。对她来说,小说家在作品中努力布置多重机关、设下重重道口、拉长视距,凡此种种并不是要活灵活现地反映人生,以写实的逻辑贯穿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恰恰相反,“多重渡引”讲求驴唇马嘴、引譬连类,以文本构造上的“意识流”集锦串联出一个“故事集”。她的作品《无岸之河》,从《红楼梦》讲到沈从文,再接入自己听来的各色故事,可谓琳琅满目。但因故事内部缺乏必要合理的联系,也就不由得不引起我们的好奇,并深感一种怪异(grotesque)的魅力正在发酵。至此,茅盾充满意识形态的“布局”意念,到了李渝这里,当另有一种宗教式的天启意味。她以“无岸之河”来召唤历史长河的形象,暗示此间人物的遭遇如何能够按部就班,一蹴而就?她投以宗教式的随遇而安,令时间的流动保持它游牧、偶然,充满褶皱的面目。或许,麦家并不熟悉李渝的作品,但一定会对她所力图呈现的历史百般周折的模样,以及流转其间的人间伦理和宗教因素心有戚戚焉。《风声》的叙事方案本就照搬自宗教典籍,其中人物在关键时刻也常呼上帝、神灵。他以“东风”刺激“西风”,再回转到“静风”,亦或者我们还可以重新排列、置换三者的关系,令当中的“引渡”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但无论如何,对麦家和李渝来讲,历史的这种突兀、扞格的组合方式,方才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如风般的流动与偶然。甚至更进一步,相比起历史记述,小说的玲珑多变,其实更适宜捕捉时间的万千变化和“浑全之体”。
物之抒情
对萨义德(Edward Said)来讲,类如麦家、李渝这般任由作品中的突兀、停顿横生而不加调和,甚至想借力使力发展出一种风格或伦理的做法,“以late(晚)、belated(迟)这类字眼形容他们,似乎无比贴切”。换言之,“晚”总以一种比较的姿态存在,它既包含时间的提前到达,也兼容世代的完而未了。而如此境况里,“当下”则成了永远“在场的缺席者”(the present absentee)。与之相对,过去和未来则成为一种“缺席的在场”。
借镜上节所言的“游牧科学”,我们不难指认,这样混沌的时间结构,毋宁代表了一个持续开放、流变生成的过程。如果说,访谈、实录是《风声》生成的现实文本,其讲述的内容是“被历史无情前进脚步忘记或遗落的境域”之一,那么,萨义德所言的这个可以寄托归家之思的“境遇”,是否还存在一个文学的文本,来应对麦家对主题及人物命运等的思考?就好像它和《圣经》在叙事模式上形成的互文关系那样。在此,我们想到的是李商隐的《锦瑟》。
关于这首七律的聚讼纷纭,已无须我们多言。麦家对这首古诗的搬用,延续了李商隐一贯引经据典的做法。诗中庄生梦蝶、杜鹃啼血、鲛人泣珠、良玉生烟的故事,早成吾辈常识。麦家以“庄生晓梦迷蝴蝶”一句来指涉顾小梦,当是对诗篇最明确的化用证据。庄生、蝴蝶互为镜像,而迷梦又惝恍流连,难分虚实,就如同顾小梦似敌似友充满暧昧,令人无尽揣想。也因此,后半句“望帝春心托杜鹃”等于坐实了,顾小梦不过是一个假托的幻形,她必以变化多端的形象来实践自己的志愿,为国效忠。颈联“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既暗含一个与“金生火”同构的“玉生烟”结构,也同时伏脉李宁玉背后必有“良人”(吾夫良明),但饶是如此,她无法逃开多舛的命运,必将如云烟消散,令人可望而不可及。想必慧心的读者早已识破藏在“李宁玉”名字里的机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谁是老鬼?其实麦家早已事先张扬,把谜底写于谜面。而如此,我们便不能草率地推断故事层层叠叠的猜谜叙事,纯是出于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闲,而应另有蹊跷。至于鲛人泣泪,则可能暗示东窗事发、身份暴露的当口,李宁玉声泪俱下感化顾小梦的情节,她以眼泪作为最后一搏的寄托和武器,来求得沧海月明,革命胜利。
麦家化用诗篇的颔、颈两联,来发展两位关键人物的命运,也或者说,分别开启“西风”和“东风”的主角叙事。而贯穿两者,当是尾联所谓的“惘然”之情。庄生晓梦是对人生虚幻的发掘,子规啼血是对归宿的迷惘,良玉生烟则是不可置于眉睫的视觉迷茫。而“惘然”之所以起势,实在肇因于锦瑟年华流逝。故此,首联五十华年或要回应“西风”中所讲的“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样的时间设定,亦或者和白小年的名字有涉。读者或要追问,纵然世事流转,可言说者仍能事无巨细,又何来“惘然”之说?实际上,“惘然”并非言“事”,而是为了说“情”。尤其当我们知道顾小梦和潘良明的夫妻关系之后,那么更应明了:革命加恋爱的故事,因为中间隔着历史和政党政治的迷障,毋宁更趋千回百转、摧折人心。表面上,东风、西风针尖对麦芒,可从另一个角度,“我”又如何不是扮演了时间的良媒。通过为人著书立说,竟暗中帮助这对天涯两隔的夫妻重续前缘、鱼雁传情。两人所接力讲出的故事固然宏大可观,却无不牵扯个人的情丝万端,其极致处,更有可能使大小反转:革命的历史俨然成为恋人的絮语,或言诉之不尽的情爱话题。至此,那个表征公共意识的“第三世界寓言”,或要因此平添一份假公济私的嫌疑。既然小我和大我从来须臾不离,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大我也有可能被转为小我,而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弃小我为大我。
是在这样的观察里,我们最后来到了王德威所言的“有情的历史”。他用这个概念来涵盖如下一种状况,即于政治剧变的世代里面,文人知识分子与时俱变,一方面既不得不直面来自革命与启蒙的征召,另一方面,也将不断触事兴咏,于崇高之中参入肉身化的七情六欲,乃至彷徨动摇。在此,“情”既代表内在自我的涌现,是情绪、情感;也指代人世实际的状况,是事情、情状。而与之呼应,“‘抒情’也涉及主体对人‘情’与人‘事’的双重介入”。对王德威来讲,抒情的关键毋宁在“人”,也唯有其在时间的流转里面,不断去触碰人、事,方能发皇情的可能,见证诗与史的对话。
而与王德威相比,麦家的叙事固然首肯有情主体的关键性,但同时也泄露对抒情容量或时限的担忧。毕竟随着人、事的代谢、消磨,由此所起的“情”,也终将转入消亡不见,也因此,“惘然之情”必定转投其他的触媒来自我安顿,在各种废墟、遗迹中重整抒情的光景。由此我们注意到,故事中另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裘庄。它既是一个大型的时间装置,包罗清代以来时至今日的百年历史,见证土匪、黑帮、军阀、日寇以及红色政权在此更迭,也因此是一个巨大的欲望载体和记忆空间。作为一个时间性的(temporal)地景,裘庄兀自岿然,甚至反客为主,它不断地经验人事,发展抒情的可能。如果说,抒情之谓是启动人我的互动、物我的两观,是以人的主观主动去与世界结交,以动制动,那么,裘庄毋宁代表以不变应万变的抒情性方案。在此,我们领会李商隐虽在诗中不断指正万物的虚幻莫测,但他毕竟情有所起,是就瑟写情,而不是完全凌空蹈虚,无所依凭。由此,“裘庄”即为“锦瑟”,它无端转入乱局,引起各种纷争,同时也见证各种人心鬼魅。是此,“静风”看似冗余拖沓,无关紧要,却着实代表一种抒情的动力学。由它作俑,引来各种人事,然后有抒情声起。麦家说,静风不静,只是吾人无察。有关、无关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情的历史,也应是物的历史,这或许是《风声》发要发出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