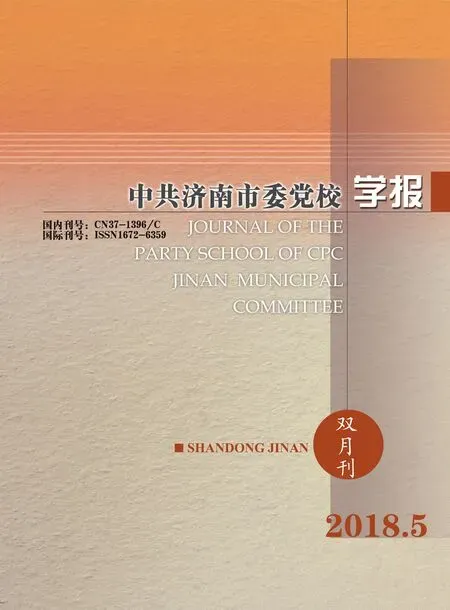宋代济南刘家针铺印刷铜版考论
周长风
一、铜版广告文字内容辨析

在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块标注年代为北宋,用于广告印刷的青铜版。该版左右长13.2厘米,上下宽12.4厘米,四周以双线为框,框内分上中下三部分内容。上层为阴刻楷书“济南刘家功夫针铺”8字。中层的中间是白兔持杵捣药图案,两侧各有4个楷书阳文,“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层7行楷书阳文广告词。每行4个字,因锈蚀漫漶,众字释读多有不同。现辨识如下:“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旅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
“误”字因残缺而难以确认,是依据上下文,并结合历史情况推测的。《宋史·兵志十一》记载:宣和元年(1119)“权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郑济奏:‘本路惟潭、邵二州各有年额制造军器,今年制造已足,躬亲试验,并依法式,不误施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下诏:“淮南运司见行修整夺到虏人粮船,虑有底板疏漏,不堪修整,枉费工料。可尽数发赴两浙转运司交割,委官相亲(‘親’应为‘視’字之误),重行修换,务要坚固,不误使用。”1980年,新疆吐鲁番文物管理所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发掘出土一件元代杭州泰和楼大街金箔铺的金箔包装纸,上面40字的木刻墨色广告印记中,有“不误主顾使用”字样。据此类广告词的说法,铜版中的“误”字得以确定。
“兴贩”前二字亦锈蚀难辨,有识作“转卖”、“各转”、“客转”、“若被”等等,“转卖”与残存字形明显不符,“各转”、“客转”、“若被”则俱嫌生硬,意义不甚明确。此二字应释读为“客旅”,一是与铜版残存字形大致吻合,二是“客旅兴贩”这一词组大量见于宋代文献。如范仲淹《禁秦州博易奏》、包拯《论茶法》、欧阳修《乞放行牛皮胶鳔》《再乞放行皮角》、 苏轼《乞罢登莱榷盐状》、朱熹《乞行下江西从便客旅兴贩米谷》、王炎《又画一劄子》、蔡戡《乞免增籴二十万石桩管米劄子》;再如宋代地方志,淳熙《三山志》、宝庆《四明志》;《宋会要辑稿》尤其是“食货”、“刑法”、“职官”中亦比比皆是。至于像“客旅便于兴贩”、“客旅不许兴贩”“商旅兴贩”“客旅私贩”之类,在宋代文献中更是不胜枚举。“客旅兴贩”在元代文献中也属常见。
铜版中的白兔持杵捣药图,源自月亮上有玉兔捣制仙药的古代神话传说。该图可视作后世所言的商标,而非装饰性图案。针铺主人选择这一创意,应是基于感性形象的联想,由悠久传说中的月宫里捣药的白兔,联想到月亮、嫦娥。月亮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因其区别于太阳的温柔、宁静、清凉,以及每月周期性变化,而成为女性的象征。嫦娥则是中国的月亮女神。针线主要为女性所用,女性是针铺的目标顾客。这便是针铺主人选择捣药的白兔作为商标和门前广告形象的文化心理。
这块铜版亦是用于印制包装纸的。这种写有印有广告、说明等文字图像的商品包装纸,古代称“裹帖”(亦写作“裹贴”)。“裹”,包裹的意思;“帖”,指带有文字的布帛、纸张。《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所列举的南宋杭州作坊中,即有专门代商家印制裹帖的作坊“裹帖作”。
二、判断铜版年代的依据分析
这块铜版是从哪里发现的,据何确定是宋代文物呢?在书报刊的大量介绍中,最多提及铜版的两个人,是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和著名广告专家徐百益。1946年初,杨宽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晚年他回忆道:那时“后来我们又从古玩铺中,买到一块‘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铜版’,这是一件很难得的珍品”。[1]1957年下半年,徐百益在上海市广告公司设计科工作。他在《八十自述——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一文中写道:“在这段时间,我到上海博物馆参观,发现一块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铜版,回来向经理汇报,由公司备信请上海博物馆拓印,寄到中央商业部组织技术局关心广告的陈新科长,他大感兴趣,从此看到了我国最古老的广告。”[2]由以上当事人亲述可知,这块铜版既非现代发掘出土,也非历代传承有绪,其断代应是由杨宽或与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同事作出的。但当事人并没留下考释文字,后来亦未见有学者和相关机构加以说明,以致至今质疑者大有人在。
笔者认为,将铜版断为宋代(指北宋,济南其后为金地),应该说大致可靠的,主要根据有四:
(一)宋代店铺习以姓氏冠名。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生产的专业化和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大为提高,随之城市的数量和规模较前代也有显著扩展。城市内各类店铺、作坊遍布大街小巷,同业竞争日益激烈,对品牌和产品的推广和传播自然竭尽心力。
孟元老著于北宋覆亡之年靖康二年(1127年),追述都城汴梁城市风俗人情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100多家店铺,门前招牌上所书店铺名号,大多数冠以主人的姓名、称呼、绰号,如李生菜小儿药铺、丑婆婆药铺、荆筐儿药铺、仇防御药铺(防御,防御使;宋代市井习以各种官职作相互称呼的敬辞)。这其中又以“姓氏+‘家’+商品(经营类别、范围)+‘铺(店)’”的格式为最多。像宋家生药铺、唐家金银铺、李家香铺、梁家珠子铺、郑家油饼店、余家染店、张家酒店。其次是招牌只写“鹿家包子”、“曹婆婆肉饼”之类,略去“店”、“铺”字样。而医药铺有的则只写“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丸)”、“柏郎中家”之类。上述在北宋张择端所绘反映汴梁风情的《清明上河图》中,俱有直观再现。
(二)铜版使用楷书字体。铜版的形制、使用方法类同一方大的印章,印章以及钱币、铜镜用字在宋代以前是基本不用楷书的,至宋代则为常见。
(三)“客旅兴贩”一语大量见于宋代文献。却未见于唐五代文献,元代也常见,搜检《元典章》《元史》便知,明清则不多见。
(四)宋代手工业作坊惯于所作器物上刻写“功夫(工夫、公夫)”一词。元代此举未曾获见。古代汉语中,“功夫”在指作事所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因之所获得的某方面的造诣本领时,多写作“工夫”。由于“工夫”笔画少,在器物上尤为常用。在宋代瓷器上也有因音同而写作“公夫”的。
1983年3月,在浙江省永嘉县下嵊公社(今巽宅镇一带)出土一批宋代银器,多有铭文,其中有“京溪供铺功夫”、“冯将仕工夫”字样。“京”指北宋都城汴梁,或南宋行都临安。“将仕”,官名“将仕郎”的简称,如同上文所言“防御”,乃敬辞。2003年,在武汉市江夏区青龙山林场发现7件窖藏宋代银器,一只银簪上刻有“王家工夫”字样。1986年5月,在江苏省常州市红梅新村发现的北宋墓里,出土一件方形铜镜,其上的印鉴式长方框内,有楷书阳文款铭“常州果子行西供使蒋家 炼青铜工夫照子”。1984年,常州市博物馆还征集到一件方形铜镜,上有铭文“常州果子行西供使蒋家 炼青铜工夫照子清记”。宋代常州蒋家带“工夫”铭文的铜镜,1930年代也曾在朝鲜古墓中发现。宋代为避开国皇帝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名讳,称镜子为“照子”、“监子”(监,通“鉴”)。
“盃”同“杯”,因方言中与“百”音近,制镜工匠把“百炼”写作“盃炼”。东晋王嘉《拾遗记·方丈山》:“有池方百里,水浅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为器,可作舟矣,百炼可为金,色青,照鬼魅犹如石镜,魑魅不能藏形矣。”后人因称精炼的铜镜为“百炼镜”,亦作“百炼鉴”。
各地出土和传世的宋代铜镜有“工夫照子”字样的极多,因绍兴三十二年(1162)至绍熙元年(1190),朝廷曾一度中止避讳,南宋铜镜也见有“工夫镜”字样。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鉴定专家丁孟在《铜镜鉴定》一书中讲道:“宋镜大致自北宋政和年间开始出现铭文。铭文绝大多数为商标铭记,格式一般都是先标明州名,再标明姓或姓名,有极少数铭文还标明店址;最后是‘照子’或‘照子记’字样。这种铭文的格式,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因此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3]
1986年12月,在浙江省义乌市柳青乡游览亭村发现50余件窖藏宋代银器,其中一件银执壶底部阴刻楷书“仙都张家功夫”。“仙都”为浙江西南部一地名。传世的宋代福建德化窑瓷盒款识有“后山颐草堂先生雕造功夫”、“颐草堂先生雕造功夫”等字样。
1978年11月,在浙江省江山市礼贤乡后亭山村宋墓出土的影青印花方瓶底部,有阳文反书“周家公夫”款。
在浙江省武义县出土的宋代印纹瓷盒(出土时间未见记载),底部印“练八郎功夫”五字。1983年,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庄出土宋代澄泥质抄手砚,砚背印长方框,内有阴文楷书铭文“枳沟徐老功夫细砚”,现藏济南市博物馆。“枳沟”,今山东省泗水县枳沟镇。1919年或1920年,在河北省巨鹿县县城内出土大量北宋澄泥质抄手砚,有专家认为是大观二年(1108)黄河决口埋覆之物。其中有钤“滹阳刘万功夫法砚”印款于砚背的。传世澄泥砚中也多见有“刘万功夫法砚”、“滹阳刘万功夫法砚”印款的。“滹阳”滹沱河之阳。“法”,标准、模式之义。
还有几点细微之处值得关注。其一,所列举的确定出自宋代北方的器物,俱用“功夫”而不用“工夫”、“公夫”。其二,“功夫细针”与宋代的“功夫细砚”同出山东,用词用字又何其相似。其三,浙江省诸暨县(今诸暨市)高湖公社大明大队寿家山出土(具体年份未见记载)的宋代铜镜,上有铭文“湖州仪凤桥南石三郎青铜镜,门前银牌为号”,后一句与济南刘家针铺铜版用语亦甚为相似。这些也都有利于铜版“宋代”说。
当然,以上所讲,并不能完全证明这块铜版为宋代遗物。有人就指出,北宋时济南称齐州,治平二年(1065年)齐州置兴德军节度,亦称兴德军,政和六年(1116年)升为济南府,此时距北宋覆亡之年,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仅仅11年。在宋代,每州一般还有一个郡名,齐州因之亦曰济南郡,宋代的“郡”主要是供王公封号之用,与民间并无关系。北宋时齐州百姓平日里还是习称济南,或二者兼用。这也很正常,那时的官府没必要强制民众在此事上处处与其保持一致。当时的人如苏轼、苏辙、曾巩、黄庭坚,还都是官员,曾巩更是一州之长,他们描写记述济南风物人情的诗文,特别是标题之外的文字,即爱用“济南”,而少用“齐州”。
综上所述,这块铜版制作年代不会是唐五代及更早,尽管不能完全排除金元甚至明清,但是最大的可能还是宋代。
三、铜版昭示的历史价值
宋代济南经济空前繁荣。欧阳修《归田录》说:“齐州赋税最多。”熙宁年间曾任齐州知州的曾巩在《齐州杂诗序》中也提到:“今其地富饶,而介于河岱之间,故又多狱讼。”打官司的多,从侧面说明人们经济交往频繁,而频繁的经济交往亦说明济南手工业、商业的发达与集中。这块铜版就是当时济南兴盛手工业、商业的珍贵遗存和有力证据。这块铜版既有生产单位、商标,又有经营范围、产品原料、制造质量、使用效果的介绍,还有对店铺招牌、销售方式、优惠条件的宣传,其内容与现代产品广告,可以说毫无二致。这块铜版还向我们透露两个信息:一是这家针铺具有相当规模,否则不会着意于设计商标、批发产品和制版印制广告;二是类似的店铺周围为数不少,所以这家针铺将白兔形象高悬门前,便于顾客认记。
商业招牌在我国出现得很早。战国《韩非子》载:“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帜”就是招徕顾客的酒旗,也称酒帘、酒幌,可视作商业招牌的前身。古代商业招牌的制作材料、外观形状各种各样,其内容的表现方式主要是文字,或配以图画。图画不外乎卖什么画什么,或者画与经营的商品、提供的服务有关联的人物、故事、场景、图案等。像刘家针铺招牌画有商标的,实属鲜见。当然,铺主也有可能是更具创意,将商标“白兔儿”制成模型,作为一种招幌悬于门前。以招牌负载信息,传播地域总归狭小,而印刷广告便可大大突破空间的限制。
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商标,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商标,比13世纪欧洲工商业行会的带有商标性质的产品标记,早一二百年。其印刷广告,亦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广告,比1473年英国出版商威廉·凯克斯顿为宣传宗教书籍而印制的广告,早三四百年。这充分证明当时济南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也居于前列。
根据这块铜版,有一位台湾学者认为,“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使用商标,建立品牌形象的民族。”宋代的济南人以其先进的市场意识、高度的经营智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这份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