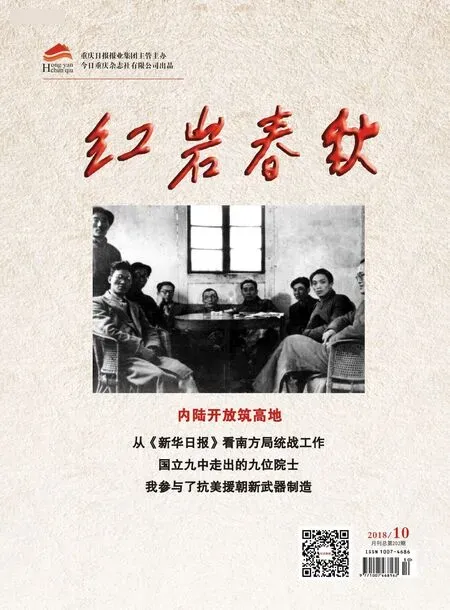漫说江河桡胡子
■陶 灵

◇1917年,川江上划船的桡胡子 (美)西德尼.D.甘博/摄
“桡胡子”还是“桡夫子”?
川江木船上的船工统称“桡夫子”,在一些支流小河里,也叫船拐子、船板凳儿、扯船子。根据不同的工种,他们有自己的称呼,如前驾长(撑头)、后驾长、二篙(闲缺、二补蒿)、撑竿、提拖(爬梁架)、三桡(抬挽、结尾)、杂工(烧火)、号子、头纤(水划子)、桡工(纤工)、杠子(岩板)等。船工之间可按工种互称,或叫连手、老庚,或喊姓名、诨名。
1986年,笔者发表散文《汤溪河的回忆》时,第一次把“桡夫子”写成“桡胡子”。第二年,又将《汤溪桡胡子》一文发表在《散文》杂志上,把“桡胡子”这一称谓直接用在了标题中。后来有人提出:下川东的云阳、开县、奉节、巫山等地,甚至湖北巴东、秭归一带,因方言发音的问题,容易将唇齿音f与舌根音h混淆不分,比如“夫”与“胡”字仅声调不同,所以将“桡夫子”喊成“桡胡子”。湖北某市新闻出版局发表的《审读简报》,还专门对“桡胡子”一词予以指证。
笔者认为,“胡子”是川江男人的别称,代表雄性与健壮,表现船工粗犷、豪迈的性格特征。而“夫”字比较文雅,“桡夫子”喊起来比较斯文。桡胡子也好,桡夫子也罢,土话和俗语并没有标准答案,大家明白其意就行。
桡胡子真的常年赤裸身体?
一提起桡胡子,人们脑海里浮现的情景是:不管寒冬酷暑,他们全身赤裸,身子匍匐着,背负长长的纤藤,在嘿哟嘿哟的号子声中艰难前行……大多数人认为,桡胡子时常涉水,衣服打湿后,干活和行走都不方便,且冬天裹着湿衣更容易生病,因此常常赤裸身体。
虽然赤身裸体,但桡胡子也怕羞。小时候的冬天,笔者在川江支流汤溪河边,偶尔会看到从船上的篾席棚里走出一个赤裸下身的桡胡子。光着的脚后跟裂开一道道血口,上身穿着一件没了扣子的破旧棉袄,用草绳系住腰,双手抱着插进怀里,腋下一边夹着裤子,一边夹着空酒瓶,瑟缩着朝小镇走去。接近小镇那坡石梯时,他赶紧穿上夹在腋下的裤子。在镇上打了酒回去,刚下完石梯,他就立马脱下裤子。
川江老水手田洪光12岁就下河推船,75岁学习电脑写作,80岁出版长篇小说《死了没埋的人》。书中写道:
发源于米仓山的南江和通江……是沟沟河,多半是上水船,大家赤身露体,在只有三尺深的小船后面,掀船和背船,强行从又浅又急的溪河中把小船从浅溪里拉过去……刺骨的冰水淹到哪里,皮肤就痛红到哪里……即使有个漂亮的女人站在他们面前,也动不了心了。
文中的“背船”并不是真的把船背起来。小河水浅,卵石滩多,河道弯弯曲曲,桡胡子常走水缓的岸边,或撑或拉着木船上行。但木船经常搁浅,于是桡胡子站在水里,用力推着船舷重回较深的水中。因正面推船力量不够大,他们就用背去顶,这就是“背船”。“背船”是常有的事,有的桡胡子还会赤裸身体或“打屌胯”(光着下身),一直在水里推着船走。
湖北巴东县官渡口镇的谭邦武,8岁学弄船,13岁当驾长,20岁已是上重庆下武汉的老江湖。后来木船被淘汰,他在60岁学开机动船,90岁还动手做了一条木船,102岁去世,被称为川江上的传奇。对于裸体桡胡子,他十分肯定地认为:川江上是没有的。因为川江水深,桡胡子都在岸上走,基本沾不到水。
川江拉纤,少则十来人,多时几十人,都是船靠岸把桡胡子送上坡。因为拉纤的同时,提拖要准备纤藤、行缆,驾长要看水势、观航漕,船必须靠岸。拉纤结束,他们又要往回收纤藤,同时靠岸把桡胡子接上船。因此,川江上的桡胡子的确不需要沾水。
巴东一带的老桡胡子说:“四川人跟我们湖北人不同,他们穿长衫,里头连窑裤(短内裤)都不穿。”过去有顺口溜念道:“四川人,本爱假,穿长衫,打条胯。四川佬,生得确,穿长衫,打赤脚,腰里系根麻索索。”
四川桡胡子穿的长衫叫衲坨,敞口圆领,短的过膝,长的到脚跟,右边腋下开口,开口处用细布带打活结,当衣扣,这样划桡、撑竿时才不钩挂。桡胡子常年在江上日晒雨淋,衲坨很快由深蓝色变成灰白色,破了补上一块疤,一层缀一层,新新旧旧,由单层变成了夹衫。
桡胡子把衲坨当成宝,一年四季不离身,夏天用以吸汗遮阳,冬天用来抵挡风雨。需要涉水时,他们把衲坨的下摆向上提,扎在腋下,便露出赤裸的下身,但上身仍穿着衣服。由此看来,桡胡子全身赤裸并非常态。
“纤绳荡悠悠”真的可以吗?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一首《纤夫的爱》,当年唱遍大江南北。
然而,歌中的“纤绳”应该是“纤藤”,“藤”与“绳”在川江木船上有很大的区别。绳,称缆绳、绹绳或棕绳,材料为棕丝或苎麻,人们用手或工具先搓绞成一根一根的细绳,再合编成粗绳。绳的质地柔韧,耐磨损,但成本较贵,沾水后笨重,主要用来拴船和升降船帆。
纤藤由多根竹篾条编织而成,一般长百丈,故俗称“百丈”。每只船大多备有大中小三种型号的纤藤,大的为南竹或斑竹篾条编织,称“坐藤”,重载木船过激流大滩时使用;中号用斑竹或茨竹篾条编成,称“二行”,船只过一般险滩时使用;小者用茨竹或水竹篾条做成,称“飞子”,船只空载或过缓流时使用。大中小纤藤是相对的,有的短航揽载船可用小船的“坐藤”做“二行”,也可用中型船的“二行”做“飞子”。
纤藤不吸水,沾水后很快会沥干。它在暴晒后容易脆断,因此夏天要经常用水淋。旧时,西陵峡一带的铺子,出售用石灰水浸泡的纤藤,而川江支流澎溪河的纤藤在编织前,篾条要用水煮。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增强纤藤的韧性和预防虫蛀。
纤藤并不直接套在桡胡子的肩上,他们肩上套的是一个布套子,称“褡裢”。褡裢在川江上还有其他名字,如搭布、搭袢、褡背、褡帕、褡索、连肩、拉帕、扯扯等。褡裢由一条白粗布做成,两头连着一根两三米长的麻绳,麻绳的另一头打有疙瘩或绑一节小木棍,可在纤藤上打活结。拉纤时,越用力,活结越紧,不会松脱。要想解开,提起麻绳一抖,因纤藤直硬,活结马上脱落。
不仅“绳”与“藤”不一样,更不能“荡悠悠”。这说来话长。

◇小木船上的纤藤
拉纤时,桡胡子们匍匐在地,手脚并用,倾尽全力,艰难前行。旁边的号子工一手打着伞,一手摇着油纸扇,逍遥地喊着号子。为防止桡胡子偷懒,号子工有时会突然跳到纤藤上,如果有踩假水(装样子)的桡胡子,立马会摔个仰八叉。这一招,行话叫“踩榨”或“上榨”。
第一个驾驶轮船航行川江的英国商人立德,在《扁舟过三峡》一文中写有拉纤的情景:
我们的船遇到向下冲的激流时,突然向水中心冲去。纤夫们被拉倒,来不及解开的纤绳将他俩拖过岩石,摔倒在江边乱石堆上。向下射去的小船虽然得救,没有翻沉,但岸上那可怜的两个纤夫,一死一重伤。
在奉节与云阳交界处的北岸,沿江有一条长长的石板坡,江中有险滩,桡胡子拉纤爬过石板坡时,常累得精疲力竭,曾有多人被累死。后来,石板坡被称作“拖板”,滩被称作“拖板滩”。这个地名见证了桡胡子的血与泪。
有一位姓罗的老桡胡子,年轻时在乌江拉船。有一次,船在滩口被激流冲打横在江中,突然像一匹狂奔的烈马,拖着纤藤上的100多个桡胡子冲向下游,谁都来不及取掉褡裢,纷纷从高高的纤道上滚下来,摔在乱石丛中。他幸好滚在一小块平地上,觉得眼睛直往外鼓,心里十分难受,好一阵子才缓过气来。再抬头一看,桡胡子们有的碰得头破血流,有的脑浆迸裂,还有的被撞伤后拖进江里淹死了,现场惨叫声呻吟声一片,惨不忍睹。
大家试想一下,还觉得“纤绳荡悠悠”吗?
桡胡子挣的钱难养家?
“脚蹬石头手扒沙,躬腰驼背把船拉,每天吃的猪狗食,死了河里喂鱼虾。”描写川江桡胡子悲惨命运的民谣中,这是传播最为广泛的一首。
1931年,从涪陵拉纤到龚滩,约180公里,因乌江上特有的“歪屁股”船(厚板船)不用风帆,要走40天左右。一趟下来,一个扯船子可得4块银元,驾长最高,是扯船子的几倍。那时,一块银元在重庆城最高可换铜钱28000文,一般情况下可换24000文左右。当时一碗小面100文,一块银元可买240碗小面,4块银元可买960碗。按现在每碗小面6元的定价,折合人民币5760元。这不算是低收入,何况当时乌江流域非常偏僻,民众普遍贫穷,买得的东西会更多。
谭邦武20多岁时跑船,因为是驾长,收入非常丰厚,一个人能养活全家18口。1941年,他与另外两个桡胡子从巴东运了一船梨到湖南卖,一船装了30吨,卖了2000块大洋。虽说那个时期物价飞涨,大米卖价比抗战初期涨了10多倍,但2000块大洋仍可买3500多斤大米,够谭邦武全家吃半年。
民国中期,澎溪河运煤船的桡胡子的生钱(工资)是每月15块银元,比县政府一个警卫班长的月俸还高5块,相当于一个班警或公役月俸的两倍。另外,货主担心途中煤炭被偷卖,每趟还给桡胡子2角“欢喜钱”,一个月给三趟。
在巫峡北岸,有一条纤道非常难行,桡胡子稍有不慎就会掉下石岩摔死。桡胡子摆龙门阵时常说:早知这么艰难,宁肯挑葱卖菜,挣点小钱养家,也不可拉船为生。由此表明,拉船的收入,比在家做庄稼高得多。
川江三峡沿岸都是高山,地瘠民贫,女子都往外嫁,男人娶媳妇极不容易。但是神农溪的桡胡子很早就在当地盖起瓦房,并娶了山外的姑娘。桡胡子虽然自己生活悲苦、艰辛,但也换来了家人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