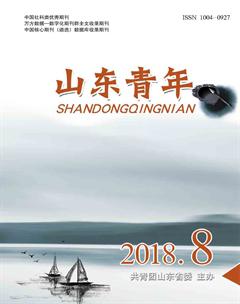马克思的需要理论
李威
摘要:当今,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逐渐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成为当代人理应重视的问题。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探究作为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类存在物的人的本性的需要的涵义,以此为基点,探究需要在大工厂时代的异化表现和原因,继而寻求需要的解放。
关键词:需要理论;人的本性;需要的异化;需要的解放
一、前言
党在十九大会议上指出,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从现实考量上来看,我们得知随着全世界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改善,艺术审美道德等精神诉求也在渐渐被提上日程;从理论考量上来看,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人的需要从来都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研究问题,马克思关心着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为整个社会进行“把脉”,寻求病根,继而实现人类需要的真正解放。可以说,从马克思出发,在理论上重新展开对人的需要的理解与关怀变得十分必要且重要。张维祥在《需要、劳动和人的本质》一文中表示,“近年来,随着人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有关人的需要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一些文章中,需要被看作人的本质,甚至是人的本质诸规定中最终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认为应从人的需要出发去说明人以及人类社会。”[1]赵科天在《“需要”概念的重新界定》一文中说过,“‘需要范畴极为重要,它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范畴,更是一个哲学范畴。在忽视主体性的旧教科书体系中,‘需要范畴被漠视,现在必须着力予以探讨。”[2]袁富民在《马克思需要理论研究述评》中表示,“当代中国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文化需要满足相对匮乏,更有‘普世价值与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乱象。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觀认同,梳理马克思地需要理论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基础性作用。”[3]但在国内现有的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研究中,依旧存有阐释不够清晰,结论过于宽泛笼统的问题。譬如仇艳艳在其文章《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中,虽然分析指出了当今的消费需要和生态需要的问题,但是在分析其原因的时候总是给人蜻蜓点水的感觉,以至于在处理人的需要的问题的解决途径上,即通过个人自省和社会教育的方式显得过于宽泛与无力。张文文在其文章《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中也犯了类似的问题,在论证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价值后也是宽泛地指出要树立并发展合理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生观。这些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没有在马克思那里找准人的需要出现异化的根本原因。本文将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阐述作为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类存在物的人的本性的需要的涵义和特征,目的是希望更细致、更深入地探究需要与人的本性间的关系,这也是国内外在研究马克思需要理论时少有的分析角度;从马克思出发,探究需要在大工厂时代的异化表现和原因,继而寻求需要的解放。
二、 需要与人的本性
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的需要,我们从马克思的文本中会发现“需要”贯穿其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提到“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这一重要论段。但马克思并没有像一般学科那样强制给需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如马克思也绝不会只用一句话来定义人一样。因为人的本性是丰富的,人是在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对象关系中不断丰富完善并实现自身的,所以我们在把握需要的时候忌讳将需要像心理学或是其他各门学科一样做抽象化、肤浅化、神秘化、片面化的理解。
从马克思的“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这个非定义的论断中,我们可以得知,人的需要具有同人的本性至少是同样的高度,那么,人的本性所具有的特性在人的需要中也是具有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如何理解人,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路径去理解探究人的需要。
在马克思那里,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4]虽然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同动物一样离不开自然,具有食色等自然本能的欲望与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与动物的本性是一样的。人和动物不同,人是有意识地通过从自然界获得的工具作用于自然界以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条件。此外,在人与自然的交流感受中,人可以发现美的规律,会在创作壁画、音乐、色彩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而这与动物的需求极大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需要同动植物区分开来,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据。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明确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所以人与动物不同,具有其特有的社会性。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需要不仅仅要从社会生产、交换、消费等社会环节中获得人的所需,更是要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获得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形成社会关系,不同的需要和生产方式使得社会关系表现为不一样的形式,呈现出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随着社会历史的向前推进,人的本性需要日益丰富,所以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具有历史性。
马克思在比较动物和人的区别时清楚明晰地说道,“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6]马克思非常重视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认为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质,也同样是因为人的这种具有意识和意志的特质,人才是类存在物。从理论领域来说,无机界里的自然物可以作为人的自然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从实践领域来说,人的肉体依靠自然产品生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将自然界变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使自然界具有普遍性。马克思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全面勾勒出了人的所有的生活领域,且将对应的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需要本性充满其中,使人的丰富的需要在不同的领域中不断发展实现着自身。
三、 需要的异化
人的应然状态是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创造生活条件来满足自身、实现自身,获得人之为人的幸福感。而不是像在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下,被剥夺所有权的无产者们每天必须像牛马一样工作十四个小时,竞争使他降为物品,降为买卖的对象。所以为了解放人类,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科学地向我们一点一点揭示人之非人状态的表现和原因。
(一) 需要的异化表现
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向前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融合创新,人的本质力量貌似应该得到充实。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在私有制的体系下呈现出相反的情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需要的异化有大篇幅的表述。需要的异化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6](P120)“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6](P54)在马克思的笔下,在生产领域、分工领域、交换领域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已变为对财富和货币的追求,资本成为人的主宰。人之为人的高尚品行荡然无存,人对金钱的欲望反噬着人自身。人的劳动成了瘟疫般地令人反感的生存下去的手段,甚至劳动的成果、生产的对象都变成与自己不相干的事物。
(二) 需要异化的原因
1、劳动的异化
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在现实感性世界里人要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来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以此来不断实现和满足自己的本质要求。不过随着工业和雇佣劳动的出现,人的这种为实现自身本性的劳动发生了外化、异化。而劳动成为这种异化现象的原因之一。因为劳动才导致了“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6](P58)第二,“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6](P59)
2、私有财产的异化
众所周知,人都有要拥有或占有某个物的权利,即私有权。作为私有权的主体即私有者同时也作为具有社会关系的人,自然离不开他们渴望得到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物质的存在无可厚非,正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财产是他个人的、有其特点的、从而也是他的本质的存在。然而,私有财产一旦转化成资本的各种形式,人的异化便成为现实。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避免不了要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此时交换的中介即金、银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为何作为私有财产的金银货币在资本时代导致人的本性的异化呢?货币作为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具有了购买占有一切东西的特性。可以这么说,货币将人的需要的一切本质力量和能力全部实现,把无变为有,把观念的、表象的存在变为感性的、现实的存在。所以说货币这种物质及其运动成为了代替人自身的真正的创造力。货币作为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完全可以代替掉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所具有的力量,人的本质异化为物。
四、 需要的解放
在上述对需要的异化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需要亦即人的本性在资本运作下受到的压迫和束缚,所以消除异化使人的需要得以解放成为现实的、历史的必然。这不仅仅是马克思的希望也是继马克思之后众多学者和实践者的希望。
(一) 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的解放
为了使人的需要恢复到它原本的模样,我们就必须照顾到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也要照顾到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和氛围,这样才有可能把人们的视角从狭隘地追求物质利欲转移出来,才能主动正视自身、回归自身。而要实现这种构想,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在原著中是这样表述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P30)广大的无产阶级在感受到“不堪忍受”的异化力量后,势必要反抗起来,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然可以做到夺回被剥夺的生产资料,自主作为生产的主体脱离资本下物的运作的操控。另外,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只有随着生产力的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4](P30)因为马克思意识到资本的触角一定是会延伸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所以要让大多数受压迫与束缚的无产阶级、各个民族普遍交往、普遍联结起来。为了实现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的解放必然要从社会生产力出发,这样才有可能让人和人间的关系回归到本真。到时,人对世界的关系也恢复到真正人的关系。人对人、人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也都是人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人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虚伪与丑恶。这种虚伪与丑恶离不开资本下的私有财产与货币,这就涉及到私有财产的扬弃问题。
(二) 私有财产的扬弃与需要的解放
需要并不是自我圆满的实体,所以,需要异化的根源不在其自身。为实现需要的解放,消除劳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离不开私有制的扬弃。
马克思在分析需要的异化时,时时处处不在批判私有制。这种批判与否定在马克思的著作文本中随处可见。马克思真正表达要扬弃私有财产应该从他探讨分工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时才开始的。所以真正扬弃私有财产首要做的就是取消分工,依据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天赋去劳作,人不再是被分配到一个操作项目的“螺丝钉”,人的劳作不再是资本的要素和费用,更不是可用来买卖的商品,人就是人自身。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6](P81)如此,人这个存在物在私有制下尤其是在资本发展的巅峰期又怎会从自身中产生出内在的丰富性实现人的真正需要呢?要从人自身产生出内在的丰富性,实现合乎人性的复归,必然需要扬弃私有制,取消分工,这样才有可能消除异化劳动,消除为交换价值而进行的生产。
[参考文献]
[1]张维祥.需要、劳动和人的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1993(3).
[2]赵科天.“需要”概念的重新界定[J].南京社会科学,1996(6).
[3]袁富民.马克思需要理论研究述评[J].重庆社会科学,2017(8).
[4]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7.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