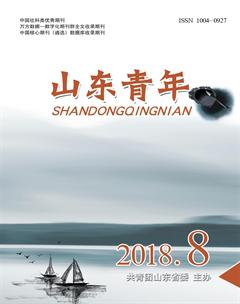论中国传统法治秩序
刘春一
引言
利于一时者,必不合于方将,合于微小者,必不合于魁硕,故一物方长之秋,必有其改制,潜易阴阳,方死方生,反是而观,旧有干局,既坚且完,改制阻力,亦以愈大,革故鼎新之难,使物归于老死,此不易之公理也。[1]
一、义利之辨与和合之道
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提到“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2]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利益,天然没有正当性,“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都是在讲这个道理,提倡为人为政应当以仁义为标准,对人热心叫“仗义”,推翻政权叫“起义”,总之,许多事情加个义便师出有名了。
一般来说 ,义是不能脱离具体对象而存在的,而且往往是存在于二元关系当中,是双向的,如果一方不配合,另一方也就“仁至义尽”了,现实生活中,以一种物质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儒家文化传统的地区最流行的是请客吃饭和礼尚往来。
在西方社会,除去神权如日中天的中世纪,则社会的整体潮流是强调追求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合理性。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段话“请你一手抓住金光闪闪的斯提克斯河,一手抓住丰产的大地,向我发一个誓言”,[5]从希腊神话中充满七情六欲的诸神,可见西方思想之源头处,不乏对利益追逐的合理认知。
即便神权兴盛的中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在解释神权之时,也必须让信众们相信上帝会给以救赎,他提出:“恩典说”即人类罪孽深重,可是上帝怀有仁慈的本性,人类又希望通过上帝的恩典而获救,一心向善,心往上帝,才会得到上帝拯救,从人间之城进入上帝之城。[6]
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成为主流,西方的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们更加强调了人拥有“自然权利”卢梭坚信存在着个人的不可侵犯自然权利,[7]孟德斯鸠与洛克也认为人的自由是国家应当实现的最高目标边沁认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面前-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是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的。”[8]在边沁看来,人性的本质就是避苦求乐,个人权利本位成为西方社会主流。
中国社会,“仁义”将整个社会以不均质的方式粘合在一起,自身权益与他人权益界限不明确,权益常常决于他人、决于集体,西方社会,个人权益的处置几乎全在己身,每个人实现自身权益的方式不同,有追慕宗教者,有追逐金钱者,有专研学术者,不一而足。
西方人重“分别”,尚“自由”,“在一切事情上,每个人应当享有实行行动而承担其后果的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的自由”[9]东方人重“同一”,尚“和合”“礼之用,和为贵。”[10]事事争取一个和字。
以自我组织的方式求利益,纷争必然不断,自然对规则具有巨大的需求,西方社会的司法体系收入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十五以上就是明证。 [11]但倘若事事求“义”,反对求利,则起码在明处,对平息纷争的规则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这是由中西文化中不同传统价值观衍生出来的。
二、由我及人的社会伦理
拥有大面积平原的中国,自秦汉以降,便以自耕农经济为主,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历百代而不易,人们更多需要处理与自己具有血缘和地缘联系的人的关系,显然对于这种信用透明的团体中发生的关系,用道德伦理来处理更具效率,除非发生严重的恶性事件,否则繁琐而周密的法律似乎没有太多存在的必要。于是伦理道德逐步发达,就有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克己复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 等,这是私法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私法上的权利关系完全是由儒家伦理道德来调节。
儒家在中国占据主流文化,讨论主体的是特定伦理关系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便讨论天下国家,也必先在伦理秩序中得到认可,正如《大学》所言“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论证伦理的合理性。
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是这样的描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12]而这推出去的波纹正是无形的伦理道德。
反观西方文明源于希腊与罗马,多山地与丘陵,只有小块的分割平原,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农业,但是海岸线绵长,地处亚欧非交界处,适宜发展工商业,在梭伦改革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工商业区域,[13]甚至连奴隶都成为交易商品的主要品种,不特定人之间频繁的贸易来往,必然导致契约的产生,用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保障交易安全。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14]而捆着这些柴火的稻草正是有形的契约。
伦理秩序的下己身可以由己身推之家庭后至于国家和天下,模糊了外界与己身的界限,而契约秩序的己身只能通过契约与我外界相联系,特定权利义务更趋与外界与己身分离,在古典的西方观念中,甚至连子女都是上帝的馈赠,中国社会,处于同一伦理圈子的人,是可以互相替对方做决定的,其隐含的前提是利他,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界限分明,其隐含的逻辑起点就是利己,任何行为都必须经过对方同意,才可以代劳。
三、天下为公的政治倫理
中国人素有天下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15]礼记的这段记载了中国人从“仁义”的起点出发,希望世界始于“和”,归于“同”,成于“一”的政治理想。
即使到了近现代,执政党所追求的目标依然是大同社会,“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国家权力和政党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入大同的境域。”[16]
依据中国传统的看法,修齐治平是中国人的理想,政治和社会的改良也必须依赖以下路径:人存政举,转移风化必赖圣贤,在一个坏的社会里,如果有少数人敦品励行,标出一个好榜样,使多数人受到感化,造成一种新的风气,社会自然得到改良。[17]
若说中国政治是仁义精神的演绎,传统伦理的扩张,那契约精神则是西方政治的基石,推而广之的社会契约就是国家建制的根本,我们口中所称的公德不过是来源于社会契约,与其称为公德,不若说是民众对共同体所负之义务。对此,西方法学家早有论述:当人们基于每个公民的同意和授权组成一个共同体时,这个共同体便有了采取行动的权力。[18]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方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最终问题。[19]
常有人说西方是法治发达,我国是人治发达,私以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西方自古奉行重商主义,确实发展出了发达的民商法,但是论及行政法,将如此巨量的人口和领土整合起来的中国显然更具经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能够维持两千多年之久,但是这一点中国人做到了,在现代化的交通媒介与现代化行政形式还没有出现之前,能够将支离破碎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力“和合”起来,堪称奇迹。[20]
秦漢时期,奴隶制已经垮台,中国社会走向了趋向于一个阶层自由流动的平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力量是趋向于平铺散漫的[21],而同时期的罗马仍然实行世袭的奴隶制和等级制:“被兼并地区的居民一般不再取得市民籍,不具有公民权,继续作为罗马国家权力之下的异邦人。”[22]甚至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古罗马也要分为行省,附庸国,殖民地等多种等级。秦汉时期,中国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已经实行了郡县制,同时中央定期派出刺史对地方政权进行监察,西汉时期 ,便设太学作为选拔官吏的途径,西方直到近代才出现这种选拔制度。
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和等级制进一步发展,从国王,大贵族,小贵族,直到骑士,采用双边契约的方式,将领土连同领土上的权力分封给封建领主,国家权力随土地层层分散出去,也就没有了中央权力,甚至连中央机构也不存在。国王只是一个最高一级的领主,而不是政治权力的核心[23],同时期的宋朝继承前代遗产,建立了完善的行政制度,选拔文官担任督军节制五官,地方政府设帅、漕、宪、仓,使地方军权,
[24]财政权,司法权,行政权相分离,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了,消除了自五代以来内乱的隐患。
总的来说,西方政治是无数个不同层次的个体通过契约制度和代议制度形成的名为民主实为资主的政治制度,这个联合体的界限是民族,中国政治就是由一个富于“天下”理想的核心集团出发,通过以忠恕为核心的礼治秩序将无数个个体纳入一体的德主政治制度,这个统一体的界限是天下,不得不提及的是,欧洲的民族主义国家理念是近现代的产物,“民族主义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的复杂交汇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并被多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吸收”[25],而中国人天下的国家观,古已有之,认为普天之下本为一体,中国人主“和合”,西方人主“分别”,此又一明证。
四、“他人之治”和“社群之治”的治理模式
若是希冀法治,则必赖司法机关以强力来定纷止争,若是希冀礼治则必赖教化来移风易俗,所以对于维持中国的传统秩序而言,其起点必然是教化,传统秩序中,教化与被教化的互动关系存在于亲子之间,师生之间以及其他的长幼关系当中,使“克己复礼”“过犹不及”礼治、中庸等思想世代相传,并在人心当中形成一套泛道德主义的价值观,当个体在群体当中做出不符合“仁”和“礼”的要求的行为时,轻则大失面子,重则感到羞耻,而耻感和面子对人的制约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他治”或者说“群治”,一般做出不合时宜的行为,在鸡犬相闻的传统社会,立刻会传遍乡里,形成舆论影响,人品的“品”字有三个口,可见古代对于一个人信用判断是口口相传的方式,更有甚者,我们得亚洲邻邦,因耻辱而自杀者为数不少,可见其威力。
处在这样一个各方监督的亚环境中,大部分人会选择过男耕女织,结婚生子的安稳生活,并且不逾矩的过完一生,但是也确有部分人视面子和耻感与无物,恣意去做一些破坏礼法的事情,这时候往往找一下德高望重的乡贤来评论是非,以此让社会秩序归于礼法之内,如果用此办法依然不能阻挡他人对礼的破坏,则要“出礼而入刑”,刑罚成为最佳的选择,传统上我国的刑罚强调教化作用,作奸犯科之人,常常要刺字游街,以便对公众进行警示,国朝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伍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26]传统秩序中,一旦发生纠纷,赶来调解的人往往是要求双方各退一步的,即便是 有礼的一方也应当发扬风度“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样将来也好见面,朱苏力在其著作中提到的“秋菊打官司”[27]就是这种情况,秋菊只是想“讨个说法”,村长被警察带走,反而使秋菊在村子里没法做人。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之所用易见。[28]道德的义务相对于法律是更进一步的,传统社会中礼治确实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作用,相对于法治的低效和高成本,礼治虽然缺乏力度,但是变动不大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传统社会中已然够用,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传统的乡土社会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了,缺乏足够信用支撑的交往大大增加,故而今日许多事情不得不诉诸于法律的强力救济,传统的伦理秩序依然存在于大部分家庭当中,把家事诉诸于法庭的毕竟还是少数,伦理秩序中,上对下也不至于是一个威权治下的状态了。
后记
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取得光辉灿烂的成就,这与其发扬和发展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有关,不过,自两汉以来,中国的礼法秩序却一天繁密化,教条化,明清时期更是搞起了闭关自守和思想控制,随着世界的推移,不合时宜的利益格局固化,繁密的礼法使人受到束缚,外界的新思想进不来,优秀的传统文化却一天天教条化,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世界趋势,终于倒在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
传统文化传承至今,最应当避免的就是教条主义,推动儒家文化融入实践,是最重要的,儒家所提倡的美德大半含有社会性,但是他们所着重的却不在他们的社会性,而在它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譬如仁与敬是儒家所极重视的,但是仁必有对象,敬也必有对象。[29]儒家的道德是相对的,若是拿到当今来,我们第一个要求便是提倡公德建设,多一些社会性道德。
再者,道德应当为不同阶层和职业而设,富勒曾经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30]假若那修齐治平来举例,那“修”和“齐”就是义务的道德,“治”和“平”就是愿望的道德,我主张要在不同职业,不同阶层建立不同高度的道德,普通人做到“修”和“齐”就足够,但政治家必须要有“治”和“平”的愿景,企业也必须有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赫伯特·斯宾塞 严复 译.《群学肆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49頁.
[2]鲁道夫·冯·耶林 郑永流 译.《为权利而斗争》[M],商务印书馆,2016年,23页.
[3]孟轲.《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14页.
[4]孔丘.《论语》[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32页.
[5]转引自赵林.《西方哲学史讲演录》[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35页.
[6]吴君.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哲学简论[D]. 大连: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1999,6月,12页.
[7]E·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68页.
[8]边沁 著 时殷弘 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58页.
[9]密尔 著 许宝魁 译.《论自由》[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90页.
[10]孔丘.《论语》[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2页
[11]牟延晨.《危地马拉大选结果出炉 昔日喜剧明星变身总统》[J].北京:环球网,2015年10月.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7-28页.
[13]邢玉波. 雅典的工商业[D].衡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6月上113页.
[14]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7-28页.
[15]魏征.《群书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64页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406页.
[17]朱光潜.《谈修养》[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34页.
[18]洛克 著 刘晓根,译.《政府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页.
[19]卢梭 著 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34页.
[20]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24页.
[2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172页.
[22]朱勇. 古罗马行省制度演化的法文化价值[D].长沙:求索, 2005年6月,197页.
[23]王霞. 论欧洲中世纪的结构特征及其对西方政治文明走向的影响[D].新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3年9月,47页.
[2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87页.
[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吴睿又人译.《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页.
[26]洪迈.《容斋随笔》[Z],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298页.
[27]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26页.
[28]班固.《二十四史·汉书·贾谊传》[M].北京:线装书局,2014年,267页.
[29]朱光潜.《谈修养》[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32页.
[30]富勒 著 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5页.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