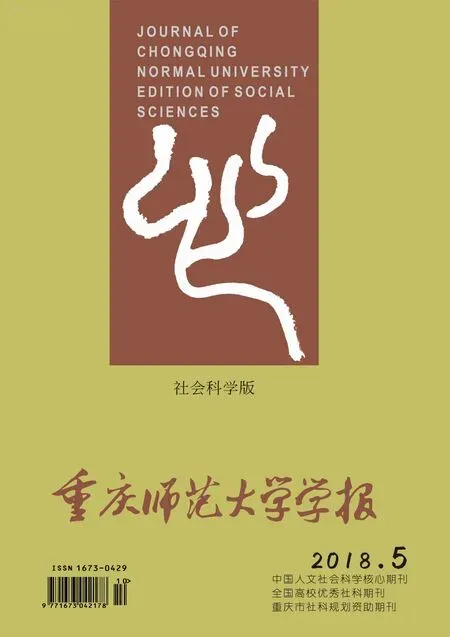抗战初期左翼文化活动与萧红、白朗的发轫
王 劲 松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由南满迁至哈尔滨。坐落在哈尔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牵牛坊”为俄式建筑,最早是白俄的手工作坊,上个世纪30年代成为当时爱国青年的文艺沙龙[1]。据1933年《大北新报》载:“按该坊之成立系冯君纠合一般文士,每日工余齐集牛坊研究文字之处。闻不日将有作品问世。”房主冯咏秋乃哈尔滨名士,早年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擅长诗画,1932年曾与刘昨非、王关石等人组织“冷星社”。“牵牛坊”的文艺活动就是从“冷星社”时期开始的。经常来“牵牛坊”的多是当地文化界人士,“他们谈论文艺、写诗作画、唱歌跳舞、朗读剧本、阅读和研究过高尔基、鲁迅、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文学作品。”“有的人是无意识在聚会中认识的,有的人是有意识想要了解谁,约到‘牵牛坊’认识的”[2]62。后来流亡的东北作家群,都是曾在“牵牛坊”会聚过的文学青年。女作家萧红和白朗就是从哈尔滨“牵牛坊”走上文学之路的。
一、“牵牛坊”左翼活动与女作家的参与
“牵牛坊”最初的社会活动是从“画展”和“剧团”开始的。由于在“牵牛坊”聚会,这些文艺青年组织了画会和话剧团。1932年秋,由共产党人金剑啸出面,组织当时哈尔滨画坛有影响的一些画家:冯咏秋、高昆、白涛、王关石、高誉民等人在道里同发隆百货店举办了一次义卖性质的画展,以赈济遭受松花江洪水的哈尔滨灾民。“牵牛坊”成员共产党人姜椿芳后来撰文称:“展览会从名称到布置的形式,在哈尔滨都算是新颖的,使人有开风气之先的感受。”[3]女作家萧红由于萧军和舒群的缘故而结识了“牵牛坊”的很多其他成员,她用两幅水粉画参加了这次义卖画展,一幅是两根胡萝卜,另一幅是一双破布鞋和一个硬面火烧。虽然最后这两幅画没有卖出去,但这次义卖画展却成为萧红参加社会文化活动的契机。画展后,经萧红提议,组织成立了一个“维纳斯画会”,主持者金剑啸,会员有萧红、萧军、冯咏秋、白涛等人,每周去“民众教育馆”绘画。组织画会的同时,1933年7月,共产党人罗烽、金剑啸遵照上级指示,又组织了一个半公开的“星星剧团”,罗烽任剧团领导,金剑啸负责导演,成员有舒群、白朗、萧红、萧军、白涛等人,多为“牵牛坊”集会成员。剧团用三个月的时间排练了三个短剧:一个是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白朗在剧中扮演律师太太;第二个剧是白薇的独幕剧《娘姨》,萧红在剧中扮演一个生病的老妇;第三个剧是白涛(张沫元)的《一代不如一代》(又名《工程师之子》)。从“星星剧团”编排的三部话剧来看,皆具有表现底层黑暗与反抗阶级压迫等左翼思想。罗烽当时以“洛虹”的笔名评价了“星星剧团”的性质与使命:“‘星星剧团’是在黑暗的时刻,蓦然于哈尔滨——丑恶与物质垃圾堆中出现的”“它是放着轻轻的脚步,鸦雀无声地走到人间家而复向民间去,它的使命就是凭着那些微的光辉,整个儿贯注于人们的心目中,正如天上的点点星星也要呈显和照耀于地球上每个人的脸。这在从来枯寐若死的哈尔滨,真是一个先锋的团体结合。”[4]
尽管排练的话剧并未公开上演,剧团也由于受到日伪监视而被迫解散,但星星剧团对哈尔滨爱国青年却起到了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作用。由“牵牛坊”聚会到组织画社和剧团,“牵牛坊”聚拢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常聚在‘牵牛房’的人们,起码都具有着爱国主义思想”“在‘牵牛房’里,有的实际就做着秘密抗日工作,宣传着共产党领导‘东山里’抗日游击队的胜利,宣传着抗日游击队的胜利消息和人民”。[1]
星星剧团建立一个月后,1933年8月6日,金剑啸、罗烽、姜椿芳等人通过官办的长春《大同报》编辑陈华,在该报创办了文艺副刊《夜哨》周刊。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多为“牵牛坊”成员。萧红为刊物起名“夜哨”,意为黑暗中值哨。《夜哨》成为沦陷初期北满左翼作家文学创作的主要阵地。从1933年8月6日创刊至1933年12月24日被当局查禁停刊,4个月期间《夜哨》共刊出21期,发表82篇作品(包括发刊词和结束语),其中萧红和白朗的作品是东北现代女性文学发轫期的重要作品。1933年10月,白朗接办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翌年1月18日,罗烽、白朗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了副刊《文艺》周刊。前《夜哨》周刊的多数撰稿人都转移到这个新的文学阵地。白朗以“弋白”的笔名在发刊词上表达了《文艺》周刊的宗旨:“文学作者它不能只是埋首在书斋里构思、设想,起码更应当推开窗户,睁开它的睡眼,和现实亲吻一下”,以“明了人类在广大的宇宙里怎样生存着,更可以听见弱者们的低吟是怎样在垃圾堆上和阴沟里打滚”[5]。从1934年1月18日创刊,到1935年2月被当局查禁而停刊,《文艺》周刊共发刊48期,女作家白朗、萧红的许多重要作品在此刊发表。
从“牵牛坊”聚会到赈灾义卖画展、星星剧团的话剧排演,再到报纸文学副刊的开创,这一系列的文艺活动反映了北满哈尔滨作家群渐趋自觉的左翼文化意识,“由于外感的掀动,彼时发刊在哈尔滨的《晨光报》和《国际协报》副刊上面所刊载的作品,便都蕴藏着一种新的动力,有血在沸腾,有汗在驰骋,无疑的,作品所代表的意识与形态,已足以令满洲文学走上一个经途”[6]。“令满洲文学走上一个经途”的自然包括其中的两位女性作家萧红、白朗,“牵牛坊”左翼文化活动对女作家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刻。萧红此间的文学创作数量之多,而白朗除创作之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积极组织及参与等,都表明“牵牛坊”对她们的影响。可以说,“牵牛坊”集会成为东北现代女性文学发轫的重要契机,这在长春《大同报》和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发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以下是萧红、白朗从1933年至1935年在长春《大同报》和哈尔滨《国际协报》各自副刊上发表的作品数量:

表1 萧红、白朗1933—1935年在《大同报》和《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数量
萧红从1933年5月6日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到同年8月底,创作时间仅为四个月,就与萧军合著出版了个人专辑《跋涉》,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可见其创作势头日上。《跋涉》收萧军作品6篇、萧红作品6篇,是沦陷初期哈尔滨左翼作家群中出版的唯一的一部单行本。哈尔滨左翼作家群中仅有的这两位女作家的早期文学创作,都是集中在1933年至1935年“牵牛坊”沙龙活动时期。萧红和白朗对“牵牛坊”左翼文艺活动的参与,无疑为当时尚处发轫状态的东北女性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牵牛坊”与萧红的左翼思想
“展开满洲女作家的名簿,首名被提到的该就是悄吟吧!”“在这个时期”,悄吟(萧红)被“称谓开拓满洲女性文艺的第一人者”[6]。这是当时满洲女作家吴瑛对萧红的评价。沦陷初期的哈尔滨文艺活动,不仅确立了萧红满洲女作家中开拓者地位,同时也为她日后南行关内奠定了左翼意识形态的基础。
由于人生中并不希望出现的充满了戏剧性的偶然因素,萧红得以接触到哈尔滨文化界的爱国进步青年。通过舒群与萧军的介绍,她踏进了“温暖而明亮的”“牵牛坊”。而最终决定她将文学创作作为终身职业和谋生手段的因素,却主要源于生存的需求。左翼意识形态对萧红文学创作的思想渗透,使她最终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而萧红走进左翼文化阵营,既有来自于反抗封建家庭和底层流浪的痛苦体验,更出于对现实生存的需求。当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性经历了她这个年龄大多数女性未曾遭遇过的人生磨难后——被家族迫害,未婚先孕的精神压力,东兴顺旅馆的被弃及作为人质即将被店主卖入妓院的精神恐惧,饥寒交迫、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涯,等等。当她踏进了“牵牛坊”,便使她倍感左翼文化阵营的温暖。
许久没有到过这样暖的屋子,壁炉很热,阳光晒在我的头上;明亮而暖和的屋子使我感到热了![7]605
使萧红感到“热”的自然不仅仅是“牵牛坊”屋子的“温暖”,而是左翼团体的积极营救和对处于困境中的弱女子伸出的援助之手。
第二天,一些朋友来约我们到牵牛房去吃夜饭。果然吃得很好,这样的饱餐,非常觉得不多得,有鱼,有肉,有很好滋味的汤。又玩到半夜才回来。这次我走路时很起劲,饿了也不怕,在家有10元票子在等我。我特别充实地迈着大步,寒风不能打击我[8] 610-611。
当一个高中还未毕业的女学生,深受外界新文化的影响,只知一心求学,并没有任何选择职业的打算,而突如其来的打击一下子将这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抛入到了社会底层。一无所有,与街头流浪汉几无差距的生存现状,使她必须抓住眼前的机遇。
女仆出去买松子,拿着三角钱,这钱好像是我的一样,非常觉得可惜,我急得要颤栗了!就像女仆把钱去丢掉一样。
“多余呀!多余呀!吃松子做什么!不要吃吧!不要吃那样没用的东西吧!”这话我都没有说,我知道说这话还不是地方。等一会虽然我也吃着,但我一定不同别人那样感到趣味;别人是吃着玩,我是吃着充饥!所以一个跟着一个咽下它,毫没有留在舌头上尝一尝滋味的时间。
回到家来把这可笑的话告诉郎华。他也说他不觉地吃了很多松子,他也说他像吃饭一样吃松子。
起先我很奇怪,两人的感觉怎么这样相同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饿才把两个人的感觉弄得一致的[9]。
因为“饿”,两萧的感觉一致,也因为“饿”,两萧才投奔了“牵牛坊”。而底层落魄女子对人生悲凉的体验更使萧红对左翼思想中反抗阶级压迫有了情感上的诉求。中学时代所获得的对文学、美术的爱好和特长,自然而然地成为谋生的手段。左翼文化阵营不仅给她提供了参与活动、施展才华的机会,更为她文学作品的发表而解决了现实的生计问题。

表2 萧红1933—1935年以“悄吟”“田娣”和“玲玲”等笔名发表的作品
从这段时期萧红发表的作品体裁而言,小说和散文居多。《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4篇,《夜哨》10篇;《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7篇,《文艺》2篇;《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1篇,共24篇。虽然萧红与“牵牛坊”结缘纯属偶然,但对萧红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相当程度地决定了她早期作品的主要思想。《弃儿》是萧红最早正式发表的文学作品,完稿于1933年4月18日,从1933年5月6日—17日,在《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连载。《弃儿》是一篇自传体散文,记录了萧红在东兴顺旅馆的困境及《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主编裴馨园、共产党人舒群等人营救经历。作为第一篇自传体散文,《弃儿》细腻的笔触着重叙述了女性生育的苦难。而随后创作的《王阿嫂的死》则是萧红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篇小说。萧红将1931年3月随继母梁氏和同父异母弟妹们在阿城福昌号屯本家居住的日子,亲眼看到家族欺压地户增租增息的残酷,对贫苦佃农的同情及自我遭受家族迫害等亲身感受融进了反抗黑暗现实的左翼思想。萧红在这篇小说中将王阿嫂生育的死难直接指向了阶级压迫。到1933年6月30日在《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上发表的《看风筝》,及1933年8月6日《大同报》副刊《夜哨》创刊号上的《两个青蛙》,已隐约可见作品中革命领袖和革命青年的形象。随后在《夜哨》周刊上发表的《小黑狗》《哑老人》《夜风》等都表现了鲜明的阶级意识。“文藻和诗情的文体,很有点与谢冰心的笔法相似,但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积极性,则又类似丁玲了”[6]。1933年10月由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出版的《跋涉》收录了三郎(萧军)和悄吟(萧红)的12篇作品,其中萧红的6篇作品中除小诗《春曲》和散文《广告副手》外,她着重收录了已发表的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夜风》和散文《小黑狗》,以直面现实的勇气表达了她日渐明朗的左翼意识。而连载于1934年4月29日至5月17日《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的《麦场》一、二部分,即是后来的《生死场》的“麦场”和“菜圃”两节,可见《生死场》的最初创意和构思并非是在流亡途中的青岛,而是在沦陷初期的哈尔滨。如果说《弃儿》还只是体现了萧红自我经历的叙事痕迹,那么《王阿嫂的死》却标志着萧红由自我的苦难体验走向了民众的苦难认同。正如满洲作家王秋莹评价:“作者的创作程度决不是概念的虚构,与浪漫的幻想,而纯粹是在现实中提炼素材”“从他们笔下写出来的人物,都是一种下层的被毁辱与损害的人们生活奋斗的故事”[10]。
收在《跋涉》中的《王阿嫂的死》《小黑狗》《看风筝》和《夜风》四篇作品都以农村为背景,通过农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地主阶级的残暴和兽性。《王阿嫂的死》中描述了王阿嫂一家人都死在了张地主的手下,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残酷本性。作为萧红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王阿嫂的死》表达了作者对亲身经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和悲悯。而《看风筝》中革命者刘成的出现则寄托了萧红朴素的阶级希望。“为着农人、工人,为着这样的阶级”,刘成“只有走一条路,一条根本的路”。尽管革命者刘成的形象还较模糊,但小说的结尾当“刘成被捕的消息传来”时,却透露出萧红对革命者的根本之路充满的乐观情绪:
那是一个初春正月的早晨,乡村里的土场上,小孩子们群集者,天空里飘起颜色鲜明的风筝来。三个,五个,近处飘着大的风筝,远处飘着小的风筝,孩子们在拍手,在笑。老人——刘成的父亲也在土场上依着拐杖同孩子们看风筝[11]。
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不久,在农村开展了苏维埃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会等群众性组织,并进一步开展了农民武装斗争。《看风筝》和《夜风》所描写的故事,就是当时东北农村的缩影。如果说在《看风筝》中萧红对塑造革命者形象还不够熟悉,那么在《夜风》中却以正面笔触直接描写了农民的武装斗争。虽然作者并没有描写大的暴动场面,也没有细致地分析底层民众思想转变的影响因素,但通过李老婆子、长青母子反映了深受剥削压迫而没有觉悟的农民阶层,一旦接触了革命者,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在《跋涉》“书后”,两萧谈到他们当时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认识,其中表达一点:“惟有你同一阶级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12]正是具有人生苦难的体验,萧红才能从朴素的阶级立场正确地分析当时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左翼思想的影响使她更加明确了阶级意识。
尽管萧红本人一直都没有隶属于任何政党,但人生戏剧性的变化使她接触了舒群、金剑啸、罗烽等共产党人,而早年受家族迫害的创伤性记忆和同情农户、弱者等善良的品格,与左翼思想反抗压迫达成了共契。研究者大都认为鲁迅对萧红的文学创作的成长影响深刻,但在东北沦陷初期萧红早期文学创作之路上,共产党人舒群对萧红的帮助和影响极为重要。1932年7月,当萧红落难困守东兴顺旅馆时,是舒群第一个去旅馆探望她。1933年,萧红、萧军准备出版他们的第一部小说诗文集《跋涉》时,舒群拿出了父亲积攒的四十元救命钱,并且还为他们联系了五日画报社。舒群对萧红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左翼思想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牵牛坊”时期舒群组织了一系列左翼文艺活动,更重要的是对萧红文学思想的渗透。两萧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的素材和构思,直接得益于舒群安排其在海军学校时期的同学傅天飞——当时与杨靖宇将军开创的吉林磐石抗日游击队的负责人,同两萧长谈。舒群也经常向萧红介绍东北抗联的事迹。萧红本人从未经历过中日战争的场面,也没有亲身目击过日本人的暴行,但《生死场》却以气冲云霄的悲壮提升了抗日文学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明是深受舒群等共产党人影响的结果。
从1932年底进入“牵牛坊”到1934年6月流亡关内,一年半的“牵牛坊”沙龙左翼文艺活动经历是萧红文学创作的初萌期。尽管此时的作品还未形成熟练的技巧和特征,但她已开始对广阔的社会题材关注。萧红的作品从最初在《大同报》《国际协报》上发表,到《跋涉》专集的出版,无疑强化了她对于自己从事新文学创作之路的肯定。
三、《文艺》与白朗的左翼使命
如果说萧红对于左翼思想的认同源于生命体验,白朗则以能动的自觉反应积极投入革命事业。与萧红不同的是,白朗始终把自己视作职业革命者。“牵牛坊”时期,白朗参与了星星剧团的组建和剧本排练。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与哈尔滨市委鉴于当时斗争的需要,为配合抗日武装斗争,决定利用敌伪报刊创建党的宣传阵地。杨靖宇授命罗烽、金剑啸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当1933年初哈尔滨《国际协报》招聘女记者时,白朗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授意下前去应试并被录取,负责该报副刊编辑,后在该报创办《文艺》周刊。《文艺》周刊便具有了秘密的政治意图,它不仅为当时的进步青年提供了一块创作园地,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发展了自己的文艺队伍。日后,带有左翼色彩的东北作家群都是出自于《夜哨》周刊和《文艺》周刊的作者群。他们流亡关内,以文化群落第一个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学的歌哭呐喊。追踪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之源,《夜哨》《文艺》功不可没。白朗创办的《文艺》周刊于1934年1月18日创刊,同年12月30日停刊,历时11个月,共出版48期,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
哈尔滨沦陷时期的白朗文学创作从一开始便以一种鲜明的阶级倾向呈现出左翼思想。最初连载于1933年新京《大同报·夜哨》第5—14期的小说《叛逆的儿子》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由于同情并赈济穷人的进步青年挨了剥削阶级父亲的暴打而离家出走,成为地主阶级的叛逆。与萧红的《王阿嫂的死》中“新写实”的客观描述不同的是,白朗直接陈述自己的爱憎情感,她常常用大段的直白叙事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病弱咳嗽的老人和他怀里“精光的小身体”“瘦小的躯肢”冻饿得奄奄一息的婴孩,以及用“一块破布包裹着下体,光着脚”“松散的发辫”“刺伤了脚”的小女孩,与走过他们身边的那些“西服革履长袍短褂的公子、老爷们,高跟艳服卷发红唇的小姐、太太们”形成了鲜明的阶级对比[13]。当时曾有人评价白朗作品“叙事多于描写,处理上感到累赘”[14],显然,这些作品呈现出作者有意识的教化功能。
白朗的一生深受丈夫罗烽的启蒙和影响。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迁至哈尔滨,罗烽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哈尔滨市委东区区委宣传委员,直接在杨靖宇将军领导下从事反满抗日宣传工作。当时的印刷机关就设在罗烽家中,白朗自觉协助了地下党的很多秘密工作,如刻写钢板、印刷宣传品等。1932年秋,她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反满抗日的外围组织“反日同盟”。

表3 白朗1933-1935年以“刘莉”“弋白”等笔名发表的作品
“牵牛坊”沙龙活动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她日后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和左翼作家的坚实基础。1935年,白朗与罗烽流亡上海,旗帜鲜明地进行抗日文学创作。此后,转辗武汉、重庆、延安。1938年,白朗在武汉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97名发起人之一。1939年,白朗又参加了“文协”组织的“作家战场访问团”,深赴山西太行山战区。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延安中央党校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革命者。多少年后,白朗回首往昔动情地说:“我这粒革命种子,是萌芽在哈尔滨的土地上,松花江是我的奶娘,抚育我成人的是党……”[15]64
“牵牛坊”左翼文化活动从一个较高的起点促成了东北左翼女作家的发轫,并且对发生期的东北现代女性文学起到了意识形态的启蒙和引导作用。不同历史阶段的女作家文学创作起点各异。“五四”时期,冰心受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以“问题小说”的形式写下了《斯人独憔悴》《两个家庭》等来探索妇女解放之路。而丁玲、冯沅君、庐隐则从女性的婚姻、恋爱与社会的矛盾为起点。东北现代女作家萧红、白朗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就将女性的苦难置于民族矛盾和阶级压迫之中,这不仅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时代大环境有关,更与普罗文学、左翼思想有意识的引导密切关联。左翼文化阵营帮助她们开拓了视野,把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从“五四”文学的个人狭小情怀扩展到社会的广阔天地。沦陷初期哈尔滨左翼文化环境,不仅鼓励了女作家参与左翼活动,而且与传媒刊物的联系也为她们的作品走向社会提供了机遇。萧红、白朗在哈尔滨沦陷初期的新文学创作踽踽起步,离不开左翼文艺阵营开创的《大同报·夜哨》和《国际协报·文艺》提供的历史机缘。借助于两大媒体,萧红和白朗的文学创作突破狭小的沙龙空间,获得了新的生长。对比考证1933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授旨创办的长春《大同报·夜哨》和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上左翼作家作品数量和比例,从中可以发现两位女作家的地位变迁。

表4 1933—1935年左翼作家在《大同报·夜哨》和《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上的作品数量
沦陷初期,萧红、白朗作品总数量为47篇,在《大同报·夜哨》和《国际协报·文艺》上为20篇,占其总数量的1/2。由此可见,满洲地下党开辟的文艺阵地为两位女作家的文学发展创造了机遇。不同于白朗的职业编辑身份,萧红以卖文为生。凭借满洲地下党与《大同报》《国际协报》等报刊的关系,萧红此期发表了24篇文学作品和一部专集(与三郎合著)。《文艺》周刊的撰稿人大多是无偿、义务写稿,经白朗向《国际协报》主编交涉,两萧每月可得20元哈大洋,使其生活得到一些保障。萧红此时期的作品都具有自叙传成份,这说明作者还不擅长虚构创作。中国知识分子纯朴的民粹思想的集体无意识,“牵牛坊”左翼思想的渗透,萧红本人情感上的主观接受,以及现实中窘迫的生存体验等因素,都最终促使了萧红将文学创作作为一条“职业”之路。
迫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危险,北满地下党的高层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为了保护中国共产党培植的新生文化力量,满洲地下党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考虑,决定安排萧红、萧军出走,并提供了相应的资助。这不仅使两萧更加紧密地靠近左翼文化阵营,更使得他们得以在关内广阔的抗战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多年之后,罗烽曾对“牵牛坊”房主冯咏秋之子冯羽深情地回忆:“三二年,三三年‘牵牛坊’也‘红’了,特别是萧军、萧红离开哈尔滨时,‘牵牛坊’‘红’得比较显眼。”“当时,在党内搞宣传工作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牵牛坊’。我是地下党,你父亲与我心照不宣,‘牵牛坊’表面上是文人聚会的地方,实际上为党做了许多工作。”[16]
萧红、白朗从个人的生命感受到认同左翼思想意识,她们的文学创作也由沙龙文化走向了社会文学。在这个“转机”中,哈尔滨“牵牛坊”左翼阵营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此后,从沦陷区流亡出去的萧红、白朗,其文学创作越来越明确地汇入到抗战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