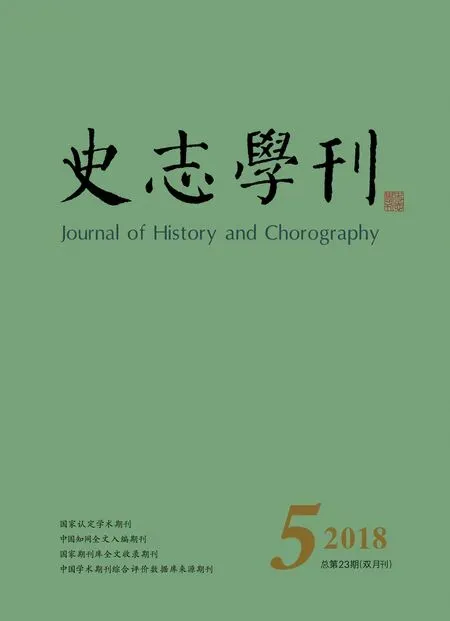辛亥革命时期商人与秩序关系评析
——以辛亥革命中的杭州各业商人为中心
颜 志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辛亥革命时期商人与秩序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秩序”,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有序状态,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带有制度含义的“秩序”概念。在本文中,破坏秩序即是指破坏社会稳定,维护秩序即是指维护社会稳定。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与秩序问题,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冯筱才完成的。冯筱才认为商人在辛亥革命中的核心关怀在秩序上[1](P312),在革命过程中,商人发挥着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作用。冯筱才更进一步将商人的行动归结为“产权—秩序”模式:政治事件冲击社会秩序;崩坏的秩序,威胁商人财产的安全;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商人会设法挽救社会秩序[1]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P18)。
虽然冯筱才宣称其以整个商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但是细绎他所举的史料,反映的多是商会、绅商的活动,对于革命中普通商人的作为鲜少涉及。马敏和朱英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商会、绅商阶层[2]马敏,朱英认为苏州商会面对革命走出的第一步,是与官厅共同维持社会秩序,消弭动乱。(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412)后来马敏扩大研究范围,在考察了全国各个不同地方的商会,在辛亥变局中的表现后,认为绅商阶层在革命中的行动目标是通过维护社会秩序,来维护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70),也没有将普通商人的活动作为研究重点。总之,目前学界对辛亥时期普通商人与秩序的关系,尚缺乏严肃的研究。
面对社会秩序的崩溃,普通商人是否是像商会、绅商一样,主要起着维护秩序的正面功能呢?商会领袖、绅商阶层站在全局上考虑问题,地方秩序自然是其首要考虑目标,但一个深嵌于市场之中的普通商人,如果其个体利益与社会的稳定发生冲突,他未必会以社会秩序为行动本位[3]罗威廉认为,商人重视利益,甚于秩序,“商人首先是要追逐利润,其次才是一个生意不受阻碍的稳定的社会。”(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P258)。
为了探究革命的振荡中普通商人与秩序的关系,填补学术空白,笔者拟以辛亥时期的杭州为个案来进行研究[1]对于辛亥时期杭州商人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蔡禹龙曾以绅商阶层为中心进行过研究,认为绅商在革命中发挥了稳定秩序的作用。参见蔡禹龙.从“纷乱”到“平和”:杭州光复前后的城市秩序.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将分别以辛亥时期杭州的米业、钱业和典当业商人为对象,去考察这些商人在风潮中的活动,考察这些普普通通的商人与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关系。
一、米商
冯筱才认为,“面对秩序的威胁,商人的天然反应自然是抵制”[2]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P86)。即是说,如果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商人的第一反应是维护秩序。可是,辛亥变局中杭州粮商的行为,与冯氏的这一论断出入甚大。
(一)抢米风潮之前
杭州的社会秩序并不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才陷入混乱,实际上,由于自然灾害引发了严重的粮荒,1911年9月初,杭州已经动荡不安,秩序堪虞。
杭州的粮食危机,源于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的严重水灾。“有若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凡有水灾、凶灾等处,闹荒、抢米,书不胜书。”[3]论今日乱机之多.申报,1911-9-24(第1张第3版).由于水灾,浙江秋粮大幅减产,大批人口受灾。“浙属风雨沈灾,秋收绝望,而灾区难民急待拯救者,屈指难以数计。”[4]浙江官绅筹赈之动机.申报,1911-9-8(第1张后幅第3版).
严重的灾害,产生大量的饥民。饥民的大量存在,对社会的稳定构成挑战。1911年九月初,杭州地区的治安形势,已经非常严峻。9月3日,余杭灾民冲击县署,围住县令,殴打警务长程某,“将程衣撕破,大帽打落”,最后,幸由官府处理得法,才没有酿成大祸[5]余杭灾民又有小滋闹.申报,1911-9-6(第1张后幅第2版).。9月6日,杭州附近的瓶窑爆发民变,千余乡民冲击米店,捣毁学校[6]瓶窑乡民抢米之警告.申报,1911-9-9(第1张后幅第2版).。9月21日,大批灾民涌入杭州,向官府跪香、告荒。由于灾民人数达二万五六千名,“沿途商店,见人数过多,咸相顾危”,浙江巡抚下令全城戒严[7]浙属灾民来省跪香记.申报,1911-9-23(第1张后幅第3版).。10月初,杭州地区灾民骚乱,抢劫大户,捣毁学校[8]杭属亦有灾民闹荒.新闻报,1911-10-10(第2张).(P2)。
虽然社会秩序已经岌岌可危,但是此时杭州米商却并未平抑粮价,抚慰民心,反而大肆投机,炒高粮价。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幅降低了杭州市场的粮食供给。往日车水马龙,商船云集的杭州米市,在一段时间内,竟没有米船前来交易,“近日因风雨为灾,竟无船到埠”[9]湖墅缺米之恐慌.申报,1911-9-6(第1张后幅第4版).,“贫民众多,买米无由”[10]大帮饥民来省告荒.新闻报,1911-10-8(第2张).(P2)。米商们乘机哄抬米价,“将储积陈粮,暗移他处,为居奇计”[11]湖墅缺米之恐慌.申报,1911-9-6(第1张后幅第4版).。
1911年8月底,米价被米商炒到“尖米每担售至七元八角起价,糙米每担六元八角”。9月5日,米商们在杭州城内散布消息,说杭州城内的存米只能满足杭州九天的消费,“传告各同行,限制门庄籴米,每户一斗,确系人多者,酌量准添,五斗以上者,一律停售”。这种同业协作进行的炒作,造起了很强的声势,“全城哄传,人心惶惧,势若真将断炊者”[1]杭垣米市之危机.申报,1911-9-7(第1张后幅第2版).。9月6日至9月7日,米商们再次合作抬价,“每家均设斗篮一具”,里面放上五六斗品质恶劣的黄糙米,对外宣称,米铺现今只有这种米,定价七元四角,仍以一斗为限。而事实上,米商手中不仅不缺米,而且数量不少。“现经确实调查,闻下城之四丰、秦邢、穗兴等大店,每家实存均在五千担以上,其余各店亦二三千担不等云。”[2]杭垣米市之恶现象.申报,1911-9-9(第1张后幅第2版).虽然后来官厅采取各种干预手段,甚至要查办操纵米价的米商,但是,米商们并未停止投机活动。“奇峰品尖米,仍私行勒价,每担需洋八元八角,且秘藏密室[3]杭垣米市回复之动机.申报,1911-9-10(第1张后幅第3版).,如非素识,或讬人商购者,不能妄尝禁脔云。”[4]浙属因灾环请蠲漕办米之呼吁.申报,1911-9-17(第1张后幅第3版).
显然,哄抬米价的米商们并不真正关心杭州的社会秩序,他们希望的是乘着天灾狠狠地捞一笔。他们的行为,不仅无益于社会秩序,反而会让城市贫民的处境更加艰难,实际上是在破坏秩序。
(二)抢米风潮
日趋动荡的时局,使贫民处境艰难。杭州“城内机房、料房,多至三四万人,十九无隔宿粮”[5]浙潮感受鄂潮之影响.申报,1911-10-21(第1张后幅第2版).。饱受米商投机之苦的贫民,终于在光复前夜,掀起了抢米风潮。
1911年11月3日傍晚,也就是杭州光复的前两天,一贫户向米铺请购半升米,被米铺以“提早收市”为由拒绝。贫民再三请求通融,但米铺仍拒绝出售。米铺的行为,激起了公愤,“一唱百和,聚集数百人,将该店捣毁”。接着,贫民骚动,将城内众多米铺打抢一空,“东街、普安街、菜市桥、联桥、孩儿巷、春坊、官巷口、平津桥等街米店一例捣毁,存米搬抢净尽。”[6]杭垣大局日急.申报,1911-11-5(第1张后幅第2版).
光复初,贫民阶层对米铺冲击,依然不断。11月21日,杭州贫民再度冲击米店。贫民们将一素有囤积投机习惯的黑心米店打毁后,四处抢米。“自东街直上,过菜市桥,至孩儿巷,内分支赴贡院前东西两桥,所有米店概被捣毁抢尽。”[7]新杭州之三大恐慌.申报,1911-11-24(第1张后幅第2版).是时,不仅城内米铺时闻被抢,水道中运米的米船,亦常成为贫民抢夺的目标。11月23日,一只米船在西湖坝附近被抢[8]西湖灞又有抢米案发现.汉民日报,1911-11-25(新闻第2版).。差不多同时,湖墅附近,也有一艘米船被抢[9]抢劫米船之骸闻.汉民日报,1911-11-26(新闻第3版).。
这时,米商终于有维护秩序的举动了。面对贫民阶层的冲击,米商们一面由米业董事出面,请求官厅予以保护,并要求组建商团[10]军政批示.汉民日报,1911-11-24(新闻第4版).,另一方面,米商们不得不暂时接受商会的建议,下调米价。11月24日,食米“起价每石又低至五元,最上等白米每石已减至六元六角”[11]米价低廉之可喜.汉民日报,1911-11-25(新闻第2版).。面对抢米风潮,米商终于停止炒价,做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事情。
(三)抢米风潮之后
贫民的冲击,使米商们暂时放弃对利益的追求,转而维护社会秩序。但米商的这种转变,只是暂时的。抢米风潮结束后,米商们故技重施,再次抬高米价。抢米风潮结束不过十余日,米价再次飞涨。笔者根据《汉民日报》《申报》从抢米风潮结束到1912年上半年对杭州米价调整情况的历次报道,制成如下表格:

序号 报道内容报道标题及日期1 近日调查米市,见起码劣米,每石忽已高涨四角,其上身各档米石无不逐一增价云。《米市骤然涨价》,《汉民日报》1911年12月5日。2 而奸商垄断,籴贱贩贵,米价仍高抬至七元四角。乡镇米店,竟有贵至九元五角者。买卖不公,孰有甚于此者乎?……恐数十万饥民,鋌而走险,大局不堪设想矣!《米业中两大蠹》,《汉民日报》1911年12月5日。《米价渐增之可虑》,《汉民日报》1911年12月13日。4 起码劣米之朔日早定价每石五元,今则迭次递增,所有该起码米,每石已涨至六元,至中上等米石,亦同时腾贵。3 起码劣米,在前数天,已增至五元四角一石。该档米石,昨日(廿二)忽又增至五元六角。其有中上米石,虽价目未增,而按之各档米身,遞次减色,已在暗中腾贵。《米价飞涨之可虞》,《汉民日报》1911年12月16日。5 省垣米市,自上月下旬以后,迭次飞涨,至起码劣米,每石须六元二角。 《劣米低价之原因》,《汉民日报》1912年1月2日。6 以阴历言,又已年尽岁暮,一班贫民,号泣载道,兹由各米铺体念民艰,暂议各档米石平价售粜,以为贫民购米便宜之计。《米价低贱之可幸》,《汉民日报》1912年2月5日。7 据米业会议,今春米价,尤有不得不涨之势。旬日之间,城垣各米铺逐档米石,已昂值大洋四角。《米价增昂之可虑》,《汉民日报》1912年3月2日。8 自上年秋歉以来,杭垣米价之昂贵,已达于极点。兹以失业贫民日多一日,而米价不稍减贱,旬日以内,米市售价较之上月每石已高涨大洋八角。《米价又忽飞涨》,《汉民日报》1912年3月14日。《杭垣绝粒之恐慌》,《申报》1912年3月24日。10 嗣后,在会各商,公同议决,自即日起,起价米以售至六元八角为度,然各商以不堪亏损,请以半月为限。9 杭垣米市存货将罄,以致市价飞涨,即极粗糙之米,每担已需七元。现查本月二十二日(二月初四)起,各米铺因颗粒无存,同时闭门歇业者,荐桥、联桥、闹市口等处共五家。《总商会集议米价》,《汉民日报》1912年3月25日。11 一班米侩,又乘此将米价高涨。□黄起码米,每石竟贵至七元二角,其上米色白净饭堪适口者,每石均需八元。《米市乘机涨价》,《汉民日报》1912年5月15日。12 米侩居奇,乘隙散布流言,谓城厢内外存米不足十日之供,过期必致绝粮,连日市盘飞涨,前后一星期,每担骤贵三元左右。《杭州米市恐慌》,《申报》,1912年 5月29日。
从上表可以看出,风潮后杭州的米价是一路飞涨。那么,此时米价的飞涨是否纯然因为粮食进价的高涨所致呢?对这一问题,虽然现在留存的当时杭州方面的史料没有明确的回答,但与杭州仅一江之隔的绍兴,却保留了这方面可资参考的资料。当时绍兴《越铎日报》的记者发现,虽然米商自称米价飞涨是“皆因进货贵,故出售亦贵耳”,但是米铺所卖的都是“旧日囤积之货”,米商是把过去低价买进的存货,以高价售卖,从中谋取暴利[1]米侩之肉其足食乎.越铎日报,1912-5-23.(P2)。绍兴都督王金发认为米价飞涨有米商炒作的因素,“各米行铺,皆以藉口无现款往贩为词,明系欺饰之语,贪图厚利,不顾民命攸关。”[2]绍兴军政分府照会山会商务分会.1911-12-31.绍兴商会档案.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藏,140-4-316.
米商对米价的操纵,必然会使贫民处境恶化,从而破坏脆弱的社会秩序。《汉民日报》记者的担心“恐数十万饥民,鋌而走险,大局不堪设想矣”[3]米业中两大蠹.汉民日报,1911-12-5(新闻第4版).,并非杞人忧天。
显然,面对动荡的社会秩序,辛亥时期的杭州米商们并未把秩序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米商们都在炒作米价,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当然,米商也是有维护秩序的努力的,但这只是抢米风潮爆发时,米商们才短暂做出的行为。风潮一结束,米商们就故伎重施,继续炒价。米商是务实的,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会想办法赚尽能赚的最后一分钱;同时,米商又是短视的,他们为了利益,高抬米价,置大局于不顾,招致抢米风潮,实在是自遗其咎。
三、钱商
金融为百业枢纽,如果金融市场爆发危机,不仅商界会受到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都会受到冲击。钱业商人作为金融市场的运营主体,在辛亥的暴风骤雨中,做出了何种选择呢?
(一)偷漏现洋
武昌起义极大地冲击了杭州的金融市场。“大小各铺,咸因鄂乱,交易均皆紧守,不愿挂欠,加以近日兴业银行各存户纷纷提款八十余万,市面金融界,大受影响。”[1]浙省防乱之恐慌.新闻报,1911-10-19(第2张).(P1)当时杭州金融市场现洋异常缺乏,“现洋奇绌,情形尤危”[2]浙潮感受鄂潮之影响.申报,1911-10-21(第1张后幅第2版).,“市面恐慌已达极点”,大钱庄缺乏现洋,持票提取现洋者,需要额外支付两元作为贴水[3]杭州防乱情形.新闻报,1911-10-23(第2张).(P2)。由于居民纷纷提取现洋,一些钱庄经不住挤兑,陷入危机,比如湖墅仑源钱庄,在受到挤兑后“陡然搁浅”[4]杭州钱业之受挤.申报,1911-10-21(第1张后幅第3版).。
然而在金融市面危如累卵之际,杭州钱商却不顾大局,做起了损人利己的买卖。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刚刚经历过“橡胶股票风潮”的上海金融市场极度恐慌,银拆陡涨至七钱以外,“洋厘亦涨至七钱八分”[5]四纪本埠惊闻鄂乱情形.申报,1911-10-16(第1张第5版).。上海银元价格的陡涨,使把银元从杭州贩往上海,有利可图。于是,杭州钱商们不断将杭州市面上的现洋运往上海。“各钱庄不顾大局,仍做掉期,致现洋纷纷出省。据最近传闻,自昨日(廿四)止共捆五十九万。”[6]浙省大戒严.时报,1911-10-17.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料(第七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P5)
钱商们的这种投机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杭州市场的钱荒,加剧了金融秩序的混乱。“一般钱侩,值此银根紧急之时,纷纷私运现洋出境,以致缺乏愈甚。”[7]杭州光复后记事.新闻报,1911-12-11(第2张第1版).钱商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受到了浙江军政府财政部长高尔登的严厉指责,“本省承疲敝之后,金融本已恐慌,乃近来访闻,不法市侩,不顾大局,仍纷纷捆载大宗现洋出口,以至周转益觉不灵,殊堪痛恨。”[8]杭垣现象种种.申报,1911-12-10(第1张后幅第2版).
显然,钱商偷漏现洋的行为,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不仅不含拯救市面、维护秩序的意图,还给本已不堪的金融秩序带来了进一步的破坏。
(二)努力救市
诚然钱商的偷漏现洋加剧了金融秩序的恶化,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抹杀钱商维护金融秩序的行为。萧条的金融市面,不利于钱商的经营。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杭州钱商确实做出很多保护金融市面的努力。
为了解决通货不足的问题,钱商们通过商会与国家机器交涉,请求官厅拨款救市。10月20日,钱典两业商人,群集商会,迫使商会总协理向抚院借拨库帑。当正在商会听候消息的钱典众商听说官厅虽答应借款,但所借多系锭银后,又要求商会总协理再去请求换拨银元[9]杭防戒严情形.申报,1911-10-22(第1张后幅第2版).。商会总协理几度往返,终于在当夜十二点半接到大清银行允放三十万龙洋的复电。众商接信后,一面刊发布告,一面再请商会致函浙江巡抚,下发龙洋与英洋等同使用的告示[1]杭垣绎骚近状.申报,1911-10-23(第1张后幅第2版).。
杭州钱商鉴于银根奇紧,还曾自行发行钱业公票。1911年11月25日,钱业商人集议,决定发行钱业公票二十五万元[2]杭垣光复后近状.申报,1911-11-17(第1张后幅第3版).,公票面值分为一元和五元两种,“由发行庄号加盖图章,即由发行庄号至十月底收回,照数付现”[3]钱业议行钞票之计画.汉民日报,1911-11-18(新闻第4版).。
但是,钱业商人危机公关的经验明显不足。他们所发行的公票,做工粗糙,“该票形式类如慈善家施送之米券,仅用铅字刷印于簿纸上,另盖某某庄号图记一方,外并无他项凭记”[4]杭州光复后记事.新闻报,1911-11-24(新闻第2张第1版).,未得城内商家信孚,无法流通[5]钱业钞票未能通用之原因.汉民日报,1911-11-22(新闻第3版).。众钱商只得“会馆集议,决意一律停发,已发行者,逐渐由发行之庄号收回兑现”[6]钱业收回钞票之集议.汉民日报,1911-11-25(新闻第3版).。
不管钱商独自发行公票的成绩如何,金融秩序大乱之时,钱商确实做出了维持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努力。
(三)做空军用票
钱商发行公票失败后,军政府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为后盾,在没有保证金的情况下,强制发行军用票,稳定了金融市场。随着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钱商资产亦相对安全。这时,钱商们不顾大局的毛病又发作了。
在动荡时期,人们往往异常重视重金属货币,而轻视纸币,这样军用票与现洋便在无形中产生了差异。钱商们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做空军用票,利用军用票与现洋之间的差价,谋取利益。“讵各钱侩,犹复贪心未厌,钻谋意外之利。杭垣军用钞票,迭经军政府通告,划一通用。乃各钱侩,接兑此等钞洋,概须贴水六十文,并前清之大龙圆兑价亦须贴水。”[7]钱侩之可杀.汉民日报,1911-12-11(新闻第2版).“所有浙江军用钞票,竟与现洋溢分出两等价值,日内愈跌愈低,竟相去二三十文不等。”[8]军用票市值不一.汉民日报,1912-4-11(新闻第1版).此时钱商做空军用票的行为,显然不利于金融市面的稳定。
显然,钱商不仅以动荡秩序的受害者面目出现,而且以金融秩序破坏者身份出现。为了利益,钱商把大量现洋运往上海;为了利益,钱商做空军动票;也就是说,为了利益,钱商践踏秩序。当然,钱商也为救市付出了努力。不过,他们能力有限,经验不足,其发行的钱业公票草草收场。总之,杭州金融秩序之所以恶化如此,并迟迟不得平复,钱商难辞其咎。
四、典商
与米商、钱商不同,典商在整个辛亥风潮中,都处于一个不利的市场格局之中,自保尚且不暇,遑论逐利。典商没有为逐利而破坏秩序,他们一直在为恢复金融秩序而努力。军人强当给典商带来的威胁更为致命,典商不断请求官厅管制军人,保卫公安。不过,典商并非没有于秩序不利的行为。典当的歇业或减少营业时间,便有碍社会稳定。
(一)典商与金融秩序
典商所从事的,是以某些物品为抵押的放贷活动,从贷款中获取利益。由于当时现洋严重缺乏,向钱商“提取现洋,每百元贴水八元”,但典商放贷利率却仅一分六厘(每百元收利一元六角),实际上放贷百元“须实耗洋六元四角”[1]当业停当之实情.汉民日报,1911-12-15(新闻第3版).。即是说,严峻的金融秩序,不利于典商的商业活动。为此,典商一方面调整经营规则,以适应此环境,另一方面努力维护金融秩序。
1911年10月19日,杭城各典当将典质物品金额上限设定为五元。由于质物取洋的人太多,20日又将上限下调至两元[2]杭防戒严情形.申报,1911-10-22(第1张后幅第2版).。21日下午,典业全体开临时会议,议定“典质衣饰仍以每人两元为限”[3]杭垣绎骚近状.申报,1911-10-23(第1张后幅第2版).。光复后,有的典当由于资金实在有限,无法支撑居民源源不断的典质,为了自保,只得禀明军政府,“每日开市二小时,只准来客赎取货物”[4]当业停当之实情.汉民日报,1911-12-15(新闻第3版).。除了限制典质额度外,典当商人还将利息削减至八厘,以吸引质户取赎,加快现洋回流[5]新杭州之危机.申报,1911-12-8(第1张后幅第2版).。
除了调整自身营业规则外,典业商人还与钱商一道为增加市面通货而奔走。10月20日,典商与钱商共同要求商会总理向官厅求援,请官厅下拨现洋,以济市面[6]杭防戒严情形.申报,1911-10-22(第1张后幅第2版).。当钱商为了利益做空军用票,“以致军用票抑价阻滞”之时,典商立即出面阻止,“乃幸城厢各当铺顾念时局,首先通用军用票及前清之大龙圆,业已定价,进出划一,故近日之间,军用钞洋,市场亦大为流通。”[7]典当顾念时局.汉民日报,1911-12-15(新闻第3版).
(二)应对军人强当
金融危机相比,军人的强当(意为强行典当)行为,给典商们带来的困难更为致命。光复后,浙江军政府财政支绌,无力应付各项开支,“凡百需财,而时难年荒,穷于罗掘”[8]汤寿潜.致光泰仁兄大人执事函.1911-12-23.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P133),“因此当时军队常常欠饷”,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便四出抢劫掳掠,或抢劫村庄、当铺和商店,或强迫当铺收当破旧衣物,掳掠骚扰,指不胜屈”[9]汪林茂.浙江辛亥革命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P258)。当时兵士在杭州城内滋扰典当,用破旧的衣服,向典商勒索,“稍与商减,即持枪恐吓”[10]杭州最近之危机.申报,1911-11-27(第1张后幅第3版).。有时士兵见典当闭门不开,竟在门外放枪。例如,1911年11月27日,四五十名士兵,在协济典门外,“开枪轰击,洞穿大、二两重门”[11]杭州兵匪滋事之可危.申报,1911-11-29(第1张后幅第3版).。
为了应对军人的打劫,典商不断与浙江军政府交涉,请求官厅保护。风潮初起,典商即召开同业会议,议定禀请军政府维持营业秩序,并且各典均安装电话,以便遇事及时与军政府联系[12]典业恐慌之不可终日.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约束军人主要依靠军政府,但军政府内部机构混乱,效能低下,军人滋扰,迟迟不能禁绝。
11月24日,包括典商在内的杭州各业商人,齐聚商会,要求总协理向军政府请宪兵保护。可是25日,不仅宪兵没有出现,而且兵士滋扰更加严重[13]杭州最近之危机.申报,1911-11-27(第1张后幅第3版).。实际上,军政府不过是“空言保护,未派一兵”。在这种情况下,典商以罢市威胁军政府[14]新杭州急须善后.申报,1911-11-28(第1张后幅第3版).。
面对典商的威胁,军政府不得不有所表示。政事部表示,已经商请司令部,“明日起酌派兵官,带同兵士,陆续梭巡”[1]政事部照会商务总会文.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军政府还发下示谕,要求军民各守秩序,如敢故违,军法从事云云[2]军政府晓谕居民人等不准强当衣件文.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可军政府的劝谕完全不起作用,士兵们横行如故。11月27日,士兵们见当铺闭门,竟在门外放排枪泄愤。11月30日,军人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在某典铺外,打死一名行人。30日傍晚,典商们群集商会,决定同行二十三家于明日一律停歇,由商会公禀都督,请军政府下发“军政府核准暂停”字样的封条,以便各典贴于门首[3]新杭州纪事.申报,1911-12-2(第1张后幅第2版).。可此轮罢市尚未实施,当夜即有散兵游勇扬言要火烧典当。12月1日下午,众典商晋谒都督汤寿潜,请都督保护。汤氏一面安慰典商,一面电饬虞廷派兵保护各典。12月2日,兵士们并未把虞廷所派保护典当的宪兵放在眼中,继续滋闹,典商“每家各被索去洋三四百元不等”[4]新杭州种种.申报,1911-12-4(第1张后幅第3版).。
典商在此次风潮中,一次又一次地求助军政府,希望军政府约束士兵,维持治安。为了使军政府赶速行动,典商“自愿”捐款助饷。起初典商提议助饷一万元,由全城二十三家,按照架本金融分摊[5]杭垣商市之悲观.申报,1911-12-3(第1张后幅第3版).。后来,典商又再三磋商,决定将报效金额提高至两万元,每月分缴两千[6]新杭州纪闻.申报,1911-12-7(第1张后幅第3版).。最后,杭城内外各典的最终报效金额是二万四千元,作十个月分期缴纳,每月缴两千四百元[7]总司令部札饬各军队文.汉民日报,1911-12-17(新闻第2版).。这笔捐款实际上是典商用来换取安全的“保护费”。
后来军政府决定“各营将校,组织名誉队,以监察不法弁勇”[8]新杭州之危机.申报,1911-12-8(第1张后幅第2版).。这里的名誉队,即指“军人自治团”。军人自治团成立后,“分队保卫城厢各典”,才抑制住军人对典当的骚扰[9]军人自治团之成绩.汉民日报,1911-12-18(新闻第2版).。
显然,典商们请求官厅保护,向官厅“捐款助饷”,是出于保护私有财产而进行的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典商要求约束不法兵士的努力,不只对典业一业有利,对整个杭州商业乃至杭州治安,皆有益处。
(三)停质与社会秩序
在不利的金融秩序与治安条件下,杭州各典或是闭门歇业,停质待赎,或是晏启夙闭,缩短营业时间。典当的这种行为,对于那些依靠典质财物以换取升斗救命食粮的城市贫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光复之后,军人的强当使“各典业大为惊慌,终日闭门”[10]典业恐慌之不可终日.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1911年11月26日,各典商“同时罢市,实行暂停五日之原议”[11]新杭州急须善后.申报,1911-11-28(第1张后幅第3版).。因为受到军人的威胁,一些典当的伙友不得不外逃保命,这也使一些典当无法开业,“各家伙友已逃空,明日万难开市”[12]杭州兵匪滋事之可危.申报,1911-11-29(第1张后幅第3版).。12月4日,杭州城内十九家典当,停歇了十一家,次日又有两家停止典当[13]新杭州纪闻.申报,1911-12-7(第1张后幅第3版).。此时即使开门营业的典当铺,也是严重缩短了营业时间,“查近来省城各典业,前因有假冒军人强当,晏启夙闭”[14]杭州府民事长照会商务总会文.汉民日报,1911-12-7(新闻第2版).,“即偶一轮开,亦不一时,辄行关闭”[15]杭州府民事长呈财政部长文一.汉民日报,1911-12-8(新闻第2版).。1912年4月,杭州城内谣啄纷纷,典商恐秩序再乱,“昨今两日,典铺又相继停当”[1]典当又纷纷停质.汉民日报,1912-4-3(新闻第3版).。
典商的闭门歇业,固然是因为外部不可抗因素所致,但是,典商的这种自保却又是对秩序不利的。典当的闭歇,使城市贫民生存困难,“一般贫民之待此举火者,生机几绝。”[2]典业恐慌之不可终日.汉民日报,1911-11-27(新闻第2版).有的贫民,因典当闭歇,流泪而还,“上日各典均闭门不开,贫民咸穿眼而待,兼有涕泣而返。”[3]急办商团之先声.汉民日报,1911-11-28(新闻第2版).有的贫民,面对停业的典当,情绪激动,“下城裕典等典门首,于本日午前十时来典贫民哄聚多人,倚待良久,甚至激忿,向门乱击,几乎酿祸。”[4]典当恐慌之愈甚.汉民日报,1911-12-3(新闻第2版).
时人对典当停质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是明白无疑的。《汉民日报》记者担心,典当停质会引发民变,“若各典故意缩短时期,严定限制,惟恐民至末路,必将铤而走险。”[4]典当恐慌之愈甚.汉民日报,1911-12-3(新闻第2版).官厅也担心典商停质会引发动乱,典当业“关于贫民生计,甚为危急。若不赶紧设法维持,不但地方秩序难于规复,势恐于治安将多滋扰。”[5]杭州府民事长呈财政部长文一.汉民日报,1911-12-8(新闻第2版).典商自己也知道停业与秩序的关系,“若聚然停当,恐生意外风潮”[6]典商顾恤穷民.汉民日报,1912-1-1(新闻第2版).。从时人的言论中,显然可知典当停质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
总之,面对不利的金融秩序和治安条件,典商的确积极地维护秩序。不过,他们虽然没有为了利益而践踏秩序,但是他们为了保护私有财产而停业、减少营业时间的行为,却对社会秩序不利。
四、结论
当把研究焦点从抽象的“绅商”阶层身上移开,转而关注那些具体的,有明确职业属性的商人,便会发现,这些商人固然有维护秩序的一面,但也有破坏秩序,不利社会稳定的一面。
就像商会、绅商阶层一样,各行各业的普通商人也有维护秩序的举动或呼吁,而且他们的这种对秩序的维护,多多少少是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米业商人是在贫民抢米风潮的冲击下,才降低粮价并呼吁组织商团的;钱业商人是在现洋匮乏,金融低迷的不利情况下,去呼吁拨发现洋,发行钱业公票的;典当业商人在金融与治安的双重威胁下,去参与维护金融秩序,并要求军政府约束军人的。
但与商会、绅商阶层不同,普通商人会在利益的驱动下,做出损害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事情。米商为了利益,不顾大局地高抬米价,直接引发了抢米风潮。钱商为了利益,把杭州的现洋运往上海以赚取差价,这是杭州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又为了利益,钱商还做空军用票,使军用票流通受阻,干扰杭州金融秩序。
除了追逐利益,普通商人还会为了自保而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典当业商人迫于金融与治安压力,停止营业,闭门自保。可是典当业商人的自保行为,却威胁贫民生计,损害社会秩序。
总之,通过对杭州米商、钱商和典商的考察,笔者认为这些具体的商人在辛亥变局中,不仅有保护秩序的行为,而且有为获利而破坏秩序,为自保而破坏秩序的行为。这些情况,与学界过往的对辛亥时期的商人的认知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