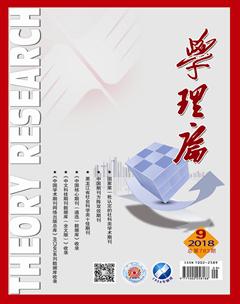新政治人类学视域下的民族志探析
李雯
摘 要: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将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展现在读者面前,民族志既可以被视为研究文化的一种田野调查方法,又可以指呈现田野调查成果的一种文本形式。民族志的发展经历了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阐释民族志以及实验民族志四个发展时期,其内容与价值追求发生了诸多转变。新政治人类学视域下的民族志,则超越了人类学壁垒,实现了跨学科运用与发展。民族志不再局限于人类学,与多学科的融合创新了实证研究范式,将互为他者、民主多元与协商一致的理念融入诸多学科的研究过程中。
关键词:民族志;新政治人类学;人类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9-0184-04
探析民族志离不开对其内涵的阐释,只有在对其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尽可能全面而深刻的解读。民族志究竟是什么?人类学对于民族志的解释如下:“民族志(ethnography),其词根‘ethno来自希腊文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graphy来自希腊文‘graphein,意为‘记述。又译文化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做田野调查,深入到特殊的社区生活中,从其内部着手,通过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描写,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此文化的基本概念”[1]106。由民族志的词根不难理解,民族志是对一个文化群体的记述,人类学家通过参与式调查,对群体内部的种种现象进行描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某一群体文化的概念分析,试图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以归纳出人类学领域的一般性规则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民族志常常将异文化作为研究基础,“没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专注自身的。民族志或明或暗都是一项比较。通过比较,民族志的描述变成了客观的描述。而对未经调和的感觉之朴素的、实证主义的感悟,同样也不是独立的,恰恰相反,它成立一种普遍性的理解,直到它对任一社会的感知都加强了对所有其他社会的看法”[2]105。传统观念中,好的民族志首先必须是以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实现其客观性,并通过认识异文化来认识本文化,即民族志在描述文化之外,也内含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之义,通过比较达到对本我的深刻认识。早期的人类学是为了迎合西方列强的需要而产生,野蛮民族与异文化为其主要研究对象,西方列强通过对异文化的研究来巩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异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逐渐缩小,西方各国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全球化浪潮也开始兴起,促使着欧美人类学家开始将研究视角放在本土文化之上。
一、民族志的兴起与变迁
(一)业余民族志
作为一种文本表现形式,民族志最初是以业余民族志的形式出现的,诸如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的《马可·波罗行记》及中国的《山海经》。這类业余民族志以记录社会中的奇特风俗为主题,常常伴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的原始部落成为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以地理发现为目的的航海家、商人、探险家游览各地,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异文化,并尝试与土著进行简单交流,利用文字记录这一过程,这些文字在描写上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记叙的内容也很肤浅,可以归结为一种对“土著人”的猎奇式书写。总的来说,业余民族志的特点可概括为,“第一,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象的内容;第二,调查时间不固定,所记内容单一而且肤浅;第三,调查者知识狭隘使民族志质量难以保证。”[3]调查者本身就不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并未受过相关文化理论的熏陶,或者是出于好奇或者是出于惊叹,而对异文化进行了记录,记录中也常掺杂着自我对异邦文化的想象,对异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入,其质量难免无法令人满意。同时,这一时期的这类所谓业余民族志也为当时的人类学家提供了资料,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
(二)科学民族志
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被认为是民族志迈向科学化的标志。在该书的导论中,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一些关于民族志写作的理念,主要包括三点:“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该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4]4这三点原则也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田野工作的三大基石”或者是“成功的三大要素”。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马林诺夫斯基多次提及科学,将科学化作为其研究的目标,力求以科学而系统的描述来再现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文化全貌。在这三个要素下,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合二为一,人类学家通过深入的参与式调查获得其他调查方法所不能得到的信息。同时这种研究方法也对人类学家自身提出了更高挑战,其必须熟练掌握当地人的语言,从各个方面融入当地文化,才能在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分析,完成民族志的书写。
科学民族志中,作者不以第一人称出现在文本中,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进行记录,以权威者的第三人称代替第一人称,力求反映社会现实。人类学家犹如一台照相机,将自己所看的情形一一记录下来,极其讲究实证与科学。这一时期,马林诺夫斯基将田野工作、民族志与理论三者统一起来,改变了人类学家通过二手资料撰写报告的传统,参与实地调查成为人类学家的“必修课”,奠定了科学民族志的理论基础与指导原则,为展开科学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良好范例。
(三)阐释民族志
20世纪60年代,派克(Pike Kenneth)创造出“emic/etic”这一描写理论,将etic视为一种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emic则是指土著的认知。受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etic在对异文化进行描述时,倾向于以西方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异文化,未能达到客观与科学。有关emic与etic之间的矛盾处于西方学者的持续争论中,在这一方面,格尔兹(C.Geertz)提出了其独到见解,形成了阐释民族志。
地方性知识与深描是格尔兹阐释民族志的两个重要武器,也集中体现了其构建民族志文本的方法。对于地方性知识,格尔兹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进行分析,作为一个etic,他进行了很好的角色转换,放下etic所持有的优越感,与当地人产生生活乃至情感方面的互动,融入当地人的社会,也即融入emic中。这种角色的转换,使得格尔兹不仅了解斗鸡活动的程序规则,更能对其背后的深厚内涵进行挖掘,以一个当地人的视角来呈现斗鸡文化。阐释民族志不再以科学性作为唯一原则,而是尽可能多地深入到被研究者的内心世界,关注不同人对文化的解释,人类学家所做的则是对他人解释的解释。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格尔兹又提出了深描这一手段。深度描写源于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他发现,即使是张合眼睑这一简单动作传达出来的社会内容却可以是丰富多样的。格尔兹深受此理论的影响,十分重视文化符号,并将文化符号放在具体的情境下进行深度分析,在《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中,格尔兹也正是将斗鸡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进行了描写,并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体现着,阐释民族志不再以制度素材的堆砌为目的,而从简单的事件或个案入手,追寻其隐含的社会内容,赋予文化符号更为深刻的意蕴,完成对意义的阐释,最终达到深描的目的。
阐释民族志阶段,人类学家曾经十分推崇的科学幻想被打破,格尔兹充满个人情感的分析占据了民族志的主流地位。格尔兹并不是一昧地反对客观与科学,他只是试图用带有文学性的民族志来反对人类学出现的唯科学主义的偏见。科学民族志更为关注的是文本形成之前是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做田野调查的,而阐释民族志则开始关注现实对象转化为认识对象的问题,关注文本的创作形式。格尔兹通过文学性描写将人文关怀重新引入到民族志文本中,不失为对科学民族志剔除人性研究的一种补充与完善。
(四)实验民族志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汹涌来袭,对语言表述的既有结构产生冲击,引发所谓的“表述危机”,在此背景下,实验民族志开始兴起。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其实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对表述文化进行了抨击,提出要对文化进行解释,动摇了功能主义在民族志中的稳固地位。而实验民族志则进一步认为,文化是建构的,人类学旨在对话。每个人都有其各自的理解的意义,民族志过程就是一种意义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民族志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之间的互动。
后现代人类学对传统民族志的批评在于,“没有给予作者一定的角色,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在注脚和前言中提到作者,给他一点无足轻重的发言机会。”[5]68实验民族志中,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经历被加入,把对对象的研究也作为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文本的文学性创作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人类学家需要在描述基础上进一步对文化进行阐释,这一系列转换对民族志的真实性也提出了更高挑战。将民族志作者的内心表现出来成为民族志真实性的一部分,真实地记录不同主体反思的声音,一改人类学家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互动中。同时,民族志作者不再以一个权威者的形象来阐释文化,而要留给读者更多空间,引发读者的共同思考。实验民族志旨在向人们说明,应当关注人类学所能达到的有限性真实,科学民族志所标榜的那种完全客观真实是不可能的,民族志只能是部分的真实。
总的来说,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实验民族志不再追求对文化的全面描述,也不再幻想民族志的完全客观性,而转向消除人类学研究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绝对界限,将文化作为一种主体的创造。1984年,人类学学者克利福德(Cliffod)和马库斯(George Marcus)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召开了一次关于民族志文本打造的研讨会。1986年,克利福德和马库斯合编并出版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一书,被视为是“反思人类学”或者是“后现代人类学”形成的标志,主张将民族志作为一种文学文本加以批评分析。《写文化》也没有提供一种可供所有人类学家参考的范式类型,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作者带有主观意识的行为,追求对多元思想的包容开放,以平等姿态展开多元对话。
二、民族志与人类学
民族志在一开始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早期的人类学也并不需要民族志。当人类学家开始反思民族志对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意义并试图对民族志进行变革时,人类学与民族志便开始共同走向科学化。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推动民族志走向科学,同时民族志的科学化发展也将反过来促进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充实其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6]。
在业余民族志时期,民族志作品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大多是一些丰衣足食而又无所事事的人周游列国所记录下的材料,带有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色彩。同时,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还只是“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他们还没有产生走进田野的意识,往往基于他人资料的整理来创作作品。可见,在业余民族志时期,人类学和民族志还处于并行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族志与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相去甚远,更多体现的是民族志作为一种写文化的文本的功能,并未形成专业系统的研究方法。
1874年,当爱德华·泰勒察觉到现有民族志存在种种缺陷后,参与编撰了《人类学笔记和问询》,试图为业余民族志者提供编写民族志的规范大纲,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类学家能够有高质量的引用资料。《人类学笔记和问询》的出版被看作是人类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人类学家开始介入到民族志的发展中,对民族志进行指导。这可以看作是人类学与民族志开始融合的一个起点,人类学家意识到民族志对人类学的重要意义,并逐渐将民族志奠定为人类学的一个基础性研究方法。此后,《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不断得以修改,指導人类学家对原始人进行观察,为人类学研究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资料。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日记中也曾提道:我写日记,一边看《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一边试着综合我得到的资料……又读了几页《人类学笔记和问询》[7]30。日记中的短短几句话就两次提及《人类学笔记和问询》,这本手册的作用与重要性可见一斑,也正是在这本手册的系统性指导下,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出版,将民族志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民族志由此拉开序幕。科学民族志时期,人类学与民族志结合起来,人类学家为民族志发展出一套科学的调查方法,民族志自身也成为一套包括田野调查在内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对于民族志还是人类学,这都是一场意义非凡的革命。科学民族志扭转了将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和民族志写作三者相分离的局面,将科学性作为评判民族志的重要准则,并将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带入到民族志研究方法中。此后的人类学家也沿袭了这种民族志研究方法继续研究非西方的部落社会,拓展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推动了民族志的不断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超然的人类学客观性只是一个神话,在人类学反思精神的影响下,阐释民族志开始发展,人类学家对民族志提出了新的要求。马林诺夫斯基不断强调“科学性”和“价值无涉”,而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格尔兹却恰恰相反,他更为强调的是“文学性”与“风格流派”。格尔兹认为,民族志作者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读者相信他们所描述出来的东西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东西,他们的确去过那个地方,他们的报告都是真实的、可信的,读者阅读之后也会身临其境,和作者拥有同样的感受。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民族志者在书写过程中就会采取一些策略,使作品带有作者个人的风格。其实,影响民族志者写作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最重要的田野经验之外,还包括作者的生活背景、世界观、价值观等。如此一来,民族志作品有向小说发展的趋势,与马林诺夫斯基之前所极力强调的“科学性”渐行渐远。虽然受不同思想流派的影响,格尔兹仍然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将民族志承袭下来,两者都极力维护民族志在人类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又进一步对民族志进行反思和质疑,进入了实验民族志时期。
民族志由一个时期跨入另一个时期,总是离不开人类学家的推波助澜,人类学家对民族志的影响使得民族志深深嵌入到人类学学科中,直至当今,提起民族志总会将其与人类学联想在一起。人类学研究离不开田野工作,更离不开民族志,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必经之路,而民族志则将田野工作的成果集中展现出来,是人类学研究的结晶。不可否认,民族志对人类学的重要意义,也不可否认人类学对民族志的重要影响。但这些都不意味着,民族志就理所应当专属于人类学,这对民族志和人类学的发展都是没有好处的。
三、新政治人类学视域下的民族志
(一)新政治人类学
新政治人类学是在传统政治人类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实现了三大突破。首先是时间上的突破,是指新政治人类学在时间上突破了传统政治人类学以1940年作为起源的界限。传统政治人类学以人类学开始走向政治领域作为其起源,而政治存在的时间却远远早于人类存在的时间,因为政治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美国学者弗朗斯·德瓦尔(Fransde Waal)通过对动物园中的黑猩猩群落进行多年的跟踪观察,总结道,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8]257。在黑猩猩群落中就已经有权力的存在,猩猩对权力的追求远远早于人类社会。因而,新政治人类学提出人类学研究权力并不以研究土著人权力为时间界限,只要研究权力都属于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新政治人类学的时间界限要推向权力存在的时间点,远早于人类社会。其次是空间突破,指新政治人类学在研究空间上的无限扩大。传统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拘泥于非国家、非制度、非体制的政治现象,主要研究的是早期社会中非正式权力的影响,讨论国家范围以外的政治,着眼于初级社会和边缘地区,对政治过程展开分析的基础上比较各种文化语境中的制度体系。而新政治人类学则不再将研究对象局限于此,扩展到对国家政治体系的研究,扩展到一切对人类行为有控制能力的因素上。最后是学科突破,是指新政治人类学在学科上实现了更多学科的交叉互融。传统的政治人类学者倾向于从人类学或者是政治学的视角界定政治人类学这一学科,新政治人类学则指出,新政治人类学不是政治学与人类学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两个学科共同建立,并在此过程中汲取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来丰富自身发展。
(二)越出人类学禁锢的民族志
自从民族志与人类学结合起来后,普遍认为,民族志研究是人类学界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这一点毋庸置疑。格尔兹曾经这样描述民族志在人类学中的位置:“如果你想理解一门学科是什么,你首先应该观察的,不是这门学科的理论和发现,当然更不是它的辩护士说了些什么,你应该观察这门学科的实践者们在做些什么。在人类学或至少社会人类学领域内,实践者们所做的,就是民族志。”[9]6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及成果呈现方式,民族志在人类学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研究人类学不能离开对民族志的认识,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新政治人类学视阈下对民族志的重新考察,则挖掘出新的运用价值,即,民族志越出“人类学”的禁锢,也可以运用在管理学与政治学等学科中。在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本主义范式一直贯穿其中,科学主义的核心是如何提高工作的效率。人本主义强调将人置于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不再将人视为经济人,而将其視为处于社会中生活的人来考虑。人本主义与新政治人类学提倡的管理学人性化不谋而合,良好的组织应该关注人的发展,激发成员的创造力会给组织带来意想不到的高效。从管理学角度考察民族志,发现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恰恰迎合了管理学人性化的需要,研究者通过亲身经历被研究者的生活环境,站在被研究者的角度体验组织的管理,能够提出更有利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利益的管理模式。民族志的相关研究方法在著名的霍桑实验中也有所体现,梅奥等学者将霍桑工厂作为“田野”,对工人进行了半参与观察,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为霍桑工厂提高效益提供了思路,并最终促进行为科学的诞生。此外,民族志在政治学历史上也发挥过作用,以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例,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期间,恩格斯根据自己在英国居住期间的直接观察和各种材料而写成这篇巨著,全面而系统地对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考察,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指出物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这篇报告带有典型的学科内容与规范,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帕特森称之为首篇城市民族志。”[10]因而,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民族志来分析有其基础与依据。恩格斯的研究对象是英伦三岛的工人,他与工人进行了许多直接交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写作风格上是自然流露,总体上偏向科学民族志,又避免了以调查员的话语为权威的风格,它带有一些实验民族志的味道,不避免暴露作者的个人感受,同样也避免了实验民族志近乎牵强地彰显个人感受,为暴露而暴露的做法”[10]。《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采用了民族志的调查及其写作方法,满足了民族志的诸多要素,作为民族志文本来考察,这本伟大巨著结合了科学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的特点,并将两者进行了很好的融合。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一个典例可见,人类学同样可以对国家制度进行考察,民族志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运用,弥补了政治学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无论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历史上的运用,都证明民族志已然越出了人类学的禁锢,在众多学科中发挥着影响。
不可否认,人类学与民族志的结合促进了民族志向着专业化发展。同时,也要看到这一结合的弊端,从科学民族志时期至今,民族志都被禁锢在人类学中,虽然在诸如管理学、政治学有所应用,也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使得民族志与其他学科之间建立起坚固的壁垒,不利于民族志的跨学科发展。新政治人类学带着重新审视民族志与人类学关系的视角,试图客观看待民族志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将民族志视为一整套严谨的田野研究方法,从人类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打破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使其在所有学科中都能发挥作用,搭起学科交流的桥梁并丰富自身发展。
(三)创新实证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规范研究主要是指研究对象的应然状态,即关注研究对象应当是什么,而实证研究则关注研究对象是什么,一种实然状态。实证主义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于1830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标志着实证主义思想的正式形成。实证研究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新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离不开对实证研究的应用,民族志的田野研究方法就是实证研究的典例,其实,除了人类学以外,其他学科的实证研究方法也有自己的社会调查与实证研究,但与人类学相比,它们的实证研究缺乏专业的民族志训练,因此,利用人类学民族志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对其加以改造和重塑,能够促进这些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人类学与诸多学科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新政治人类学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田野工作是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方面,对其他学科展开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田野工作的优越性在于,调查者在与被调查者相处的过程中对其和所处的周围环境进行调查,观察他们在真实世界引导和现实条件约束下的所有行为,这种做法是偏向于自然主义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某一具体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发生,不受外力影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避免了受实验室条件约束或受某种外力干扰下的人工反应。田野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的田野调查,这一过程要求调查者深入实地,在当地工作和生活6个月甚至6个月以上。调查者长期与被研究群体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活动,将自己当作是该社会群体中的一名成员,在感情和生活上与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观察和感受他们的生活,获得真实的一手资料,更好更全面地了解该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不过,研究者在参与被研究群体的生活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持专业距离以便适度地观察和记录资料。这种长时间的参与式调查可以使调查者融入该地的社会生活之中,与当地人一样,对所生活的环境充满关心,对未来的生活抱有一种希望,对当地的文化、价值观念持有一种信仰,从而形成对研究对象文化的深入剖析。田野工作的第二方面表现为研究者的主观认识,这些认识包括田野研究者在特定的田野环境生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看法和感受、所做出的行为、以及适应环境的过程等内容,也包括田野研究者为了更好地做调查所必要的角色转换以及角色重塑,此外,还包括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也正是实验民族志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在文本中体现研究者本人反思的痕迹。
田野工作是民族志的特色所在,新政治人类学要求将这一要素有机地与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相互融合,形成民族志写文化的共同体,将互为他者、民主多元以及协商一致的理念带入诸多学科的研究过程中,促进学科交流,共同创新实证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美]盧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M].王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6.
[2][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105.
[3]高丙中.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J].思想战线,2005(1):75-81.
[4][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
[5][美]乔治·马尔库斯,[美]米开尔·曼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8.
[6]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3):58-63.
[7]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7:30.
[8][美]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M].赵芊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报社,2009:257.
[9][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6.
[10]何国强,李亚锋.人类情怀和阶级使命的又一结晶——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调查思想[J].思想战线,2013(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