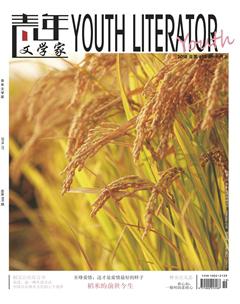神女应无恙
邹贤中
一
小时候,我比较爱哭,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伸出右手的食指,放在嘴边,轻轻地“嘘”一声,然后看了看四周,见没人,才说:“别哭了,否则阿玲就不喜欢你了!”母亲的表情是凝重的,是严肃的,好像阿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或者说是跺一下脚大地都得震三下的超级重要的人。看到母亲如此严肃,我连忙噤声,慌忙地去看四周,好像阿玲已经站在我的面前。好像她不喜欢我,我会丢失什么重要东西似的。说来也怪,阿玲是什么人?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就这么在乎她是否喜欢我呢?
说得多了,我就有了忍不住的好奇,问母亲:“阿玲是谁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母亲说完,又叹息一声:“可惜阿玲比你大六岁,要是大个两三岁就好了。”母亲的语调里有着无法弥补的遗憾,我不知道母亲在遗憾什么。阿玲是谁?她比我大与我又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绕来绕去,解不清,那就算了吧。
那天刚好是周六,一大早,我们吃罢早饭,母亲叫住了正打算出门玩耍的我:“别出去了,明天是你外婆生日,我们今天就得过去帮忙。”我早就想去外婆家了,只是苦于已经上学,平时没什么时间去。到了周六日,做不完的作业、干不完的农活加上适当的时候,还要和本村的狐朋狗友们混一下。“狐朋狗友”这个词和我的第一次见面,是源自父亲之口。那天,我们玩得太疯,父亲爆了粗口,你不要和他们玩,那都是狐朋狗友,会带坏你的。综合以上三点原因,我上学之后就没去过外婆家了。显然,去外婆家比和狐朋狗友厮混更具有诱惑力,我明显地站住了。就在我高兴的当儿,母亲再次给我送来了一个重磅消息:“今天,你可以见到阿玲了。”
喜讯来得如此之快,平时在外惹是生非的我竟有点忐忑不安起来,就像新媳妇即将见公婆一样害臊了,在母亲的督促下,我换好了衣服,一起去了外婆家。
酒席一直是湘南地区的一大特色,过生日、老人辞世、结婚、生娃、高考……这一切都离不开酒席。再后来,酒席之风愈演愈烈,入党、当兵、加薪、升官、乔迁都要做酒,实在没有酒席可做了,也要找酒席来做,比如:高兴。今年天年好,五谷丰登,值得做酒;成绩一般的儿子考了满分,人高兴,也值得做酒……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们这些孩子们喜欢做酒,毕竟可以吃得满嘴流油;大人们却愁死了,吃酒席得上礼。而且别人请你喝酒,你还不能推辞,否则那是看不起人家,是大不敬!好吧,既然这么多人都做酒,我也掏出了不少钱,那我也来做酒吧,怎么也得捞回点本钱吧?不想做酒,却必须做酒,所以,父老乡亲们除了在田里地里刨食,就是在做酒或者准备做酒的路上。
我们到外婆家的时候,还没有来客人。客人要晚上才来的,目前到来的就是母亲的几个姐妹以及她们的孩子们。她们和母亲一样,都是来帮忙的。做酒是一件热闹、隆重的事情。既然涉及到了隆重,肯定就少不了麻烦。你看电视上的走秀、颁奖、会议、拍卖、商业活动,隆重吧?可是你知道有多麻烦吗?有多少幕后人员在忙这一切吗?撰写文案的、布置场地的、购买物资的、端茶倒水的、打扫卫生的……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忙活。越是隆重、越是光鲜、幕后的付出就越多。农村做酒也不例外,需要提前买菜,虽然说大部分青菜是自家的,但是荤菜得出去买,各种配料得出去买;得洗碗筷、准备桌椅板凳并洗干净,很多时候桌椅板凳是不够的,需要把本村的桌子全部借来;还要洗菜、配菜……有女儿的人家是幸运的,每次做酒席,女儿们可以来帮忙。
我和大娘、阿姨的小孩子们有了伴儿,如脱缰的小马驹四处撒野。等我们回來的时候,母亲的身旁却多了一个女孩儿,十一二岁的样子。她穿着较为朴素,下身是一条当时非常流行的健美裤,黑色的。健美裤有弹性,把她细长的小腿绷得紧紧的,如天鹅的腿一样,细长细长的;上面是一件格尼格子衣服,在右肩处,还有一块补丁。农村人常年劳动,而右肩是绝大部分人承担重物的部位,干体力活的人都知道,那地方衣服是最容易坏的了。那块补丁与衣服如犬牙般严丝合缝,不仔细看,几乎是看不出来的,足见缝补者的手上功夫了。她留着齐肩的头发,不长不短,恰到好处;胸部隐约藏着两坨什么,好像两只振翅欲飞的白鸽,我不好意思再看。只好将目光上移,那是一张好看的脸,白净,五官恰到好处地分布在脸上,很耐看,有一种天然的质朴之美。
“这就是阿玲。”母亲打断了我的思路,“快过来叫阿玲姐。”
原来,这就是母亲一直以来吓唬我的人。我原以为她是一个五大三粗、凶神恶煞的人呢,却没想到她这么美。我甜甜地叫了一声阿玲姐。她高兴地应了,招招手,叫我过去坐。她的声音是那么地好听,脆脆地,如珠落玉盘,又如黄莺出谷。
她们正在洗菜,都是晚上要招待客人的。根据舅舅的推算,外婆的大寿会有三十桌的客人。三十桌是什么概念呢?桌是四方桌,一桌八人,这就是两百四十人了。我们把吃酒席叫“吃十个碗”,也就是说,一桌需要十个菜,如此一来起码需要三百个碗。不是精致的碟子盛菜,而是大海碗,这一切才显示出主人的豪迈来,显示出后辈的雄厚财力来。所以,不提前半天准备,根本来不及。
我和小伙伴们搬条小板凳围坐在阿玲姐的四周,看她们干活。她们有的在择菜,有的在切菜,有的在剪辣椒。阿玲姐左手拿着辣椒,右手持着剪刀,麻利地把辣椒剪得细细的一片,她双手翻飞,好看极了。青辣椒和红辣椒交相辉映,让人眼花缭乱。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着天,大娘向母亲打趣:“二妹子,看上阿玲了?可以定去做童养媳嘛……”阿玲的脸上飞上了一抹潮红,母亲讪讪地:“大姐,莫乱说,莫乱说,娃还小着呢。”
她们谈论的这些东西,让我似懂非懂,不由地害羞起来。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去疯的时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健步而来:“阿玲,回家吃饭了。”原来,已经到了午饭的时分。
“她婆,这都到了吃饭的时候了,阿玲还在这里帮了一上午的忙,就在我们这里吃吧。对了,您老也在这里一起吃。”母亲说着,一把拉住准备起身回家的阿玲。
老人走得更近了,一边应承着母亲的话:“晚上再来吃,现在吃,可不像话。”
阿姨说:“她婆,不就是多添双筷子添个碗的事情吗?别说阿玲帮了一上午的忙,就是没帮忙也得吃饭。”
大娘、母亲、阿姨一齐站起来,她们各自把双手在身上的围兜上拍一拍,一起拉着婆婆和阿玲进屋了。“这怎么使得了?我什么都没帮你们做,使不得啊。”阿婆嘴上推辞着,人却跟着母亲进屋了。
中午还没有来客人,就外公外婆、舅舅一家再加上我们,满满地坐了两桌子。大人一桌,我们小孩子一桌。阿玲被强行拉到大人那一桌去了。
席间,我听见母亲说:“她婆啊,阿玲才十二岁,这书还得继续读啊。”
阿婆沉默了一下,说:“有啥子办法呢,我们两把老骨头现在别说赚钱,就是地上有钱捡,也捡不到了。她三个舅舅能力有限,生活压力也大,那几个弟弟读书都困难,自然照顾不到她了……唉,要怪只怪她父母死得早……认命吧。”
这句话是很不合时宜的,场面显得有点尴尬。我别过脑袋望去,阿玲正在扒饭的手停顿了,她的双眼有些痛苦的神色,她凝固的手臂与背影,形成一个忧伤的剪影,让人看着,心里堵得慌。
还是外婆打破了冷场:“她婆,我这女儿不懂事,您别介意。女孩子嘛,有条件就多读书;没条件,就算了。您给她一口饭吃,也是对得起她死去的爹娘了。”
“阿玲这么漂亮,现在男多女少,将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求着要呢,您老家的门槛都会被踏破的。那时候,您就享福啦。”大娘笑着对阿玲的阿婆说。
场面瞬间就热闹了起来。
事后我才知道,这个阿婆是阿玲的外婆。阿玲的父母去世得早,作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农村,女儿在他们眼里就是赔钱货,谁肯带着这么一个女娃儿呢?阿玲的父亲没有兄弟姐妹,是独苗。所以,父亲那边的亲戚自然是无法收养她了。剩下的只能让母亲这边的亲戚来收养了,然而,阿玲的几个舅舅却是推三阻四,有的说自己已经三个孩子了,实在没能力了;有的说,自己虽然目前就一个孩子,但是未来怎么说还得再生一个;一个说,我身体不好,自己家庭忒困难了,哪里能养活她?
阿玲成了众人都不肯接手的烫手山芋。两个老人家破口大骂,你们这群没良心的,这可是你们姐妹的唯一苗子啊,你们都不管,要啃倒我们两把老骨头吗?骂归骂,三个儿子除了低头不语,却就是没有收养的意思,老人家没辙了,只好自己带着。这一带,就到了读书的年龄,村人纷纷说,老人家没钱就算了,女孩子不读书也没事。老人家挡住别人的闲言闲语,送阿玲去读书;读到三年级之后,老人家实在无力再送,只得去求几个儿子,一年学杂费四百多块钱,你们平均分摊下来,也就是每人一年给一百多块,平均下来一天只出四毛多钱就够了,她的生活费我来解决……三个儿子勉为其难地送阿玲读了一年书,在这一年里,他们更加喜欢使唤阿玲了,帮大舅放了牛,怎么说也得帮二舅喂猪吧?既然老大老二的事情都做了,怎么也得帮三舅割鱼草吧?阿玲忙得陀螺转,三个舅妈还不满意。
一年后,他们没有继续再送的意思,就在外婆准备去继续找三个儿子理论的时候,阿玲选择了放弃,她阻止了阿婆,她不想再上学了。唯一跳出农门的希望被亲手扼杀了。准备地说,是被无形之手扼杀的。就算外婆去求舅舅又有什么用呢?舅舅就一定要承担起她上学的责任吗?法律好像并没有这样规定吧?
阿玲成了家里的一双手,每天跟着外公外婆在地里转,还要承担起帮舅舅看护孩子的责任以及其他临时安排的各种农活,阿玲懂事,外公外婆老了,已经没有能力种田了,就种点地,三个舅舅每人一年给老人家四百斤谷,这只能让自己和外公外婆饿不死。至于生活上的零花钱,就需要自己去赚了,比如摘金银花、摘山苍子,卖花生、大豆,这些都是自己去賺的。既然自己吃的饭是三个舅舅供给的,自己怎么能不帮他们干活呢?
她辍学的那一年,刚好十二岁。
二
此后的日子里,我和阿玲很少见面。毕竟我的事情也挺多的,然而阿玲的身影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多么听话、多么懂事的小姐姐啊。其实,这个词“听话、懂事”是母亲强行给我灌输的,我小小年纪,哪里懂这个呢。在我不听话的时候,母亲就说:“你得学习一下你阿玲姐,你看人家多懂事!”“跟你说,以后找老婆就要找阿玲这样的,肯定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婆媳关系就好相处了。”母亲补充说。
母亲说得太多,我隐约地感觉,阿玲将会成为我未来找媳妇的标准。
我才多大啊?我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一个刚刚上学的孩子,母亲未免太深谋远虑,太高瞻远瞩了。其实,农村这种“高瞻远瞩”的女人多得是,她们跟自己玩得好的朋友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指腹为婚;或者在孩子几岁的时候,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姻定下来。当然,他们还是很正式的,交定金、立字据,甚至请公证人。他们把孩子当成了玩具般的私有财产,丝毫不觉得自己违背了道德和人性。这后来,有的人确实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婚姻,也有幸福的,更多的是不幸。孩子长大了,有的人后来有了更好的对象,就开始反悔,如此一来,双方难免要扯皮。
我八岁那年,又到了外婆过生日的时间,我急切地想去外婆家,想去见见阿玲姐,我很是想念那个漂亮的小姐姐。母亲告诉我,阿玲已经出去打工了。母亲叹口气:“阿玲真懂事,这么小就出去给家里赚钱了。”是啊,阿玲太懂事了,她才十四岁,标准的童工。阿玲是去亲戚的饭店打工的,一个远房亲戚在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高速服务区开了一个小饭店,专门做长途司机的生意。亲戚对阿玲的外公外婆说,孩子在家打鱼草能赚多少钱呢?一年能赚到一千块吗?累死也不行,不如去给我帮忙,洗洗碗筷,上菜什么的,包吃住,我给她两百块钱一个月!两百块钱,外公的眼睛亮了。外婆说,她还小,这不合适吧?
外公打断了老伴,你懂啥。人家说行就行!
阿玲就这样跟着从未见面的亲戚去了遥远的远方。最初的新奇很快就被整天的洗洗刷刷代替了,当然,阿玲是知足的,管吃住,一个月还有两百块钱呢。这是她之前想都不敢想象的。
和阿玲一起做事的还有一个男孩子,比阿玲大两岁,来自贵州一个贫寒家庭。他在厨房帮忙,给厨师们洗菜、配菜,经常受大厨的刁难。由于年龄相仿,再加上相同的经历,两颗心很快就走到了一起。这也是正常的,从小缺少父母之爱的女孩子最容易醉倒在关怀她的男性怀抱里。
在亲戚的店里,还有一些浓妆艳抹的女服务员,她们做事少,主要工作就是和男客人聊天,每次好像聊得很投机,很多时候,还会去房间,悉悉索索地不知道干些什么。出来的时候,女服务员的脸上一片潮红,男人的脸上尽是满足的神色。
我再次见到阿玲的时候,她已经十五岁了,那是在她的婚礼上。和她结婚的是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男人是我隔壁村庄的,我曾经见过。男人的脸上写满了自豪,阿玲的美貌足以让任何一个拥有她的男人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男人的眼睛里发出狡黠而亮堂的光。那天,阿玲姐穿着洁白的婚纱、高跟鞋和高挽的发髻衬托出她出尘的高雅。略施粉黛的脸上有一点潮红,却掩饰不住苍白的痕迹。她身材高挑,鹤立鸡群般将一干乡下女人都压了下去。
这分明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还没完全盛开就被别人摘走了,我心里有着一阵莫名地难受,好像自己的稀世珍宝被别人抢走了。
一个周日,我在院子里做作业。母亲在和邻居婶子一边打毛线,一边在聊天。婶子感慨着:“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咋就嫁给了强呢。”
母亲接过话茬:“强这人,不行,好吃懒做,家里还有一个厉害的婆婆,阿玲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强就是阿玲姐的男人。
母亲顿了顿,继续说:“有什么办法呢,她就是被那个亲戚所害,所谓带她去打工,帮助她,其实就是看上了阿玲已经含苞欲放的身体。”母亲压低了声音,好像和邻居婶婶在密谋。不过我还是听得一清二楚。虽然对这些事情不太懂,但是结合联想,我还是隐约地得出了事情的大致轮廓。
原来,阿玲在南方打工的时候,虽然和那个男孩子有了感情,但是仅仅是限于心灵上的彼此取暖,一旦涉及到了将身子给对方,她是万万不干的。当然,后来她很后悔这个决定。
那天,来了一拨客人,其中一个领头的男人看到正在上菜的阿玲,不禁感慨不已,我走南闯北那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你看,她纤细的双腿,走路夹得紧紧的,想必还没开苞。
男人的话引来其他人的浪笑:“哥,看上了?那就把老板叫过来,开个价。”
远房亲戚过来了,凑近领头的耳朵,说:“她还是一个雏儿呢,性子烈,没有这个数儿,绝不可能。”说着,伸出了一个指头。
领头问:“一千?成交!”
“在后面加个零,一万!”
“你打劫啊?你这里服务员,最多也就五百,她凭啥要一万?”领头很不服气。
“那些五百的,身子都不知道被多少男人上过了。这个还不到十五岁,开苞还可以带来好运呢。”远房亲戚神秘地一笑:“她现在正在谈男朋友,你下手可要快,要是被那个穷小子吃了头槽食,可就后悔莫及了。”
领头的心思被拨弄得痒痒的:“五千,一口价!”
阿玲的第一次就这样被亲戚在谈笑之中出卖了。
亲戚叫阿玲陪领头喝酒。阿玲不喝酒,领头很是善解人意,“不喝酒没事,可以喝饮料代替嘛。”亲戚的店里很多饮料,阿玲第一天到的时候,亲戚给她喝过一瓶,后来再也没有喝过。阿玲喜欢那甜甜的味道。她就喝了饮料,喝完没多久,她就感到头晕,远房亲戚把她扶到了房间休息,她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等她醒来,发现下体火辣辣的疼,已经晚了。
婶婶说:“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这亲戚禽兽不如!对,咋不去告她呢?”
“告啥?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懂法律,也不知道法院的门往哪开。再说了,自古以来,衙门就是有理无钱莫进来。”母亲的话里是极度的愤慨!
“好白菜都被猪拱了!其实那贵州男娃子还真不错,阿玲的身子都没了,他没有嫌弃,还千里迢迢地追到了这里。”婶婶有点羡慕地说。
“这还不怪阿玲那几个舅舅,说什么贵州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嫁过去也会受苦。人家阿玲愿意跟着贵州仔走,可是他几个舅舅硬是喊打喊杀地把人家赶走了。妈的,还不是怕捞不到钱!嫁在近处,聘礼可不少,那些没有管过她死活的舅舅却在这事情上打了主意。”母亲愤愤不平。
三
再次见到阿玲的时候,我十岁,她十六岁。那天,她抱着孩子来到了我家。我为她感到震惊,十六岁,很多人才刚初中毕业,或者读高一,她都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印象中,阿玲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记得一年前,她虽然没钱,穿着朴素,但是打扮得干干净净、漂亮极了,好像电影里面的明星。现在,她的身上被孩子尿得花花绿绿,尿渍印泛着盐花儿,衣服上,喂孩子掉的飯粒儿干巴巴的粘着,一层又一层,就像开了酱油铺子。孩子突然闹腾起来了,想必是饿了。阿玲当着众人的面掀开了衣服开始奶孩子,粉嫩的半截身子就这样露出外面,暴露在众人的眼帘里,她丝毫没有做姑娘时的那份羞涩;记得四年前刚认识她的时候,一句话玩笑话都会让阿玲脸色绯红。她的头发也不再是油光水滑,而是胡乱地披散着;曾经洁白的脸上也不再保养得清秀红晕,而是胡乱涂抹了两块钱一瓶的雪花膏,乱糟糟的。如此模样,她居然还怡然自得地可以出来见人。
阿玲对我母亲说:“婶,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母亲劝她:“不管怎么说,日子还不都得过。”
阿玲犹豫了半响,说:“这日子还怎么过?人家结婚了,都是媳妇当家,婆婆做甩手掌柜。我们家却完全相反,我一分钱的家都当不了,连每月买卫生巾的钱都需要问她要。”
我问:“买卫生巾干嘛?”
“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母亲白了我一眼。
我低着头,努着嘴,很不服气。就在这时,吃着奶的孩子又哭了起来。阿玲的脸上升起了厌恶之色:“都是你这个讨债鬼,你害死我了!”她把生活的不顺一股脑发泄在孩子身上。
母亲继续劝慰她:“孩子还小,哪里懂做母亲的苦。”
阿玲哭了,母子同时放声大哭。
哭声让我的心为了一颤。该有多大的委屈,才能发出这样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一个大男人,就不为你想想吗?”母亲问。
“他嫌我脏。”阿玲的声音细如蚊呐。
“也不看看他自己是什么货色,凭他那好吃懒做的样子,就不该娶妻生子。既然娶了,就不要嫌弃。”
“婶,别说了。”
阿玲回去的时候,母亲给她送了一袋鸡蛋。阿玲不要。母亲生气了:“她死小器,连自家的鸡蛋都不给你吃,还要拿去卖钱。你现在还在奶孩子,身体要紧。”那个“她”,显然是阿玲的婆婆。
“我带回去也会被她拿走,我也吃不到,我真的不要了。”阿玲的话才出口,母亲的脸煞白煞白:“她狠毒到了这个地步?这可不是她的啊。”
“哪有媳妇作践自家婆婆的呢?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肯定不会乱说的。外婆瞒着几个舅舅给我带来的那些鸡蛋,我是一个都没吃到。”阿玲泪又流了下来。
“可怜的孩子,你从小没妈,要是不嫌弃,就把我当妈吧,每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做。”
“真的不用了。我在外面跑,她会骂我的,说我不干家务,好吃懒做。我得走了。”阿玲挡开了母亲的鸡蛋,背影越走越远。
邻居婶婶探出头来,“唉,这么小,就这么遭罪了。她那婆婆还很年轻,这罪不知道要遭到什么时候去了。”显然,母亲和阿玲的话她都听在耳朵里。
“女人的身子很重要啊,一旦丢了,就不值钱了。”母亲感慨着。
“切,那可不一定,还不是她那几个舅舅害的?如果她跟了那个贵州仔,没准现在过着幸福日子呢。贵州仔可没嫌弃她失去的身子。”婶婶反驳道。
两个女人就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
四
我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外出打工,这是我们那里绝大部分孩子的出路。打工潮已然兴起,在家种田已经没了盼头。去读高中的没几个,能够进入大学的就更少了。反正读了大学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还不如早几年去打工挣钱。这是大家普遍的思想。
我要去打工的事情被阿玲知道了,她特地来到了我家里:“听姐的,打工没出息的,好好去读书吧,那是你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子。”她说的情深意切,这时候的阿玲,一副严重营养不良的样子,脸上也看不到什么肉了。她都这样了,还关心着我。我的眼角湿润了,但还是去了远方。
打工生活的苦楚,我不想过多地言说。一年后,我回到了离别已久的故乡。故乡在我面前已然生疏了,才一年的光景,我和故鄉已经格格不入。那栉风沐雨、历尽沧桑的大树还在,然而树上的鸟窝却没了;那当年滋润一村庄人的深井,此时已经干枯,如大地望向苍穹的一只没有眼泪的盲目;而瓷砖、茶几、沙发、冰箱……这些城里的物事已经成为生活不可阻挡的激流进入了农村,包括城里的思想,性解放、嫖娼、六合彩、赌博、白粉、拐卖儿童……古老的农耕文化已然消亡。这一切,让我惊慌失措。
我魂牵梦萦的田园牧歌的故乡已经彻底消失,让我恨不得马上逃离。
我回来的那天,阿玲也来了。那年我十七岁,阿玲刚好二十三岁。这是一般人刚刚大学毕业的年龄,是朝阳刚刚升起的年龄,是最具朝气蓬勃的年龄。阿玲却已经枯萎了,她骨瘦如柴。她拉着孩子的手,孩子的脸上如猫抓过似的,纵横交错,脏兮兮地,人怯怯地站在阿玲的后面。阿玲手里提着一个布包,抖抖索索了很久,从布包里拿出一袋子鸡蛋来。“婶婶,这是给贤中的,他现在正处于长身子的时候,这土鸡蛋很不错。”
母亲坚决不要:“你哪来的钱买鸡蛋?”听得出来,母亲没有责怪,而是关心。
“婶婶,这是我偷偷藏的。每次母鸡生蛋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藏一个。家里鸡多,她发现不了的。”
我记得,阿玲说过,家里她连一分钱的家都当不了。这一袋子鸡蛋怎么也有三十多个吧?也就是说,阿玲起码收集了一个多月,才攒齐了这些鸡蛋。这哪是鸡蛋啊,分明是沉甸甸的爱,也是不可言说的血泪。我的心为了一痛。
母亲紧紧地抓着阿玲的手:“这些鸡蛋我是万万不能要的。你给孩子吃吧。”
阿玲也握紧了母亲的手,许多话都在不言中。
吃完午饭,母亲让我帮忙带一下阿玲的孩子,小孩子刚开始比较害羞,跟我混了一会儿,也就熟稔了,带着并不吃力。母亲和阿玲在隔壁房间叙话。
“婶婶,我就是吃了没有妈的亏,要是当年一狠心跟小平走就好了。”小平是那个贵州仔。“那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回忆的伏流在她的心头闪过,滋润着那颗已经干枯的心。
“年轻的时候,谁能看得到这么远呢?那时候,也没人为你做主,你几个舅舅喊打喊杀,刘家和媒婆又连哄带骗,把你推进了刘家这个火坑。”母亲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我真后悔,为什么要把这身子留着呢?我要是早给小平,什么事都没有了。”阿玲又哭了。
“叔叔,妈妈又哭了。”阿玲姐的孩子仰着头,对我说。
“妈妈经常哭吗?”
“嗯。”
“走,叔叔带你去玩。”我带着孩子出了房间。
远远地,我还听见母亲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晒老母。我当年要是把你留下就好了。”
“婶,这使不得,我比他贤中大那么大,何况,我的身子脏了。”阿玲有点忸怩。
我走出槽门院子,外面是延绵的群山,这巍峨的群山啊,你们阻断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局限在这小小的一城一池之得失上。那条唯一通向山外的路,比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还要拥堵,又有几个人可以走出去呢?我为阿玲的命运感到深深地悲哀。一年的打工生活,也让我对自己的模糊的未来产生了莫名的担忧。
“叔叔,你在想什么呢?”
我说:“我想拥有一双翅膀。”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和阿玲叙话已毕。阿玲带着孩子回去了。我责怪母亲:“您怎么没有打发阿玲任何东西呢?”
“打发她东西是没有用的,她根本拿不到。没准回去还要吵架,她婆婆肯定怀疑她偷了家里的东西给我,否则我怎么会打发她东西?”母亲说:“你放心,我硬塞了两百块钱给她,她真不容易,一分钱都没有啊。买卫生巾都得问老公要钱。”
“她老公真是个废物,他是要跟他娘过一辈子还是跟阿玲姐过一辈子?”我很是生氣。
“天下总会有一些无能的男人。唉,她婆婆太厉害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话,说不清呢。”
五
我又去了广东。大概半年的光景吧,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阿玲疯了。
我心头一颤:“怎么疯的?”
母亲支支吾吾,却不说清楚。
这个当年高傲得如女神的女子怎么就疯了呢?我心烦意乱。这才半年的时间,上次见到她的时候,虽然她脸上苍白得毫无血色,但是头脑还是清醒的,怎么就疯了呢?我连忙给故乡其他人打了电话,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阿玲和同村早年一个垂涎她美色已久的男人睡到了一起,并且被她婆婆发现了。这下可是炸了马蜂窝。婆婆疯狂地打她,那个好吃懒做的男人更加嫌弃她了,叫她滚。他们还闹到了阿玲的外公外婆家和舅舅家里。外公外婆老了,没脸见人,闭门不出。几个舅舅推卸责任,她是死是活,与我们没关系。
渐渐地,大家发现阿玲的神经不太正常了。她开始在村庄里晃荡:“我是不肯的啊,我是被迫的啊。”说着说着,她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眉开眼笑,“阿玲,要不我们也跟你睡一觉?”女人们却不宽恕她,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贱货,我怎么没见有人强奸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十五岁就被人强奸了,还有脸说。”有些老女人没有在村里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她讲当年被强奸的悲惨经历。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才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
阿玲絮絮叨叨地神经质地在外面说,婆婆和男人嫌她把脸面都丢尽了。
但没过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没有人陪她流眼泪了,后来全村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是不同意的,我是被迫的。”她们说。
“阿玲,你又来了。”大家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不是被强迫的吗?后来怎么就依了呢?”
“我喝了饮料,晕过去了。”阿玲说。
“我是说你和本村人睡觉的事情。”大家帮他纠正。“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才行,不然人家怎么进得去!”
“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死死地压着我。他用双手抓住我的双手,双腿压住我的双腿,然后就进去了。”阿玲比划着。
阿玲神经质地和大家辩解着,却越描越黑。然而,她乐此不疲。却不知道,大家听着笑话,都在隔岸观火。
那次,我在看书,当读到“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这句话时,眼前又闪动着阿玲当姑娘时的情景:她处子苗条的身材,走起路来如春风摆柳,婷婷袅袅,脚步轻盈;她的嗓音美妙甘甜,听着如饮甘甜;她的微笑灿烂纯真,令人陶醉;那双杏眼好像会说话,光泽明亮,如一弯新月,一泓秋水。我不禁感慨,神女真的会无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