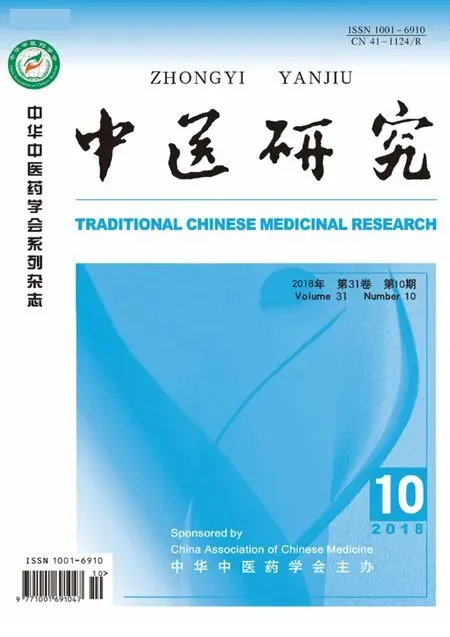基于语料库的《黄帝内经》中“阴”“阳”的认知隐喻构建及意义映射*
邝计嘉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17)
“阴”“阳”这两个字,具有极强的中国文化特征和鲜明的中国特色,阴阳学说是古代先民对日常生活、生产经验的概括,体现了古代思想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勇气,并且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特征[1]。《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中医学系统理论集,奠定了中医学的模式和发展方向,其中有关“阴阳学说”的内容非常丰富。认知语言学强调人类体验对概念系统的决定作用,而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也以古人对自然环境的体验为理论背景,这两者的契合使认知语言学与中医学的结合成为可能[2]。笔者从认知语言学学的角度,采用语料库驱动的方法,以《黄帝内经》为蓝本,分析“阴”“阳”在中医学里主要的意义建构,并分析其阐释人体规律、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的认知理据[3]。
1 认知语言学与中医学的契合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概念及语言系统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并得到理解的,认知和意义都是基于体验的。人们通过对身体以及社会功能、关系、活动等一系列的体验,从而与外部的客观世界相互发生作用。隐喻是人们用一个事物来理解另一个抽象事物的认识世界的重要的认知方式,植根于语言和思维,植根于人类思想中的概念结构,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重要基础,也植根于文化,其核心内容是“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在“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 这一认知背景下,《周易·系辞下》所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成了古人认识世界与自身的重要手段与方法。“取象比类”是中医学用以认识疾病、阐释医理的重要思维方式,在其影响下,中医学语言呈隐喻性[4]。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中医学语言,丰富了中医研究的角度,也使中医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
2 阴阳的起源及语料库统计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里的一对范畴,最初涵义是具象的。春秋时期的《诗经·大雅·公刘》一书中提到:“既景既冈,相其阴阳。”就是阴阳二字的本义,指的是日光的向和背,即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察今》一书中则提到,“侌”字意为“正在旋转团聚的雾气”。“昜”意为“发散气体”“阴阳”的意义已经扩大,用以表明物质世界的本质—运动中的气体。后来意义进一步扩大,引申为气候的寒暑,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状态的躁动与宁静等。先秦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阴阳已由日常观念提升到一个理性水平,以《老子》第四十二章中的“万物伏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为开端,形成了具有哲学意味的抽象概念,也标志着阴阳学说初步形成[5]。古代医家将阴阳概念引入医学领域,使其成为中医学理论运用中最重要与最基础的哲学概念,并以此概念为基础,在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中医学思维模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内经》中描述道,阴阳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
运用Antconc软件对自建的《内经》语料库进行检索,结果见表1“阴”“阳”和“阴阳”在《内经》中的词频与标准化词频。见表1。

表1 “阴”“阳”和“阴阳”在《黄帝内经》中的词频与标准化词频
由表1可见,阴阳的词频数都比较高,阳的标准化词频略高于阴的标准化词频,这也从量化数据的角度佐证了二者的重要和基础地位。因此,研究二者在《内经》中的隐喻建构原理,意义如何从日光的向背扩大到“阳”为所有将人体具有推动、温煦、喜悦等作用的物质和功能,以及“阴”为具有凝聚、滋润、抑制作用的物质和功能,对于丰富中医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3 阴阳的隐喻认知过程
美国语言学家莱科夫(Lakoff) 和约翰逊(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提出“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理论[7]。中医学中关于阴阳的概念和理论首先是一个从“自然之阴阳”的“始源域”向“人体之阴阳”的“目标域”思维映射的隐喻认知过程。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中所云:“人生有形,不离阴阳。”
3.1 阴阳与方位隐喻
借助方位隐喻(也叫空间隐喻)来理解其他概念,如“时间”“亲属关系”“社会结构”“音乐”和“情感”,是人类语言的一大共性[8]。在阴阳的方位隐喻中,空间概念如“内外、上下”等的空间关系和特征映射到非空间关系和特征上来,并用来理解非空间方位概念[9]。《内经》中存在大量的以阴阳的方位隐喻来认识人体的描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3.1.1 阴阳与内外
阴阳最初的涵义为“日光向背”,运用到一个密闭的容器上,也就是容器外向着日光,容器内背对着日光。因此,可以得出“阴是内,阳是外”的基本隐喻。延伸可以得出:人体内是阴,人体外是阳。《素问·阴阳离合论篇》直接给出界定,“外者为阳,内者为阴”。因此,将此隐喻运用到中医学领域中,将人体视为一个容器,在对人体的这一容器的认识中,就自然将人体内归属为阴,人体外归属为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言:“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运用到人体的经络系统的阴阳属性划分时,阳经行于肢体的外侧面,阴经行于肢体的内侧面。值得注意的是,古典哲学在阴阳的认识上,是“阴阳之中复阴阳”。阴阳既可以标识相互对立的事物或现象,又可以标示同一事物内部对立的两个方面[10]。中医学受此影响,在人体内为阴的情况下,对体内脏腑做进一步的阴阳划分。《灵枢·寿夭刚柔》记载:“是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在内者,五藏为阴,六府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
3.1.2 阴阳与上下
由阴阳“日光向背”的意义得知,阳处更温暖,更靠近日光,阴为相反。在对应“上下”这一相对范畴时,自然就得到了“阴是下,阳是上”(YIN IS DOWN, YANG IS UP)。所以在对应"天地"这一相对范畴时,依据“阴是下,阳是上”的基本隐喻,也就得到了“阴是地,阳是天。”在《素问·阴阳离合论篇》《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灵枢·阴阳系日月》《灵枢·经水》等都反复提到“天为阳,地为阴”的这一基本概念。再进一步对应到中医学对人体的认识,在人体保持站立时,靠上的部分为阳,靠下的部分为天。《内经》中是以“腰”为具体的界限。正如《灵枢·阴阳系日月》和《灵枢·经水》切言:“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足在下则称为阴。有学者提到,在《内经》[11]中,“足”的阴阳配属是矛盾的,因为《灵枢·阴阳系日月》中云:“腰以下为地……地为阴。”足在腰之下则称为阴。但是在《素问·阳明脉解篇》曰:“四支者,诸阳之本也。”认为四肢都属阳。其实并不然,因为阴阳的定位前提是必须把比较的事物纳入同一个范畴[12]。对每一个事物的阴阳认定都需要放在范畴内进行。也就是说,阴阳本身就具有相对性,当四肢和头部放在一个范畴里,就遵循的是“阴是下,阳是上”的基本隐喻进行划分。而对于“四支者,诸阳之本也”,历代医家、后世注家都有不同看法,其范畴和隐喻来源也与前者不同。如其中之一的解说,“身在内,四肢在外,故四肢者阳也”,就是根据上文提到的“阴是内,阳是外”而得出的认识。
3.2 阴阳与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指用一种结构清晰的概念来建构另一种结构模糊的概念,使两种概念相互叠加,从而能够将谈论某一概念各方面特征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个概念[13]。《内经》将人体生命活动的依据归结为阴阳,而阴阳的关系为既对立又统一,故其认为二者保持相对平衡,人体内外才能协调统一,而疾病的发生从根本上说乃阴阳的相对平衡遭到破坏、出现偏胜偏衰的结果[14]。在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时,阴阳这对抽象概念被隐喻为战争双方,也就有“阴阳是战争中对立的力量”。
起源于《内经》的八纲辨证[15]中是临床最基础和适用范围最广的辨证方法。八纲辨证中,阴阳辨证是最为重要的,正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指出:“阴阳为医道之纲领”“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在解释两者的对立关系时,在中医学辩证中,阴证和阳证中的描述就是以两者作为战争双方的两个实体概念来理解。在战争过程中,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如《素问·逆调论篇》中记载:“黄帝问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为之热而烦满者何也?岐伯对曰: 阴气少而阳气胜,故热而烦满也。”其中的“阴气少而阳气胜”描述了“非常热”的“热而烦满”症状的病机要点,从语言认知隐喻的角度,也就是战争双方力量多少悬殊的对比。如阴虚、阳亢都是阴阳渐进式变化的产物,阴阳任何一方的不足,导致制约对方的力量减弱,引起对方的偏盛,即阴虚则阳亢。
值得注意的是,《内经》中对阴阳的描述不仅是将二者分离成两个独立的部分,在描述两者的对立关系的基础上,也描述了两者的统一关系,同时更进一步阐释为“阴阳之中更有阴阳”,正如太极鱼中的两个点。因此在在解释两者的统一关系时,《内经》不仅借助“阴阳是战争中对立的力量”的隐喻,还借助了“阴阳是共同战斗的力量”。在这一隐喻中,阴阳是属于同一方的力量,他们共同战斗的是“邪气”。依据此隐喻,阴阳共同作用,各司其职,产生正气,人体才能正常运转,阴阳是万物生长之本,而疾病发生的原因也就是阴阳不协调-不是作为对立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是不能共同产生作用的一方力量,对抗邪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有文:“阴生阳长,阴杀阳藏。”张介宾的《类经·阴阳类》中对此句的解释为:“阴生阳长,言阳中之阴阳也,阴杀阳藏,言阴中之阴阳也,盖阳不独立,必得阴而后成……阴不自专,必因阳而后行。”阴阳消长是一定限度内的量变过程,阴阳转化则是消长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质变。
4 小 结
阴阳学说在《黄帝内经》中非常重要,不仅有来自语料库的数据支撑,也有历代中医家在阴阳学说上进行的多种阐释发挥。本文从认知语言学学的角度,采用语料库驱动的方法,列举了阴阳在中医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借助隐喻如:“阴是内,阳是外”“阴是下,阳是上”“阴阳是战争中对立的力量”“阴阳是共同战斗的力量”进行意义的进一步拓展,揭示了《黄帝内经》中“阴”“阳”的意义建构是以隐喻为基础的,并分析其在阐释人体规律、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的认知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