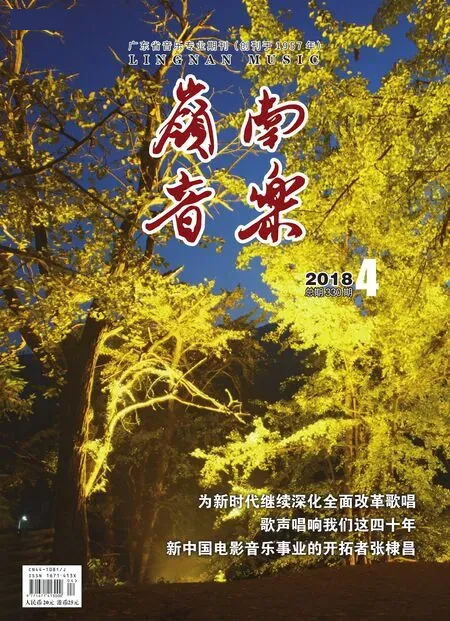有话要说……
——伯恩斯坦1957年关于音乐创作的演讲稿[1](续)
文|

是什么让人有话要说?是交流的需要。你们这些芝加哥大学的学生都喜欢说我们孤独,我们是“孤独的人群”,是的,我们真的很孤独。我想,交流是20世纪被讨论得最多的词,我说的不只是电子方式的交流。每个人都想与其他人拉近距离。埃里希·弗洛姆一直在写书,在很多著作中说我们多么没有爱的能力,而爱又如何是使我们获得这个世界上交流的温暖唯一的途径;我想这是事实。唯一的问题是爱并不是唯一的途径。艺术也是一种方式。通过艺术进行交流。所以我想可以说,当听到莫扎特一个温暖的乐句,一种类似于爱的东西正在接近我们。我们是否可以用玛丽·贝克·艾迪的一句话来解释“艺术是爱”?我想是可以的。我没有在提出一个挑衅性的绕弯的问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毕加索就是爱呢?杰克逊·波洛克是爱吗?格特鲁德·斯泰因是爱吗?如果艺术等于温暖,等于爱,那毕加索就一定是爱。
自然,这种有话要说的冲动会发生在你有话要对他说的人身上,这里的他就是听众。我知道自己写音乐时总是想到听众——不是因为打算写音乐,也不是因为实际上在写——而是在写的行为过程中会有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那就是听众将要听到。我有很多作曲家朋友,也读到过关于以前的作曲家的类似文献,他们说感觉不到听众。这些人坚持说不管是否有人听到,他们都要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也并不在意。他们的头脑中没有特定的人,特定的听众,他们总是指向巴赫、布鲁克纳和其他自称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创作的人。也就是说,一首乐曲的创作是一种神秘的献祭。布吕克纳就这样创作了自己所有的作品。这是他向上帝献祭的方式。巴赫也是。另外,我们知道巴赫是一个极其功利主义的作曲家。我们知道,巴赫必须在下周日上演那部大合唱,因为他们需要。他们需要复活节的耶稣受难曲和其它的作品,他写了这些作品,然后就改编成键盘乐来教学,他还为提琴手改编了提琴曲,为管风琴手做了管风琴曲。如何解决这个小冲突呢?这又一个挑战性的问题。
这里的“有话要说”是否太过意气用事?就是说,我们无法用升F调去陈述事实。音乐创作无法告知任何人任何事,除非明说,不然创作出的音乐也无法告知任何人它描述了什么。如果当初把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命名为贝多芬“卡夫卡变形记”交响曲,都是同样的音符,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卡夫卡”交响曲,而不是“田园”交响曲。实际上,就算贝多芬说,“我写了一首田园交响曲,灵感来自乡村的幸福情怀,它这样开始……”,那也并不意味着就是田园音乐。有什么是田园的?它是田园,只因为有人告诉你们这是田园。现在,如果告诉你们这是卡夫卡蜕变的开始,主人公格雷戈·萨姆萨早上醒来……嗯,他感觉不一样了,今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有点不一样了!
我想这样把整个乐章过一遍,把“田园”交响乐和卡夫卡的故事并排查看。也许不会处处都说得通,但也足以让人明白,不必用“快乐的乡间情怀,快乐的农民在绿野上嬉戏”这个说法,把所有的都套在音乐里。在最后的乐章中,暴风雨来临、消失,最后的雨滴落下,牧羊人的笛声平静地响起,宣告风暴结束,太阳升起,这一切很容易被当成变形的结束。风暴是关键,而牧羊人的笛声则是余音。希望大家明白了我的意思。
因此,作曲家所讲的内容从来都不是写实的,不能望文生义,而必须是情绪上的。但一定是在平静后回忆集结起来的情绪,这种平静,当然是我所描述的沙发上的半睡状态。哦,不应该说“沙发”——不只在沙发上。必须是平静地回忆集结起来,因为要彻底消除那种不切实际的说法,激昂的音乐永远不是由情绪激昂的作曲家写出来的,表现绝望的音乐也永远不会是感到绝望的作曲家写的。大家能否想象一个心情绝望的作曲家,在想要自杀的情绪中,打算放弃一切,却坐在钢琴前,写下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怎么可能?我会连写下自己的名字都做不到吧!很多十九世纪浪漫的无稽之谈总是在描绘作曲家创作时的心情。但这只是事后回溯。回看当时,我们看到贝多芬写“田园”交响曲时漫步在树林中,坐在岩石上,看着溪水流过——就拿出了笔记本!坐在岩石上是没法写交响乐的。必须回家,坐在椅子上,最好放下百叶窗,自然景色一眼都不去看,因为那样会分散注意力。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将赋格的第三声部融入其中。
坐在岩石上观察溪流中的种种迹象,这些迹象会变成音乐,但却不会在感受到溪流美丽的当下变成音乐,正如在感觉绝望时无法写一首绝望的慢板一样。因此,如华兹华斯所言,这种情绪必须被回忆集结,因为如果要和人们交流,就必须在交流的状态下进行,而不是在绝望受困的情绪状态下。
关于这个概念,(这里的概念指的是“有话要说”这个具有魔力的伟大词语)我要说的最后一件事是:谁在乎你是否有话要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烦恼。就是说,在座有多少人会介意罗伊·哈里斯是否还会再写一首交响曲——就是心灵深处真心实意的在乎。而我不只在说罗伊·哈里斯,可以是任何人!对比一下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新剧即将上演时所引发的激动,餐桌上的谈话,早餐时的兴奋——“哦,天哪,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新剧!”——对比一下我或任何人的新弦乐四重奏下周将首次公演的消息。“哦,天哪,某某作曲家新的四重奏!”看出来了吧?
所以,世事无常。大约勃拉姆斯在维也纳写交响乐的时候,维也纳人说:“啊,天哪,勃拉姆斯的新交响曲!”,他们是认真的。当威尔第或普契尼在米兰写歌剧时,米兰人说,“哦,天哪,一部新的普契尼歌剧,一部新的威尔第歌剧!”这是个大事件,属于他们的大事件。我们得不到了。所以,也许一切已经结束了。这是个问句,不是事实断定。
至此,我们只谈到了这个概念的纯音乐方面。但无论构思是什么,许多非音乐方面的影响都会发生在这个出神状态中。我一直坚持音乐元素的原因是,音乐从根本上倾向于抽象,其运作通常独立于非音乐性的事务。即它是非写实的。一个音符就是一个音符,对此可做的事情很少。升F就是升F,没有任何意味。它不像单词。它不像面包这个词,不管在诗歌里如何使用,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某种含义。不管多么诗意地说有,它的意思还是有。看一幅画,每个人看到的是差不多的概念图。但升F,却根本没有什么概念性。就是说,它是难懂的,是不透明的。这是一种可能的说法。有很多的音符,那就是你所听到的、那就是你所理解的,无法看穿它们去理解它们之外的任何意义。你能看穿文字,它们是透明的。
当然,单词也会有不透明的用法。如果格特鲁德·斯泰因[3]写道:“to know, to know, to love her so”(“要知道,要知道,要如此爱她”)或“it makes it well fish,”(“它使它成为完美鱼”),这些都是不透明的词,因为无法透过它们看到什么。理解这些词就像理解音乐给出的音符一样,如果这些词够漂亮,我想大家会因它们本身而对之青睐有加。但是,音符不总是这样的,除非像“田园”交响曲,作曲家告诉人们他希望大家想到的音符之外的东西。
那么,哪些非音乐的东西进入了画面呢?其实,第一个就是创意的可行性。躺着进入出神状态时,根据作曲家的类型,某处的某样东西会受到审查:那就是对创意的选择, 不管它多么无意识。我们称之为可交流性,用它把在意交流和不在意交流的作曲家区分开。也就是说,我之前提到了一些朋友,他们说,“我不在乎是否有人听到;管它呢,我就坐在象牙塔里写。”这话从来都不可能是真的。一些东西会来自外部世界,并在可交流性方面对创意做了一些限制。还有其他许多外部世界的东西会成为创意的条件——比如民族主义。这在十九世纪是特别强烈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所有的艺术都在进行大型运动,诸如李斯特写了匈牙利狂想曲,肖邦写了波兰玛祖卡舞曲和波洛涅兹;突然就有了西班牙音乐(之前从未真正有过西班牙声响的音乐);有了格雷格的挪威音乐,德沃夏克的波希米亚;突然就有了一种叫法国音乐的东西;突然德国音乐以德国方式表明立场。所有的这些民族主义都不是音乐问题。民族主义什么都是,却不是音乐;它是附加在音乐思想上的非音乐想法;因此, 如果以任何方式感受到了民族主义, 那就意味着非音乐的元素进入了出神状态,成为正在进行的创意的条件。对美国人来说,我想这自然会以爵士乐的形式发生。这对我来说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种影响是多么无意识或多么有意识?也就是说, 如果特意坐下来写一首美国音乐,我想可能会写出一首相当糟糕的作品。如果无意识中想到的东西听起去像是美国的,如果它碰巧借用了爵士乐,很可能还会是一首更好的作品。这已经被一再证实了,因为不管是衍生于美国传说还是美国风尚的作品都会更完整、会成为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可以编一个你能想到的最无聊的主题。坐下来写这首曲子,我说,“这太无聊了,再说,听起来也不是很有美国味。”那么,怎么才能让它美国化呢?嗯,我可以给它加点爵士乐技巧。比如说,用布吉尔摇摆节奏[4]写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用规整节奏。这很简单。现在它开始多了点个性,多了点趣味。可以让它更有爵士乐感,可以做很多事。做这些都是非常有意识的,因为我知道要怎么做。
我有一些作曲界的朋友是这样谱曲的,一直都有作曲家是用这种方法谱曲的,也有作家这样写作,画家这样画画。最后他们也能做出几乎令人信服的作品。然后——假设大家没有和我一起经历过那个小过程——我走进卡内基音乐厅准备演奏一首曲子,是大家从未听过的新曲子。假设我先以好莱坞式的浮夸开始介绍,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这在卡内基音乐厅会给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实际什么都没做。它不值一文。但这种音乐总是会出现,不仅符合要求,还会引起巨大轰动。大家总能知道它是发自内在还是来自外在。而奇怪的是,能够分辨出最好作品的人,不是批评家,不是其他的作曲家,而是公众。从长远来看,公众如果是只野兽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小动物,确切地知道它是否得到了“麦考伊”[5]。即使他们讨厌音乐,也知道这是“麦考伊”。即使他们在听韦伯恩的四重奏,不喜欢韦伯恩,他们知道这是真的,韦伯恩是一位真正的作曲家。其中的原因是他们能感受到交流。他们能分辨出这音乐来自于内心,而不是在某个人的头脑中杜撰出来的。
可以影响出神状态及其概念的有一个小清单,我会大略地过一遍。要说的还有流行的时代趋势。这和爵士乐产业有点关系,但又不尽相同。就是说,可能突然会发生巨大的转变,忽而背离音调,忽而朝向音调。这巨大的转变可能是朝向室内乐,朝向新组合,为交响乐团以外的团体作曲,朝向合唱作品,或朝向某些风格。我无法一一细说,但这无疑是非音乐性的问题。另一方面,真正的趋势则处于流行趋势的对立面,这些真正的趋势就是音乐史的一部分。真正的趋势和流行的趋势之间的区别和前面说的一样,即内在和外在的区别。
然后就是这样的考虑:评论家会怎么说?(老实说,作曲家可能会想到的这一点。)要考虑:我的作曲家同事们会怎么说?应该怎么做才能给他们留下好印象?还会考虑:我上一个作品是什么?现在应该写怎样的作品?这又是一个非常外部的考虑。“上一部作品是一首忧郁而艰难的悲剧交响曲;因此,下一部作品应该是轻快的,与上一部有所不同。”或换个行动方针:“上一部作品是一首忧郁而艰难的交响乐,大获成功,也许应该再写一部忧郁的悲剧交响乐,因为那似乎是我擅长的。”或者“这么写评论家喜欢……”或者“公众喜欢我写这种,而不是那种;所以,应该坚持写这种。”或者反过来——“就因为他们喜欢我做甲,我偏要做乙,因为我必须让公众了解我的最新情况,他们不明白……”所有这些都会涌进来。
然后是整个社会事务和社会结构的规定。这很复杂,不能细说,但我们应该提到苏联,那里最不好的社会结构规定范例当然还在继续。我最近收到一封朋友来信,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记者,他写了一篇报道说,苏联的作曲家小组又打起了一直以来的战斗,在定出新规则前所有的作曲都已经停止了。当然,这是很极端的,其他国家的情况要温和得多。我们不受法令的支配,但要受其他各种方式的支配——由供给和需求,指挥者要演什么不演什么、由公众希望、太难、不太长等等情况来决定。
其次是其他艺术的影响,来自其他艺术作品的灵感——来自自传、图画、书籍以及其他人的故事。躺在床上时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会挤进概念体验。也有“尝试与其他艺术共进退”的因素,音乐总是有点落后于其他艺术。因此,音乐有一个额外的任务就是努力跟上其他运动,比如印象派,远在音乐之前在绘画和诗歌中扎根了很久,表现主义也一样。绘画中比如立体派的各种扭曲也是如此,还有建筑的功能主义。音乐中的功能主义大约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现。但是,这些都是影响作曲家的音乐之外的想法。例如,如果他必须为一个特定的场合写一个作品,它还有其他的考虑。如果他受委约为某一特定的表演或特定的指挥或管弦乐队写一首乐曲,他会考虑这些演奏者最擅长的东西,构思可能会受到制约。如果我为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6]写歌,那将不同于为珍妮·图尔(Jennie Tourel)[7]写的歌。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事,例如,“有多少时间写这东西?只有两个星期?那就得写个短的了。如果有很多时间,可以写更长的。”
我们差不多都说了。这些是永远不应该考虑的问题,但却都会被考虑。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自我批评,头脑中的审查官会说,“别这么做,这是照抄……别那么做,过时了……别那么做,太粗俗了。”而这个小家伙,不管他是谁,只要是个好作曲家,无论是睡着了还是醒着,他都在工作呢。
我所提到的一切在每位作曲家身上都是合理的。运作的好坏区别仅仅相当于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比例。这完全取决于他如何愉快地决定将某个原则付诸行动。如果他无法决定,他是幸运的。如果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他是幸运的。如果他必须做出决定,那他可能根本就不算是作曲家。
注释:
[1]原文是由伯恩斯坦1957年2月19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的一次非正式演讲的录音所转写的讲稿,题目是Something to Say…,收录于2007年由Amadeus Press出版的The Infinite Variety of Music一书。
[2]译文由星海音乐学院青年作曲家王阿毛博士提供音乐术语译审,星海音乐学院作曲教授房晓敏全文审阅,特此感谢!
[3]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作家与诗人。
[4]Boogie, 以布鲁斯乐曲为基础的一种节奏强烈的摇滚乐,(惹人跟着跳舞的)强节奏快速摇滚乐。
[5]美国俚语,指真正的,真品(非替代品)。
[6]Maria Callas(1923-1977)出生于美国的希腊花腔女高音,以其戏剧性的歌剧角色而闻名。
[7]Jennie Tourel(约1900-1973)犹太裔美国歌剧女中音,在歌剧和独奏演出中都很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