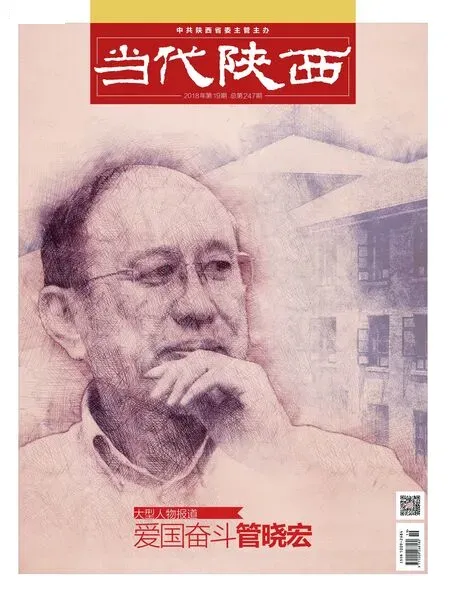那个年代,那么青春
——忆我的母校吴堡中学
◎张维迎(北京大学)
高中时代,难得的是读了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更难忘的是,那些曾经共同奋斗的师友

张维迎教授在吴堡中学60周年庆典上发言 冯东旭//摄
一
我是吴堡中学高75届的学生。之所以能成为吴堡中学的一员,要感谢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当时吴堡县共有三所学校提供高中教育:任家沟中学,宋家川中学,郭家沟中学。宋家川中学俗称“二中”,无论资历还是声望,是名副其实的“第二中学”。
我的第一志愿填写的是任家沟中学,一是想上全县最好的学校,二是我一位要好的发小已经在任家沟中学读高中,他比我高一级,我非常希望能和他在一个学校。但我收到的入学通知是到宋家川中学报到。说实话,我当时有些失望。
入学后我才知道,是我一位小学老师“操作”的结果。这位老师名字叫冯德斌,当时在县政府负责伙食管理工作,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给新生分配学校时,他正好在场,一看到我的名字,就说这个娃娃我认识,让他到二中读吧!这样,我就被拨拉到宋家川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吴堡中学。
冯老师的想法,一是,任家沟中学虽然距离我村近,但地处山沟,交通不方便,上学需要步行60华里,宋家川中学距离虽远一些,但在县城,可以搭便车;二是,我在县城读书,可以见大世面,他还可以照应。
入学报到之后,我一度还曾想转学到任家沟中学,冯老师说,你别看宋家川中学现在不如任家沟,将来一定超过任家沟,城里毕竟比农村有吸引力。
顺便说一下,冯老师对我印象好,一是,他教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学习成绩好,“孺子可教也”;二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曾把捡到的一把裁纸刀交给他,他说这是“拾金不昧”,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了我。
“拾金不昧”,是我学到的第一个汉语成语!
二
我们那一届新生是1974年春天入学,当时邓小平复出后正在大刀阔斧搞整顿,包括教育界的整顿,“四人帮”却针锋相对搞“批林批孔”,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在我们读高中的整整两年期间,“四人帮”压过了邓小平,教育界尤其如此。
我们入学不久,教育界就树起了两个“反潮流”英雄,一个是北京小学生黄帅,她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另一个是辽宁知青张铁生,他在参加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考试时,理化交了白卷。
很快,全国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的浪潮,工宣队进驻学校成为最高决策者,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学生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参加生产劳动。
在这种大环境下,宋家川中学也不可能置之事外。值得庆幸的是,出于对学生的爱和职业精神,我们的绝大部分老师仍然克服困难,坚守教学岗位,兢兢业业地履行着教师的职责,也严格地督促学生好好学习。
比如说,先后给我们上数学课的魏光华老师和魏峰老师,完完整整地讲完了高中数学课本的全部内容,他们写满黑板的数学公式,我至今历历在目。
就我所知,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学过完整高中数学课的并不多,我高考时数学能得到较高的分数,后来能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问题,与他们给我打下的良好的数学功底分不开。
给我们上语文课的蒋维礼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又自学函授中文专业,知识面广,讲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深受同学们喜爱。
1977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宣布后,老师们很快就分头编写出了各门课程的高考辅导材料,提供给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学。我在农村准备高考的时候,魏峰老师从县城给我邮寄来了一大卷油印的数学辅导材料,这些材料是她自己编写的。在我上考场的前一天,康毅老师还在他自己家里帮助我复习地理和历史。
这些,都让我终生难忘。
我要特别感谢一下李务滋老师。她是一位充满母爱的老师,把学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曾两次犯“政治”错误,但每一次,她都说“都是些孩子,私下劝说劝说就可以了”,让我轻松过关。她不仅没有因此歧视我,而且对我充满期待,在我毕业的时候送给我一本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
在我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之后,她曾为我喜悦过,也曾为我担忧过,让我感激不尽,也让我歉疚不已。
我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在那个年代,或者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或者由于个性刚直不阿,我们的老师中的一些人一直背着沉重的政治枷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被剥夺了人的基本尊严。
比如马志伟老师,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被划为右派,从北京发配到吴堡,先后在枣林峁中学和宋家川中学任教,吃尽了苦头,直到1980年才调回北京,与妻子和女儿团聚。他桃李满天下,但2010年离开人世时,没有享受一个像样的葬礼,我是唯一一个有机会在医院太平间向他的遗体鞠躬的弟子,看到他冷冻的遗体,眉毛上还结着冰碴儿,我顿时泪流满面。
马老师临终前,托付他太太把一件半新不旧的绵羊皮外套转给我,说这是他在宋家川时穿过的,很保暖,或许我还用得着。
三
我们高中二班总共63位同学,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县城,三分之二来自农村,有干部子弟,但绝大部分是农民的孩子。家在城里的同学生活条件相对好些,农村来的同学大部分生活艰苦。但同学们都能平等对待,相互帮助,结成了一生的友情。城里的同学并不歧视农村来的同学,干部子弟也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事实上,与我个人关系最要好的同学,有好几位是城里富裕家庭的孩子。课余时间,他们骑着自行车带我逛街,让我这个乡巴佬逐步熟悉了城里人的生活。周末和节假日,我曾去多个同学家吃饭,有时吃完晚饭就睡在他们家里,他们的父母对我很热情,让我感到非常温暖。我上大学期间,几个同学还给过我经济上的接济,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在我母亲下葬的时候,好几位中学同学专程来为她老人家送行,让我感动不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班上有两位同学的父亲在县电影院工作,我和他们同桌,关系要好。凭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在高中两年期间,我没花一分钱就看过了县电影院放映过的所有中外电影。
这事在今天看来,确实有些不恰当,但当时不这么想。如果不这样,我是没有可能进电影院的,5分钱一张的电影票,也不是我能负担得起的。
当然,高中时期交往更多的还是农村来的同学,因为我们都住在学校的窑洞,在一个锅里搅稀稠。十几个青春少年睡在一条炕上,吵吵嚷嚷,打打闹闹,自不待言。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同学们之间分享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食品。
那时候,一天两顿饭,晚饭是高粱米粥,下午四点半就吃过了,到晚上九点的时候,饿得肚子咕咕叫,必须吃点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否则难以入睡。家庭富裕些的,干粮可能是干馒头片或副食店买的糖提子;家庭贫困些的,干粮是红薯干或晾干的土豆擦擦。泡干土豆擦擦,就像现在泡方便面一样,抓一把放在碗里,倒些开水,盖上盖焖一会就好,吃起来真香。在我的记忆中,比现在的方便面香。可能是由于土豆便宜,在自己没有东西可吃时,也总能从别人的袋子里抓一把,泡着吃,没有人在意。有时候,富有的同学也会给大家分享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馒头片。通常是,离家近的给予多,因为他们回家次数多,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慷慨一些。
我敢肯定的是,我吃别人的比别人吃我的多,因为我可供分享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有件事说起来让人难为情。那个时候,男生睡觉一般都不穿睡衣,而我在高中二年级之前,连裤头也没有穿过,睡觉时脱光衣服,赤条条躺下盖上被子。
记得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我们换了宿舍,我和薛亚平同学挨着睡。他看到我赤条条躺下,就问我怎么连裤头也不穿,我说我从来就不穿裤头,我没有裤头。他说,不穿裤头睡眠不文明。这样吧,我有两条,就借给你一条穿吧。这样,我就穿上了他的裤头,毕业的时候,又把裤头还给了他。亚平同学的父亲当时是《榆林报》的社长,算个大官,又是文化人,但家在农村,也算不上富有,所以亚平生活很节俭。他因病英年早逝,我没有机会报答他,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借我裤头穿。多么希望他在九泉之下能听到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
高中两年也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有权的人必须公平!
当时每个班都有一位伙食委员,登记同学们报饭,负责收饭费和粮票,开饭时还要掌勺舀饭。其他班的伙食委员几乎是一学期换一个,而我这个伙食委员一当就是两年。究其原因,一是总务长孔令启老师说我账目清,现钱粮票从未出过差错,二是同学们觉得我公平,掌勺时不会偏三向四,也不会给自己碗里多舀一片肉。
那时候,只有过节的时候菜汤里才放些肉,平均每人也就两三片,多得一片就相当于现在拿到一个大工程。

吴堡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