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只不死鸟
——怀念恩师王富仁先生
何希凡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大约三十年前,曾在一个小报上读到一篇中学生写的短文,题目是《壮哉,不死鸟》,内容虽然早已记忆模糊,但“不死鸟”这个意象却长久地吊住了我的胃口。我明知它不过是个比喻,但每当想起它,总是要追寻这世间究竟有没有不死鸟。从古至今,多少痴心妄想者都在苦求着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汉武帝等威加海内之辈都曾有过“服黄金,吞白玉”之举,但到头来不免是“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看来,世间真的难以有不老不死之人了。如果真有不死鸟,那也算得上生命的奇迹,但后来知道那也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郭沫若长诗《凤凰涅槃》篇首的小序就说:“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斯’(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这其实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凤凰,亦即“不死鸟”,在《孔演图》和《广雅》等文献中都有记载。由此可知,凤凰之能不死,必先经过死而“更生”。我想,鸟尚能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怎么就不能创造同样的生命奇迹呢?没想到,在我平淡无奇的人生中竟有缘际遇了真正的“不死鸟”。
“不死鸟”之死
2017年5月2日傍晚,文学院领导傅学敏教授打来电话说,半年前曾拟定请王富仁老师来我校讲学,现在可以请他老人家过来了。我拿着电话犯了踌躇,因为几周前我曾给王老师打过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家的保姆,她告诉我说,王老师又去了北京。我知道,自从王老师被确诊为肺癌后,就一直往返于北京与汕头,只要北京的放化疗结束,他就要回汕头去给学生上课。虽然他一直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曾对我说,除了医生告知他患了癌症,自己并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我也曾在心里期盼着奇迹的发生,但多次的放化疗,这一次去到北京究竟是什么结果,谁也难以判定。我只得对傅学敏老师说,等我与王老师联系上了再说。谁知我刚挂了电话,伏俊琏老师就发来信息:“著名现代文学专家、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于今日19点20分在北京逝世。”噩耗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巧合,就在文学院师生几个月的热切期待即将实现之际,它却瞬间变成了泡影!泪水潮湿了我的眼眶而没有充溢,因为我不相信富仁师这么快就走了。
窗外突然间雨暴风狂,室内也有了阵阵寒意,我忽然想用王老师生前并不感兴趣的俗套礼节为他撰写一副挽联,但我却想写出最不落俗套又最能契合他的生命本质的内容。只要读他晚年的文章,那无比健硕而大气的文笔,那强大的思维运动力量,你怎么能够想象这是一个身罹绝症的老人生命终结前夕的绝笔?只要深味他波澜壮阔的学术生涯,你看他的身上可曾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历史回光返照?他虽然曾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但他何曾表现出丝毫的学霸气与领袖欲?他是凭着自己著述煌煌的最诚实的学术劳作高擎起中国现代文学的猎猎大旗,他的思想锋芒和学术个性不是为了逞一己之能,更不是为了猎取一己之名利,而是满含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爱,满含着对自己所献身的学科命运的深切系念,满含着对后学的万缕仁爱!但他这一走,一个时代的稀有之音渐行渐远,他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正如魏晋时代的嵇康临终前之广陵散绝!我没有想到,撰写一幅挽联竟然伴着整个风雨长夜,当陕西师大的著名学者、书法家,也是王老师弟子的李继凯仁兄见到我撰写的这幅挽联,当天就不吝他漂亮的笔墨书写出来:
椽笔犹健硕,先生岂求一己富,长恨苍天摧人哲;
大纛失飘扬,后学俱感万缕仁,但悲学界绝广陵。
“不死鸟”与我
当我来到大学教书之前,要把王富仁的名字和我联系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略知王富仁,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改变了过去几十年间鲁迅研究的强大惯性,是学术界思想解放的标志,也是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他名满天下,也招来了惯性的严重质疑。我在给师范生讲鲁迅的时候,也偶尔谨慎地搬用了他的一些见解,但我从来没有奢望有朝一日会直接面对他,还能听他的课。1993年7月,我来到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当时的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被安排任教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与此同时,学校同意我先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记得是年9月14号到了北京,我的导师是新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名家朱金顺先生,他向我介绍了即将开课的六位教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王富仁、童庆炳、郭志刚等先生。王富仁的名字已不陌生,因他是本专业首位博士,而且当时还算学术新锐,他的著述已凸显出鲜明的个性锋芒,字里行间流淌着学术主体的生命自信,我料想他一定是一个有些脾气乃至有点傲慢的人,而像我这样一个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却尚未学术起步的渺小灵魂,怎敢去擅扰一个大学者宏图杰构、吞霞吐锦的滔滔思绪?我想早一点见到他,但他的课安排在1994年春天,我就把读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和《先驱者的形象》等著作当作与他的提前会面。偶尔也能从老师和同学口中听到他的故事,听到他独到深刻的见解,他的面影已经在我心中渐渐鲜活起来,但整整一个学期,尽管数度经过他所住的丽泽8楼下,还是不免有叩门无路之虞。

王富仁著《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
春节假期刚过,我就赶回了北师大,校园虽然还凛冽着寒意,残霜还横陈在道路左右,但图书馆前的草坪已经微吐绿意,迎春花也稀疏地开了,北京干燥的气候与还算淡蓝的天空已把暖意送到心头。记得正月初九开学,在领略了朱金顺、刘勇、李岫等老师的精彩讲授之后,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王富仁、郭志刚、童庆炳三位先生登台,他们都是中国学界的顶尖级学者:郭志刚先生是老一代现代文学研究名家,尤以孙犁研究蜚声学界,而且因为对孙犁的几十年私淑,其高华雅洁的文笔似与孙犁同构,也因为他对我的多年错爱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学术文笔。童庆炳先生是中国文艺学的泰斗,不仅在文艺理论上著述等身,声名卓著,而且还涉足文学创作,出版过两部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培养过莫言、余华、毕淑敏等著名作家,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教父”。童老师2005年来我校讲学,十余年后我们师生重逢,童老师竟与我动情拥抱,当着我的众多学生说我是他的老学生。王富仁老师给我们开了《鲁迅小说研究》,这是他誉满天下的专攻。他的精彩不是人们常见的精彩,从来没有讲稿,但口中飞珠溅玉,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严密的逻辑常令我们猝不及防,他不断颠覆着我们的惯性思维,拨开现象的花絮,撩开似是而非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人性真相、文化真相和历史真相。听他的课你会感到新鲜而陌生的刺激,你也会感到自我的渺小。但即使如此,我对他积久存有的敬畏惶恐之心却渐渐烟消云散了,你看他那一身老农民的打扮,你看他那刚过知天命之年却已布满沟壑的脸庞,你看他那一头染过的黑发却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调皮银丝。虽然也穿着蓝色的西装,因为它并不笔挺而略显褶皱,你仍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头脑中置换出他曾经被称为“公社干部”的那一身老式中山装。他接连不断地抽烟更增添了人间烟火气的质感与厚度,我们实在是在被他熏陶啊。神秘感一旦消失,他在我的心中渐变为亲人和朋友,有些问题想和他讨论也就再没有了先前的心理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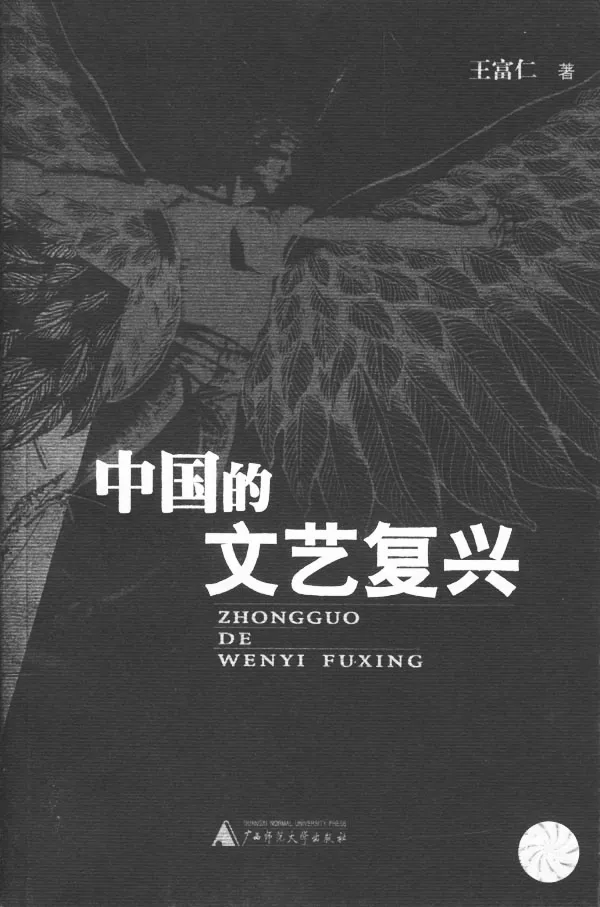
王富仁著《中国的文艺复兴》
因为上一个学期我曾就茅盾1940年代的未竟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写了一篇论文,得到过李岫老师的热情鼓励。在此之前我也读到过富仁师的关于鲁迅和茅盾小说比较的长篇论文,其中关于《霜叶》的一些观点我深以为然。于是趁一次课间休息,我并没有过多体谅他讲课的辛劳而不失时机地凑上前去向他表达了自己的一点浅薄看法。我说,学术界都认为这部小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按照作者的最初构想写完,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半成品,而我却认为这部小说好就好在没有写完,如果写完了就一定不如现在的更好。没想到富仁师对我大加赞赏,当即鼓励我尽快成文。我自然大喜过望,连续熬了很多长夜反复修改,也请一同进修的同学帮我把关,然后我和富仁师约定在他家里交谈。还记得先后有三个下午就在他家的饭厅,我和他在饭桌对面而坐,他还是那么随和慈祥,但我能感受到他读了我的文章已经没有初次谈话的激动。他首先问我究竟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然后指出我的两处引文说,你引用的这些话有什么高明之处?能帮助你有哪些独特的思考?这些话你自己都应该说得出来,何必要引用呢?引用是为了推动你的思考和论述,让你做出超越别人的表达,否则,为引用而引用有什么意思呢?你对小说原作做了那么多繁琐的分析,自认为很精彩,你究竟是在写讲课教案还是在写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呢?分析作品应该是为你的新鲜见解服务,与此无关的分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连珠炮似的问题把我打蒙了,我表示还要继续思考,继续修改。然而,富仁师为我这篇匮乏学术品格的文章前后所花的三个下午时间并没有打上句号,越到后来,我越是感到了富仁师那一连串问题所蕴含的价值,因为我知道了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对研究对象有了浓厚的兴趣,也不仅仅是对文学文本的烂熟于心,而是要有对于研究对象与众不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也要尽可能对已有的同类研究成果有超越性的进展,否则,我们就根本没有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发言权。我也深知,作品研究不是繁琐滥俗的赏析,研究作品的过程也就是表达思想、揭示学术主体自我发现的过程。别人的见解再精彩,如果被我们去重复证明,那就是无效、无意义的劳动。后来,读到富仁师更多的论述,我进一步知道了学术研究不能只靠灵感的闪现,仅仅读了很多书或者很有学问,仅仅有了足可骄人的才华,这些都不等于学术本身,才华和学问要靠学术主体的生命和思想去照亮。但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特别重视才华与学问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拿着这个标准去比较周氏兄弟的时候,总是想用周作人的才华和学问把鲁迅比下去,而鲁迅卓越的思想常常被人们忽略不计。富仁师并不轻视一个人的学问和才华,但他是希望我们这些想要吃“学术饭”的人更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有了这些感悟,我没有放弃当年那篇文章,经多次修改,几至十年辛苦,终于在2002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富仁师当年严肃追问的意义也绝不仅止于砥砺我写成了这篇文章,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让我懂得了学术研究的基本道理,这些并不高深却为很多吃学术饭的人一再忽略的道理伴随着我的学术生涯,我渺小的学术生命就靠这些道理而有了方向,与此同时,我也把这些足以终生受用的珍贵启示渗透给我的学生。
“不死鸟”之不死
我是富仁师的学生,这是真实的,但作为他的学生我又是不够格的。他早年的硕士生和后来的许多博士生都是中国学界的风云人物,如果我胆敢在他们面前自诩是富仁师的学生,他们一定会做出权威性的澄清,在王门弟子中谁也没有听到过我的名字,而一个仅仅听过富仁师一学期课的进修生定会令他们嗤之以鼻。然而,他们何曾想到,一个渺小的灵魂与一个伟大灵魂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有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精神牵连。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与富仁师是纯洁的君子之交。他有几位博士生与我略有交往。刘殿祥就是当年我们在北师大进修的同学,当他知道我与富仁师的深交,不无歆羡地说,你比我们更幸运!这种幸运不只在于富仁师每出新书不但一定要寄赠给我,还会寄赠给我的学生,更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他要我帮他把有关他的“新国学”观讨论的文章搜集出来,编辑成书,并与我商讨了书名,他要私人出钱帮我出版,还口口声声说:“我完全可以帮你,我有这个经济能力。”虽然后来种种原因,这部60余万字的书最终流产,但富仁师的一番拳拳爱意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二十几年来,我用心读了他的每一篇文章,虽然多是长文,但没有一篇不彰显着他的原创和独创,而且行文之间绝少学究气、学霸气,每句话都似汩汩清泉自心底流出,是那样的明白晓畅,又是那样的震撼人心,几乎人人都能读懂,却很少有人能说得如此到位。我曾经多次对我的学生说,富仁师的文章都是“高水平的大白话”。我还发现,富仁师越到后来越是很少去研究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话题,但老题目一到他的笔下你就不能如风过耳,你虽然听到很多名人讨论过这些话题,但王富仁一旦发言了你就得用心看看。比如,关于最受争议的鲁迅的《青年必读书》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新诗的诸多问题,关于一再被人翻云覆雨的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问题,关于胡适与学衡派的历史定位问题,等等,这些都经很多学人一再言说,但当富仁师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深宏之论。

课堂上的王富仁先生
自然,富仁师不是完人,他也有自己的生命局限,也有自己的知识盲点,他的论著甚至也有些许的知识硬伤,同行中也有对他的这些并不完美私下非议者。我就曾听到过一个年轻教授居高临下、声色俱厉地批评他的不是,甚至说他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但当这些人面对他整体性强大的学术生命,面对他那些力能扛鼎的论著时,都不得不投以折服的目光。
就我个人而言,最幸运的是每次和他通电话都在不经意间作了没有预谋的长谈,一旦触及到感兴趣的话题,听富仁师滔滔不绝的惊人之论实在是难得的精神洗礼,有时直到说得我的电话没电了方才罢休。北师大的一学期听课竟然延续到二十几年的教益。
他初到汕头大学又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却在身患背疮打着吊针的疼痛之中坚持为我的书写了长达五千余字的序言,并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作为学术界作序最多的著名学者,他的拳拳之爱岂止于我,简直可以说洒向学界都是爱!
如此生命健旺而具有凌云健笔的人怎么会死呢?但他却实实在在地走向了生命的尽头,只是他站在生死之门上比谁都显得更加从容淡定。当我知道医生已经确诊他患了肺癌后心情很是沉痛,他反而还来劝我:“活得再长也不过是这世界的匆匆过客,岁数是给别人看的,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生命的质量。我王富仁活了76岁也不算短寿了,我此生只要对得起自己的事业,没有做有损于民族的事,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当我劝他不要在病中写作,这样会更加使病情恶化,他却自有一番道理:“你不知道,写文章使我分散了对病的注意力,相反有助于病情的稳定。”他的这些话不是强词夺理,而是真正懂得生命意义的肺腑之言。听了他的这一番话,我这个向来怕死的人也有了向死而生的生命启悟。于是,我想起了他很喜欢的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一个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活得如此清醒,如此不失生命的尊严,他那凛凛风骨撑起的挺拔身姿哪里就会倒下去呢?他怎么会真的死去呢?我相信,几年之后,几十年之后,乃至更长的时间,学术界不会停止对王富仁学术高度的瞭望,更不会停止对他的学术著述意义的阐释,因为中国学术有了他和他的同道的介入,才有了不一样的学术风貌和精神风景!当一个人的生命之光具有了历史时空的穿透力,我敢确信他并没有死,因为在我的心中,他实在是一只鲜活异常的不死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