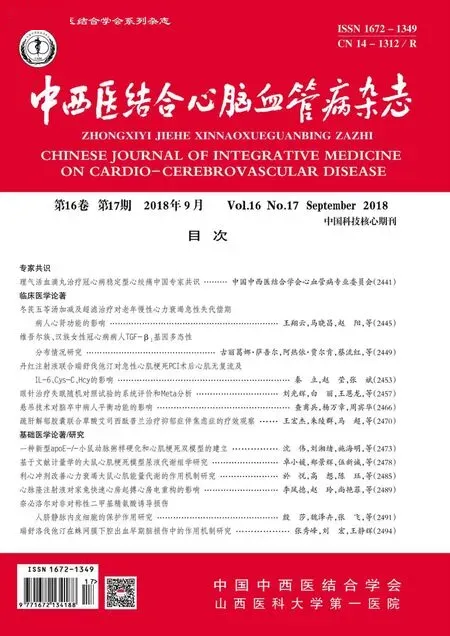右丙亚胺预防化疗药物心脏毒性的临床研究
,
近半个世纪以来,恶性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以药物化疗为主的内科肿瘤学已经成为肿瘤临床治疗的支柱手段[1]。蒽环类药物因其抗肿瘤谱广和有效率较高,所以受到极大的重视,自1963年发现阿霉素(多柔比星)以来,又陆续有多种蒽环类药物问世,常用的有柔红霉素、4-去甲氧柔红霉素、米托蒽醌、表柔比星、吡喃阿霉素、阿克拉霉素等,该类药物作用机制主要是直接作用于DNA,对处于细胞周期各阶段的肿瘤细胞均有杀灭作用,为周期非特异性药物(CCNSC)[2]。CCNSC类药物的特点是在机体能够耐受的剂量范围内,其杀伤能力随用药剂量增加而增加,但由于蒽环类药物存在心脏毒性,使用剂量往往不能达到理想标准和疗程,从而限制了其抗肿瘤的疗效[3]。其心脏毒性在老年和儿童病人表现尤为明显,一旦发生将导致病程延长并且逆转困难,因此及时加入心脏保护剂降低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尤为重要[4]。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心脏保护药物有参麦注射液、果糖二磷酸钠注射液等,由于这些药物能够兴奋心肌,增强心肌收缩力,提高射血分数,因此可以有效保护心肌细胞[2],但对于化疗药物所致的心肌损伤疗效不明显,右丙亚胺(dexrazoxane,DEX)是目前唯一上市能预防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制剂[5]。本研究观察右丙亚胺对蒽环类药物化疗所致心脏毒性的影响及不良反应,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6月—2016年10月在我院进行化疗的恶性肿瘤病人60例,其中白血病30例,恶性淋巴瘤20例,乳腺癌10例,分为DEX组和对照组,各30例。DEX组男14例,女16例,年龄22岁~74岁(49.72岁±4.53岁)。对照组男11例,女19例,年龄24岁~75岁(48.95岁±5.04岁)。两组病人肿瘤分型、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恶性肿瘤分型详见表1。

表1 两组恶性肿瘤分型 例
1.2 纳入标准 ①所有病人确诊为恶性肿瘤;②乳腺癌病人均经手术治疗和病理组织学确诊,按TMN分期处于Ⅱa、Ⅱb期;③淋巴瘤病人处于Ⅲa期以上;④病人对化疗方案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①有心肌梗死病人,心绞痛,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脏瓣膜病史;②一种以上恶性肿瘤病人;③临床资料不完整病人;④不配合医护人员病人。
1.4 方法 两组均接受蒽环类药物为主的化疗方案治疗,对照组单纯行化疗,DEX组在第1次化疗同时即开始应用右丙亚胺,在给予蒽环类药物前30 min给予右丙亚胺静脉输注,右丙亚胺∶蒽环类药物10∶1[6]。所有病人均给予6周期化疗,对于骨髓抑制严重者加用细胞刺激因子,成分输血,感染高危者预防性使用广谱抗生素及抗真菌药物等辅助治疗[7]。
1.5 观察指标 观察心肌肌钙蛋白I(cTnI)、左室射血分数(LVEF)、心电图变化,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及3级~4级的毒性和总的毒性。治疗前,所有病人均行心脏评估、肿瘤评估、用药史及体能评估,并行常规血液学、血清生化检查,于每个周期治疗前及治疗完成后3周进行随访,包括cTnI、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血压监测等。cTnI采用ELISA测定。

2 结 果
2.1 两组化疗前后cTnI比较 DEX组化疗前后cTn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化疗后cTnI较化疗前明显升高(P<0.05),两组化疗1周期~6周期cTnI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表2 两组化疗前后cTnI比较(±s) μg/L
2.2 两组化疗前后LVEF比较 两组化疗后LVEF均有所降低,但DEX组降低程度不明显,与化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降低明显,与化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化疗后LVEF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表3 两组化疗前后LVEF比较(±s) %
2.3 两组心电图异常与心律失常发生率比较 DEX组心电图异常、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4。
2.4 两组非心脏毒性比较 两组非心脏毒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级~4级的毒性和总的毒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5。

表4 两组心电图异常与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比较 例(%)

表5 两组非心脏毒性比较 例
3 讨 论
急性髓系白血病常用诱导及强化治疗方案为DA、MA、TA、AA方案,均包含蒽环类药物,乳腺癌标准化疗方案为CAF或CEF,其中蒽环类药物是基本用药。ABVD和CHOP方案分别是霍奇金淋巴瘤和中高危非霍奇金淋巴瘤一线治疗方案,近年来通过增加蒽环类药物剂量提高淋巴瘤的治愈率已经逐步取得共识[8]。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主要是通过氧自由基介导,慢性、迟发性心脏毒性与累积剂量有密切关系,其作用机制为:①在心肌细胞触发凋亡;②膜损伤;③基因表达改变;④蛋白活性改变;⑤DNA损伤[9]。蒽环类药物作用后,心脏发生的损伤主要表现为心肌水肿、细胞消失、间质纤维化、心肌细胞肌浆网扩张,其心脏毒性分为3种:急性、慢性、迟发性。急性心脏毒性反应短暂、可逆,不造成慢性心功能损伤,而慢性和迟发性心脏毒性与累积剂量密切相关,一旦发生损伤,病程不可逆转,呈现明显量-效关系[10]。同时,在使用相同剂量蒽环类药物时,女性较男性更易发生心肌收缩抑制现象,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将导致左室射血分数下降,随后引起一系列不良反应,在妇女儿童身上尤为明显。对于肿瘤长期生存者,其发生心脏相关事件危险是正常人群的8倍[11]。有研究表明,应用蒽环类药物治疗后病人因心脏原因引起的标准化死亡率比预期高8.2倍,且长期存活病人发生心脏衰竭的风险增加15倍,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增加10倍,脑卒中发生风险增加9倍[12]。
右丙亚胺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唯一蒽环类药物心脏保护剂,是EDTA衍生物,非肠道给药,早期用于抗肿瘤转移治疗,但由于其仅对小鼠淋巴细胞白血病L1210和S388有作用,对肺癌、肠癌、黑色素瘤转移无效,因此未能大规模用于临床[13]。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研究发现,右丙亚胺和蒽环类抗生素联合用药具有显著的心脏保护作用,在多柔比星、表柔比星、柔红霉素、米托蒽醌使用同时加右丙亚胺会明显减轻心脏毒性,而其抗肿瘤活性不受影响,右丙亚胺通过铁鳌合起心脏保护作用,防止蒽环类药物-铁离子螯合物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由基,自由基可导致周围心肌组织的氧化损伤[14]。
目前预防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最常用的方法是限制其用量,但事实上蒽环类药物引发的心脏毒性在低剂量时就已出现。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在第1周使用蒽环类药物时就出现血清cTnI浓度的升高,显示蒽环类药物对病人的心肌损伤。因此,有效预防或减少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心脏保护剂的应用还可以增加蒽环类抗肿瘤药物累积剂量和用药疗程,并且在首次使用蒽环类药物时就减轻心脏毒性,才能真正改善病人远期生存质量。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临床资料研究表明,应用右丙亚胺可以改善使用蒽环类药物治疗时对心脏的损害作用,在每次给予蒽环类药物的同时使用右丙亚胺已经在多项随机对照研究中被证实可以显著降低心脏毒性[15]。本研究也显示,使用右丙亚胺对蒽环类药物引起的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并无明显影响亦未增加新的毒性,表明其不增加非心脏毒性。
综上所述,右丙亚胺对蒽环类药物所致的心脏毒性有明显预防作用,并且对已形成的心脏损害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可以保障蒽环类药物安全地完成规定周期的化疗,而不会出现严重的心脏和非心脏毒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