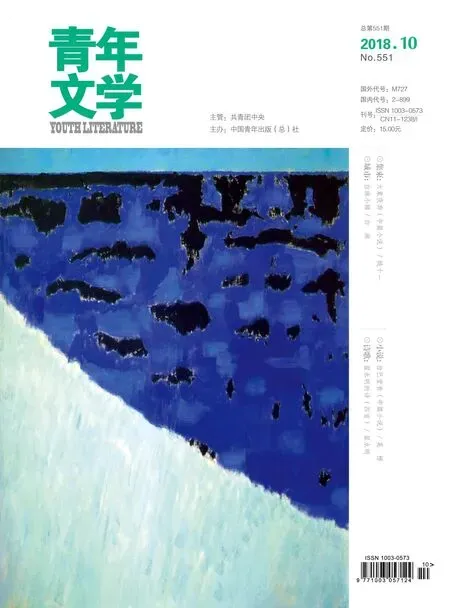执 念(上)
⊙ 文 / 侯 磊
北京人对于古城的旧念十分固执。他们会用五十年前的名字来称呼一条胡同,会在城墙拆除五十年后,仍会按二环路的标准来区别城里和城外,仍采用进城、出城来指代从胡同到海淀区的中关村。那里是全国计算机业的中心,但在旧念中,海淀是个镇子,中关村是个村子。而在北京的南面,总有一些街道有曾经的南边“最后一座楼”,即街道楼房的最南端,再往南,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都是一片片荒地;直到二〇〇〇年以来,楼群才迅速扩张,如海水漫过沙滩。
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片工地,又在转眼间成为国际都市。每次开车从北向南走在东三环上,看着一座座大楼,京广中心、中央电视台、苹果社区、快要竣工的中国尊,西面是世贸天街、国贸中心、富力城……现代感极强的建筑让人觉得这里是香港、是纽约,是任何一处现代化都市。
夜幕中的王府井大街
唯有市场能穿越历史,因为人总归要出来逛街的。
夜幕中漫步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看着眼前几幢变形金刚一样的新东安市场,没承想眼前浮现起儿时逛东安市场时的情景来。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地方还是那块地方,风景却不是那时的风景。
沿着这条三华里长的王府井大街往南,南边的一段成了步行街,步行街一路由北向南。巨大砖头一般的新东安市场,带有五十年代色彩名称的妇女儿童商店,亨德利钟表店;肯德基与麦当劳,露脐装与低腰裤,服装鞋帽与珠宝钻石,四联美发中的领袖像上依旧和蔼可亲。来来往往的人,黑的人白的人,红头发绿头发的人,操着河南话陕西话的人;叽叽喳喳叫着日本话和韩国话的成群结队的旅行团,高个子的欧美人士,长得像圣诞老人的外国老头搂着国产年轻穿牛仔裤的小美人;满大街的霓虹灯,满大街的路灯,满大街的昏黄中夹杂着五彩的走廊。外文书店里放着“绵羊绵羊sheep,sheep sheep sheep……”的英语教学法;穆斯林大厦不知改了多少次名,但我只记得它是装饰有绿色阿拉伯文字的穆斯林大厦;往南的百货大楼里东西又贵又不好,楼前仍然矗立着劳模张秉贵的塑像,塑像前装满了喷泉,缥缈之间,好像他依旧在柜台前一把把地抓糖果。
然后是,一堆促销的电子产品专卖店;各种品牌打多少折扣返多少优惠券,让利促销百分之多少的专卖店。医疗器械店里巨大的人参和鹿角陈列着,还有成大桶地泡有毒蛇、蟾蜍、蛤蚧的药酒,胖大海的冲剂,防蚂蚁药的口袋……盛锡福帽店中周恩来戴过的帽子的模型还在展出,同升和鞋店里还是老式的千层底,碧春茶叶店门口的免费品茶,汲古阁文物店里的名人字画和笔墨纸砚,工艺美术商店里仿制的青铜鼎和兵马俑,新华书店里名人们的图书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畅销排行榜上……旅游电瓶车上的导游们满嘴跑火车地叫嚷着北京文化。反正,这里当年是王爷府的井;反正,离这里不远,有协和医院和老舍故居。
霓虹灯的颜色在人眼前到处乱跑,人也跟着灯光乱跑,急匆匆地浏览,跟商场合影,奔跑着从这个店进去,那个店出来,女士负责挑选,男士负责刷卡和扛包,孩子们负责哭闹和吃零食。到处是震耳欲聋的音乐,人群在一锅煮沸的腊八粥里翻滚着,你在这口锅中,如一个人面对着上下班高峰时期的地铁大厅,看一辆辆列车隆隆而过。
每一家肯德基旁必会有一家麦当劳;这条大街往北面,是有篮球运动员塑料像的利生体育用品店,店门口还有两个球形的蹦极玩具,不时有人花上百十来元过一把瘾;到处都是启功和杰二爷(爱新觉罗·溥杰)的题字。人群中夹杂着衣衫褴褛用长竹竿挑着大麻袋捡可乐瓶子的乞丐,有老夫少妻也有少夫老妻,人们在霓虹灯下狂欢,尽情地狂欢。
王府井,曾经的王府帅府公爷府都已不见了踪影,井也成为一块铸铁的铜牌。被建筑师批评和被商家追捧的大楼设计,座椅、路灯、垃圾桶、车站、电话亭,卸下来天线的无轨电车,它们都在大街上跑着。
藏饰店,店员穿着藏袍,店里放着藏歌,墙上是唐卡和修行者的照片。东华门内的小吃街人来人往,小吃摊的竹扦子上张牙着海星、舞爪着蝎子,点头着蚕蛹和压扁着蜈蚣,它们将下油锅,裹满辣椒面和孜然粉跑进人们的肚肠。孩子们还在数蜈蚣的腿,观察蝎子的尾巴。羊肉串和黏玉米裹着臭豆腐干的味儿从远处飘来。小饰物店中有石粉制成的假玉和驼骨筷子,大明眼镜公司仍有配眼镜的学生。三十八元一袋的真空包装北京烤鸭和十八元一斤的天津大麻花铺满柜台,人们在免费领促销的小袋洗发液排起长队互相推搡,两个散发小广告的团伙暗地火并,小偷们互相照应着向学生模样的女孩的背包下手……这里少了些站街女,少了摇头丸。
夜色的味道很浓,霓虹灯的世界让人想起老上海。老上海的色调会更幽暗、更昏黄,也更柔和。而王府井更有种纷乱的艳丽。
我回忆着从前的老东安市场,那市场都是望不到头的小商家,每家一间不大的屋子,也有的在屋子前出来摆摊。所有人的头顶都有个拱形的铁皮制顶棚,每逢下雨时叮叮咚咚外加哗啦啦地响。这是清末以来北京最早的大型市场,因离东安门近而得名。有一阵改叫“东风”,后来又改了回来。北京人是不爱改口的,把“东安”“东风”混着叫。东安门是皇城东边的门,皇城不是故宫,是二环路以内、故宫以外的一圈城墙,或许这就是北京的“一环”吧。故宫的东门叫东华门。这里是东安门,清末北洋兵变时毁了,现在只剩下遗址。而市场却留了下来,一直留到我小时候,好像它要等我吃玩一番后,才默默地退出历史。它退出了,只剩下王府井的教堂,那时的教堂门口还不是广场,隐藏在一片房子后。
那时的我像只馋猫,那时好吃的真多,糖耳朵、糖葫芦、冰棍,一种广味卤制的卤鸡腿,淡红的颜色,外面的那层皮又甜又腻让人回味很久。这好像是东安市场的东面,而北面好像有一家奶油炸糕,炸得黄中带着棕红的奶油炸糕,里面是鲜黄的奶油色,上面撒落着雪山一样的绵白糖。
每当我发现一种从来没上过糖葫芦的水果串成了糖葫芦,发现一种新型的冰棍,都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有一次我见到了有人举着一种绿色的冰棍,就满处去找,跑遍了东安市场的冰棍摊,满处问有没有卖绿色的冰棍。没有卖时,只好去买蜂蜜冰糖核桃仁做馅、两张圆形白纸一般的面皮的茯苓夹饼,我搞不清茯苓究竟是外层的“白纸”还是里面的馅。茯苓夹饼不仅越做越小,还发展出把果冻一般的软糖来做馅,据说是推出了“新口味”。
真不知是人长大了还是栗羊羹变小了,天知道放久了的艾窝窝会变硬豌豆黄会变味,山楂糕不再酸而杏仁豆腐不再甜。天知道为什么拆了胡同而在商场地下做成模型,人们不再穿长衫而官府菜馆男人装上辫子女人绑上旗头……市场变了,旧京的风物没了,但生活总不会变。就当东安市场是北京的巴黎拱廊街吧,北京的拆了,我们到巴黎去看。
消失的会馆
我们和古代离得并不遥远,比如八〇后一代,很多人从小在老家,还住过几百年以前的老屋,按照老年间(北京话:指过去、从前)的习俗来生活。可下一代却没有这么守旧了,生活被现代化彻底改变。以前,似乎只感觉到了四合院的脏、冷、地方小,冬天烧蜂窝煤、没厕所、没法洗澡,现在“煤改电”了,修给水系统、排水系统也不费劲了。

⊙ 郭大公· 剧场入口
四合院是四面房,可不是四面都有房就能叫四合院。胡同是四合院的载体,在一条宽阔的大胡同中,两边都是错落有致的大门,门内都是深宅大院,午后的阳光穿过胡同中浓密的树枝照到墙上,映出人的影子。有句俗话叫“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在民国时北京的胡同有数千条,现在只有几百条了。南城(崇文、宣武地区)除了前门、珠市口附近留有一部分胡同以外,其他都“身归那世”了。而北城有了金宝街、金融街,沿途也“扫荡”去了不少。
那些多进的四合院都拆了盖楼,改为了学校、机关。而南城有几处古建筑,特别值得记忆一番。北京的会馆多在南城,是明清时期外省的士绅们,在京集资兴建的聚会联络地,相当于驻京办事处。会馆有大有小,建筑多样,南城的很多街上,会馆是一家挨着一家。顺着菜市口往南路东,很容易找到东西向的保安寺街,还能看到保安寺街七号的陕西关中会馆。
关中会馆意义重大又建筑精巧,是陕西商帮的缩影。“陕商”号称为“西秦大贾”“关陕商人”。明清时期,西部贸易几乎被陕商和晋商联手垄断,巨大的财富被他们攒下来流传后世。陕西商人是在康熙乾隆年间发家,会馆也是随之旱地拔葱般地翻建。这里要提一个人,陕西韩城的大学士王杰,他是不少清宫剧中的主角,历史上是他把和珅送上了断头台的。他在乾隆二十六年(公元一七六一年)中了状元,号召集资兴建了这座关中会馆。会馆于一七六二年建成,在民国时还大修了一次,直至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二年陆续拆迁完毕,享年三百五十岁。
关中会馆是金柱大门,门墩是狮子的模样儿,旁边挨着它的院子也是金柱大门。两个大门连着,在胡同里望去很是气派。会馆里是三进院,十几间房,房子不大却很精致,二进院、三进院的正房都是漂亮的小楼,单层的挑高都足四米,每座楼能有近十米高,关中地区的建筑风格充斥其间,这在四合院中不多见。这里楼上楼下都是旧式的门窗,侧面临街的窗户很小,想必是几百年来没太多变化。小楼中部的木构上都刻满了雕花,原先的木头楼梯一时找寻不见,在楼后又修了两座石梯,不过是一层层的水泥台阶,是后来人们上楼的地方。
会馆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倒台而关门大吉。到了民国年间,军阀陈树藩主政陕西,他四处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广种鸦片,横征暴敛,陕西怨声载道。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爆发,陈树藩投靠直系、奉系军阀,强派捐款两百万两,印发纸币五百万元并强换现金,陕西各界开始了强烈的抗议。而陕西居京的学生,集中到这座关中会馆里来开了“驱陈大会”,并致电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身为陕西三原人的于右任请予支持,最终在一九二一年五月,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陈树藩。
尘埃总有落尽的一天。二〇一二年七月,关中会馆被全部拆除。
而不远处的南横东街一百三十一号,曾经是会同四译馆。
走到宣武区东西向的南横东街上,从前的景观是南北两边都是古朴的平房,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南边是老式的楼房,北面是胡同;如今北面成了新式高楼,玻璃窗上反射的阳光映得人眼睛发花。在北面的楼群中,有一座新建起来的庙宇似的建筑,是会同四译馆。
会同四译馆,又名会同馆、四夷馆、四译馆,是中国元、明、清三代朝廷接待外国进贡使者的地方,相当于礼部下属一个司级的衙门。这个机构要翻译来往的书信文件,组织编纂外国史志,培养通译,接待来华使者的食宿等。这组织在京城内有很多馆舍,到了乾嘉年间,往来的外事人员越来越多,内城的馆舍开始紧张起来,有不少馆舍又缺乏修理有碍观瞻,就把朝鲜、越南、琉球、回部往来的使臣安置在南横东街这里。在《宣南鸿雪图志》中,还特意标出了这座“会同四译馆”。
建筑是个很古老的建筑,有影壁、前后大殿,还有个西跨院,呈现明末清初的风格,前殿是个三开间硬山脊,主殿是三开间的庑殿顶,黑色的琉璃瓦。庑殿顶是古建的最高样式,一般用庑殿顶的建筑很少,多是明代的特征,故宫的太和殿是重檐庑殿顶。据说这里还曾保留一扇木制的屏风,上面的雕刻是日本风格,推测是琉球使者进贡时留下的。院中更是古树参天。
曾经有争议说这里是一座古寺,但不管这里曾用做什么,它都有过二百五十岁以上的年纪。迁建怕是做不到将建筑物整体原地抬起来往旁边搬家,技术上还不成熟;也做不到把所有的砖瓦木构一一编号重新组装,这样还是太费钱了。至于拆了是否复建一个,也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仿佛是一夜之间,游客们都要进个老房子看看,而住在老房子中的人却是越来越少。老房子拆了,能回迁的就地上楼,不能回迁的搬到郊区。
任何事情都有得有失,你想右手拿到些东西,必须把左手得到的放掉。我们有了手机,那就必然不会写信;有了高铁,那永定河就必然断流。要盖新楼,老房子就必然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沦为废墟。
小吃天堂
每逢冬日漂流在外,日子久了开始想家,这时我总能看到路边有一个脏兮兮的小摊,里面用白瓷盘摆满了黑乎乎烂糟糟的糖葫芦,旁边一个大牌子:正宗北京大糖堆。那种感觉就像进了胡同,我会毫不犹豫地去买而顾不得是否会吃坏,并告诉他们,北京叫糖葫芦而天津才叫糖堆儿。糖葫芦不是摆在瓷盘里,而是绑在大扫帚棍上卖的。
北京是天子脚下,却没有什么北京菜,有也是各路菜系的改良和满蒙等民族的菜肴。至于官府菜私家菜更是渲染而已,大清国的工作餐就是官府菜;自己做饭甭管好吃不好吃都叫私家菜,更是没有什么风味了。但北京却有自己的小吃,这小吃是从有皇上有城墙的时候,吃到了没皇上没城墙的时候;从王公大臣吃到普通百姓,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既然是小吃,就要小,小到可以拿着满大街走着吃。味道要浓,吃一次就记住,离得老远就能闻见。坛子肉不是小吃,不能举个大坛子满街溜达,累了放下,拿牙签扎两个这么吃。
我住北新桥,在簋街没有兴旺时,东直门内一到傍晚是一拉溜的夜市小吃。但我对这没有什么兴趣,而是北新桥十字路口东南角,现在地铁站的位置,却是一家不错的冷食店。每天傍晚,母亲总是带着我去逛东直门的夜市,却从不在那里吃东西,返回时去那小店吃杏仁豆腐和奶酪,及各种口味的水晶糕、可可儿糕。一个小巧的盘子里放上一扁块晶莹剔透果冻般的甜品,上面再放几枚樱桃山楂之类的果料,足以让一个孩子去天堂玩一圈了。这也许不是个恰当的比方,但一想,那如玉般洁白醇香的杏仁豆腐在冰凉的糖水中,一把小瓷勺在里小心翼翼,生怕把杏仁豆腐弄碎。到口中不是碎,而是化了,便想不到什么更好的词来形容。至今梅园冷饮店开得到处都是,我只想一个人去坐坐,找找儿时杏仁豆腐的滋味。不像别人,要想着怎样和哥们打嚓(北京话:指拿别人说笑、寻开心),怎样哄女朋友开心。
春天没有豆沙馅的春卷,夏天没有冰镇的酸梅汤,秋天没有赛过梨的心里美萝卜,冬天没有山里红的冰糖葫芦,再从四合院中搬进了二十四层的塔楼,耳边听不到儿时的吆喝,这种生活也就不是北京的生活。北京的生活要在吃完金拱门和肯德基之余,还要到附近的稻香村买一斤栗子羹或羊肝羹,再给未来的丈母娘带上几盒茯苓夹饼。当小吃店逐一加入某家饮食集团时,他们的味道就和价格一样统一了,也都成了某家饮食集团的味,而不是小吃的味了。为了吃小吃,只能再去残存的后海河沿,爆肚张家的果子干,牛街小巷里的清真小铺,和磁器口的老豆汁店了。而那里的豆汁总是出沉淀,在北京人看来,这是没熬开。
说起旧京小吃中的极品——豆汁,我总是不断地告诉别人一个形而上的真理:“豆汁和豆浆的本质区别是:豆浆是黄豆做的,豆汁是绿豆做的。”这真理我一直在不懈地普及着,可效果甚微。那些说豆汁如何馊,灌肠如何臭,炸糕是如何油的人,却不知自己一代代是靠这馊食臭食与油食养育长大传宗接代的。我刚学会骑车不久,从北新桥骑到右安门去看金中都(金朝一共有“上京”“中都”“南京”三个首都,“上京”在会宁,“中都”在北京,“南京”在开封)时的城墙。那一天太阳暴晒无比,晃晃悠悠地骑车至几近虚脱。终于,我骑到了牛街,发现了一个凉豆汁店。店不大,像过去胡同口山西人开的大酒缸,供人们在那里站着喝酒用,也就像《孔乙己》里写的那种小酒店。而这个豆汁店的几个大缸里全是满满的凉豆汁,一块钱一位,喝饱了算。豆汁在浇花用的水舀子和粗瓷大碗之间交错着,那时正看了《水浒传》,喝豆汁时学了一回山大王。牛街改造成高楼林立的社区,回族兄弟们告诉我,过开斋节不如从前热闹了,而那魂牵梦萦的凉豆汁店也不知去哪儿了。
怀旧是极易引发的。穿出件几十年前流行的衣服叫老土,而吃几十年前流行的饭菜却叫时尚。野菜窝头都进了大饭店,而北京的小吃却越吃越变了味儿。——不好吃了。儿时那种走街串巷卖豆汁麻豆腐的,如今都搬到了东华门的夜市,搞旅游蒙蒙外省人罢了。
时代变了,小吃也在变。那么多家曾经的老字号小吃店一一关了张,要么就是合并装修,改成大饭店开业。都大饭店了,那还叫小吃吗?只带来价格的飙涨和味道的不存。价格涨了会降下来,而味道失了很难找回来。生活节奏在加快,因为没有时间做饭,人们去吃快餐叫外卖,自己做小吃就更不可能了。做小吃又麻烦又不赚钱,会做的老师傅们渐渐离世,而徒弟拿不起活儿,或干脆跑了改行。家传的是传不下去了,孩子没人愿意做一辈子小吃,收徒弟又都是外地人,把不住老北京的口味。年轻人不吃中餐都去M或KFC,上海荣华鸡之类的国产快餐又竞争不过。虽然还有烤鸭和涮肉,但在北京能吃到的美味和饮食带来的享受还是越来越少了。马蹄烧饼失传了,炸油鬼失传了,南府苏造肉失传了,羊霜肠也失传了;总之,都见不到有卖的了。
豌豆黄越来越小,艾窝窝越来越硬,豆面糕越来越不甜,糖耳朵干得能当武器了;稻香村依旧过年过节排大队,隆福寺、护国寺小吃街依旧兴旺,东华门依旧是各地旅行团集中的地方;过年过节的庙会小吃除了涨价还是那样,小吃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味变了,难吃了,而没变的是失传了,或者见不到了。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样子”。我想说天堂也应该是小吃店或美食街的样子,要一边喝冰镇酸梅汤一边看小人书才是。因为见到小吃不仅是吃,不仅是童年和家,还是某地文化的存留,是一带风物人情的集合。对孩子来说,出去吃小吃好比上了一趟天堂。按照成人的观念,一提上天堂容易联想到死亡,可孩子不会,他们觉得只有天堂才会聚集了那么多好吃的。也许,那就是我们回不去的童年与故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