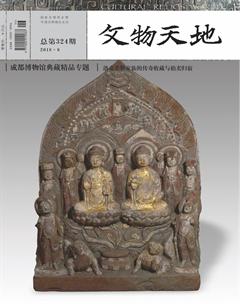成都博物馆藏蜀王陵出土陶俑初探
方若素



俑是专用以陪葬的人形或动物形明器。以俑随葬在我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夏商时期有以活人殉葬的习俗,随着以各种材质制作的俑的兴盛,以俑随葬逐渐取代了人殉,并逐步成为丧葬器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出土有规模浩大、组合固定、排列有序的陪葬俑群,被认为是墓主生前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俑的制作与使用于商代末期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萌芽,秦汉时期勃兴,隋唐进一步发展,宋以后逐渐衰微[1],但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明代,为达到“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巩固明王朝统治秩序的目的,朱元璋曾先后三次分封诸皇子为亲王,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封藩制度,对诸王的名封婚禄、礼乐仪仗、官属护卫,宫殿宗社以及丧葬陵寝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套制度被明朝历代皇帝奉为万世不变的祖制,一直延续至明末。全国的名都大邑与边陲要塞皆在分封范围之内,藩王生前在当地享受着“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尊崇待遇,死后则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营造规模巨大的“地下宫殿”。在各地的藩王墓中,保存完好者出土文物数目多者成百上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规模浩大、类型多样的陪葬俑群,如山东邹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木雕彩绘仪仗俑群,人物、车马及仪仗器共计730件(套)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各类陶俑总计202件[3];陕西西安秦简王朱诚泳墓出土的彩绘陶仪仗俑群,计有320余件'明宗室墓葬出土陶俑群对于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明代宗藩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是明代藩王墓葬最典型的一大特征。
成都博物馆古代史陈列明清部分“丹楼生晚辉——明清时期的成都”就展出了一组出土于成都东南郊潘家沟蜀王陵的陶俑。本文选取了部分不同类别的陶俑,试作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一、陶俑的分类
有明一代,成都为蜀王封地。从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分封第一代蜀王朱椿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末代蜀王朱至澍投井为止,蜀藩共历10世13王,总计267年,与明王朝同时告终[5]。作为四川全省范围内唯一的宗藩,蜀王不仅在当时对成都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历史遗存。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基础建设工程的推进,陆续有明代蜀藩王陵墓在成都北郊、东南郊被发掘清理[6]。
成都地区目前已经过科学发掘的蜀藩陵墓包括1970年发掘的凤凰山悼庄世子朱悦熑墓[7]、1979年发掘的十陵镇蜀僖朱友壎墓[8]、1991年发掘的十陵镇蜀昭王朱宾瀚墓、1997年发掘的潘家沟无谥蜀王陵及其史妃墓、1999年发掘的琉璃乡潘家沟蜀王次妃王氏墓[9]、2004年发掘的蜀怀王朱申凿及其正妃徐氏之合葬墓[10]。根据目前已公布的发掘资料,大多数陵墓地宫均多次遭到盗掘,地宫内器物遭到不同程度的扰动与破坏,留存物多为陶质模型明器,其中又以陶俑数量最多。
在明代蜀藩陵墓出土的陶俑中,除明初朱悦嫌墓陶俑烧造水平相对较高外,其他蜀藩陵出土的模制陶俑,或因陶俑主要作为明器使用之故,造型普遍较为粗率,大多数陶俑胎釉结合疏松,烧制温度较低,出土时釉彩剥落较为严重,因而艺术价值并不能算太高。但出土陶俑往往规模庞大,类型丰富,一般有武士俑、乐俑、仪仗俑、侍从俑与文官俑等几类。保存相对完整者如悼庄世子墓出土陶俑500余件,蜀僖王陵出土陶俑达425件。这些陶俑虽刻画粗糙,但大致表现出了服饰、动作上的差别,加之其组合关系与方位布局,我们仍能从其中获取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成都博物馆展出的一组彩釉陶俑,来自于一座无谥蜀王陵。陶俑人物造型尤其是面部较为粗率,衣纹线条稚拙僵硬,但陶俑均有彩绘或施以彩釉,服色亮丽,细节丰富,较为少见。由于该陵墓尚未公布原始发掘资料,在此对该组陶俑的代表类型分别进行详细介绍,并结合藩王陵墓出土陶俑分析解读。
潘家沟无谥蜀王陵出土陶俑主要有以下几类:
1.武士俑
彩绘陶将军俑(图一),高91厘米,边长33.5厘米,端立于朱红色方形台座上。黑髯红唇,怒目圆睁,头戴凤翅兜鍪,后缀顿项。肩披项巾,巾上绘红点花纹。披鑲红边黄褐色身甲,着浅黄色窄袖战袍。腰系带。朱红色腿裙下露出身甲。足着黑靴。双手上下叠放于胸前呈握执状,所执物已失。彩绘陶将军俑(图二),高84.5厘米,边长34.5厘米,端立于朱红色方形台座上。大眼圆睁,头戴凤翅兜鍪,顶有朱红璎饰,后缀顿项。肩披白地红点小花项巾,着镶浅黄边朱红色身甲及护臂,肩甲上饰兽头,下有衣袍飞出。腰束革带,朱红色腿裙下露出身甲,足着黑靴。双手亦上下叠放于胸前呈握执状,所执物已失。
这两尊将军俑彩绘清晰,雕刻细腻,同墓中其他陶俑相比,尺寸较大。成都地区已发掘蜀王陵也出土有这种头戴风翅兜鍪、身披铠甲、持物站立的武士俑,高度多在60厘米左右。蜀僖王墓出土武士俑手持物仍可辨认,为方天画戟或板斧;悼庄世子墓前庭两厢各有3名武士俑,手中持矛,腰佩弓箭,正殿门前两侧还有两名高84厘米的武士俑,形制与前庭武士俑相似。山东鲁荒王墓也中有两件此类木雕武士俑,出土时位于前室门外东西两侧,持长柄金瓜[11]。这类俑的盗甲与明代武士一般穿戴的笠形盗和鸳鸯战袍有较大区别,不似实用铠甲,有较强艺术化处理,其高度与其他俑亦有明显区别。《明集礼》中记载:“初,洪武二年,敕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乐工十六,执仪伏二十四,控士六,女使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四,门神二,武士十,并以木造,各高一尺。……后定制,公、侯九十事者准此行之。余以次减杀。”结合其放置位置可知,这类武士俑应为“门神”,主要承担守护墓葬的职能。
2.乐俑
彩釉陶乐俑(图三),宽11.5、厚11.9、高36.4厘米,立于方形台座之上。头戴镶边圆帽,着黄色圆领窄袖长衫,腰束黄色绦带,足蹬皂靴。抱琴。彩釉陶乐俑(图四),宽11.5、厚10、高36.2厘米,立于方形台座之上。头戴镶边圆帽,着绿色圆领窄袖长衫,当胸饰方形黄花,腰束绦带,足蹬皂靴。双手举于肩上,一手已残断,一手举于嘴边,手中所执物不存,似乎正在吹笛。
乐俑是蜀藩陵墓出土陶俑中的基本类型之一。悼庄世子墓中庭两厢及正殿后都发现了乐俑,中庭两厢各有一排乐俑,戴黑色金鹅帽,着穿盘领窄袖黄褐色长衫,正殿后为五人一组,四人抬鼓。蜀怀王陵墓出土乐俑见于报告者,有击鼓俑与吹笙俑,头戴笠帽,着绿色右衽窄袖长衫。山东鲁荒王墓中乐俑共计42件,手持各种乐器,较为完整,包括吹笙俑、击拍板俑、吹笛俑、吹箫俑、击鼓俑等,头戴黑色筒式平顶冠,着盘领长衫。江西益庄王墓简报中报告有弹琵琶、拨月琴以及笙、箫、鼓、笛之俑。此类乐俑应属王府宫廷宴乐中的乐工。
据《明史·乐志》,明代宫廷宴乐乐队的演奏形式为台阶旁由歌工和乐工唱奏,台阶下由舞士们表演舞蹈。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乐器分配,以演奏不同类型的乐曲。作为皇家礼制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宫廷音乐也被反映在明器模型中。另据《明史·舆服志》,洪武十五年(1382)规定了王府乐工冠服,“凡朝贺用大乐宴礼,七奏乐乐工倶红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有花鼓吹冠,锦臂韝,皂靴,抹额以红罗彩画,束腰以红绢。其余乐工用绿绡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无花鼓吹冠,抹额以红绢彩画,束腰以红绢”[12]。但由于陶俑均为明器,制作并不能完全刻画出典章制度之规定,乐俑的服饰也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和地域差异。
3.仪仗俑
彩釉陶仪仗俑(图五),宽12、厚11.2、高37.5厘米,立于方形台座之上。头戴乌纱帽,着黄色圆领窄袖长衫,腰束革带,足蹬皂靴。双手举于胸前,作捧物状,所捧物不存。彩釉陶仪仗俑(图六),宽11.2、厚10.1、高36.9厘米,立于方形台座之上。头戴黑色圆顶笠帽,着黄色交领右衽长衫,腰束绦带,足蹬皂靴。双手一上一下置于胸腹前,做执物状,所执物不存。与蜀僖王陵出土陶仪仗俑相类。
彩釉陶骑马仪仗俑(图七),长26.5、宽10.7、高34.8厘米,立于长方形台座上。骑俑头戴黑色圆顶笠帽,身着黄色交领右衽长衫,足踏马镫,端坐于马上,双手一上一下置于胸腹前,做执物状,但所执物不存。胯下之马略显矮小,四肢粗短,身未施釉,马身绘有凌乱的黑彩,马鬃、马尾与四蹄涂黑,鞍鞯齐备,施黑釉。蜀怀王陵墓出土骑马仪仗俑形制与其尤其类似。彩釉陶骑马鼓吹俑(图八),长19.6、宽11.9、高35.6厘米,立于长方形台座上。骑俑头戴黑色圆顶笠帽,身着黄色交领右衽长衫,领、袖、下裙为黑色,足踏马镫,端坐于马上,胸前置一鼓,手已残断,应作持鼓或击鼓状。胯下之马矮小粗壮,马身绘有彩,黑马鬃,鞍鞯齐备,施黑釉。鼓吹是明代军礼用乐的三种主要形式之一,与前文所述手持鼓、琴的立式乐俑不同,此件骑马俑即属于军礼用乐系统,是出行仪仗中的重要一环。彩釉陶骑马武士俑(图九),长20.9、宽11.3、高34厘米,立于长方形台座上。骑俑头戴黑色圆顶笠帽,身着黑色交领右衽长衫,腰系革带,佩刀,足踏马镫,端坐于马上,双手置于胸前,仍做执物状,但所执物不存。胯下之马矮小粗壮,马身無釉,但绘有黄色点彩,马鬃、鞍鞯与络头施绿釉。蜀怀王陵出土也有骑马武士俑,区别之处在于其腰佩弓箭,身穿铠甲。
仪仗俑是藩王随葬俑群中数目最大的一部分。洪武六年,太祖朱元璋曾制定亲王仪仗:“宫门外设方色旗二,青色白泽旗二,执人服随旗色,并戎服。殿下,绛引幡二,戟氅二,戈氅二,仪镗氅二,皆校尉执。殿前,班剑二,吾杖二,立瓜二,卧瓜二,仪刀二,镫杖二,骨朵二,斧二,响节八,皆校尉执。殿门,交椅一,脚踏一,水罐一,水盆一,团扇四,盖二,皆校尉执。殿上,拂子二,香炉一,香合一,唾壶一,唾盂一。”[13]此后洪武十六年、建文四年及永乐三年对仪仗器具略有调整,但整体规制不变。鲁荒王墓中甚至出土了保存相对完好的木质仪杖明器,包括班剑、戟、槊、金瓜、钺、仪镗、响节、伞等,大略与规制相吻合。潘家沟蜀王陵仪仗俑手中所执之物即或为不同类型的兵杖。
我国古代帝王的仪仗最初起源于扈驾之卫士。如《周礼》中的虎贲之士本是负责保卫周王及宫廷安全的士卒,后逐渐在庆典、出巡、丧葬等仪式举行时,履行仪仗职能,成为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逐步完善形成特有之规制。兼有护卫与礼仪功能的皇家仪卫制度,滥觞于先秦,成型于汉晋,发展并鼎盛于隋唐宋元,至明清已形成承袭有绪的完备制度。正如《明史》所言,就仪卫制度而言,“历代制度虽有沿革异同,总以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慎重则尊严,尊严则整肃,是故文谓之仪,武谓之卫”[14]。因而自秦汉时期开始,高等级墓葬尤其流行以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等表现出行与仪仗场景,而随葬俑相比二维图像而言更加直观立体,是表现这类题材的重要载体。
4.侍从俑
彩釉陶侍从俑(图十),宽11.6、厚8.6、高37.4厘米,立于方形台座之上。头戴高冠,着黑色交领右衽长衫,腰束革带,足蹬皂靴,领、下裙两侧及革带施绿彩。垂手扶革带站立。彩釉陶侍从俑(图十一),宽11.8、厚11.1、高36.1厘米,立于方形台座之上。头戴乌纱帽,着黑色圆领窄袖长衫,腰束黄色革带,足蹬皂靴。双手上下举于胸前,做执物状,所执物不存。彩釉陶侍从俑(图十二),宽11、厚9、高36.5厘米,立于方形台座之上。头戴方冠,着黑色圆领长衫,袖微宽,胸前有黄色方形花纹,足蹬皂靴。双手相握胸前,做捧物状,所捧物不存。这组俑头戴乌纱帽或高冠,多系革带,或拱手或垂手。悼庄世子墓、蜀僖王墓、蜀怀王墓皆出土有侍俑,据报告这类俑一般位于墓室后殿,其身份或为王府中的内使或侍者。
二、陶俑的空间配置与意涵
中国古代素有为墓主人营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死后世界的传统,以使墓主人即使在地下亦能永享其在生前曾经拥有或渴望拥有的富贵安乐。具体而言,墓室空间与其中的图像、陈设互相配合,共同构建起不同的生活场景,最终为墓主人创造了一个象征意义强烈的永恒空间[15]。上文所介绍的这批微缩化陶俑类型众多,包括武士俑、乐俑、仪仗俑、侍从俑等,都是蜀王构建地下宫殿的重要“道具”。其组合关系与空间配置都是丧葬观念的产物。由于潘家沟蜀王陵尚未公布原始资料,我们只能借助其他蜀藩陵墓探索蜀藩陵墓陶俑的一般空间配置与蕴藏的意涵。
根据既有考古材料,蜀藩陵寝布局具有高度一致性,蜀王地宫布局皆以中轴线为基准,从墓室八字门开始,依次建造前庭、正庭、正殿、中庭、圜殿与后殿,庭两侧布局廊庑厢房,门楼与殿堂均为仿木建筑结构,部分甚至加盖琉璃建筑构件,与地上王府的建筑格局基本一致,可谓从王宫制度浓缩简化而来,直接反映了“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
而据悼庄世子墓发掘简报对陶俑在地宫中布局的记述,前庭两厢为武士俑及马俑。正庭左右两厢各有三排仪仗俑,第一排为牵马俑,第二排为乐俑,第三排为兵仗俑,左厢,右厢。正殿两侧各有武士俑两尊。中庭有五名击鼓俑,四人抬鼓,一人敲鼓。中庭两厢则以象辂为中心构成了庞大的仪仗俑群:象辂前置六匹马和九个牵马俑。
象辂两边各置三排仪仗俑。第一排除牵马俑外,皆手执乐器,第二、三排的仪仗俑执不同类型的兵仗。左厢仪仗俑共157件,右厢仪仗俑共154件。后殿两侧排列侍俑,后殿中室沿墙依次排列面向棺室的侍从俑(图十三)。由此,我们可以借此推知蜀藩陵墓中陶俑的组合及其布局是如何具体构成了不同场景,并真正为蜀王创造出一个与其生前世界高度重叠的地下世界。前庭是整个墓室建筑的前导空间,在前庭安放“神化”的武士俑表示从此已经进入不属于生者的神圣空间。正庭、正殿、中庭与圜殿实际上对应的是地上王府自端礼门开始至存心殿而终的区域,是墓主人治事议政、举行仪典的空间,因此,仪仗俑与乐俑在此组成仪仗队,表现墓主人生前出行设宴时的隆重场面;最后的后殿对应王府的寝殿,属于墓主人起居生活的空间,则主要以负责墓主日常起居的侍从俑填充。由此,充满仿木建筑元素的石质墓室空间与分布有序的各类随葬俑相互配合,进一步强化了以“地宫”拟“王宫”的丧葬观念,并最终构建起蜀王的地下王宫。
[1]长谷部乐、刘志国:《中国陶俑的历史》,《陶瓷研究》1991年第3期,第156—158页。
[2]山东博物馆:《鲁荒王墓》,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31页。
[1 2 3]佚名:《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第48_52页。
[4]肖健一:《明秦藩家族谱系及墓葬分布初探》,《考古与文物》2007 8 9 * * * 13 14 15年第2期,第93—98页。
[5]陈世松、李映发:《成都通史》卷五《元明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6]薛登、方全明:《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第21_37页。
[7]佚名:《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第306—313 頁。
[8]翁善良、朱绍文、卢引科等:《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第41_54页。
[9]卢引科、刘骏、李绪成等:《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成都考古发现》1999年。
[10]谢涛、颜劲松、荣远大等:《成都市三圣乡明蜀“怀王”墓》,《成都考古发现》2005年。
[11]同[2],第 208 页。
U2](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6册。
[13]同[12]。
[14]同[12]。
[15]巫鸿:《黄泉下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