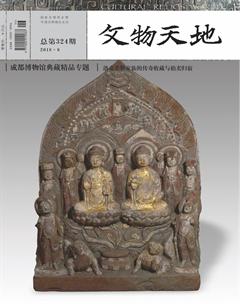舞转回红袖 歌愁敛翠钿
张宝琳



巴蜀地区是我国汉代画像砖(石)发现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选取成都博物馆藏六块乐舞百戏题材画像砖,展示两千年前的汉代成都人民丰富多彩的娱乐场景。
一、刻线成舞:成都博物馆藏舞蹈画像砖
西晋左思《蜀都赋》载:“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飇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1]可见当时成都城内,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宴请宾客时的场面,择一良辰吉日,赌酒促席,乐者抚琴击节、舞者伴之,热闹非凡。
歌舞宴乐画像砖(图一)[2],方形砖,画面可见六人,属小型宴饮场面。右上方两人席地而坐,为观舞者,男子头戴高冠,身着长服,女子头挽双发髻,面前放置有杯、案等物。左上方同样席地而坐两人,均身着广袖长服,男子双臂前伸,双手正在鼓瑟,瑟一端放于腿上,尾端置于地,身份或为“乐正”。旁有一女子,头挽高发髻,应为歌者。下方两人,头戴高冠长服者,躬身站立,点鼓打拍,以助舞势;右边舞者,戴冠着广袖长服,举袖起舞,长袍拂地,衣袖翻折。
歌舞杂技画像砖(图二)[3],方形砖,图像可划分为上、下、左、右四部分,整个宴饮场面颇具规模。画面左上席地而坐二人,男子头上戴冠,身穿宽袖长袍,女子头上梳双髻,应为观赏者。右上为杂耍场面,二人均上身赤裸,梳椎髻,一人双手跳七丸;另一人左肘立瓶,右手应为执剑跳丸。左下方跽坐两位吹奏排箫的乐人。右下方男女两伎配合舞蹈,男伎梳椎髻,头上带有发饰,上身赤裸,下穿阔裤,作屈膝状,手中执鞞鼓,为倡优形象[4];女舞者,头挽双发髻,腰间束带,手中执拂,拂尾飘扬,左脚向后提起,脚下似踏物行走起舞。
杂技盘舞画像砖(图三),长方形砖,共2块,应为同模所制。画面有三伎人,左边为杂技场面,共有七案相叠,最上面有一女伎人,头上梳双发髻,身穿贴身衣服,在倒立的同时,利用下腰,两脚弯曲向前,为之“反弓”。中间一人,为倡优形象,头梳椎髻,上身袒露,下穿阔裤,半蹲姿态,正在表演跳丸。右边女伎,为舞者,头梳双发髻,身穿广袖束身衣,双手执拂起舞,脚下置鼓、盘,舞者左脚上提,跳跃于鼓面。
鞞舞画像砖(图四),长方形砖,砖面3人,砖面上方有廊。左侧一人,倡优形象,上身袒露,着裤赤足,做滑稽表演,左手握鞞鼓。中间伎人,为舞者,头上戴冠,身穿广袖长服,腰间有束带,腿微曲,翩然起舞。右侧一人袒露上身,下穿阔裤,昂首举臂,手中似为舞剑,右脚上提踏鼓,以鼓点掌握舞蹈节奏。
宴饮观舞画像砖(图五),长方形砖,左上角残缺。画面为乐舞场面,左侧两人席地而坐,一人鼓瑟,瑟两端置于二者腿上;另一人面部残缺,右手微微抬起,或许为歌者。右侧画面为一男一女正在对舞,居左边者为女子,身穿博袖长服,束腰,双腿略微屈蹲,举臂舞蹈;男子着博袖素衣,下穿长裤,右脚独立站姿,左脚向后勾起舞蹈。
二、翥凤翔鸾:常见的汉舞表演形式
汉舞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融合了外来文化的因素,表演形式受到杂技、武术、说唱的影响向高难度发展,乐舞百戏的共同出现,扩大了舞蹈的表现能力,丰富了传情达意的手段,民间百戏俗舞逐渐备受人们喜爱。六块画像砖中的舞蹈形式,包括长袖舞、拂舞、盘鼓舞、鞞舞四种,基本上涵盖了当时成都地区较为普遍流行的舞蹈形式,本文仅简要介绍以上四种。此外,建鼓舞、剑舞、驼舞也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俗乐舞蹈形式,灵星舞则是祭祀后稷的特殊舞蹈形式。四川地区还有一种特有的舞蹈——巴渝舞,多出现在崖墓的石棺图像中。
(一)长袖舞
长袖舞,是我国古代最为流行的舞蹈形式,基本特征是舞者手中不执任何物品,以舞蹈衣袖为主,运用长袖交错飞扬表达舞蹈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舞赋》载:“罗衣从风,长袖交横。”[5]其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今,现代戏剧中的水袖,便是继承和发展的典型代表。有关于长袖舞的文献记载,早在周代便已出现,《周礼·春官·乐师》载:“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郑司农云:“人舞者,手舞……人舞无所执,以手袖为威仪。”[6]至战国时期,《韩非子·五蠢》载:“长袖善舞,多钱善贾。”[7]汉代,是长袖舞的发展时期,《西京杂记》载:“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8]受此影响,汉代长袖舞图像常常呈现“翘袖折腰”之势,注重腰部与衣袖的线条,两者相互呼应,突出女性舞者的柔美,也因此长袖舞舞姿极其富有美感。这种舞蹈形式,在画像砖(石)和陶俑等考古资料中是最常见的。
馆藏六块画像砖中,歌舞宴乐画像砖、鞞舞画像砖及宴饮观舞画像砖中带有长袖舞者形象,按照衣袖可分为两类:广袖(图六),又被称为博袖,通常泛指袂部宽大的样式;套袖(图七),指从博袖之内延伸出一截直袖型的窄长袖,是蜀地舞者衣着最为普遍的袖式[7]。除了在衣袖上有所区别外,舞者均身穿长服,上半身弯折幅度较小,以腰间的束带略凸显出“折腰”之姿。因长服及地,舞者动作主要以头部回望、手臂上举、腿部微屈为主,看起来有着厚重繁缛之感,却又体现出端庄雍容。这一点与山东、河南等地有所不同,兩地发现的画像砖(石)的舞蹈图像上,舞者腰肢纤细,长袖飞扬,舞姿轻快飘逸,婀娜多姿(图八、图九)[10]。
(二)拂舞
拂舞原为江南地区的民间舞蹈形式,后釆选进入宫中供皇亲国戚们欣赏,并用于宴享乐舞。关于拂舞的起源,学术界普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三国东吴时期[11],《晋书·乐至》有载:“拂舞,出自江左。旧云吴舞,捡其歌,非吴辞也。”[12]另一种观点认为拂舞起源于汉代[13],《乐府诗集卷五十三·舞曲歌辞二》载:“汉、魏已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14]按照《晋书》记载,拂舞词赋保存有五篇,分别为《白鸠》《济济》《独禄》《碣石》《淮南王》。其中关于《淮南王》的作者《古今注》载:“《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15]认为此篇应为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所作《碣石》则为曹操东汉末年之作《白鸠》为拂舞传入孙吴后才釆用[16]。萧亢达先生便是以《拂舞》釆用的词赋演变过程,认为其起源于西汉。
拂舞极易与巾舞、长袖幅混淆,同样是因其所用舞具而得名,其特点是有柄可持,一端系以麈尾或麻绳、旄牛尾等物,并以所系物名之[17]。分为长拂和短拂两种,通常女性舞者执长拂,姿态婉转绰约,多出现在巴蜀地区的画像砖图案中,如歌舞杂技画像砖、杂技盘舞画像砖(图十);中原地区发现的拂舞画像砖中,多是男性舞者,手执短拂,舞姿阳刚豪放,如山东滕州大郭汉舞画像石(图十一)[18]。
(三)盘鼓舞
盘鼓舞,其起源现无法考证,约在魏晋时期逐渐失传。在汉画像砖(石)资料中,带有盘鼓舞形象的很多,足以见得这种舞蹈形式在汉时的受欢迎程度。与其他舞蹈形式相比,盘鼓舞极其注重艺术技巧,运用放于地上的盘或鼓,完成難度较大的动作,或飞舞长袖,或踩鼓下腰,或按鼓倒立,或身俯鼓面,手、膝、足皆触及鼓面拍击,或单腿立鼓上,或正从鼓上纵身跳下。《淮南子·修务训》载:“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骛。”[19]盘鼓舞在画像砖(石)图案中,经常与杂技、倡优等共同出现,两者间相互呼应,使画面更加生动,表达整体欢乐的气氛,值染出诙谐活泼的艺术风格。
按照人数来分,可以将其分为独舞、对舞和群舞。独舞,是画像资料中最常刻画的表现形式(图十二、图十三)[20],有的单独出现,也有的与百戏形象一同出现,但独舞形象中感受不到舞者与倡优之间的互动。这与对舞不同,对舞中,踏鼓或踏盘舞者边有倡优伴舞,明显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有配合动作(图十四、图十五)[21]。群舞,在现发现的盘鼓舞图像资料中,较为少见,以二到三人为主,具有一定组织性,进行表演(图十六)[22]。傅毅《舞赋》中有所体现,载:“于是合场递进,按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轶态横出,瑰姿谲起。眄般鼓则腾清眸,吐哇咬则发皓齿。”[23]此外,通过对图像资料的研究,可以发现盘鼓舞的舞蹈形式中,作为舞具的盘、鼓并不是一定要共同出现。以馆藏的三块带有盘鼓舞形象的画像砖来看,鞞舞画像砖中,独舞形象的倡优艺人,脚下仅踏有一鼓,以鼓为中心进行表演,舞蹈动作幅度非常有限(图十三);歌舞杂技画像砖中,执拂舞者脚下倒扣三个盘,从动作上看,应该是手上挥拂,脚下踏盘,在盘上行走表演(图十),文献中也有所记载:“搦纤腰而互折……历七盘而蹤蹑”[24];杂技盘舞画像砖中(图三),舞者腾跃于鼓上,足踏鼓面击打节奏,手上配合完成动作,这种表演形式在汉代画像砖(石)资料中是最常见的,充分表现了盘鼓舞所具有的欢快的旋律感。
(四)鞞舞
鞞舞的起源现无从考证,流行于民间,汉代开始在宫廷宴饮中出现,文献记载“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25]。所用舞具为鞞鼓,属鼗类,在乐舞中为辅助乐器。《宋书》载:“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谓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则鞀、鞞即鞉类也。”鞞舞的表演形式结合了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本为民间俗乐舞,舞蹈诙谐活泼,后因演出环境所致,观赏者对其表演的艺术性有所提高,画面中便带有一定的礼节性,也因此图像资料较少。现今发现的画像砖(石)上,鞞舞常常以集体形象出现,舞者衣着也随着表演场所的变化而逐渐庄重(图十七、图十八)[26],如在安徽宿县褚兰镇汉画像石墓中发现观舞图画像石,上刻画舞女多达20人,其中7人执鞞鼓,表演鞞舞[27]。流传至蜀地后,与俳优融合,加入了说唱形式,形成了自身特点,较之北方,世俗化气息更加明显,如馆藏鞞舞画像砖及歌舞杂技画像砖中的鞞舞舞者形象,均为男性,上身赤裸,以倡优形象出现,以配角的身份出现于女性舞者边,为之伴舞,鲜少有独舞(图十九)。
三、歌台舞榭:画像砖所见的表演场合
通常皇室贵族及豪富大吏家中会豢养乐舞艺人,用来在宴请时表演助兴,很少有民间表演的记载。有学者通过对文物资料的研究,认为当时的乐舞百戏表演主要是厅堂、殿庭、广场三种场合[28]。
馆藏歌舞宴乐画像砖(图一)、歌舞杂技画像砖(图二)、宴饮观舞画像砖(图五)应属于家庭式小型的宴飨场合。厅堂是汉代较为正规的宴饮场合,多是达官豪吏自娱或宴请宾客。《蜀都赋》有载:“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善曰:曹植《箜篌引》曰:置酒高殿上。”[29]因此,在画像砖(石)资料中最常出现。
大型的乐舞百戏表演,受厅堂场地面积和杂耍表演规模所限,往往会改在堂前的庭院内。叠案反弓的形象在河南、山东等地的画像砖(石)上发现较少,四川郫县东汉石棺上的宴饮乐舞百戏图中有所体现,宾主坐于堂前观赏,艺人在庭院中表演(图二十)[3Q]。馆藏杂技盘舞画像砖或为大型百戏表演中的局部体现,场合也应属此类。
彭县九尺铺东汉墓出土有一方鼗鼓画像砖(图二十一)[31],与馆藏鞞舞画像砖应是同模所制。廖奔先生的《中国早期演剧场所述略》一文中认为也属于在厅堂表演。据《汉书·严助传》载:“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32]表明倡优艺人社会地位极低,其表演形式也与厅堂宴饮的雅乐不同,更加滑稽俗化。虽至东汉民间俗乐兴盛,形成雅俗共赏的局面,但表演艺人的地位却没有较大变化。遂宁出土的陶房乐舞说唱俑(图二十二)[33],俳优艺人位于下檐右侧,与乐舞表演者分置上下两处,可见其地位。故馆藏鞞舞砖的表演场所,本文更倾向于认为是在堂外廊下。
四、汉风蜀韵:蜀地乐舞文化的地域特色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中央王朝开始了向西南地区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被迁徙者包括百姓、豪户、罪人及俘虏等多种身份。《华阳国志·蜀志》有载:“秦惠文王封子通国为蜀侯……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至汉初,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仍在继续。移民和西南夷的开发,加速了成都平原经济的发展,加之文翁兴办石室,儒家思想在蜀地传播,并与本土文化融合。武帝时期实施的抑商政策,致使蜀地的工商业者被迫转移到农村,加速了土地兼并,新兴的豪族势力出现,并快速发展壮大。东汉早期光武帝曾试图限制其发展,却因多方阻力最后不了了之。至东汉中后时期,政治上的放任,使豪族势力空前加剧[34]。成都现发现的东汉文化遗存,数量上远超西汉,便是受豪族势力强大、厚葬之风盛行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东汉时期的蜀地民间俗乐盛行,以倡优为例,文献有载“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儕像”[35],而纵观南阳、山东出土的画像石图像,倡优形象很少出现在宗教祭祀场合及较为正式的宴饮场面中。馆藏歌舞杂技画像砖也是蜀地乐舞世俗化的体现,画面中长袖舞者与倡优艺人,形成“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对比,两者却又能相互应和,共同起舞,体现了雅乐与俗乐的兼容并蓄。这种带有鲜明特征的乐舞文化的形成,也是因豪族阶层受儒家礼乐制度的影响,在精神上向往儒士风雅之姿,却又不能摆脱自身的奢侈放纵的习性,成为蜀地豪族践行儒家文化与本土文化融汇发展的独特方式。
汉代是蜀地文化发展的高峰,民族间的交流,创造了乐舞百戏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历经二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原样保存下来的汉乐舞表演形式几乎没有,虽有文献资料记载,却不能够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体如游龙,袖如素霓”[36]的景象。随着近年越来越多的绘有舞乐百戏的画像砖(石)被发现,线刻出生动的乐舞表演环境,用夸张的艺术手段表现出舞姿,成为研究成都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乐舞文化的宝贵实物资料。
[1](晋)左思:《蜀都赋》,《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一册),郑州大学出版社,年,第240-241页。
[2]高文、王锦生编:《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3]高文、王锦生编:《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4]索德浩、毛求学、汪健《四川汉地俳优俑——从金堂县出土的徘优俑谈起》一文中指出,汉代还有一种艺人为倡优,从事乐舞、杂耍、魔术、滑稽等百戏表演,范围大于俳优。
[5](汉)傅毅:《舞赋》,(南朝梁)萧统选编、李善注:《文选》,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第362-366页。
[6]李学勤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6页。
[7]陈秉才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07年,第265-277页。
[8](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9]张紫靖:《东汉蜀地画像砖石的乐舞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第52页。
[10]《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11]郑永乐:《拂舞源流探析》,《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41-45页。
[12](唐)房玄龄等:《晋书·乐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
[13]萧尤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14](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
[15](晋)崔豹:《古今注·卷中·音乐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16](南朝)沈约编《宋书·乐志》中载:“扬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词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
[17]萧尤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18]《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68、269页。
[19](西汉)刘安:《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中华书局,2009年,第262-276页。
[20]《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
[21]《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天津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22]《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23](东汉)傅毅:《舞赋》,(南朝梁)萧统选编、李善注:《文选》,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第362-366页。
[24]原句出自东汉张衡《舞赋》,因文本残缺,故文章引自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8页。
[25](南朝)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366-390 页。
[26]《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27]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第524页。
[28]廖奔:《中国早期演剧场所述略》,《文物》1990年第4期,第62页。
[29](晋)左思:《蜀都赋》,《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一册),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0-241页。
[30]龚廷万、龚玉等:《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 年,图 88。
[31]严福昌、幸晓峰等:《巴蜀古代乐舞戏曲图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32](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33]严福昌、幸晓峰等:《巴蜀古代乐舞戏曲图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24頁。
[34]罗开玉、谢辉:《成都通史·秦汉三国(蜀汉)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6_207页。
[35](汉)桑弘羊撰,王利器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225页。
[36](汉)傅毅:《舞赋》,(南朝梁)萧统选编、李善注:《文选》,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第362—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