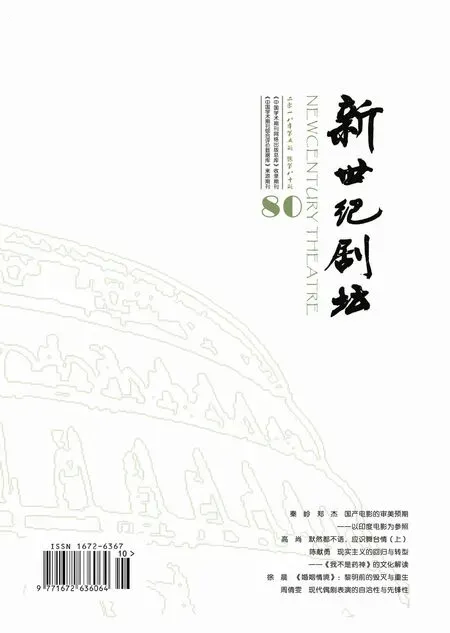现代偶剧表演的自洽性与先锋性
——以“拉妈妈剧院”2015年偶剧演出季为例
伴随着大众媒介的更迭,古老的偶剧艺术面临全新的挑战。将偶剧视为某种地域文化的标签,并固守某种陈旧的传统叙事,注定丧失主观能动性和艺术创新能力。如何把握住偶剧艺术的本体性特征,同时在作品观念、形式嫁接上追求大胆的创新,展现一种新的艺术可能性,是现代偶剧亟需面对的新命题。
拉妈妈剧院(Lamama Theatre)是美国纽约外百老汇著名的实验剧院,自1961年成立以来,致力于为戏剧艺术家提供排练和演出场地,每个演出季三个剧场会推出超过100场演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多位表演艺术家。偶剧演出是“拉妈妈”的经典保留项目。早在1962年,创办人Ellen Stewart邀请Pagoon Kang Wouk 和他的偶剧团队来演出,建立起了这一延续50余年的传统。2015年的偶剧演出季在10月进行,笔者观看了所有五场演出,包括《仙鹤:上天入地》(《Crane:on earth,in sky》)、《膝栗毛》(《Shank’s mare》)、《怎样的孩子……》(《The Child Who》)、《灯火通明的今晚何须打开夜灯》(《No need for a night light on a light night like tonight》)、《未定义的部分》(《Undefined fraction》),本文的研讨将在此基础上展开。
一、体现自洽性的民族偶剧
偶剧源于民间,世界各民族历史悠久的偶剧表演均体现了本民族最本真的文化特质,其可传承性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然而“传承”包含了作品可传播性以及文化传统可保存性这两方面,而偶剧表演在戏剧文本性和现场表演性这两方面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需要编导方协调其比例。
巴别塔的存在使得异域观众必须面对不可避免的语言隔膜,这是否会令戏剧的现场表演性和传播性大打折扣呢?另一方面,为了打破观众的语言隔膜,换取更为广泛的接受度和传播效应,是否就必须舍弃民族语言,强调语言文字以外的现场表演性呢?这一两难的困境确实客观存在,各国艺术家在艺术实践过程中必然要对这一问题有所回应。
《仙鹤:上天入地》讲述了北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故事[1],主创团队来自设计剧院(Devised Theater),该剧团的基本创作方式是摒弃欧洲戏剧传统的剧作家中心制,推崇集体创作及基于戏剧意象的无文本创作。整个故事并不复杂,仙鹤作为最主要的戏剧意象和灵魂角色,在演员的操控下,它时而感受大自然的恩泽、时而体验和其他动物间的竞争、时而与土著居民和谐相处。在开阔的长方形演剧现场,空中以及地面的偶剧表演常常同时展开,以玉米壳、树枝制作的走兽和飞鸟风筝在演员的操控下,呈现出极佳的现场表演性。此外,全剧所有的吟唱和对白部分均采用了印第安土著语言,现场的观众绝大多数无法听懂土著语言,然而脱离文字,观众依然可以理解剧情。《仙鹤:上天入地》成功地在观众心中植入了一个美妙的艺术形象:仙鹤——并以此指代印第安民族内在的精神力量——大自然拥有一种可自洽的力量。
“自洽性”不仅体现在该剧的故事主题中,更体现在作品形式中:只可意会的偶剧肢体表演、无法言传的土著语言,是否不可兼容?格洛托夫斯基谈及这一问题时,其观点可做参考:“台词可以是偶然拾来的,甚至说,它必须是偶然拾来的。重要的是通过身体和发音技术给台词以一定程度上和正常情况下所没有的裨益。”[2]在该剧中,身体和发音起到了主导作用,在一个统一、宏阔的戏剧主题中,它们各自作为重要的戏剧元素,交替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所吟唱的台词虽为土著语言,但却能让观众领会其内涵。
二、跨文本与跨媒介的偶剧创作
偶剧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然而“民族的”并非顺理成章地就能成为“世界的”。从“民族”走向“世界”,译介是一种传播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方式,相比之单向度的传播,操持不同语言的各民族戏剧工作者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开展艺术创作,则有望同时达成“传播”与“交流”这两项功能。
大型偶剧《未定义的部分》改编自西班牙黄金时代剧作家喀德·隆巴卡《生命是场梦》(Life is a Dream)。该故事人物众多,且包含多条线索,为了使作品更为凝练,改编并舍弃了部分角色和故事线索。但是对于不了解戏剧文本的观众而言,试图理解每一位出场角色以及人物关系依旧相当困难。创作者虽然创造了诸多富含象征意味的偶人形象:例如悬吊在空中可活动关节的巨手——象征命运之无常及不可撼动;又如幼年波兰王子Segismundo的微缩版铁丝偶人形象——圈禁在铁笼中丧失自主能力的囚徒……这些精美的偶形象确实有助于戏剧主旨的阐发,但是对于观众而言,仅凭借演出说明书,靠猜测与想象自行拼凑剧情,难免使一部制作精良的偶剧在传播性方面大打折扣。
相比较而言,《膝栗毛》(《Shank’s mare》)的可传播性更佳。在文本同样缺省的情形下,异域观众却更易理解剧情,并和剧作本身产生更密切的交流关系。这出偶剧由美国导演Tom Lee和日本偶剧艺术家西川町( Koryu Nishikawa V)合作完成。作为日本东京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偶戏世家西川町家族的传统技艺可追溯至古老的日本偶剧艺术“Bunraku”(称为“文楽”或“人形浄瑠璃”),西川町家族偶剧第十五代传人Koryu Nishikawa V致力于将日本传统偶剧推广至世界。而美国偶剧艺术家Tom Lee生于韩国,长于夏威夷,艺术活动起步于纽约拉妈妈剧院,他尤其擅长偶剧多媒体实时演出,致力于探索傀儡剧的综合性操控技术,他和西川町偶剧艺术的相逢,得益于公益性艺术家扶持计划[3],十年前他赴日本师从西川町先生,如今则携手合作:原汁原味的日本人偶造型、独特的偶剧操控方式[4]、现场演奏的日本传统乐器三味线与尺八、同时亦加入形式新奇的多媒体实时操控技术,传统与现代之间体现出恰到好处的和谐之美,令人惊叹。
《膝栗毛》的戏剧文本出自日本民间故事集《东海道中膝栗毛》,而英文译名“shank’s mare”则取自18世纪的苏格兰。颇为巧合的是,东西方文化对“膝栗毛”/shank’s mare的解释恰有暗合的意味:shank’s mare是指“人的腿”(膝盖至足踝的一段),“膝栗毛”则是指骏马膝盖以下的栗色皮毛——两者均寓指徒步旅行,不借助其他交通工具,最终走向目的地——主创者抓住了东西方文化中具有普适性的主题:“身体力行、探索求真是人类最可贵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设计两个故事平行展开:其中之一是讲述一位日本武士期望儿子能够茁壮成长,然而在一次比武中,儿子重伤不治,父亲痛不欲生,随后背井离乡,踏上流浪的征程,内心饱受道德、良知的追问;而另一个故事则颇具西方特色:老科学家皓首穷经,夜观星象,而他的徒弟则每日替他擦拭望远镜,有一日老科学家终于领悟,闭门造车绝不是领悟科学真知的途径,必须行万里路,才能找到他苦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他的徒弟随同他一起踏上漫漫征程,直至遭遇暴风雪,老科学家和徒弟体力不支倒下,老人将御寒的衣服披在昏睡的徒弟身上,颤颤巍巍地登上最后一座山峰,手指天际最亮的启明星,含笑而终。徒弟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坐在实验室的工作台前,原来这是一个年轻科研人员的南柯一梦,时空穿越,他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先人的科学探索精神……两个平行故事,一者关乎良知道德,一者关乎科学理性,它们之间的交汇点出现在神鹿的不期而至——一个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戏剧桥接方式。创作者在跨文本创作中,并未忘却留白处理,意犹未尽之处,古朴神秘的日本乐曲徐徐而至,倾述着人类面对前路茫茫,但绝不会停下独立探索的脚步的决心。

《膝栗毛》剧照
《膝栗毛》采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多媒体技术,但并未舍弃日本传统偶戏的质朴之美。在舞台前侧,摆放着微型雕塑,从民居、水塘、树林、荒野、山峰以及现代城市场景一应俱全,灯光与置景师一个人负责所有的场景调度和灯光调度。他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装载小型摄录机的滑轮小车可以实现镜头在诸多场景之间平移,而投影装置在舞台正后方将平滑运动的场景和原地运动的偶人结合在一起,制造了角色在旅途中行进的视错觉。灯光与置景师还运用另一个老式幻灯片投影机,利用ipad播放一些简单的特效、动画,甚至一些特写都是利用一截偶人的手配合道具来完成。这些技术手段并无特别高深之处,但是其宗旨特别明确:必须将机械装置的自动性降低到最低程度。换而言之,灯光与置景师具有绝对的现场操控权,他手动控制灯光,手动幻灯片操作、摄录机实时拍摄投影——不言而喻:只有“人”本身才是戏剧的主人,戏剧现场的节奏、吐纳依赖于人的有机活动。为此,技术手段可以是简陋的、但却不失生动性,观众甚至可以将灯光置景师的全场活动看成是表演的一部分。日本传统偶剧加入了奇妙的多媒体置景,意味着传统的观剧方式在改变,而流行文化元素也适度地取悦观众:例如借助多媒体展示四格漫画和广告POP字体[5],在多媒体戏剧情境中,观众既体会到开放灵活的现代剧场观念,同时也为古老的艺术传统而折服,两者并不抵触。
跨文本、跨媒介是传统偶剧走向现代、登上世界舞台的有效尝试。创作者只要掌握其“度”,不将平等的“跨”界变为单方主导的“越”界,则能有效规避失衡与失当。
三、模糊界限:从偶剧到实验戏剧
“拉妈妈”作为纽约重要的外百老汇剧院,“实验性”是其贯彻至今的艺术宗旨。偶剧采撷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人类文化历史进程中的活化石、活标本,但这并不代表偶剧必然尘封于历史的土壤,相反,偶剧的一些基本特点可作为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表征:例如操控傀儡的戏剧意象、面具的符号象征、无文本的演剧形式,在独具眼光的艺术家眼中,偶剧同样可以成为当代先锋艺术的一块丰富的实验田。
《灯火通明的今晚何须打开夜灯》(《No need for a night light on a light night like tonight》)是一部充满诙谐意味的偶剧。这部作品的表现形式为“人偶合一”,将演员与偶的操控与被操控内在化。演员头上嵌套着一个几乎和肩同宽的正方体纸盒,画上不同的脸谱,即代表不同的角色。这些面具有其共同特点:僵化、古板、严肃,令人联想起极权统治下的人们的面部表情。纸盒头套如同一个累赘,限制了肢体的行动,角色以稚拙的肢体动作,努力从事着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饮食、交流、听音乐、绘画、旅行、购物……他们并未试图摆脱沉重的头套,而是全然接受了僵化刻板的面具,但是在面具背后,可以感受到角色所有的努力(或者说戏剧的“最高任务”)即:日常生活。他们仿佛被某种力量所操控——例如:习惯于统一步调、搬着小板凳规规矩矩地坐成一排……但是他们自发地组织日常生活,当他们努力适应着沉重头套、并不断化解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意外时,这种温和的“反抗”得以显现。这其中微妙的戏剧张力令观众在笑声中深思。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言:“身体马达式地过着自己习惯的生活,而心灵却过着自己的较为深刻的心理生活。”[6]这部偶剧的基本动作和核心观念即围绕着两者的悖论展开,亦构成了该剧强烈的戏剧性。
以“讲故事”为主的传统偶剧如何发掘“造型”和“动作”本身的“戏剧性”,而非传统亚里士多德式的“戏剧性”?这或许是一个极有启发意义的命题。
法国偶剧《怎样的孩子……》同样在挑战这一命题,唯一的偶人是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由一位女性演员操持人偶(在部分桥段中,这位女演员扮演他的母亲角色),而另两位与偶人合作演出的则是身手敏捷的杂技演员。在煤渣铺成的长方形演出场地上,杂技演员以高难度的技巧呈现各种肢体表演,而木偶男孩则充满好奇地探索着周遭的事物。整出戏剧同样是片段式结构,但戏剧故事相当晦涩,原因在于其他片段式的偶剧尚且拥有前后一致的角色设定和人物关系,但是在这个故事里,人物关系是随机的,人物形象是前后不一致的,孩子时而顽劣、时而充满好奇、时而无辜弱小,而成年演员对其则时而呵护、时而顾若罔闻、时而暴虐无情。偶人伴随着真人杂技演员肢体造型(静态)与动作(动态)交替出现,戏剧的多义、暧昧性也同时在考验着观众的理解力。剧中出现一段台词的诵读为法语,且并未提供字幕,对于语言不通的观众而言,只能依靠偶剧造型和即兴动作来理解本剧。杂技表演脱离了单纯的技巧观赏层面,成为了戏剧情境的一部分,制造了种种平衡与不平衡的随机变化,仿佛吊线锤(plumb-bob)一般引领了观众的注意中心。回到上文所谈及的命题,放弃文本层面的“戏剧性”,对于偶剧而言,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也并非是不可企及的。当代观众如果能欣赏现代舞剧的抽象构成,对于偶剧的造型与动作中所蕴含的戏剧性,自然也能加以理解。
四、挑战常规:偶人与操纵者的关系
偶剧表演与其它戏剧表演最为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个偶人操控者。当我们试图确认舞台上的表演角色时,究竟该如何认定呢?偶人是显而易见的表演角色,而除此之外,偶剧操控者则往往隐身其后,以复杂的技巧操控偶人做出各种复杂的动作或表情,传统偶剧的“隐身其后”包括布帘相隔或是演员身着黑衣,目的在于为偶人留出特定的演出空间。如此看来,偶戏操控者似乎可认为是“看不见”的演员,传统偶剧演员并不拥有完整的演出空间,这似乎让人怀疑,“演员”——作为被观众观看的对象——隐形人一般的偶剧操控者究竟还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表演角色呢?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验偶剧越来越多地尝试人偶同台,甚至人偶一体。上文介绍的《灯火通明的今晚何须打开夜灯》即是一例。我国的木偶剧专业人士对人偶剧的盛行表达了极大的忧虑,并不认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偶戏”。其理由在于:其一,人偶剧对于操控技术并不讲究,甚至不需要专业的技术训练即可完成,这将导致偶剧的业余化;其二,人取代偶破坏了偶剧的本体性——“人对偶的操纵,是木偶剧的本体。”[7]事实上为艺术表现形式划定界限是一种偏于保守的态度,与时俱进的态度是:偶剧业余化、偶剧本体性的变异并无损于传统偶剧所持有的艺术特色。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对偶的操控”是否能构成偶剧的唯一本体性,恐怕也值得商榷。
纵观“拉妈妈”的偶剧季演出,各创作、演出团体确能做到不拘一格,大胆挑战传统偶剧的程式,对于“人-偶关系”这一基本的偶剧本体性课题,贡献了更多的阐发空间。
(一)“人-偶”合一
这种偶剧表演接近面具偶的演出形式,人即是偶、偶即是人。《灯火通明的今晚何须打开夜灯》明显属于此类。
(二)“人-偶”从属关系
这是较为传统的偶戏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判断从属关系应当由演出空间的归属权决定。在传统偶戏中,偶戏演员通过娴熟的操控性表演不断降低自身在舞台上的存在感,换而言之:人类演员的技巧越娴熟,偶人的肢体表演越生动逼真,观众的目光被吸引至偶人身上,进而降低了偶剧演员自身的存在感——使其退守舞台深处的不仅是黑色的着装,而且是“去表演性”的表演。归根结底:“偶”从属于“人”的绝对操控,“人”从属于“偶”的表演空间,两者藉此完成了两种交换,但每次交换均不是对等关系。在本次戏剧季中,人偶从属关系的表演形式在演出片段中均有所呈现,但没有一部作品从头至尾贯穿某一种固定的表演形式。
(三)“人-偶”对等关系
对等关系是指人与偶共享表演空间,拥有对等的角色地位,可产生正面的戏剧冲突。在《仙鹤》一剧中,偶剧演员代表土著人民,演员身着华丽的民族服装,他们操作动物偶的整个表演动作亦可看作是人类和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和谐共处,动物偶在行动时,人类演员并未完全退让出演出空间,而是担任观察者及共处者的形象;而在《未定义的部分》一剧中,操控偶人波兰王子Segismundo的演员同时也扮演了王子的看守及师傅Clotaldo一角;在《怎样的孩子……》中,小男孩偶人的操纵者常常在一些特定场景扮演其母亲的角色。
通常而言,人偶对等关系的确立,建立在偶剧操控演员的表演可信度之上,此外,为了便于观众理解,人与偶的角色关系多半为驯养者与被驯养者的关系:人类与动物、母亲与孩子、囚徒与看守……这类角色关系令观众在观赏偶剧演员的操控动作时并不感觉突兀。唯一的一次例外在《膝栗毛》中,武士偶人的操纵演员,原本身着黑衣,隐身其后,但武士角色在一次比武中贪生怕死,不敢应战,它突然转向背后的操纵演员,向其表示:是否可以代为一战?黑衣演员开始推脱不已,后来只能勉强应战。武士偶的这一邀约动作,令观众大感意外,忍俊不禁:因为这意味着“偶”在戏剧情境中突然让渡其演出空间,如同人与自身的影子相分离。这不仅是直接将人类演员从幕后邀至台前,更是将操控者直接从自身割裂出来,使之与其对等。
(四)“人、偶”分离/独立系统
在这种人偶关系中,人和偶虽然也共享舞台空间,但并不产生直接的交流。《未定义的部分》中,高悬于空中的巨大的“手”偶由演员单独操控,这一缓缓摆动手指的偶形象并不参与舞台中的戏剧故事,但是作为重要的象征,对于全剧的主旨有揭示作用。《怎样的孩子》中的大量戏剧场景,杂技演员的表演和人偶也是相分离的。在观众眼中,煤渣场地中的杂技演员演绎着成人世界的多舛征途。偶人小男孩稚拙的身体语言和杂技演员柔韧的身体语言形成鲜明的对比。人偶分离系统往往定义了两个不同的戏剧时空,作为一种隐喻修辞,直接参与戏剧整体意象的建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未定义的部分》中巨大的偶造型艺术,同样可以嫁接于其它舞台艺术中,事实上这是偶剧艺术的一个发展方向,音乐剧《狮子王》、舞台剧《战马》以及众多知名的舞台作品均看到了偶剧艺术独特的美学价值。

《未定义的部分》剧照
拉妈妈木偶戏剧演出季仅是世界各地众多木偶剧演出的一项个案。各国民族偶剧的传承发展路径对于中国的偶剧艺术有着积极的镜鉴意义;当然我们同样不应忽视偶剧艺术的本体性研究,但对于偶剧艺术本体性研究要有发展的眼光,而不是固守于以往的认知,有传承,亦有变通,古老的偶剧艺术才会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偶剧艺术的多元、开放式发展,对于戏剧表演艺术的多样性而言,意义深远。
注释:
[1] 奥奈达人与奥吉布瓦人:前者为美国纽约州、威斯康辛州印第安人,后者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2] [波兰]耶日·格洛托夫斯基著.[意大利]尤金尼奥·巴尔巴编.魏时译.迈向质朴戏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152
[3] 该项目为:NEA/TCG 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designers
[4] 偶剧演员坐于活动轮椅上,既操控偶人的手部与头部动作,同时偶人的脚部置于偶剧演员的足背之上,使之可以活动。
[5] 由于全剧几乎没有对白,因此为表现主人公重要的心理活动,使用了上述方法,但仅出现一次。
[6]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郑雪来译.演员创造角色[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108
[7] 徐馨.人民网[EB].两千年来中国木偶剧的三大悲剧:小心丢了偶http://culture.people.com.cn/GB/87423/13183159.html 201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