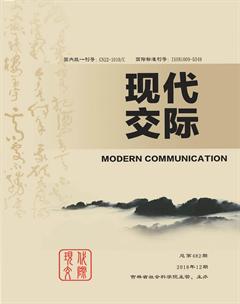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浅析
孙丽丽 罗雅丽 伍雅澜
摘要: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分析哲学的经典。基于对弗雷格对专名的思考,罗素区分了专名和摹状词,并用摹状词理论解释了语言哲学中的独角兽、同一律和排中律等三大问题,为哲学家研究指称理论提供了基础。后世学者如斯特劳森、克里普克等质疑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对三大问题的思考。现阶段,研究者把言语行为、认知语言学等视角引入了摹状词理论的探讨中。
关键词: 名称 摹状词 命题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2-0072-03
1905年,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罗素在《心灵》(mind)杂志上,发表了《论指谓》(On Denoting)。(储修伟,2014)这篇文章是他自己最看好的个人哲学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陈述了摹状词理论,论证了该理论的意义,并说明了摹状词逻辑分析对分析知识的作用。这一理论是根据罗素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所展开的,是分析命题的逻辑形式的有力工具,被视为分析哲学的经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成为语言哲学、逻辑学和形式语义学的主流思想(周允程,2015)。该理论自提出以来,一些学者如斯特劳森、克里普克对此提出了异议(郭立东,2012),一些学者则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了解读。本文拟对罗素的摹状论的产生背景、主要思想、研究者们对摹状论的质疑,以及摹状论的现状展开探讨。
一、罗素摹状词理论的产生背景及特征
20世纪初,西方哲学产生了一种思潮,把哲学问题归结于语言,因此不少哲学家把关注点转向了语言的本质及语言的使用问题。其中对简单命题即主谓式命题受到了哲学家的特别关注。简单命题可以分为性质命题和关系命题。前者是对某一对象的性质的阐释,后者是对两个以上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两个命题都有主谓结构。弗雷格(G. Frege)根据主谓结构区分了专有名词和概念名词。其中专有名词和主语对应,表达某个对象,概念词对应的是谓语,表达某个概念。通过主谓命题,弗雷格指出主词具有指称功能和谓词具有归属功能。他构建了自己的名称理论,他指出“我称每个代表一个对象的符号为专名。每个陈述句若是涉及用词的所指,则应把它理解为专名。一个单一对象的标记也可以由多个于此或者其他的符号组成。为简便起见,这些标记均可称为专名”(弗雷格,1994),把专名和摹状词统称为专名。
罗素接受了弗雷格对主谓命题的部分看法,认为一切命题可归属于主谓命题。并接受弗雷德把所有通名视作谓词的观点(陈晓平,2012)。罗素对弗雷格的专名理论提出了异议,并提出了摹状词理论。
在《摹状词》一文中,罗素写到:“我们有两种东西要比较:1)名字。一个名字乃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直接指一个个体,这个个体就是它的意义,并且凭它自身而有这意义,与所有其他的字的意义无关;2)摹状词。一个摹状词由几个字组成,这些字的意义已经确定,摹状词的所有意义都是由这些意义而来”,把个体分为专名和摹状词。他认为专名是所提及名字独一无二的指称特定的对象,如曼哈顿、撒哈拉大沙漠、冥王星、某人的名字等,并进一步把专名区分为逻辑专名和普通专名,前者包括这、那这种表示已经认知对象的指称时候才能使用的词语,除此之外都属于普通专名,并认为普通专名在本质上是一个缩略的摹状词(王丽珍,2017)。罗素指出摹状词是通过对事物特定特征的描述来指称该事物的词组。摹状词旨在描述对象特征,而非突出指示功能。通过摹状词的使用,实行了唯一存在性判定。罗素把摹状词分为非限定性摹状词(indefinite description)和限定性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两类。非限定性摹状词不仅表示泛指,而且表示不确定的指称某一类事物如“一本枯燥的教材”“一项艰难的任务”等等。限定摹状词是罗素摹状论的研究重点。限定摹状词是有特定的指称对象,结构一般由限定词the、形容词和普通名词组成。如“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世界上第一台电视”等。
摹状词理论为哲学家们研究指称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摹状词能有效解释哲学上的独角兽为代表的虚构事物的存在问题。独角兽问题来源于很多哲学家认为语言和实物是一一对应关系,认为命题的主词必须存在,如果它不存在,那么人们就不提它了。所以说“某物是不存在的”必定是不真实的或者是无意义的。罗素对虚构事物的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认为“独角兽”“阿克琉斯”“女蜗”等不是专有名词而是摹状词,是多种特征的结合,由此避免他们存在的意义。同理,摹状论能有效解释“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这样的命题。众所周知,法国早已是共和制國家,国王不再存在。罗素认为“当今法国国王”并不是指代着实际存在的对象,而是断定的是“有且只有一个对象是当今法国国王并且是秃子”。即把这个命题拆分为三个并列子句,即1)至少有一个人现在是法国的国王,2) 最多有一个人现在是法国的国王,3)那个担任法国国王的人是秃子。由于第一个子句是假的,现在法国没有国王,因此这个命题是假的,而非这个命题没有意义(刘宇红,梁晓波,2004)。
摹状词也能解决哲学中“Scott is the author of Waverley”是否有意义的问题。由于Scott是Waverley的作者,“the author of Waverley”指的是同一事物,既然指称满足统一性,那么应该可以相互替换而不改变其意义,因此就会推出Scott is Scott这样的无句子,而这个Scott is the author of Waverley是显然有意义的。这个句子体现了哲学上的同一律问题。罗素的解释是,Scott是一个专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指称唯一个体,没有辖域而言;the author of Waverley是一个限定摹状词,具有辖域的性质,辖域是自由的。因此Scott和the author of Waverley存在着逻辑功能的本质区别,两者不具备可替换性。
摹状词还试图探讨哲学中的排中律问题,根据排中律,两个相互矛盾命题中,正反命题中必有一命题为真。以如下矛盾问题为例,“美国国王是英明的”和“美国国王是不英明的”,这意味着无论哪个命题是真的,都证明美国国王是存在的,而这不符合现象的事情。罗素把这个语句拆分为三个命题:1)存在一个x,x是美国国王,2)对于任意一个y, y是美国国王,但是那么y就是x,3) x是圣明的。而这个命题中1)存在一个x,x是美国国王是假命题,因此两个正反两个命题,无论美国国王是英明的还是不英明的,都是假命题。通过引用逻辑方法,揭示了命题的逻辑结构和语法结构是不同的,阐述了人们日常沟通中产生混乱的原因。
二、研究者们对摹状论的质疑
摹状词解释了语法主词无指称的命题是达成意义的方式,并通过逻辑分析来确定命题的真假,杜绝了“本体论承诺”,因此被视为分析哲学的典范(李章吕,2009)。后世的哲学家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以斯特劳森的抨击最为瞩目。他们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对摹状论意义、句法和专名问题的理解不同。罗素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与它的所指具有同一性,而斯特劳森认为罗素混淆了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所用来表达的东西(张安民,2005)。斯特劳森以“我感到热”这一句子为例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任何人都可以用“我感到热”这个句子,因此“我”可以指称任何人,并用词来挑战罗素的意义论。在句法方面,斯特劳森和罗素也有分歧。以罗素的“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为例,罗素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句子都有真值,而本句子是假命题。而在斯特劳森看来,表达式“法國国王”不能指称任何东西,因此使用它作出的陈述不具有真值,这是“真值空缺”的表现。罗素的逻辑规则是一阶逻辑的,即非真即假的二值原则,而斯特劳森的不具有真值的判断则要求承认除了真、假之外有第三种值。在专名问题上,罗素认为普通专名是缩略的摹状词,由于摹状词不是主谓命题真正的主词,因此普通专名不能当主词,只有逻辑名词才能充当主词。而斯特劳森否认了逻辑专名的存在,并认为专名不是摹状词。斯特劳森的这些观点,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不赞同罗素关于独角兽问题,同一律和排中的看法。针对独角兽问题,斯特劳森认为不存在主词所指对象的语句有无意义的问题;针对同一律问题,他否认了二值逻辑中语句不能同时为假的观点,并提出三值逻辑论;关于排中论,他把“a=b形式”的语句称作“验明陈述”而非罗素的“恒等式”,拒绝从等值的角度来衡量a和b。
逻辑学家、哲学家克里普克称,《论指谓》中的许多例证是值得质疑或可以断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例子有悖于罗素自己的哲学或者事实。赛尔从言语行为对摹状论进行了反驳,认为摹状论与言语行为的一般理论相符,无法揭示摹状词在语内行为的使用。在他看来,限定摹状词的作用在于指称,是命题行为的一部分,是支撑表达式。 我国学者褚修伟也指出:“罗素对meaning一词不审慎的使用,首先是直接导致了在重要论证中存在的一系列自相矛盾或纠缠不清,最根本的是它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罗素摹状词理论无法剔除弗雷格的‘涵义这一概念。”厘清这一点,可以修正“罗素维护了意义即指称的看法”这一常见的不准确说法,从而更清楚地、更客观地认识罗素这一哲学典范之作的真正意义”。
三、摹状词研究的新转向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人工语言的视角, 对传统逻辑中主谓语句进行语义分析,试图寻找世界的逻辑结构和规则,用逻辑结构分析的方式解决了哲学和逻辑学中的诸多难题。他所讨论的摹状词意义是基于社会共同体和公共的语言框架,与语境、说话者无关。斯特劳森以日常语言的视角,把语境、说话者的意向、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因素引入对句子的分析当中。他区分了语词的指称性和归属性,强调了语境对语句的影响,促进了摹状词理论从语义到语用的转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旋,2014)。
一些学者从其他视角关注摹状词理论。约翰·赛尔从言语行为论视角反驳了罗素的限定词摹状词理论。赛尔指出摹状词并非只出现断定中,也会出现在其他言内行为(illocutionary tasks)中,但是发现用摹状词理论解释其他言内行为中的使用时,会出现荒谬的结果(郭立东,2012)。
刘宇红和梁晓波(2004)尝试着使用认知语言学来解读摹状词理论。他们运用了认知语言学中图形背景理论来解读“法国国王是秃子”的命题。在认知语言学中,有两组重要的概念,一组是与突显观(prominence view)相关的图形(figure)与背景(ground)概念,另一组概念是射体(trajectory)和陆标(landmark)。前者常常用脸与花瓶的幻觉图(face/illusion)来说明图像感知与背景的关系。后者在认知语言学中广泛运用。认知语言学家用射标和陆标来描述述谓结构,把主语视作射体,宾语视为陆标。运用射标和陆标理论来看罗素拆分的“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的三个分句中,可见第一句“至少有一个人现在是法国的国王”和第二句“最多有一个人现在是法国的国王”在数量关系中卡住了上下端,确立了陈述对象的唯一性。第三句“那个担任法国国王的人是秃子”把陈述对象置于一种结构关系中。图形背景理论把陈述对象与陈述部分置于由射体和陆标组成的概念体之中,验证了罗素的陈述对象与陈述部分之间是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与罗素否认限定摹状词与客观世界的指称关系的观点是相符的。
通过摹状词的句法演算,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指出语言在本质上不是表征性的,避免了不必要的本体论预设,给后世带来了深远影响。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对语言本质的讨论,为我们深入探讨语言的运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晓平.关于摹状词和专名的指称问题——从语境论的角度看[J].哲学分析,2012,3(1):31-49.
[2]褚修伟.“意义”的含混:论罗素摹状词理论之无法剔除“涵义”[J].当代外语研究,2014(6):98-108.
[3]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M].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郭立东.言语行为论能用来反驳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吗?[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8-24.
[5]李章吕.论斯特劳森对罗素摹状词理论的批评——从殊型句和类型句的角度[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45-48.
[6]刘宇红,梁晓波.摹状词理论的认知语言学透析[J].外语学刊,2004(1):37-42.
[7]王丽珍.浅谈罗素摹状词理论[J].现代经济信息,2017(14):362-364.
[8]张安民.从斯特劳森与罗素的论争看摹状词理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9-13.
[9]周允程.摹状词的句法演算及其本体论、知识论意义[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0(1):118-123.
[10]周璇.摹状词理论:从语义到语用[J].外语学刊,2014(4):6-11.
责任编辑: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