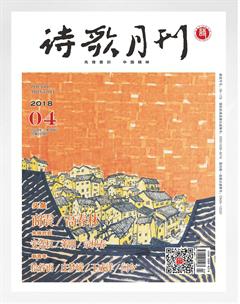暗夜中的哀痛、持守与光辉
2018-09-18 02:11
诗歌月刊 2018年4期

(朵渔:《星空辽阔,让我无言以对》,《山花》2018年第3期)
朵漁的诗歌经常以其谦卑与骄傲,以其交汇着哀痛与愁闷、欣悦与悲悯、正义与愤怒的深切情怀,感怀于人世万物。无论是我们卑微的生命,还是冗杂的日常,抑或是那些撼人心魄的灾难与悲剧,他都能够且俗且圣,向下且向上,以一己之浩茫接通天地,洞穿来自良知与灵魂的光芒,自然、率性、诚实,有奇崛的修辞,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坚持和实践着他“以个人的名义,为世界/重新安排一种秩序”的追求与抱负。所以在这组诗中,个体生命的真实处境以及它的得救的困难与可能,仍然是其最基本的主题。星空之下,我们虚无、绝望,“我们在尘世,如此这般,写着我们的生/或死,写着人生的小确幸或小灾难”(《如此这般》);“我们讨论着严酷的现实/和不可能的未来,似乎己无路”(《诗与生活》);像是一群罪人,我们“走在流放的途中”(《罪人》);“在新的救主到来之前/我们只能退回到眼泪里”,“在当前的寒冷中”,似乎“只有眼泪可作为/可燃物”,给自己以些许的温暖和勉强的光;即使是遗忘(《非人》),即使是欢爱与肉欲(《救赎》),也难拯救我们的生存;“我们都是活生生的死者,濒死者或/延迟的死者”(《无法拒绝的客人》)……我不知道——或许也能知道——为什么朵渔会有如此的哀痛?正如他所自问的,“我为什么屡次提到死亡”(《我为什么屡次提到死亡》)。但是在另一方面,不管如何,在朵渔的诗歌中,我们不仅向死而生,我们同时也在面向着星空。在暗夜中,在星空下,“万有在夜空中化为诸神”,我们仍然有“夜的光辉”(《夜的光辉》),“那持守者的精神”,已经闪烁于“清晨的蓝光”(《一切,都还在建设中》)……
猜你喜欢
汉语世界(The World of Chinese)(2019年5期)2019-11-11
科学与财富(2019年31期)2019-10-21
世界家苑(2018年11期)2018-11-20
当代旅游(2018年6期)2018-04-21
新高考·英语基础(高一)(2016年7期)2017-07-06
大众理财顾问(2016年12期)2017-01-07
科普童话·神秘大侦探(2016年9期)2016-10-28
奥秘(2016年2期)2016-03-23
投资者报(2016年9期)2016-03-17
故事林(2008年9期)2008-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