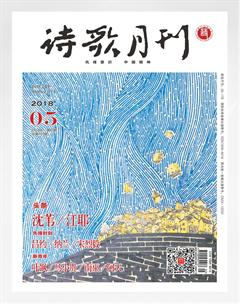草根、自然与心学
李建春
读李少君的诗论与诗歌,对我的知识结构和视野是一个挑战。我感触很多,却有不知从何措手之感。作为新世纪诗歌的重要发言人,李少君的话语和活动的影响力,在当代无出其右。相对来说,他作为诗人,只是他诗论观照下的作者之一。他认真写诗,是在他成名之后。这让他与一般诗人有很大的不同。我这里把他的诗与诗论并谈,是有一定风险的。不能把他的诗看成诗论的演示。因为即使他不写诗,他的诗论也是当代诗坛的洪钟;他个人的诗歌,实际上也超出了他的诗论(也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我完全可以不采用他的概念对他的诗进行另类解读。但是我又感到很难避免。这很自然。在此,我首先是把他作为一名诗人,然后才是诗论家,进行必要的观照。
李少君的诗论格局很大。应该说,他的诗论在宏观上,是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文化政治视野。当代诗的“草根性”,新世纪诗歌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就是他在全球化背景下,参照多元文化主义在地域性的立场上提出的,也暗合了国内的新左派思潮。“自然诗歌”得到了他个人写作经验的滋养,但是也兼顾全局。“中国文学是一种心学,西方文学是一种人学”的观点,尽管还没有充分展开,在我看来,已具有与“草根性写作”同样的原创性和更强大的穿透力。“草根诗歌”在他的操作下,已成为地域写作、民间写作、乡土写作、“新红颜写作”、打工诗歌等的总领。“自然诗歌”远超汉语的隐逸传统,包括山水田园诗、游仙诗、禅诗等,在当代,则是试图恢复异化的心灵与自然的亲密,间接地也恢复词与物扯断的纽带,恢复写作与生活的自然关系。“心学与人学”的分际,背景则是新儒学与现代神学,试图把当代文学引回到中国的道统上,重拾已失落的“文心”(此词出自诗人杨键)。其所指也大,其所立之地具体而微,落实到心、情、意,在诗的发生和意义世界建立上,进行了颇独特的辨别,以便像王国维那样,区分境界的品级和差异。“中国文学的心学意义”,如果在批评上确立了,对于接续中断百年的中华文脉,功莫大焉。
但论归论,写归写。李少君个人的诗歌创作除了在气质上与他的文风有相通的地方,并没有得到他自己诗论的多少“指导”(反而对之有启发)。比如他并不符合“草根性”的特点。他是一个有士风的诗人(这是他的身份、视野决定的),同时又思考着做一个“新隐士”。他的语言世界,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爽气,没有通常的沉迷于词语的纠结感觉,有理性的底蕴,却从不在诗中作观念的游戏。这是看尽了繁华之后直人作为诗人的初心。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一上来就是“新世纪诗人”。他的诗,毋宁说是与三四十年代和台湾现代诗一脉相承。作为优点,他绕开译诗的影响,但他没有得到西方诗歌已嵌人当代汉语肌理的焦虑的精致。他的语感是粗壮的。他的胸襟和前提很大,但是对象很小。他的视角很实际,写自然,可写到人神程度,但不脱离社会常情;也写爱和痛,多半用一种旁观的口吻。他没有黑暗的意识,一触及到撕扯就止住,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很特别,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个有底蕴的中国人性格。他所实践的这些,已进人他的诗论,在一本诗集的自序《我的心、情、意》中,他说:“诗歌是一种心学”,“也是一种情学”,“诗歌,最终要创造一个有情的意义世界”。在《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初年属于“草根性”的时期,是一个“向下挖掘的阶段,也是接地气和将诗歌基础夯实将视野开阔的阶段”,代表了诗歌的一种进程,他将之定义为“一种自由、自发、自然并最终走向自觉的诗歌创作状态”。与自媒体等多种因素有关的草根化之后,他认为当代诗歌需要进人“向上超越的阶段”,或许也可称之为重新精英化,以“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这时他个人的诗歌出场了,在草根化的归类之后,尝试着“向上超越”。他倡导的“自然诗歌”,在我看来,就是自觉地建立的现代意义世界:作为与自然和谐共在,以有情有义的方式提升境界的“心学”,而不是“上帝已死”之后孤零零的“人学”。孤立的“人”,必然导致分裂的“心”,在现代性焦虑中不可自拔,这又涉及语言和张力方式的问题。那么他个人的写作,对于新的美学原则的意义就呈现出来了。
“一条大河/是由河流与村庄组成的/一个村庄/是一条大河最小的一个口岸/河流流到这里/要弯一下,短暂地停留/并生产出一些故事/杏花村、桃花村、榆树村/李家庄、张家庄、肖家庄/牛头村、马背村、鸡冠村/又在河边延伸出/一个个码头、酒楼与小店铺/酝酿着不一样的掌故、趣闻与个性/然后,/由大河,把这些都带到了远方/并在远方,以及更远方/传散开来”(《河流与村庄》)。这首诗写于2006年,从中看不出“个人性”这个1990年代诗歌必备的标尺。经过1990年代之后,重新把“共性”的经验作为诗,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对“盘峰诗会”之后的格局置之不顾,而从一个全新的起点开始。这个起点就是“神会”。这种明明白白的,看似没什么深度的句子,如果不是在一个地方盘桓得久了,种种印象、感受凝聚升华,绝对写不出来。写出来像是描述一条定律,没有个人性可言,却分明是一个人在大地上长久漂泊之后的赞美。诗性的语言就是这样奇特,少君在瞬间认出了它。他找到了一口新的诗泉。少君找到的这口新的诗泉,与特定的时、地相关的意象,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早已明确,并通过题襟雅集脍炙人口——它的新,只是新在被新诗忘却!
《河流与村庄》是一首草根诗,具有接地气的显著特点。但又并不忠于特定地域,暗含了一个游客的综合的眼光。兴尽而止,缺乏宋诗的文气和字眼,却也因为“篇终接混茫”,具有初唐草创的格局,严格说来它是一个终结。至于要追寻他表达的持续动机,他怎样在自然中重建一个“有情的世界”,可参考这首《海之传说》:“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草虾花蟹和鳗鲡献舞于宫殿/鲸鱼是先行小分队,海鸥踏浪而来/大幕拉开,满夭都是星光璀璨/我正坐在海角的礁石上小憩/風帘荡漾,风铃碰响/月光下的海面如琉璃般光滑/我内心的波浪还没有涌动……/然后,她浪花一样粲然而笑/海浪哗然,争相传递/抵达我耳边时已只有一小声呢喃/但就那么一小声,让我从此失魂落魄/成了海天之间的那个为情而流浪者。”
这首诗的高度,在于把与自然的关系追溯为一个源始性的事件,因此也是再造神话。“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伊”,此处指海洋女神,或自然之神。少君对草虾花蟹等的描述有点龙王、哪吒故事中虾兵蟹将的味道,又糅合了古希腊神话的宁静肃穆,作为他“内心的波浪还没有涌动”的背景。他的语气是悬置的、戏剧性的,“然后,她浪花一样粲然而笑/海浪哗然,争相传递/抵达我耳边时已只有一小声呢喃”,将一个少年的情窦初开描述为初开于自然。因此自然对于诗人,也就成了情人的幻象。自然性是社会性的原型和寄托。是情、义的浓缩,而不是“忘情”的道之面容,“新隐士”的意蕴即在于此。少君的“隐”,带有“逃情”的意思,但决没有逃避社会的意思。相反,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然诗写成了风俗诗。“但就那么一小声,让我从此失魂落魄/成了海天之间的那个为情而流浪者”,还真有点海枯石烂的感觉,忧郁到一定程度,也就简简单单了。我理解了少君为何对重新写诗“感激”,他是真有可说的东西,那“一小声呢喃”,把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当代的境遇变幻出来。
关于怎样对待自然,《垂杆钓海》玄妙地提示:当用一根线“将整个大海牵起来”;关于《新隐士》的生活态度,“一个孤芳自赏的人”“不过是一个深情之人,他说:/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动情/包括美人、山水和萤火虫的微弱光亮”。关于自然在当代人生活中的可行的位置和原因,《四行诗》中的四句说得再明白不过:“西方的教堂能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吗?/我宁愿把心安放在山水之间/不过,我的心可以安放在青山绿水之间/我的身体,还得安置在一间有女人的房子里。”
高居翰(James Cahill)在他的著作《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一书中,论述了中国山水在董其昌等晚明画家的笔下,开始呈现出表现性的抽象特征,放弃了宋画中山水可居可隐的古典理想,原因在于受到晚明混乱的政治生态和王阳明心学、李贽思想等的影响,以及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版画的视觉渗透。少君在《四行诗》中提出的问题“西方的教堂能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吗”,正是明末清初朝野士人在“西儒”面前典型的疑虑。现代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鉴于民主在中国的困境,竟冀望于基督教广传以彻底改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真是不知今夕何夕。且不谈文化之争,教堂即使对于西方人,也未必是“心安之所”,它激活的存在之思恰恰是不安的:在一种荒诞感中,服从爱的绝对命令以实现超越。应该说“心安”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的追求。晚明以来,山水已只是“朝隐”“市隐”的符号,一种东方式分裂的表现媒介。
这也是“人学”和“心学”的区别。细看还是文化底蕴的差异,而不是现代性的问题。“人学”强调人的存在,在启蒙之后的宇宙中,或主宰式的,或孤立荒诞的;“心学”则从关系着眼,心、情、意着眼于伦理中的感受和态度。所谓境界的提升,不是如基督教世界中只有向上或向下的一维,而是在横向上,存在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和谐关系中。五代以后的中国山水,往往是人画得越小,越高古。董其昌以后的“清四王”,山水中很少画人。这当然也是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案,或许在于如何重新把人“安放”到自然中去。李少君的“新隐士”是一个现代人,他只能用“游乐”的方式实现某种寄托,渔樵耕读的基础已不存在。因此自然、前现代生活只是一种乡愁。
“暮色,恰是最古老的一抹乡愁”(《暮色》)。乡愁,是华人世界的存在之维度,是永远抹不去也不应该抹去的。少君也真的做到了重新把人“安放”到自然中去。方法无他,他只是注意到自然中,特别是景区中现代人的存在(相对于都市,属“半现代”),并与之发生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不可靠。比如在《山中小雨迷谁人》这首诗中,他想象着在某山中小街,“一位貌美如花的年轻老板娘/她不知犯下了怎样的滔天大罪抑或/遭遇了怎样的惊险变故/来到了此地,甘于寂寞”,而“我”,“一个到此地短暂居住的过客”,“心中暗恋她的美丽”,“直到有一天,我带走了她/彻底离开了此地,消失在人海之中”,把一个“半现代人”重新带人都市,对于双方有什么意义呢?“在关于此事的各种版本中/只有我的形象是固定不变的:/一个被山中小雨迷住的诗人/一个在山中小雨里迷茫的诗人”。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依托于自然环境的“风俗诗”。类似的狂想之诗、好奇之诗很多,比如《岭头黎家爱情》《桃》《在昭通》《她們》《七仙岭下》《文成的青山》,等等。那么他回到都市之后,也倾向于在日常中发现嵌人自然因素的、具有风俗特色的人文景观,如《花坛里的花工》《反体制》《虚无时代》《诗的危险性在于过于平静》《上海短期生活》等。
“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三三两两,影影绰绰/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我们走下青山,走人烟火红尘/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我是有背景的人》)。这首诗是少君的文化宣言,我将其作为此文的结尾。“我们是从云雾深处走出来的人”,可以理解为一群“仙人”,因为我们是汉语——一种神性的、直观的、象形文字的承继者。“云雾派遣的特使”也就是“仙界”的特使。“云雾”作为“仙界”,还可以理解为汉语的直观思维——这是“心学”的特征,只有在与“人学”、逻辑性相对时,才是“虚幻”的。这种源于汉语的诗性思维赋予我们的心灵以“时隐时现的诗意”,从而能够对抗以都市生活为特征的现代性的宰制,维持我们文化的活力不衰。
“我们是有背景的人”,这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