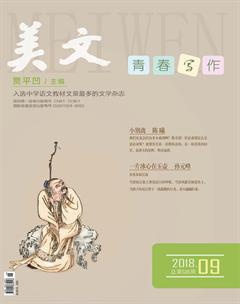洋学生趣闻
何杰
何 杰 南开大学汉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学研究。曾赴拉脱维亚大学讲学、任教两年,同时在波罗地海语言中心讲学。曾应邀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一篇论文入选。出席第6届、9届、11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2009年论文入选美国布莱恩大学北美语言学会议。2012年应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邀请赴美交流学术。出版有《现代汉语量词研究》等三部专著;出版词典、教材共三本;出版散文集《蓝眼睛黑眼睛——我和我的洋弟子们》。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2006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
1.请你吃鞋
我的美国学生中有个大男生,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叫“长大”。可我觉得他一直长不大。
每次叫他回答问题 ,他胳膊腿都像断了线一样耷拉着,有气无力地站起来。回答问题也像是说临终遗言似的,声音像个太监一样,女里女气。
我问:“怎么回事?”
“老师,我吃得不多,就这么点儿。”他用大拇指掐在小拇指肚上。
这也太少点儿了吧?
“别听他的,老师,他的外号叫‘嫂子,前面还得加个‘赖字。”另一个学生说。
就是这么个小饭量的“嫂子”要去进行语言实践,住在农家。午饭时,他吃了人家一碗红烧肉。那哪是什么碗啊?跟我们的小洗脸盆一样大!“赖嫂子”的饭量不但让我这个老师傻了眼,连老实厚道的大爷忍了半天,也不得不开口了。大爷半天“吭哧”了一句:
“俺不是舍不得叫你们吃,俺是怕俺那茅房受不了。”
“长大”好像并不明白“茅房”是什么地方,继续吃。我忙说:
“一会儿还有非常好喝的汤。”“长大”仍继续吃。我看他没听懂,于是用英语翻译出来这句话。可那时,我的英语还真的挺“赖”,许多单词的发音都似是而非,结果,我说想请他喝汤,却说成了“You will drink the shoes.”
我把“请他喝汤”说成了“请他吃鞋”(shoes“鞋”和soup“汤”发音相近)。
“長大”满眼问号,小声地问:“这是中国农村的风俗习惯吗?”我回答:“ Yes.(是的)”而且态度坚决。
“长大”立即礼貌地起身,离开饭桌。他直对大爷说对不起,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吃够了。
2 .春木立志
他叫春木,日本学生。一天,春木来上课,大夏天却戴着个帽子。我问春木:“上课怎么还戴着帽子?”
春木捂着脑袋,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要是摘了帽子,就不美丽了。我问为什么,春木说他今后一定努力努力学习汉语。我不明白这个一提叫他念书,他就头疼的弟子,今天怎么主动说要好好学习了?春木告诉我,他去了理发店。
他指着前头的头发,对理发师说:“这个,剪,不要。”
理发师一听,“嘁嚓咔嚓”,三下五除二,利落地挥舞着剪刀,没多久,前头的头发没啦!其实,他的意思是“这个,不要剪”。
春木着急了,忙说:“不要,不要。”理发师说:“都不要啊?”又“嘁嚓咔嚓”一通。春木就成了这副“不美丽”的尊容了。
春木这回可知道了汉语词序的作用。果然厉害!老师早就讲过:
“包子——里走。”是吃包子的(人)往里走。
“里走——包子。”变成“往里走——你这个‘包子。(‘包子代人)”。词序变了,语义也就改变了。
春木哪注意呀?不过这回春木可是下决心了。可是我们的春木“一定好好学习汉语”的大志立了没几天,又撒气了。倒是有一次过生日,叫他又立了志。
最爱吃肉的春木过生日,请客,却来到一间素食店。
五花肉上来了(豆腐做的,真像),我只夹了半块。不是不想吃,而是一大盘菜,肉只是在盘心中间放了几片。
这回大家都学着“嫂子”,用大拇指掐在小拇指肚上:“我们吃得不多。”
春木一脸无辜。
我那天特别高兴。我感谢春木,因为这个聚会,我见到了拉脱维亚老乡。她们是来过Party的两个拉脱维亚女孩,是南大的邻居学校——师大的学生。她们就住在拉脱维亚道加瓦河河西。
拉脱维亚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在那儿教学两年,难忘啊!
我立即向她们打听我的朋友,他叫“巴卢大”,也住在道加瓦河河西。我很想知道他生活得怎么样。她们摇摇头。但当我说起他有三个女儿时。她们一齐猛晃脑袋:“老师,别问了,有三个女儿,那就没太平日子啦!”
“我们都是圣女(剩女)!!!”
说话的女孩还特意告诉我,她的话里有三个惊叹号。
“嫂子”和春木都嘟囔起来:“本来就嫁不出去,还想作和尚(吃素)?”
“老师,你不知道这里有多贵,还一块红烧肉也吃不到!都因为她俩,要不,我怎么会来这鬼地方,吃什么素食!”
原来,春木订餐厅,请拉脱维亚女孩帮忙,订“速食餐厅”。他想快吃完,再去歌舞厅玩儿。结果,却到了这里。
同音,意不同。春木这回又立志了:
“回去我一定一定好好学汉语。”
3.由“问”引出来的悲哀
下课,美国学生纳斯丁像从闸门里喷出来一样,直扑到老师的讲桌上。他趴着身子,凑到老师的面前,完全忘了美国人的礼仪:与人交谈,特别是与女士说话,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他非但没有保持距离,还把手捂在嘴边,凑到老师的耳边,小声地问:
“老师,对不起。什么叫‘流氓?”
老师告诉他“流氓”的词义内容。
奇怪,为什么问起这个词?
纳斯丁鼻子都快掉在桌子上,一脸委屈:
“有人叫我‘流氓,悲哀呀!”
老师可了解,纳斯丁是个规矩的学生,就是有点爱耍小聪明。他的汉语刚刚学了一年,就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他能阅读汉语短文,还可以用汉语给他的中国朋友写信呢!可他说汉语就是总不注意声调。
大家知道,汉语一个音节有四个声调,声调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纳斯丁可没想到声调有这么重要,老师提醒他,他也不注意。这不,出笑话啦!
聪明的纳斯丁,此刻一脸傻气。向老师讲起了他的“悲哀”:
纳斯丁去古文化街转悠,他想买一个中国花瓶。他走进一家工艺品商店,商店里有许多瓷器,茶壶、茶碗、花瓶,各式各样的,漂亮极了。售货员小姐也很漂亮。纳斯丁非常高兴,他走到柜台前,很有礼貌地说:
“小姐,我要一个花瓶,请你给我拿一下。”
“你要哪一个?”
“我要那个蓝的。”
“给你,你看看吧!”
“好,就要这一个。多少钱?”
“十六块五。”
“好,给你钱。”
纳斯丁掏出了钱,可又想起中国的瓷器,景德镇出产的最有名了。他想问一问售货员小姐,这个花瓶是不是景德镇的。可是,他把“问”字的声调说错了,“问”字的声调是四声,他说成了三声,结果变成了“吻”。
“小姐,我还想吻吻你(问问你),这……”
“什么?”
售货员小姐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惊吓地瞪大了眼睛,看着纳斯丁,说:“你想干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跟你们外国人可不一样!”
“对,对,我只是想吻吻你(问问你)……”
“坏蛋!流氓!”
售货员小姐生气地把纳斯丁推出了商店。
纳斯丁花瓶没买成,还挨了一顿骂。
怎么回事呢?这样的事能问谁呢?
纳斯丁只好忍气吞声地等到了第二天,这才有了在课桌前的那一幕。
4.学会谦虚的斯蒂温
小李要结婚啦!小李的好朋友,美国留学生斯蒂温当然也来参加婚礼啦!
婚礼那天热闹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婚礼跟现在的可不一样,一般去不起饭店,都在家里办。
不太大的新房,迎门的墙上贴着大红双喜字,床上、柜子上摆满了客人们送来的礼品,什么被面啊,茶具呀……美不胜收。新郎穿得西服革履,帅极了。新娘呢,穿着红色纱裙,美若天仙。
来参加婚礼的人挤满了屋子。人们都向新郎、新娘说着喜庆的话。斯蒂温也向小李表示祝贺,而且他还不断地夸奖新娘:“小李,你的新娘真漂亮。”
小李忙说:“哪里,哪里。”
斯蒂温可糊涂起来。他问小李:“你不知道新娘哪里漂亮吗?”
大家都笑了。
没办法,小李只好给好朋友解释了半天。中国人的礼貌用语习惯不像外国人。在西方社会,如果有人夸奖你,你要高兴地说“谢谢”。中国人则一般都使用“哪里,哪里”,或是“不好、不怎么樣”等谦虚用语。
斯蒂温学会了。
从那以后,他说什么话都喜欢谦虚一番。别人夸他歌唱得好,他就说:“唱得不好,瞎唱。”别人说他车骑得不错,他就说:“骑得不好,瞎骑。”别人夸他中国字写得还真好,他就说:“写得不好,瞎写。”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有一次,他和小李在大排档吃麻辣烫,还点了几瓶冰镇啤酒。可能吃得太快了,刚吃完,他就觉得肚子不舒服,叽哩咕噜的。一下不小心,没憋住,放了一个屁。
小李笑起来,说:
“你真行,好家伙!屁放得可真响。”
斯蒂温这回可找到给老师表现的机会了。他听后马上回答:“放得不好,瞎放。”
小李忍不住大笑起来:“你真是个‘老外。”
“我知道我是个‘老外。”
小李说:“我说的,不是你说的‘老外。我说的是你不懂中国文化的‘老外。”
斯蒂温又晕菜了。